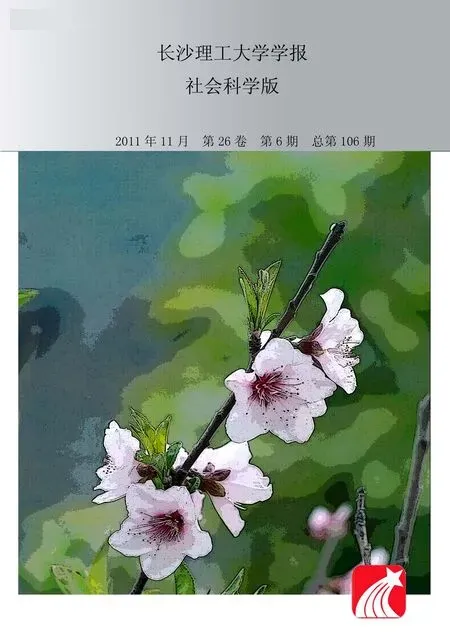斯坦贝克作品“动物化倾向”再认识
——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人与动物
徐向英
(漳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文学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作为20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一直吸引着广大读者的目光。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似乎并未遗忘他当年奋笔疾书写下的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篇章。美国斯坦贝克研究中心曾在2001年和2002年举行了纪念斯坦贝克诞辰100周年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可谓盛况空前,有力地印证着这位作家之于当代读者的意义。显然,斯坦贝克并没有离去,他的作品还在读者的心中流传。①
不过正如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斯坦贝克的作品同样从其问世开始就不乏争议和非难。客观地讲,这里既有特定的时代因素,同时也有评论家本身的立场等因素。以他的作品中出现的大量动物意象为例,20世纪30~40年代部分评论家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家玛格丽特·马歇尔认为,斯坦贝克小说很大的缺陷就在于斯坦贝克对他所描写的人物的态度上,“在《罐头厂街》中,斯坦贝克先生在处理人物时,就好像他们是微小动物,他们就如他所喜欢观察的那些青蛙,狗,猫,章鱼等动物一样地生存着、生活着。他人性化它们的方式有时让人即难堪又反感”,[1]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泰斗级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评论,他认为斯坦贝克作品一个永恒不变的根基是他对生物学的着迷,动物的习性和行为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动物化的倾向是他塑造个性人物相对不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斯坦贝克几乎总是描写低等动物,或者就是描写发育不全、几乎处于动物层次的人”,“斯坦贝克先生没有能够像劳伦斯或吉普林所做的那样,浪漫地将动物提升到人的地位,而是将人降到了动物的水平”。 埃德蒙·威尔逊还列举了具体的作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蛇》里的实验室是他小说的主要意象,象征斯坦贝克先生将人类动物化的倾向,中篇小说《煎饼坪》的派萨诺人简直就不像是人,倒更像能逗人发笑的猪,松鼠,兔子一样的可爱的小活玩偶。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人则好像是人类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被赋予了一群纵身跳海的旅鼠。[1]
埃德蒙·威尔逊等批评家提出的斯坦贝克小说的“动物化倾向”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50年代初文学评论界对斯坦贝克的普遍反映。在他们看来,斯坦贝克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动物,是把人降低为动物,因此文本具有动物化的倾向。本文试图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就斯坦贝克文本的这一特色重新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批评展开反批评,由此重新认识斯坦贝克的作品及其写作理念之于今日文学写作乃至环境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一
众所周知,从人类诞生伊始,动物就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远古时期的人类面对着的既不是轰鸣的机器,也不是闪烁的灯火,相反,他们直接交往的对象就是能够作为他们生存要素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动物。今天我们能够在史前的壁画上发现大量栩栩如生的动物意象,在文学作品中能读到神采奕奕的动物诗句不是没有原因的。以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为例,作品中就有着大量的动物意象。比如在描述希腊勇士阿基琉斯与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之间的那场恶战时,作者就调动了猎狗、小鹿、苍鹰、野兔等意象。当捷足的阿基琉斯疯狂地追赶赫克托尔时,作者将之比作猎狗在山间紧紧追赶小鹿。而赫克托尔也不甘示弱,从腰边抽出又长又重又锋利的长剑,“有如高飞的苍鹰”,猛扑过去,“一心想捉住柔顺的羊羔或胆怯的野兔”。[2]《圣经》是西方最重要的宗教典籍,作者同样酷爱借用动物作为人类的比拟对象,类似以赛亚中“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的句子俯拾皆是。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文学的领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类似杜甫的《白马》、李贺的《猛虎行》、白居易的《晚燕》等更是直接以动物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由此可见,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动物作为人类天然的描写对象一直是文学钟爱的意象。可以说,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文学与动物结缘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流行,文学作品中的动物意象并非斯坦贝克的独创。
和这些文学先辈一样,细心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在斯坦贝克的作品中,有关动物的意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作品中,狗、龟、兔、蛇、鼠、乌鸦等小至昆虫,大至猛禽的动物形象可谓比比皆是。《珍珠》是斯坦贝克创作的一部不足三万字的短篇小说,但文中的动物意象如繁花般密集绽放。印第安渔民奇诺因得到一颗大珍珠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敌人,他“现在是一头动物,躲藏着,攻击着”;贪婪的珍珠收购商“有许多双象昆虫一般的手”,在看到奇诺手中的那颗稀世珍珠时,眼睛“象鹰眼似的又沉着又残酷,一眨也不眨”;奇诺冲出黑暗与想来偷珍珠的小偷搏斗时,他的妻子胡安娜的“嘴唇像猫的嘴唇似的向后缩紧,牙齿龇了出来”;为逃避追踪者奇诺带着妻儿“像一条迟缓的蜥蜴一样慢慢地爬下那光滑的山肩”,而那几个追赶者则“像闻到温热的嗅迹的狗一样兴奋地哼哼着”,②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和《荷马史诗》、《圣经》、《诗经》等文学作品相比,斯坦贝克是否赋予自己的动物意象以新的文学意义?当他在文本中不遗余力地将人与动物联系起来时,他是否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传统?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他和先辈的相同之处在于,当他描写人类的言行举止时,他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今天所谓的“拟物”的修辞手法,赋予了人以动物的特性。然而,斯坦贝克不仅仅停留在将人比作动物、人与动物如影随形这一层面上,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这样一些更加特别的场景时,我们就不难看到斯坦贝克小说描写动物时与先辈的差异了。同样在《珍珠》这部小说中,当奇诺揣着珍珠带着妻儿逃离到一座石头山上时,遇见“山猫把逮住的禽鸟带到这儿来,撒下羽毛,用他们血淋淋的牙齿舐水喝”;小说《致一位无名的神》中主人公约瑟夫·韦恩因为在东部家乡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就携家带口来到西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一个山谷小镇谋求生存,初来乍到这个小镇,当他骑马穿过草地时,听到一声痛苦的尖叫声,他转过丛树一眼瞧见一头巨大的野猪,弯曲的镣牙,黄色的眼睛,蓬松杂乱的粗红毛,臀部盘坐在地上,“正撕咬着一只仍在尖叫的小猪的后腿;不远处,一头母猪和另五头小猪在恐怖的尖叫声中跳跃着逃走了”。[3]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第三章,斯坦贝克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写主人公汤姆从监狱出来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只乌龟不屈不挠地在布满风沙和汽车、行人等各种阻碍它前行的公路上艰难爬行的情景:“陆边的草地上有一只陆龟在爬行,不知怎地转向一边,拖着它那隆起的甲壳在草地上走着。它那粗硬的腿和长着黄爪的脚吃力地从草丛中缓缓穿过,并不是真正在走,而是一路在推着和拖着他的甲壳前进。大麦须从它的甲壳上溜下来,苜蓿的芒刺落在它身上,又滚到地下。它那角状的尖嘴微微张着,一双凶狠而可笑的眼睛在指甲般的额头直瞪瞪地望着前方……”[4]
山猫逮住禽鸟,野猪撕咬着一只仍在尖叫的小猪,陆龟克服阻碍吃力地前行……,从这些场景不难发现,当斯坦贝克的笔墨触及到人类的求生存状态时,作为参照系的总是那些动物求生存的画面。可见,与前人作品中调动的动物意象不同,斯坦贝克并不仅仅是为描写动物而描写动物,不管是将人比作动物、展示人与动物相似的动物性的一面,还是在作品中将人类的生存竞争与动物的生存竞争相提并论,他都是站在整个生物物种竞争的宏大背景下来展示人与动物共有的生存法则、自然界的物种循环和残酷的进化链条的,因此他笔下的动物就具有了新的内涵。这样一种写法,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拟物”修辞手法可以概括,它更多承载了新的对人与动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协调等规律的思考。
当然,深入理解斯坦贝克写作的这一特色,还需要我们了解斯坦贝克本人的生活实践、文学理念和哲学思想。不如此,就无法对埃德蒙·威尔逊等批评家的批评展开深入的反批评,也无法解答读者至此产生的这样一些疑问:比如斯坦贝克在文本中为何如此集中描写人与动物? 斯坦贝克为何要展示人与动物相似的动物性的一面?支持着斯坦贝克进行这一探索的合法依据何在?如果说这样做有意义的话,他的意义体现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语景下重新加以认识。
二
从现存的大量资料来看,斯坦贝克是少有的关注海洋生物、生态环境的美国作家之一。他从小就对家乡附近太平洋沿岸蒙特雷海湾里的各种海洋生物有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除了英语和文学外,他还特别喜欢生物学,上大学时,他修了动物学和海洋生物学的课程。1923年夏天,他和妹妹玛丽参加了斯坦福大学分校霍普金斯海洋研究站开设的海洋动物学暑期课程,从此开始了他对海洋生态的着迷。1930年他认识了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里科兹,对大海的热爱与对海洋生物的共同兴趣让两人一见如故,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友谊。他们经常一起到海边拾集海洋标本,观察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进行科学实验研究,1940年两人一同前往科特斯的海(现在的加利福尼亚湾)进行为期六周、4000英里的实地科学考察,次年两人合作出版了《科特斯的海航海》。可以说,斯坦贝克对海洋生态的兴趣是终身的,各种海洋生物的生活、活动总是令他着迷,这一特殊的生活经历成就了一位特殊的斯坦贝克,他不仅在文学界是一位成名小说家,如今他也是一位在科学界得到了认可的被称作“生态先知”[5]的业余海洋生态学家。
斯坦贝克之所以在作品中将人的描写与动物的描写相提并论,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生活实践让他意识到了今天被科学不断证实的、自然界经久不变的一条规律,即物种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就意味着在生物学上意义上,人类与动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同族关系,都是生命形式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就是一条巨大的‘存在链’,这条链将人与自然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仅仅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份,用一句生态箴言来说,即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联系。这也就是他在《科特斯的海航海》中所明确表述的,“如果能以一种联系的眼光来观察,那么很明显,物种仅仅是一个句子中的逗点,每一物种即是金字塔的点,也是金字塔的基……人与一切联系着,与所有的现实,已知的和未知的,不可避免地联系着……万物即一物,一物即万物——浮游生物,波光粼粼的大海,旋转着的星球,不断延展的宇宙,都被时间之弹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6]1962年,斯坦贝克出版了环游美国的游记《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一书,书中再次表达了这种万物相联的思想。在途经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南莫哈韦沙漠时他遇到两只郊狼,他说,要射杀它们很容易,杀掉它们,也是为民服务,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眼中郊狼是害兽,它们偷鸡,为数繁多的鹌鹑以及其它的猎鸟都因它们而数量锐减,但面对郊狼,斯坦贝克问自己:“我干嘛要介入?”他的手指迟迟不愿碰触扳机,因为他很清楚“在万物关系的微妙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被绑在一起。”[7]斯坦贝克的这个思想与被誉为世界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野生动植物管理之父的阿尔多·利奥波德在其有着“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美誉的著作《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像山那样思考”的整体主义思维有极其相似之处。
如果说,斯坦贝克在作品中将人的描写与动物的描写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一直是业余的海洋生态学家,意识到人与动物的同族关系,那么斯坦贝克为何要在作品中展示人与动物相似的动物性的一面呢?理解这点,必须从理解斯坦贝克的非目的论哲学思想开始。
斯坦贝克是非目的论哲学思想的信徒,这一思想构成了理解斯坦贝克世界观及他小说创作手法的重要依据。在游记《科特斯的海航海》中,斯坦贝克详尽地阐述过这一非目的论思想。在他看来,目的论思想关注的是生活“应该是”什么、或“也许”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与目的论思想不同的是,非目的论思想关注的是生活实际“是”什么,即对“现实”的思考和接受,它不去追究因果关系的“为什么”,也不去不切实际地幻想理想“可能”是什么。在斯坦贝克的多数作品中,尤其是早期作品中读者不难发现非目的论思想的痕迹。1936年出版的《胜负未决的战斗》被出版商和评论家认为是一本宣传社会改革的小册子,是政治宣传单。其实斯坦贝克在这部小说出版前的1935年1月15号,就在给朋友乔治·阿尔比(GEORGE ALBEE)的信中说过“这本书是残酷的,我仅仅想记录意识,不做判断,只是记录而已”。[8]1935年2月4号他给出版商的信中又重审 “我想这是一本残酷的书,不带感情,因为里面没有作家的道德观点”,[8]他不关心故事的主人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他描写的只是‘人’,所以不管是暴力,还是温柔,也不管是肮脏的宿舍,还是美丽的苹果园,他都完全客观地、不带感情地观察,并一丝不荀地写下来。在回忆录《爱德华·里科兹》中斯坦贝克曾经回忆了自己写作《蛇》时的经过:“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后来我把它写成短篇故事,我写它只是因为这件事发生了,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无法回答这里面的哲学含义是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很简单,事件就是这样的。”[9]1947 年 7 月 31 日斯坦贝克与战地摄影家卡帕进行为期40天的苏联之行, 次年出版了《俄罗斯纪行》一书。对这一次苏联之行斯坦贝克说他的任务是 “如实地报道,如实地记下我们的所见所闻,不带评论,不对我们了解不够的事件下结论”,即,不做评论者或分析者,只做一个观察者。圣何塞州立大学斯坦贝克研究中心主任苏姗·丝琳劳(Susan Shillinglaw)1999年在此书再版的前言中写道,“《俄罗斯纪行》一书是以一双记者的眼睛捕捉细节,不带目的的观察,仅仅记下亲眼目睹的一切”。[10]苏姗认为在许多方面,这正是斯坦贝克从事创作20多年以来一直在相当成功地做着的事情,是斯氏最具特色的写作风格。简言之,非目的论思想及其创作手法特点,就是认真地、细致地观察现实世界,并有如摄影机般地如实地、客观地呈现现实世界,不带有主观评价的成份,用斯坦贝克的话说就是:“事情这样,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6]
从非目的论的思想出发,意味着斯坦贝克不可能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样子来描写,而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他既要表现人性中神性的一面,也要表现人性中动物性的一面。他之所以在作品中赋予人以动物的特性,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还不断穿插诸如黄狼鼠杀死松鼠,大鱼吃小鱼,猫头鹰猛扑啮鼠,鹰俯冲攻击野兔,野猪吃鳗鱼却又被狮子吃掉等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血腥场面,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人的原初的自然本性的客观呈现,即,跟所有其它动物一样,在生存面前,人类同样具有掠夺性的求生本能,这是生物遗传性使然。人类在文明的外衣下斯文礼貌,但一旦遇上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又何偿不像这些动物呢?斯坦贝克笔下不乏这样的人物,《愤怒的葡萄》中的银行家、大农场主,《珍珠》中的医生和珍珠收购商,《伊甸之东》中的卡西等等,其残忍与动物相比有过犹而无不及,更多了一份奸诈、阴损和猥亵。在散文集《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直言不讳地直接把人类比作是接近于掠夺成性的食肉动物:“是占有、贪婪、可怕和侵犯型的弱肉强食者,什么都吃,无论是生的还是死的,具有蟑螂和老鼠的天赋。”[11]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大都是社会的贫穷者、被压迫者,生存构成了他们主要的追求目标,为了最基本的吃、住、穿,他们不得不苦苦地努力挣扎,这是人在生物层面为求生存的本能反应。不管是人类的求生本能或是人类在利欲的驱使下的贪婪,斯坦贝克这种非目的论式的描写都是在客观地呈现人性中的动物性的一面。
从生物链的角度出发,斯坦贝克意识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即人是动物世界的一部分,必然深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动物性的一面,而从非目的论思维出发,斯坦贝克必然会直面现实,客观地呈现人类动物性一面的残酷现实。这正是斯坦贝克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动物意象和描写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的深层原因所在。
三
回到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对斯坦贝克小说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到,埃德蒙·威尔逊等人之所以排斥斯坦贝克小说的“动物化倾向”,实际上是基于人类优越于动物的认识而产生的。这是长期以来人与动物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截然不同地位的直接反映。
如前所述,尽管拟物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远古时期就已存在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但是这并意味着动物享有与人同等的地位。相反,西方哲学思想传统的主旋律是动物低人一等。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提出因为动物只使用身体服从本能,自然比人类低贱,他的这一思想构成了日后西方传统的一个部份。基督教经典《圣经》告诉人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最最接近神的样子,具有与上帝形象的相似性。中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经院神学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神学大全》中论证了无理性生物不能主宰自己的行为,与有主宰自己行为能力的人类不是同类,所以只有人类才是最完美的存在物。17世纪二元论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动物不能使用语言表达思想,与人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他直言不讳地说动物充其量是一部机器而已。18世纪德国伟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同样肯定了理性优越论这源远流长的传统。[12]在西方,虽然人们如何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和争论,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人类优越论,尤其是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的这几个世纪,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人类也一步步繁衍出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最终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高贵无比。用生态批评家尼尔·埃文登(Neil Evernden)的话说就是:“的确,甚至一提到人与一切都有关联,或人与其他生物有共同的生物关系,就会被某些人看成是对人类的冒犯。”[13]
除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之外,批评家本身的立场与视野同样影响了他们对斯坦贝克作品的认识与评价。以埃德蒙·威尔逊为例,埃德蒙·威尔逊本人的文学批评深深植根于19世纪的人文传统,他的代表作《阿克瑟尔的城堡》所关注的作家就主要是叶芝、瓦莱里、T.S.艾略特、普鲁斯特、乔伊斯、斯泰因等人。这些作家大都是高雅文学的代言人,笔下的人物主要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反观斯坦贝克笔下的人物,他们无不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人民,边缘人群、智障人群。比如《煎饼坪》中的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各种高加索人的混血儿,《胜负未决》中的罢工工人,《人与鼠》中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固定的住所,农忙时节以打短工为生近乎行乞到处流浪的农业季节工人,《愤怒葡萄》中被沙尘暴赶走的破产、逃荒农民,《甜蜜星期四》中的流浪儿、鸨母、妓女;《天堂牧场》中那个时刻想要钻进地底下与青蛙为伍的的图拉勒西图,《约翰·熊》中那个有着惊人记忆力和模仿力,却是个呆小病患者的主人公约翰·熊,《人与鼠》中那个虽力大无穷,却不能独立生活、经常惹事生非的弱智者莱尼,《罐头厂街》中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佛兰基,等等。
斯坦贝克笔下的这些人物没有优美的仪表,没有文雅的举动,相反他们言辞怪诞,行为滑稽,性格缺陷,在埃德蒙·威尔逊等批评家眼中,这无疑是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等级界限,是剥夺了人所有高贵的品质,自然令他们匪夷所思难以接受,引起广泛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
结语
对于人的地位的过分夸大,对于大写的人的迷信无疑已经对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随着环境危机的越演越烈,人们越来越关注非人类世界,也迫使人们对传统认识提出挑战和质疑,重新去审视100多年前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即较高级生命形式是由较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人与动物处于一个心理和行为的梯级上,在结构和能力上具有连续性。这份关注已经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掀起的动物解放运动和环境运动中得到见证。当今的科学研究与发现已进一步印证了达尔文的理论洞见,比如,人类几乎与普通黑猩猩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结构。今天,当人们用一种全新的环境视野来阅读斯坦贝克的作品时,就会发现他作品的“动物化倾向”表面上似乎是将人降至动物的水平,损害了人的尊严,实际上是还原了事实的真相,有力地反拨了对人的地位的过分夸大。他的作品在全球仍受到不断的关注和欢迎与他作品的“动物化倾向”是分不开的,斯坦贝克比这些批评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遵循着文学的伦理,即面对真实,反映现实的伦理,而且还在于他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界休戚相关的命运。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本身的要求来看,还是从今天的环境视野来看,斯坦贝克的这一写作特色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2002年斯坦贝克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斯坦贝克研究中心联合了近30个图书馆、大学和出版社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中心于2001年8月2-5日在他的家乡萨利纳斯召开以“美国作家的诞生”为主题的第21届斯坦贝克研究联欢节。次年的3月20日-23日,纽约成功举办了第5次国际斯坦贝克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teinbeck Congress),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学者、批评家、诗人、剧作家、电影制片商等各界人士,他们提交的论文由斯蒂芬·乔治编辑同年以书名《约翰·斯坦贝克:百年礼物》出版。第30届斯坦贝克艺术节(30th Annual Steinbeck Festival)2010年8月5日-8日在萨利纳斯的国家斯坦贝克中心(National Steinbeck Center)举行,吸引了来自加州和美国全国各地读者、研究者和民众出席。
②文中所引《珍珠》中的文字均自朱树飏选编《斯坦贝克作品精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P292-361。以下同。
[参考文献]
[1]McElrath, Joseph R,Jesse S.Crisler Susan Shillinglaw Et.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81.
[2]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06-510.
[3]John Steinbeck, To A God Unknow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5, P6.
[4]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15-6.
[5]Tamm, Eric Enno, Beyond the Outer Shores: The Untold Odyssey of Ed Ricketts, the Pioneering Ecologist Who Inspired John Steinbeck and Joseph Campbell,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2004, P4.
[6]John Steinbeck and Edward F. Ricketts, Sea of Cortez. New York:Paul P. Appel Publisher, 1941, P217,137.
[7]John Steinbeck,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2, P212.
[8]Elaine Steinbeck and Robert Wallsten, eds., John Steinbeck: A life in Lette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5, P98,105.
[9]John Steinbeck, The Log From the Sea of Cortez, with a profile “About Ed Rickett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 Pxxii-xxiii.
[10]John Steinbeck,A Russian Journal with Photographs by Robert Cap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9,Pvii.
[11]Susan Shillinglaw and Jackson J. Benson eds., America and Americans, and Selected nonfiction-John Steinbec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2, P393.
[12]彼得·辛格, 汤姆·雷根.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曾建平,代峰译)[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胡志红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