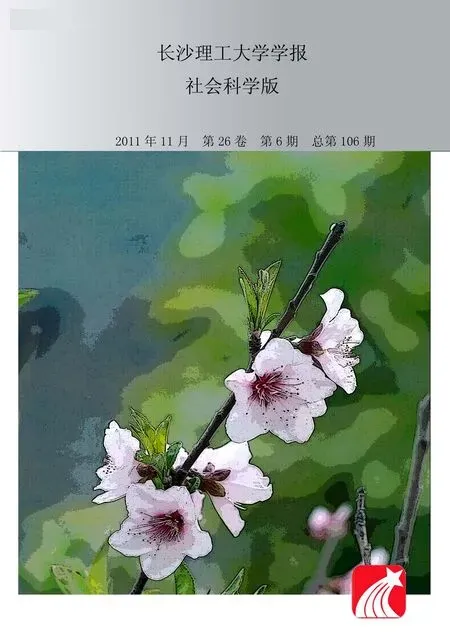地域学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诗歌
张德明
(湛江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由于一个人的出生、成长总是与一定的地域环境、地域文化和地域个性紧密相连的,因此可以说,每个诗人的心灵深处都会深烙上较为鲜明的地理学印迹,那种特定的地域意识和地域特性也将在他们的诗行之间不时悄然地流溢出来。这种情形的存在,注定了从地域学角度研究诗人与诗歌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学术方法。在我看来,从地域学视野上考察当代诗歌,既可以将其以往被忽视的某些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揭示出来,也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诗学维度上敞现当代诗人别具一格的地方性生命经验和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地域学的角度出来,对当代较为优秀的几个诗人加以粗略的分析和阐释,以期揭示他们诗歌中各自不同的审美内涵,并为人们重新认识当代诗人与诗歌提供一个新的方案和路径。
一、潘维与江南
潘维号称“江南才子”,他是一个很性情的诗人,他的名作《今夜,我请你睡觉》创制出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新奇世界,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思维冲击:
永远以来,光每天擦去镜上的灰尘,/水无数遍洗刷城镇,/但生活依旧很黑,/我依旧要过夜。/茫茫黑夜,必须用睡眠才能穿越。//西湖请了宋词睡觉;/广阔请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睡觉;/月亮,邀请了嫦娥奔月;/死亡,编排了历史安魂曲;/非人道的爱情睡得比猪更香甜。//睡觉,如苦艾酒化平淡为灵感;/如肥料施入日历,抚平紊乱;/使阴阳和谐,让孤独强大;/一种被幸福所代表。//可没有人请我睡觉。/为什么?!为什么/比愚昧无知还弱小多倍的地球上,/居然没有人请我睡觉。/怀孕希望,有智慧体从醒悟的眼光里跃出来,/全部喊道:潘维,汉语的丧家犬,/今夜,我请你睡觉。
“茫茫黑夜,必须用睡眠来穿越”,读到这样的句子,只觉得一股对于人类生存莫大的绝望与悲观之情如飓风一般呼啸而来。“今夜,我请你睡觉”也许是一个极其俗气的话语,但被诗人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历史和哲学韵味,诗题与内涵之间巨大的意义反差鲜明凸显了全诗的审美张力,诗歌由此具有了不凡的艺术品质。“西湖请了宋词睡觉”、“广阔请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睡觉”,从如许非凡的造语中,我们已经领受到潘维逼人的才气。而最后一节里,诗人通过“为什么没有人请我睡觉”的质问与邀请其睡觉的众喊这两个情景的设置,将个体对于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的双重失望委婉而含蓄地表述出来。
熟悉潘维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句口头禅——“孤独啊!”潘维常挂于嘴边的这句道白,很多人只当作一种玩笑话来听取,而我认为,这话恰恰是他内在潜意识的不自觉流露。正是由于诗人内心深处有着无法排遣的孤独感,因此一个总喊着要“请你睡觉”的人,自己却常常是一个“失眠者”。《我,拥有失眠的身份》这样写道:
我,拥有失眠的身份。我愿献出/一个三角形:坚定的金字塔。/在无尽的旋转中,它跪向一条深蓝的水,/如仆人,用一条未调教好的狗/对着广阔,撒下季节的哀伤。/今夜,武装起来的明亮,匪徒般蜿蜒于/水乡阴寒密布的千丝万缕中。/记忆,割开多汁的风,转身留下凌乱的背影。/噢,酿蜜的脚步盘旋着皮革的沉重,/如挣扎的窗帘随着剧烈的一扯,便断了气。/从我的脉搏上,切得出汉语的命数,/仿佛我是藏身于根部的汉奸,随时准备/向世界公开灵魂的约会暗号。/在隆隆的接近里,铁轨中弹般卧倒,/沿渐渐微弱的往事,浓密如羽的睫毛开始松弛。/星光,滴破屋顶:冬天闯入。/寄生于花瓣上的,是最优秀的那滴黑夜,/它引领着拥挤的现实,穿过我的生命。
一向潇洒谈笑的潘维,为什么要在这里公开自己“失眠的身份”?一个异常看重“睡觉”的诗人,他为什么总是深陷“失眠”的困境之中呢?这是因为饱含忧患意识的诗人,痛感古典的消散,传统的沦失,现实的变味所致。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理性地察觉自己所处的环境里,“明月”已被伪装,记忆只有凌乱,而异质性的东西正在慢慢浸透中国文化的肌体,“寄生于花瓣上的,是最优秀的那滴黑夜,/它引领着拥挤的现实,穿过我的生命”,古典的汉语文化,悠远的历史传统,连同充满神韵和风华的江南世界,正在默默地沉没于历史的风烟之中。一旦看清如此的惨象,谁还可能安然入眠呢?
在现代化的魔爪四处伸张的历史语境里,那个燕语呢喃、草长莺飞、如诗如画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了,代之而起的是喷着黑雾的高大烟囱,高分贝震响的重型机器以及大地上满怀纷乱与焦虑的现代人群。潘维用他的诗歌描画了令人沉迷的梦中江南、纸上江南,为那个逝去的锦绣江南唱出了最后的挽歌。你看他的《遗言》:
我将消失于江南的雨水中,/随着深秋的指挥棒,我的灵魂/银叉般满足,我将消失于一个萤火之夜。//不惊醒任何一片枫叶,不惊动厨房里/油腻的碗碟,更不打扰文字,/我将带走一个青涩的吻/和一位非法少女,她倚着门框/吐着烟,蔑视着天才。/她追随我消失于雨水中,如一对玉镯/做完了尘世的绿梦,在江南碎骨。//我一生的经历将结晶成一颗钻石,/镶嵌到那片广阔的透明上,/没有憎恨,没有恐惧,/只有一个悬念植下一棵银杏树,/因为那汁液,可以滋润乡村的肌肤。//我选择了太湖作我的棺材,/在万顷碧波下,我服从于一个传说,/我愿转化为一条紫色的巨龙。//在那个潮湿并且闪烁不定的黑夜,/爆竹响起,蒙尘已久的锣钹也焕然一新的/黑夜,稻草和像片用来取火的黑夜,/稀疏的家族根须般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黑夜,//我长着鳞,充满喜悦的生命,/消失于江南的雨水中。我将记起/一滴水,一片水,一条水和一口深井的孤寂,/以及沁脾的宁静。但时空为我树立的/那块无限风光的墓碑,雨水的墓碑,/可能悄悄地点燃你,如岁月点燃黎明的城池。
“江南的雨水”,那是多么富于柔情和缠绵的江南圣景,那是孕育了多少象征江南风情的故事与传说的自然之物,这次被潘维搬用来虚拟和描摹一个江南才子别具一格的死亡场面。“萤火的夜晚”、“太湖的棺材”、“无限风光”的“雨水的墓碑”,一场轰轰烈烈的生命远行,借重的却是风情万种、低徊婉约的江南物象,显露着“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江南之情。一个人即使赴死也对这江南胜景不依不饶,千扯万拽,牵绊无已,这情景里折射着对古老江南的极端留恋。自然,潘维所塑的江南在现实人间已经难觅踪影了,只能在纸上、在梦里、在诗中寻见。在这个意义上,潘维的“遗言”不过是一次用诗行记下的思念江南、想像江南的梦话而已。
现实中的潘维在性格上比较清丽柔婉,有江南才子习惯性的轻软放怀之风,在生活的追逐中也不乏江南人的闲逸和快活。然而,他的诗是沉滞的,是凝重的,让人读来有喘不过气的感觉。只是由于人为按压进去的伤古之怀、念旧之意过重,潘维的诗歌时而会不自觉地流溢出某种阴性化的脂粉气来。这一点或许也从另外的层面映证了潘维的诗是一个本真的江南人写下的有关江南的诗。
潘维在2004年杭州的一场大雪之中,所写出的《苏小小墓前》一诗,是一首以富有传奇色彩的古代江南女性为情绪背景来书写自我心灵世界的佳作。生于1964年的诗人潘维,在不惑之期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年过四十,我放下责任,/向美作一个交待,/算是为灵魂押上韵脚,//也算是相信罪与罚。/一如月光/逆流在鲜活的湖山之间,/滴答在无限的秒针里,//用它中年的苍白沉思/一抔小小的泥土。/那里面,层层收紧的黑暗在酿酒。// 而逐渐浑圆、饱满的冬日,/停泊在麻雀冻僵的五脏内,/尚有磨难,也尚余一丝温暖。// 雪片,冷笑着,掠过虚无,/落到西湖,我的婚床上。
《苏小小墓前》总共三部分,上引是其第一部分,已可看出全诗的核心情绪。一个四十岁的男子,显然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都有了较为深邃的体验和觉识,这或许是古人称那些入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为“不惑”的原因。从常理推断,进入不惑之年,一个人有关生命的担负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会若山石一样沉淀在心的。但潘维却举重若轻,在四十岁之期居然能轻松放下责任、负担、使命,而立于一个沉埋在历史风尘中的烟花女子的墓茔之前,追索和寻觅某种诗意人生。这是怎样的襟怀和心意呢?或许只有情韵婉转的江南文化才能培育出这样的风流才子,培育这样洒脱飘逸的襟怀和心胸。“西湖,我的婚床”,如此绝妙的造语,精彩地诉说了诗人对江南历史和江南文化的留恋和至爱。
二、陈先发与桐城
陈先发的诗歌创作牵连着中国当代新诗诸多值得关注和追问的问题,这注定了对他的阐释可以从许多径路上展开和延伸。陈先发首先是一种“现象”,80年代末出道,90年代成名的他,新世纪之后在创作上发生了重大转型,骤变为一个以题材奇特、语言耐嚼、长短诗兼擅而独立于诗坛的个性鲜明的诗人,这种个性使他既迥异于当下其他诗家,也迥异于90年代的自己。陈先发其次代表了一种“经验”与“方法”的成功尝试,他的诗歌为当代诗人如何将传统文化的血脉与个体生命经验和精神气息融汇起来,灌注于诗行之间,从而构建心意辗转、余韵缠绕的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新诗美学提供了范例。陈先发身上体现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当代新诗地理诗学和文化诗学建构的表征。在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条件下,陈先发不仅将桐城派的精神传统作了不失精彩的现代汉语的诗性书写,还以此为基点,扩延为对中国新诗的民族品格的思考与塑造上。他一方面寻找古典传统阐发的现代性出口,另一方面又注重新诗现代性的中国经验赋意,在以古观今和以今发古的双重维度上不断拓展着诗的疆土。他的诗体现出多重性,既是古雅的,典丽的;又是现代的,繁复的。是一种深烙着地域性格、民族色彩和现代性气质的艺术样式。
陈先发1967年出生于“户户翰墨馨香,家家灯火书斋”的桐城,他的骨子里流淌着桐城文人“多朴厚”、“尚气节”、“敦廉耻”(姚莹《东溟文集·吴春鹿诗序》)的精神血液。“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方苞语)的桐城派,为这个古老城市铸足了文化底气,也为后人树立了求学问道的励志碑铭。在桐城这块土地出生和成长,是陈先发的幸运,也给他以无形的压力。他日后的复旦求学和诗坛打拼,或许与这种无形的压力有直接关系。
几乎与一个历史朝代同兴衰、共存亡的桐城派,可以说是一个从特定的区域意识和地理经验上对中国文化本体加以接受和重新诠释的文学派别。从这一点来说,陈先发看重“地理灵性”的诗学主张,或许正是来自于桐城派成就自身的艺术启示。在长诗《写碑之心》中,陈先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总是说,这里。/和那里,/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所受的地理与轮回的双重教育也从未中断。”可以想见,诗人所受的这种教育中,一定少不了耳濡目染的桐城派文化传统。伟大的文学总是带着地气的精神产品,也就是“地理灵性”的衍生物。对诗人来说,地理既是他观照世界的思维起点,还是一种经验的原点和文化的气场。尊重“地理灵性”,就是对个体心灵经验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就能对人类当下的生存现状作最为真实的记录和历史的还原。《黄河史》一诗如此写道:
源头哭着,一路奔下来,在鲁国境内死于大海。/个三十七岁的汉人,为什么要抱着她一起哭?/大街,在田野,在机械废弃的旧工厂/常常无端端地崩溃掉。他挣破了身体/着一根白花花的骨头在哭。他烧尽了课本,坐在灰里哭。/连后果都没有想过,他连脸上的血和泥都没擦干净。/秋日河岸,白云流动,景物颓伤,像一场大病。
这是站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基点上,对“黄河”进行的诗意烛照,“黄河”的今非昔比、面目全非,被诗人予以病态的写照,并夹杂以哀痛和哭诉的情绪处理。诗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追问从而植根于一个富有历史景深的中国语境上,并借助民族化特征鲜明的中国经验而传达出来。
陈先发几乎所有的诗歌都以质疑现代性为思想起点,不过他从不空发议论,也不滥自抒情,而是有力地继承了桐城派主张“言有物”“言有序”“修辞立其诚”的文学理念,在具体的情景设置和触手可及的情绪伸展中,将自我对现代化的深邃反思与对中国文化的别样理解隐曲而精妙地呈现出来。《前世》启动了“陈先发式”的书写模式,在古代故事与民间传说的现代演绎中,既将自我的历史理解和超历史的诗化因子输入代表民族情感记忆的古事之中,又借古典事项侧面而隐讳地传达自我对现代文明的深层透视和理性拷问。全诗如下:
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不必等到血都吐尽了。/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他哗地一下就脱掉了蘸墨的青袍/脱掉了一层皮/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脱掉了云和水/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又脱掉了自已的骨头!/我无限誊恋的最后一幕是:他们纵身一跃/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暗叫道:来了!/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碧溪潮生两岸//
只有一句尚未忘记/她忍住百感交集的泪水/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说:梁兄,请了/请了——
梁祝化蝶的传奇故事,在陈先发富于个性化的诗歌版本里,有了许多新意。在《前世》里,爱情主人公原有行为的被动性已化为主动,凄绝的死亡已经孵化出令人惊艳的永生,他们反抗的决绝与爱情的坚贞之间构成互文互诉的映照关系。这不只是历史传说的重写,而是现代性生命体验的传递,对梁祝决绝反抗的叹赏里寄寓着诗人痛切地批判现代性、渴望逃离浮躁当下的精神立场。
陈先发观照现实的角度也是独特的,颇富意味的。他拒绝对眼下之景做直截了当的书写与阐发,而是以语意缠绕迂回,古今情景杂糅的艺术表现形态,在历史的纵深中展现并重构现实场景,巧妙抒发自我繁复的心声。《鱼篓令》一诗写曰:“那几只小鱼儿,死了么?去年夏天在色曲/雪山融解的溪水中,红色的身子一动不动。/我俯身向下,轻唤:“小翠,悟空!”他们墨绿的心脏/几近透明地猛跳了两下。哦,这宇宙核心的寂静。/如果顺流,经炉霍县,道孚县,在瓦多乡境内/遇上雅砻江,再经德巫,木里,盐源,拐个大弯/在攀枝花附近汇入长江。他们的红色将消失。/如果逆流,经色达,泥朵,从达日县直接跃进黄河/中间阻隔的巴颜喀拉群峰,需要飞越/夏日浓荫将掩护这场秘密的飞行。如果向下/穿过淤泥中的清朝,明朝,抵达沙砾下的唐宋/再向下,只能举着骨头加速,过魏晋,汉和秦/回到赤裸裸哭泣的半坡之顶。向下吧,鱼儿/悲悯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我坐在十七楼的阳台/闷头饮酒,不时起身,揪心着千里之外的/这场死活,对住在隔壁的刽子手却浑然不知”,这首诗是颇富意味的。虽然是在当代的地理中穿行,但诗人借助往前回溯的时间意识,将过往朝代巧妙地插入,使现实情景一下有了历史的厚度,中国本土文化的生命基因在现代性的情绪感知和灵魂体验中被激活。
为了追求诗歌气息的纡徐萦绕和不断升腾的诗意效果,陈先发采取了多褶皱构建诗歌句式与段式的艺术手段,这使他的诗歌常常显得风姿绰约,饶有趣味,同时也造成了其诗婉转有余,舒展不够;缠绕过多,清朗不足的毛病。这或许是注重义理、考据的桐城遗风在当代诗歌中的某种延传。不过,陈先发秉承的这种婉转和缠绕的表达方式,对于遏制当代诗歌写作日益口水化和直白化的不良趋势来说,又不失为一种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写作策略。
三、雷平阳与云南
雷平阳的诗集《云南记》从一个草根的生命视角上,写出他眼中所见的昭通和云南,写出他理想中的云南与现实的云南之间的矛盾、摩擦、纠缠和搏斗,写出在现代化侵占和覆盖下,云南这块集聚着中国品类最多的少数民族的土地上历史生态和文化生态正在日益失衡、少数民族独特珍稀的文化传统正在不断沦失的残酷现实,写下他内心的不安、苦闷、彷徨和焦虑,写下他的爱与恨、歌与哭、奔走与停留、躁动与稍安。雷平阳的诗里,由此饱含着热量、血液、情感与体温。
在《亲人》一诗里,雷平阳以“逐渐缩小的过程”一语来生动喻示自己对身边事物不断归于内心的真爱:“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只会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在诗中,“逐渐缩小的过程”一语,诗意地诉说了爱的真谛,它有效抵制了那种把爱播向五洲四海的虚妄,以富于真理性的声音告诉我们,世上真正单纯、朴实、触手可及又温度不减的爱其实就是对亲人的爱。
雷平阳好长时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曾经有人把他当作21世纪诗歌中类型写作的代表,这是因为他的那首诗:《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这首诗在地理学构图上显然是对郦道元《水经注》的一次盗版,而“向南流X公里,……河”“又南流X公里,……河”“又南流X公里,……河”的句式铺排,绝对不是一首正常诗歌的语言秩序。这首诗诞生之后,称赞者捧其上天,誉其为极有创新意义的诗作,反对者贬其入地,直接称其为复制性的无效写作。而我看来,雷平阳如此将三十三条河一路陈列下来,其实是在提醒人们关注它们的命运,这些河,有些暂时存在着,有些正在消失,有些早已名存实亡。现代化的魔掌正向它们一一伸过手去,它们的生命朝不保夕。
雷平阳深信诗歌的精神性力量,他将自己的诗歌看作“纸上的旷野”[1],他希望用这“旷野”为迷人又渐渐远去的故乡准备了广阔的承载空间,为不断沦丧的传统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提供可以永生的精神地盘。怀着某种悲切,他在《在坟地上寻找故乡》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从野草和土丘之间的空隙/眺望几公里外,我生活过的村庄/那儿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它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冶炼厂/一千年的故乡,被两年的厂房取代,再也/不姓雷,也不姓夏或王。堆积如山的矿渣/压住了树木、田野、河流,以及祠堂/我已经回不去了
谢有顺称雷平阳的诗歌创作是“有根的”“有方向感的写作”[2],我认为是相当有道理的。雷平阳的根深扎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而他的方向就是用诗的文字为不断逝去的那些文明星火和传统血脉提供最后一片栖息之地。面对“隆隆的机声”“通明的灯火”,他丝毫不现目睹现代文明终于落户于偏远贫困乡村的喜悦,而是莫名的伤怀一涌而上,堵住了他的心灵。在现代中国,“回不去”故乡的抱撼,恐怕不是雷平阳一个人才有的。
正是因为痛切地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铁蹄正在肆意地践踏乡土中国的脊背,焦虑和不安便始终萦绕在诗人的心头。这种生命状况,促使诗人混迹闹市,却常有避世之念,身在红尘,却有看破红尘之心。《寺庙》一诗写曰:“有没有一个寺庙,只住一个人/让我在那儿,心不在焉地度过一生/我会像贴地的青草,不关心枯荣/还会像棵松树/从来都麻木不仁/我会把云南大学的那座钟楼/搬到那儿去,卸掉它的机关/不让他,隔一会儿就催一次命/我一旦住在那儿,就将永恒地/关闭,谁也找不到我了/自由、不安全、焦虑/一律交给朋友。也许,他们会扼腕叹息/一个情绪激越的人、内心矛盾的人/苦大仇人的人,从生活中走开/是多么的吊诡!可我再不关心这些/也决不会在某个深夜/踏着月光,摸下山来/我会安心地住在那儿/一个人的寺庙,拧紧水龙头/决不能传出滴水的声音”。 “一个人的寺庙”,这是多么清明沉静的世界,它或许是雷平阳的某种生命理想,但又是充满悖论的永远也无法变成现实的理想。我想,真要给他一个孤悬于山岭上的清幽寺院,挚爱人间的雷平阳也未必就会入住进去。但他用这种独特的表述,突出地呈现了守住自我、归于内心的精神追求。
《祭父帖》是雷平阳近期创作的长诗,可以说是他长诗创作中的翘楚之作,也是当代长篇诗作的精品。诗人通过对父亲的祭奠和追忆,将那个特殊的年代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进行了诉讼和鞭挞,也以此来深度返观和拷问自己的灵魂。虽然诗歌与那段历史和政治有涉,但诗人的语言却是极为朴实、沾着泥土气息和味道的话语,丝毫没有政治的语词。父亲的仙逝给诗人带来的心灵痛楚无疑是巨大啊的,在诗中,雷平阳以一个独特的方式来表露这种痛苦:
我跪在他的灵前,烧纸,上香/灵堂中,只有他和我时,我便取出刚出的新书/《我的云南血统》,一页一页烧给他/火焰的朗诵,有时高音,烧着了我的眉毛/有时低语,压住了我的心跳。
“烧书”的细节展示,突出的是诗人悲痛已极的内心状况,“云南血统”字样的出现,则暗示着诗人与亡父在地域板块、生存空间、生命理解上的某种一致性。诗人接着用了很多的笔墨,追述父亲苦难和卑微的一生,尤其父亲的卑微,被诗人放在显微镜上加以精细的呈示:
无论何时,都应该是圣旨、律法、战争、政治/宗教和哲学,低下头来,向生命致敬!可他这一辈/以上的更多辈,乃至儿孙辈,“时代”一词,就将其碾成齑粉/退而求其次的生,天怒、土冷;只为果腹的生/嘴边又站满了更加饥饿的老虎和狮子;但求一死的生/有话语权的人,又说你立场、信仰、动机/没跟什么什么保持一致。生命的常识,烟消云散/谁都没有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心。同样活于山野/不如蛇虫;同样生在树下,羡慕蚂蚁
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的思考是冷峻的,也是深沉的。通过父亲生存现状的写照,诗人告诉我们,父辈(不只是父辈,其实还包括我们)卑微的生存,其实是与一个民族所处的时代氛围、政治气候乃至所属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
在《祭父帖》中,一生卑微地苟活着,低着头走过人世的小路的父亲,到了晚年,则老迈颓唐为“灵魂走丢了”的人。雷平阳如此陈述道:
如今用作灵堂的地方,堆着玉米的小山,刚一进门/我就看见他苍白的头,像小山上的积雪/喊一声“爹”,他没听见;又喊一声“爹”,他掉头/看了一眼,以为是乡干部,掉头不理,在小山背后/一个锑盆里洗手。念头一闪而过,那小山像他的坟/走近他,发现一盆的红,血红的红。他是在水中,洗他的伤口/我的泪流了下来,内心慌张,手足无惜/也就是那一天,我们知道,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灵魂走丢了。
这样一个“灵魂走丢了”的人,他将在苦难与不幸中顽强求得生存的愿望,最后蜕变为一种无奈的符号。我们由此就能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到了这个时候便显示出双重的悲哀。
《祭父帖》是为一个卑微的生命所作的传记。对于“父亲”,雷平阳没有将其圣化,而是将他放在平常人的生命层次上来定位,又将这个普通农民置放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去描述,具体而微地呈现他的沉重肉身,他的卑微灵魂。在一个平凡人的生命行旅中看到历史的踪迹和中国人的现实遭遇,这是《祭父贴》体现出的最大的思想价值。
可以说,雷平阳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在诗歌尤其是长诗中常常会投入超剂量的感情因子,如果不用叙述,雷平阳诗歌中的抒情意味一定会过于浓烈而令人难以承受。好在诗人有着拿捏有度的本事,他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为了减缓抒情的强度,淡化抒情的浓度,惯于大量使用叙事性的艺术技法,诸多沉稳的叙述语的穿插和渗透,极大弱化了诗歌的抒情力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住了雷平阳作为本质上的抒情诗人的一面。
[参考文献]
[1]雷平阳.云南记·自序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谢有顺.雷平阳的诗歌:一种有方向感的写作[J].文艺争鸣.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