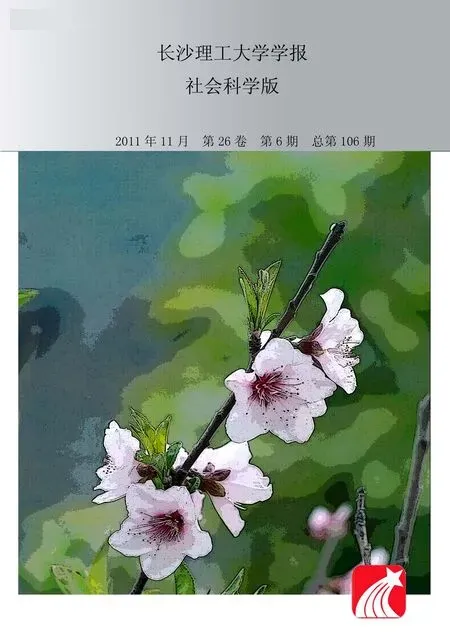国内科学精神研究述评
易显飞, 张裔雯, 文 祥
(1.长沙理工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4;2.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精髓, 是人类精神中不朽的旋律。托尔斯泰说过: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科学精神是科学发展的支柱,是科学腾飞的动力。本文拟对国内科学精神问题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及评价。
一、关于科学精神内涵与本质的已有研究
对于科学精神的内涵,专家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给出了各自的回答。1922年,梁启超在南通发表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认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上世纪40年代竺可桢在分析近代科学先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生平事迹基础上,认为科学精神具备三个特点:(1)依理智为依归,不盲从与附和,只是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1]
蔡德诚从科学研究的本征出发,认为利学精神是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善于“辨误识伪”,勇于“去伪存真”的的“求真”、“求实”、 “求真知”的精神。据此,他认为科学精神的要素和内涵应包括六个方面: 客观的事实依据;理性的怀疑与批判;多元化的思考;基于权利平等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2]科学史学家刘钝认为,科学精神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在本体论意义上要坚持外在物质世界的可知论哲学,要以客观世界本身来解释客观世界;在方法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不盲目迷信权威,以实验、实践为标准的实证主义原则。[3]李惠国认为,科学精神的内涵包括:实证精神;分析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革命精神。[4]刘晓玉认为,科学精神是求真的,崇尚客观性,并试图把个别的、感性的经验抽象为普遍的、统一的和简洁的概念或范畴。[5]
胡守钧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生存发展的优秀传统和生命线。科学背后有其所传承的东西,那就是科学传统。科学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和科学传统有着必然的关联。如果科学丢掉了这个优秀传统,那么科学也就不可能发展下去。所以传统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从纵向来讲,科学精神贯穿古今;从横向来讲,科学精神横跨所有科学。科学知识可能会过时,被淘汰,会被新的科学知识所取代。但是作为科学的优秀传统-科学精神不可能被淘汰。淘汰了科学精神,科学就没有生命了[6]。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的已有研究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人文精神一般更多地对人类的“生存意义”、“精神家园”、“终极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活动实践中形成的系统性价值观。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和指导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和科学精神注重理性与逻辑相比,人文精神更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尊重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与人生的意义,重视科技与物质生产的人文价值等。[7]
袁豪认为,随着基于科技发展的人造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使得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日益加深。从而,本是同源的科学与人文开始分离。19 世纪末,德国掀起了“两种科学”的对立,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呈现出日益对峙的趋势;时至20世纪20、30年代,这种对立更是被逻辑实证主义所推崇。这样自然科学取得了强势地位,人文科学则日渐边缘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公开“决裂”,不仅造成了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隔阂与对抗,而且造成了“现代性”气质主导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8]
关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共同点,杨叔子认为:人文所追求的是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的;而科学所追求的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的。因此,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这个知识,这个认识,越符合客观规律,就越真,就越科学。人文不但是一个知识体系、认识体系,而且是一个价值体系,伦理体系。这个知识、认识、价值、伦理越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越善。[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余谋昌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相互作用。我们要提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同时提倡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10]”。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嵌入、 互相促进与共同发展的。[11]人文精神给予科学精神的正确的价值导向,而科学精神则可以外化为物质力量从而保证人文精神的实现。要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就要在人文和科学的全面理解中塑造当代的人类精神,以促进“两种文化”的协调发展。华裔着名数学家丘成桐说:我致力于数学研究,并不是为了金钱或名利,而是被数学的优美和伟大深深吸引。科学是真善美的统一,科学精神的求善求美正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中国人文文化颇有研究的涂又光教授指出,人文精神,需要在科学中养成。[12]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以计算机、生命科学和通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万能论”也逐渐为人们所抛弃,很多问题是无法依靠科学技术自身来解决的。同时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诸如生态的、人文的、社会的负价值。科学与人文其实是一种互相形构而非目前那种对立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人与自然”关系的走向,人及人类社会自身命运的走向,是人类真正地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并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基础。[13]
三、关于科学精神的价值已有研究
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学精神;温家宝总理在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强调要树立科学民主精神,要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和完整的人格。那么为何要如此重视科学精神呢,科学精神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呢?
夏从亚认为,发扬科学精神,首先,可以提高主体的素质,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离开科学精神的培育;其次,科学精神的形成可以为科学发展、认识进化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再次,科学精神是战胜封建思想,战胜伪科学、反科学行为的最有力武器;最后,发扬科学精神既是国家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其本身的重要内容。[14]
吴家德认为科学精神的价值在于,科学求真精神的弘扬,能为科技进步与创新提供条件。科学精神的大力弘扬,可以推动思维方式创新,为科技的进步与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科学求真精神的大力弘扬,还可以加强我国的高科技研究和基础研究,从而实现科技的跳跃式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使科技发展转向经济发展,使科技研究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最终又为科技的进步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15]
黄涛指出:从科学发展史来看,科学精神可以说是对科学发展起着“灵魂性”支撑的作用。科学的每一次提升和革命都依赖一定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而科学精神就是科学使之成为科学、并能持续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最初人们把科学简单的看作是一种静态知识、一种知识体系,到后来人们把科学的认识由静态发展为动态,把科学看作一种认知世界的动态过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从一种知识到一种过程,乃至深化到一种社会建制、一种方法、一种思想、一种精神。[16]
施威指出科学精神的传播对当代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科学精神的传播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其次,科学精神传播有利于合理的“扬弃”民族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有利于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革新与重建。再次,科学精神的传播有利于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推动。最后,科学精神的传播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17]
申振东对于科学精神的价值特别强调了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首先,科学精神具备社会生产力功能。蕴含在科学过程中的科学精神是与科学实践相伴相生的,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不断质疑、批判、创新的精神力量促进了近现代科学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次,科学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精神中的理性、批判、求实以及创新等,提升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的认识,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性是整个世界的头等大事,并借助于科学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以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科学基础。再次,科学精神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发展。科学精神所蕴含的理性、无私利性、团队合作、宽容、奉献精神等特性,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提供一种伦理范式与伦理姿态。[18]
四 关于中国的科学精神已有研究
早在1922 年,维新派的梁启超发表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他认为,如果只是懂得科学原理本身,而没有科学精神,中国将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就要成为被淘汰的国民。[19]
毕明皓认为,当前中国科学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众科学精神的缺失。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和政治哲学说比较发达,但相对的科学理论比较薄弱。这主要受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推崇整体的、辩证的认识方法影响。第二,学术界与教育界科学精神的缺失。相比于平民阶层的科学精神,学术界与教育界科学精神的缺失的影响更为深刻,这种科学精神滑坡与“失范”普遍存在,它主要表现在功利主义色彩浓厚,在利益的驱使下,学术界往往表现为一种极其浮躁的利益主义心态。第三,官员科学精神的缺失。在中国,官员作为政治的主导者和行政的干预者,他们的民主意识精神思想和社会责任感如何,能直接反映整个社会的法治和道德水准。归纳起来,部分官员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有三种,首先是盲目决策。其次是弄虚作假,最后是贪污腐败。[20]
王晓勇认为,从古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人文精神发达,科学精神落后的国度。思辨能力与逻辑思维落后,应用科学或技术发达。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非自觉的,而是受外部环境逼迫的,是与“富国图强”的主题相联系的,传统的中国观念是:学习任何科学技术知识,必须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否则一概拒斥,这也是滋生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沃土。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一直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而优则仕,可见科学精神未在中国萌发,科举制度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21]
竺可桢认为, 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 因此在向中国引入西方自然科学时, 既要有不盲从附和、不武断蛮横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22]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独树一帜,但是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却处于边缘状态,并且我们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基本上来于西方,对此,竺可桢采取“拿来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在引进西方科学时,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对于我们来说知之甚少,从而导致我们对科学精神的模糊认识。同时,东西方的差异造成了科学精神的异化。竺可桢认为这种“模糊认识”与“异化”主要体现在:第一,由于语言和思维的差异而导致形式逻辑的匮乏,中国一直以来偏爱辩证法,但科学的基础却是逻辑的思辨能力。第二,中国哲学把追求“道”为目标。当用“道”来指导行为时,就显得有些徒劳。第三,中国人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而不是自由,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思想。这种和谐本身没有错,但“真理在开始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这部分少数人就变成了不和谐因子了,成了社会和谐的破坏者,这样,这些求真的人就成为了和谐的牺牲品了,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虽然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况,但那是为了教会的权威)。第四,中国人对知识本身很少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即使是中国哲学家对知识的应用也远比抽象的知识感兴趣。在实践上,主要反映在统治者往往注重任务的应用性研究而轻视基础性研究。就整体而论,对逻辑的严密性、自然界的数学化、对实验结果的重视以及理性的批判等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相对薄弱的。[23]
毛建儒认为,总的来说,中国科学精神的特征具体地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求是不足。求是是科学精神中最根本的表现,即求与事实相吻合。中国的科学精神中,求是的精神是存在的。但中国的求是精神还有许多不足:求是只存在于具体的直观领域,没有上升到一种普遍的精神,中国所关注的更多是伦理道德;把求是作为一种手段却不是目的,求是仅仅是为了应用而不是对真理的一种追求。第二,求真不足。中国科学家解决问题往往都就事论事,并没有把这个过程当做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没有看到这在整个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的哲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并非是解决理论上的悖论而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它也不可能成为精神层面的东西。第三,求用大于求是和求真。求用属于人文精神的范畴,并非是科学精神的成分,但在中国的科学中“求用”的踪迹处处可见。不仅如此,中国科学精神还时时受到求用的制掣。[24]
五 关于科学精神研究的综合评价
科学精神是科学中的“灵魂”,它贯穿于科学实践中、凝结于科学建制中、体现于科学方法中、内化于科学家的“范式”中。无论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还是在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上的发展,都是离不开科学精神的。科学精神一方面外化为社会的科学意识,渗透到社会大众的意识深处,与人文精神融会贯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根本性和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它内化为科学家的科学观念。成为维护科学共同体的价值基石,引导科学工作者的言行,保证科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对科学精神展开研究,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情。国内关于科学精神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科学精神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科学精神的价值与社会功能;中国科学精神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这些问题域的研究,可以说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加可喜的是,近几十年来,涌现了一批以科学精神为主题的相关着作,如王大珩,于光远的“论科学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叶福云等着的“科学精神是什么”(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袁运开、王顺义编的“世界科技英才录-科学精神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顾家山的“诺贝尔科学奖与科学精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陈洁的“尤里卡:科学精神的别样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王兵的“科学之灵:论科学精神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这些着作反映了科学精神确实纳入到了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并成绩斐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此类问题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①从研究内容看,尽管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科学精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做出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但依旧缺乏对科学精神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已有研究只是侧重对科学精神的内涵与结构等问题研究,而对于科学精神的历史演变、科学精神的发生学机制、科学精神的实践哲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几乎较少涉及。②从研究视角看,已有的科学精神研究,基本上局限于科学文化、科学伦理与科学的价值哲学的研究范式,较少从科学史、科学与经济、科学与政治等维度去进行解释,从而使已有研究缺乏历史的厚度与宏观把握的宽度。③从研究思路与方法看,已有科学精神研究偏好于对科学精神的理论建构,忽视结合历史与现实中的科学家的科学实践对科学精神进行具体微观分析,较少采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科学精神问题。④从研究效果看,由于已有科学精神研究远离科学实践本身,远离现实社会,对中国科学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关注力度不够,导致相关研究结论过于抽象,对科学实践缺乏真正的引导作用。已有研究所存在的上述问题,给我们对科学精神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席泽宗:科技史十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3-44.
[2]谢维营,严乐儿:关于“科学精神”的研究述评[J].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00-103.
[3]刘钝:文化一二三[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42.
[4]田明山,倡导科学精神[J].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32-33.
[5]刘晓玉,童继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5(2) : 187-188.
[6]胡守钧:科学精神[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7-8.
[7]袁豪:简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J].法制与社会,2007(1):589-590.
[8]袁豪:简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J].法制与社会,2007(1):589-590.
[9]孙德宏:关于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N].工人日报,2002-10-31.
[10]谢维营,严乐儿:关于“科学精神”的研究述评[J].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5):100-103.
[11]刘晓玉,童继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5(2) :187-188.
[12]王建平:论科学精神[J].沧桑,2009(4):140-141.
[13]袁豪:简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J].法制与社会,2007(1):589-590.
[14]夏从亚,刘冰:科学、科学精神及其价值探讨[J].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35-38.
[15]吴家德:科学精神的当代价值[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2):6-8.
[16]黄涛:科学精神内涵及社会功能浅析[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4):14-15.
[17]施威,颜家安:论科学精神及其传播[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2):58-63.
[18]申振东:论科学精神与人的全面发展[J].贵州大学学报,2007(4):1-3.
[19]夏从亚,刘冰:科学、科学精神及其价值探讨[J].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35-38.
[20]毕明皓:当前科学精神的缺失重建[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60-61.
[21]王晓勇:科学精神与诺贝尔奖[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9):60-64.
[22]竺可桢:竺可桢文录[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41.
[23]郭慧志,徐婕:科学精神的界定与传导[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2-3.
[24]毛建儒:论中国科学精神的特征[J].学习论坛,2010(2):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