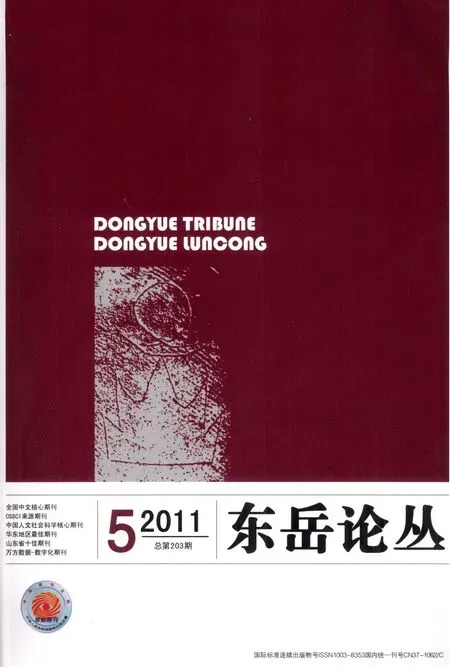“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
——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日)吉田薰
(日本女子大学)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
——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日)吉田薰
(日本女子大学)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新民;死生观;佛教;墨子;宗教;精神文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这时的明治日本正在向“文明国”迈进。但抵达日本后,梁启超针对“新民”读者创办的《清议报》(1898年 12月),则开始对列强诸国所提倡的“文明”提出疑问。《清议报》介绍国外新闻时,颇关注日本媒体以及日本国内对“文明”的批评。根据《清议报》新闻的介绍,日本媒体很坦率地指出西方的矛盾,认为西方各国在东亚的举动与和平会议的精神相悖;西方人所说的和平不是世界和平,目前中国成为他们的角逐之地,何况他们的公法只限于国际法的领域,乃是基督教徒之间的僻见①《论万国平和会议》,《清议报》,第 24册,1899年 8月。;而且有的日本报纸还指出,对于非人道的国外新闻,日本国内不论是所谓新知识派还是论坛、甚至于各宗教信徒,都只是保持沉默②《文明国人之野蛮行为》(译日本报),《清议报》,第 65册,1900年 12月。。日本国内这些相互矛盾的“文明”观引起了梁启超等在日中国人的注意③典型的例子是大阪博览会事件。在大阪博览会上,人类学者坪井正五郎所设计的学术展览由于含有中国、朝鲜、冲绳县等国家或地区的人无法接受的内容,因而受到神户领事官和中国留学生的严厉批评而被撤掉了。参见坂元ひろこ:《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进化论·人种观·博览会事件》,《思想》第 849号,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包括日本在内,以“文明”自命的各国的所作所为却并未遵守“公法”,他们的殖民地主义政策令各民族陷于生死之间④周作人:《说死生》,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将国外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输入本国,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一直得到中肯的评价,但梁本人对国外文化是如何解读和消化的,这一点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笔者以前讨论过在明治国家盛传的“祈战死”和“日本魂”等风潮之下梁启超如何看待幕末志士和武士道,以图建构针对“新民”的文化⑤拙文《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与消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 2期。,在本文中,笔者继续关注的是,在“轻死”之风盛行的时代中,梁启超怎样探讨死生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注意到“宗教”关心死后的“不死”世界。其实,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注意到西方各国提倡文明时,其文明和“宗教”是有密切关系的。梁启超批评康有为鉴于西方基督教的存在而把孔子当作教主,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西方基督教的作用,要用“宗教”来推动改革和革命,这一思路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是很普遍的。在此,笔者将探讨梁启超何以执着于“死生”问题,并由此涉及梁启超对“宗教”、“精神”的关注,以总结其死生观的演变和发展。
一、从佛教入手探究“宗教”
继《清议报》之后,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1902年 2月)。与《清议报》相比,《新民丛报》像一般综合性杂志那样很细致地设置了不同的学术栏目。但在所谓的学术栏目中,我们会发现“宗教”这一栏目并不常见,仅仅有时会出现而已。而且在这个栏目中,梁启超的文章只有三篇。第一篇是批评康有为的孔教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第 2号,1902年 2月),接着是《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第 19号,1902年 10月)、《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第 23号,1902年 12月)。梁启超此前并不喜欢谈宗教,乃是因为觉得其偏于迷信而阻碍真理①中国之新民:《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新民丛报》第 19号,1902年 10月。。《新民丛报》所刊载的梁启超有关宗教的论文确是不多,可梁启超并不是没有关心宗教,相反,他试图应用宗教。
梁启超对各国志士抱有很深的关注,指出他们怀抱着强烈的宗教思想,这成为他们成就伟业的原动力。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宗教徒,他们的宗教以至诚为条件,并不是迷信的。而且,所谓的文明国家最尊重信仰自由,认为各宗教的高下不在教义的优劣而在于信仰的虔诚与否。这是梁启超对宗教的一个观点。这样,宗教的功用就被应用在梁的《新民说》里,明治维新时的王学和禅宗,曾国藩的克己的锻炼,都可以作为修养成宗教思想的典范②中国之新民:《续论自由》,《新民说八》,《新民丛报》第 8号,1902年 5月。。尽管梁启超对原来的意见仍有所保留,即认为宗教有迷信的要素,会覆盖真理,妨碍谈学问③中国之新民:《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新民丛报》第 19号,1902年 10月。。
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中批评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而强调历史是进化的。在梁启超看来,“天然”是随意发展的,因而今后需要人有意识地参与天然的发展,由人力引导发展的方向④中 国之新民:《论进步》,《新民说十》,《新民丛报》第 10号,1902年 6月;《续论进步》,《新民说十一》,《新民丛报》第 11号,1902年 7月。。梁启超提倡群治的进步,如同注意到在国外小说对社会的功用那样,他随即关注到各国的“宗教”,于是标榜佛教在本土的功用,强调佛教和群治应该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还提出跟基督教相比,佛教具有自己的优点⑤中国之新民:《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新民丛报》第 23号,1902年 12月。。梁启超认为不仅中国和基督教不合,而且西方在中国宣扬基督教的时候是别有用心,是以宗教为名而谋取自身的利益,如果不谨慎的话,会招致祸害。而另一方面,他指出佛教的优点是智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总是参与世间,其信仰是无量的,是平等的而非差别的,自力的而非他力的。跟基督教相比,这是佛教更加完善的地方。此外,借用佛教的因果说,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腐败是由于前人种下的恶因所得的恶果,那么现在的人就不能借责备前人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从现在起自己就造善因的话,随着善因的积累国家将来就有望强大;而如果自己也造恶因的话,国家将来也只能得到恶果。特别是对于佛教所说的“魂”经由因果报应思想而对群治产生的影响,梁启超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梁启超来说,“宗教”还很明确地包含着对高尚的道德和社会的复原。这样梁启超否定了宗教中的出世观念,在他看来,谭嗣同便是因为明白生与死的关系,不贪图一己的和眼前现世的享乐,培养出不怕死的精神,因而成就了事业。梁启超把这种对待佛教的方式叫做“应用佛学”,他这篇文章也是典型的“应用佛教”,把佛教教义当作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⑥中国之新民:《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新民丛报》第 23号,1902年 12月。。
此外,关于佛教,除了其对群治的有效性之外,梁启超还注意到佛教讲人死后的世界的观念——来世。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很少涉及来世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死的问题也曾被意识到,但儒学用“名”谈生命延长以对待死的问题;道家则解释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如老子和杨朱就认为不管怎样的生,最后的死是一样的,所以还不如乐生;神仙派认为有术可以长生不死。这是中国古人对死的态度⑦中国之新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 18号,1902年 10月。。在其他国家,不管是古代埃及还是印度婆罗门或是基督教,他们都意识到死后的事情,但在梁启超看来都没有穷究其理,只有佛教对此作了最为彻底的追究,“谓一切众生本不生不灭,由妄生分别,故有我相。我相若留,则堕生死海,我相若去,则法身常存。死固非可畏,亦非可乐,无所罣碍,无所恐怖,无所贪恋。”⑧中国之新民:《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 18号,1902年 10月。
梁启超由此特别强调佛教在中国不是宗教而是哲学,并期待借助佛教在中国创造出新文明。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以后,就被融合于中国固有文化。到了近世,康有为、谭嗣同等提倡佛教,提出佛教的复兴。而梁启超看重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消化能力,说中国人有能力把先秦、希腊、印度以及欧美文明融合在一起①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 22号,1902年 12月。。梁启超认为,基督教是“迷信宗教”,中国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佛教不是“迷信宗教”。但在“宗教者,亦循进化之公例以行者也”②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 22号,1902年 12月。的认识之下,为了证明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不是迷信的“宗教”,强调中国从印度接受大乘佛教,这足以表明文明的高度,并且佛教的很多部分比起在印度来反而是在中国得到发展,中国人的“迷信宗教”之心也很淡薄,因此中国佛教是跟哲学融合而发展的③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 22号,1902年 12月。。
梁启超认为中国佛教具有哲学因素,以此试图讨论佛教和群治的关系,但对“宗教”与教育的关系,梁启超表示警惕。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的开头就有以教育代替宗教之论,但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不能发表议论。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德育也就得到发展,到时信仰什么都没有害处。在日本,其时正围绕宗教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井上哲次郎引发的“教育和宗教的冲突论争”是其中之一。梁启超则认为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候,以避免将宗教牵涉进有关教育的争论之中去。关于“宗教”,梁启超把它与“信仰”和“迷信”联系在一起,始终保持很慎重的态度④关于梁启超和“宗教”,巴斯蒂有过详细的考察。巴斯蒂:《梁启超与宗教问题》,《东方学报》第 70册,1998年。。1899年接到姊崎正治的邀请,梁启超在日本哲学学会会议上以中国的宗教改革为题发表讲演。这次讲演主要介绍康有为的孔教。此时,梁启超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只是介绍中国“宗教”的动向,介绍春秋三世说是把中国古代文明中的观念设定为未来的进化主义,康有为独创的孔教为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这里所说的宗教的涵义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因而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也特意补充中国不是宗教的国家,数千年来没有宗教⑤任公:《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 100册,1901年 12月。。并强调与“宗教”有联系的康有为,从阳明学进入佛学,于禅宗尤有会心,康有为的心是如佛般的,不断地体味世俗之苦,这直接关系到他现在所从事的救国救民的行动⑥任公:《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 100册,1901年 12月。。梁启超一边配合“宗教”这个题目,一边与此保持距离,认为康有为作为提倡孔教的宗教家,其支柱在于佛教,他通过常住于世俗的磨炼而得到修养。
梁启超认为基督教则含有迷信的成分,不能满足中国士君子的要求;并且中国从佛教得到的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营养,而不是宗教方面的理念⑦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 22号,1902年 12月。。梁启超对宗教的根本看法还是注重其迷信的成分。当前的急务是为了现在中国的救亡,用新学说改造中国思想。而且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近代欧洲也互不相属⑧中国之新民:《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新民丛报》第 10号,1902年 6月。,因而梁启超就强调政教分离⑨光 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定一尊”就是拒绝外部思想的流入,是改革的障碍。由于侵害思想自由,梁启超反对“定一尊”的宗教设定。可梁启超不否定孔子。梁认为康有为为了救国没选佛教而选了孔教,从中国风俗历史来看这是“不得不然”的。孔子是教育家、经世家,不是宗教家,是与宗教相对的存在,为了控制宗教所造成的迷信的危害,儒家作为“新民”所需要的个人修养不可或缺。但是探究死后世界的不是儒家而是佛教,这是佛教优于西方宗教的地方,并且中国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哲学接受佛教的。
二、“有我”与“轮回”
1898年梁启超抵达日本时,他所关注的是当时日本盛传的武士道。可要传播给“新民”读者时,梁启超就需要探讨如何解读武士道,以应用在“新民”的建立上。因而梁启超就用他的方法,关注到幕末志士、德富苏峰的作品、阳明学、遗民以及儒家,把它们相结合而界定“新民”精神⑩拙文《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与消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 2期。。而关于“死”,一个国家的国民如何面对它,这是军国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在日本,这个问题被设法用武士道或神道等应付过去。当时,佛教和基督教只被允许在宗教范围内所生存,并且也抵敌不过“国家主义”的体制。而像井上哲次郎所提倡的那样,这些问题被与“国民道德”相联系。
1904年梁启超发表《中国之武士道》,杨度为其写序。在序中杨度重新回顾日本的宗教,认为日本武士道是儒家和佛教的融合,在高桥五郎《宇宙论》的基础上,杨度介绍灵魂死后灭不灭的论说①森纪子:《梁启超の佛学と日本》,《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版。,说人和畜生之别在于精神。并引用加藤咄堂的《死生观》,指出死法有健全的和不健全的。
加藤咄堂之论死法也,分为六种,健全者三,不健全者三。健全者,一曰,视死生如一,谓圣哲之达观者;二曰,死于个人而生于社会,谓以死成仁者;三曰,信天命,谓当事变而不乱者。不健全者,一曰,自死以断痛苦,谓自杀者;二曰,以死为得未来之生,谓情死者;三曰,以死为得精神之安慰,谓迷信死后之幸福者。②杨度:《中国之武士道·杨叙》,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上海:广智书局,1904年版。
梁启超受到杨度此文的启发,于 1904年撰写《余之死生观》,在《新民丛报》发表。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已说到佛教在轮回阶段如何切合于人事,在此梁启超又把轮回即解脱之前的生死反复的阶段、无明和真如的世间作为讨论的前提,以人自身处于社会中这一时期来讨论生死。梁启超从最初就没有把佛教的解脱作为目的,而是关注解脱之前人的行为,他把佛教的羯磨和进化论的遗传性作为重点,把世俗的人的精神作用作为主题。利用佛教的“识”,即世间是心所照出的映象这一观念,梁启超指出,“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以人处于世俗的这个阶段为主题,探讨生与死的问题。人不可离开这世俗社会,而前次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谈到“形”“魂”之别时,讲佛教的“魂”是永恒性的这一思路在此则被否定,梁启超说佛教没有像基督教那样谈灵魂,并强调从佛教因果报应和进化论的观念来看,人所做的事情在其死后也会留存于世间。在这个思路下,孔子被提出,孔子是用自己的“名”贡献于世间。当下的人物推动时代而使社会进步,这有赖于个人的私德和公德的影响力。梁启超的生死观接续着《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的论述,注重于探讨人解脱之前的状态如何能够联系于群治。之前,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唯心》,在这篇文章中也解释天下万物的现象都归于“我”③任公:《唯心》,《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 36册,1900年 3月。,即便讨论轮回时也仍然离不开“有我”。
梁启超很关心轮回,但这篇文章中他如此重视“有我”,并描述人死后也会给群治留下影响力,引起了蒋观云的反响。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开始连载《佛教之无我轮回说》。蒋在开头就说,读了梁启超的文章就感到关于轮回中的无我是怎么达到的并不太清楚,于是想重新探讨无我的过程。
蒋的文章首先确认佛教的印法,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静寂的基本精神态度,讨论达到无我之前有什么样的过程。梁启超是没有把达到解脱作为目的的,因此可以说,蒋观云是为了补充梁说而作。不过,蒋氏强调的还是精神应有的方向,关于这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都是一样的④观云:《佛教之无我轮迥说》(一),《新民丛报》第 3年第 18号,1905年 4月。。于是关于所谓死生观,蒋观云提出个人死后为社会的人们所继承的“人群寿命说”。死去的人由于被他人记忆而似乎获得一种生命的延续,蒋氏就此给予评论,同时提到梁启超和杨度都持有类似的看法。蒋观云解释,根据梁启超的看法,各国都提倡名誉的价值。关于梁启超以前提到的常陆丸事件⑤中 国之新民:《子墨子学说》,《新民丛报》第 57号,1904年 11月。1904年日俄海战中,日本军舰“常陆丸号”被俄军击沉,但全舰官军拒绝投降,全部自沉海底。井上哲次郎与浮田和民展开争论。浮田认为那样的结局没有意义,兵士成为俘虏后,在俄国学习也并无不可。对此井上予以强烈反驳,说浮田是站在西方人所说的“自杀是野蛮行为”这一立场上,而他自己则特别强调武士道精神。有关梁启超的相关论述,参见拙文:《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与消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 2期。,蒋观云在此又指出“义务战争”与“名誉战争”成为争论的论点,“名誉战争”获胜了,这表明名誉在人群寿命说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于是蒋观云也重视对群治的功用,也跟梁启超一样很关心日本国内盛行的尚武风潮,认为武士道在中国相当于墨子,而对中国的游侠之风没有像日本那样产生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感到遗憾⑥观云:《日俄战争之感》,《新民丛报》第 46·47·48号,1904年 2月。。关于死生观,蒋观云根据佛教的轮回观来谈论,对于其在社会上的作用也表示关心。但另一方面他还指出,庄子和列子也有轮回观,用庄子和列子的话来说,就是顺应自然。而且庄子有万物的观念,佛教没有产生万物的原初,只在万物之间互相转化,所以庄子比佛教有更广大的宇宙。孔子也谈“天”,也有能够与佛教作比的宇宙观。作为超越佛教的宇宙观,蒋观云重新确认儒家和先秦诸子的“天”的观念,同时作为人的死生观之一种,而介绍佛教的轮回说。在探讨无我轮回的过程中,则用佛教的教义讨论中国哲学的正当性。蒋观云的讨论渐渐地倾向于道家,根据孟子的养心之理谈心理的修养,在儒教中特意抽出孔子和颜子的对话中“坐忘”的概念,这与“无我轮回”成为对照。蒋观云在此补充说,如果大大活用这些资源的话,能创造出比武士道更好的东西①观云:《养心用心论》,《新民丛报》第 3年第 22号,1905年 12月。。如此,蒋观云一边考虑佛教轮回观,一边着重于用中国哲学来发展精神世界,并且联系到国民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遗民,蒋观云也给予很高评价,并且追问现在中国人该有怎样的道德②观云:《国家与道德论》,《新民丛报》第 3年第 16号,1905年 3月。。梁启超和蒋观云都关心如何面对死生,梁启超始终执着于“有我”,蒋观云试图讨论“无我”,但他们一方面显示死后还能够保留生命的“名”,另一方面尽量活用中国经学来克服他们面对的尚武风潮。
梁启超关注宗教的影响力的时候,也注意宗教何以成就其影响力的核心所在,在梁启超看来,那即是灵魂的观念③中国之新民:《子墨子学说》,《新民丛报》第 3年第 1号,1904年 6月。。梁认为墨子具有宗教的性质,但他们没有讲灵魂,所以不能普及。包括墨子在内,梁启超注意到中国经学的关注点都在世间,“牺牲其本身利益之一部分以求家族若后代之利益。此种习性我国人之视他国,尤深厚焉,此即我国将来可以竞争于世界之原质也。”④中国之新民:《余之死生观》,《新民丛报》第 3年第 12号,1905年 1月。梁启超毕竟关心有助于国力的文化,所以关于佛教的轮回、“我”和社会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此虽然跟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究理是其所长,但是宗教所讲的死后世界,仍是不存在“我”的世界,梁启超不能那么轻易地接受顺从“宗教”的教义进入“无我”的世界。他始终重视的是“我”和社会的联系,其实这是康有为所提倡的孔教思路的延伸,“世界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强调“世界”的重要性,才能说孔子的思想多关注世间的事,这就把孔教和佛教焊接在一起了。康有为是要排除掉佛教的出世思想,而用佛教的其他思想如对极乐和圆满的追求,来确证儒家入世思想的合理性⑤《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 69页。。梁启超面对宗教时,重新承认并进一步剖析死后的问题,试图使得它与世间的价值连在一起。
三、鬼神论的补充和扬弃
梁启超断言,要说宗教,灵魂是最重要的因素⑥《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 18页,第 4页,第 43页。。讨论梁启超的死生观问题时,笔者认为还需要考虑到梁启超把墨子视为“世间”的宗教而给予关注。梁启超说,一般宗教是讲出世的,关注死后的世界,比如耶稣讲死后的天国,佛教讲死后的极乐世界,而墨子讲的则是世间的⑦《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 18页,第 4页,第 43页。。作为世间的“宗教”的墨子,在梁启超的两篇著述《子墨子学说》(1904年)和《墨子学案》(1921年)中得到讨论和体现。梁启超特意指出,墨子的“天志”、“明鬼”、“非命”诸篇构成了墨子的宗教思想。关于梁启超的墨子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它在引入西方学术、建立中西融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开拓意义⑧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此,笔者想关注梁启超对“明鬼”的解读,以使之与灵魂问题相关联。
梁启超认为灵魂乃是讨论死生观的关键之处,但在梁启超看来《明鬼篇》是墨子宗教论中最赘疣而无谓的。不过,梁启超也认为需要明确表示墨子的鬼神论决不是迷信,而是改良社会的一个法门;对于有没有鬼神的问题,墨子只是依赖经验论而已,因而梁启超不得不强调明鬼论是上古时代野蛮信仰之遗习。在《子墨子学说》中,梁启超表示明鬼论还是需要的,也特意把“明鬼”和“实行”连在一起,挖掘出其精神价值,认为其精神跟民德的强弱升降很有关系,也产生了义侠精神⑨《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 18页,第 4页,第 43页。。
墨子的实行,要普及的话,应该需要道德意义。梁启超特意提到义务观念和名誉观念会让人敢于实行轻生死的行为。但梁启超认为轻生死问题的最大关键在于灵魂的观念。佛教有涅槃、轮回、天堂、地狱,基督教有末日审判,梁启超把这些观念归结于义务观念和灵魂观念的结合,说墨子也涉及到这一点。而且此时,对梁启超来说,处理灵魂问题时,其时流行的学术可以成为最大的后盾。梁启超说,以往的哲学家认为所谓鬼是属于不可思议的领域,认为这不是我们这个愚昧的身体所包含的脑力所能研究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敢完全肯定,说死后一定没有鬼。梁启超此处特意提出:现在有“鬼学”(文言称为“魂学”),已慢慢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科学了,就是英语所说的“哈比那罗支”,日本译为“催眠术”。根据梁启超对“魂学”的解释,自己的灵魂和别人的灵魂互相影响,也关系到各种动作,这些动作以前属于神秘不可思议的,现在都能有原理可以解释了;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明白了生理和心理的关系而已。而佛教说的三界惟心、万法唯识等义理,现在也可以明白了。根据“魂学”,假如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可靠,一定另外还有聪明的、强固的、有自主权的、可以依靠的东西。墨子的明鬼,也就是表明了这样的东西的存在。此物一旦明确了,人对于生死的观念,就会看得很轻,没有障碍和恐惧。于是梁启超说,泰西伟人的事业,大多数靠的是信仰,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其实,梁启超还是注重道德责任,因而先确定支撑着死生观的东西都跟道德责任相辅相成,墨学的实行,也是以道德责任为前提的。而能够使人乐于去践行这种道德责任的动力在于魂学。魂学的功用很大,它能解释明鬼论和实行的关系。梁启超如此推崇“魂学”而引进它来补足明鬼论,要使之与实行相关联而得到应用。由此在《子墨子学说》的明鬼论里,可以看到当时梁启超需要建立替代尚武的一种宗教似的死生观。只有建立起死生观,才会愿意去忍受现世的苦难,但这种宗教的意义,墨家没有像佛教或基督教那样,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用来解释,梁启超也就无法信服墨子的学说,只是单单提取了他“轻生死”的观点,再把儒家的道德修养、道义之类的意义用作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梁启超曾用“迷信”来形容日本的“祈战死”,也意味着他感受到了这里面含有的某种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精神与墨家相类似,但梁启超仍然无法对宗教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只能追寻出儒家的道义来进行说明,这是从理性上易于理解的①以上参见拙文《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与消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 2期。,并且试图引进“魂学”来对应死生问题。
除了灵魂问题之外,梁启超认为在墨子的宗教思想中,“天志”和“非命”也是重要的部分,其实,由此也可窥见梁启超考虑宗教时顾虑的问题所在。梁启超从“天志”看到了有些与基督教相同的地方,即主宰者的意志代表一切。所谓仁人,就是在钜子制度里所通行的仁人,这些都是类似于教皇体制的,很难表现普遍的民意,也不如“道并行而不相悖”②《墨子学案》,第 30页。。此外,墨子不认可“命”,梁启超认为凡是可以用“力”的地方,“命”一定没有作用,他要强调决定性的因素是“力”而不是“命”。梁启超认为佛教的因果说可以帮助证明墨子的学说。他讲佛教的因果,注重的是现世。就像梁启超要求人参与“天然”的发展那样③中 国之新民:《论进步》,《新民说十》,《新民丛报》第 10号,1902年 6月;《续论进步》,《新民说十一》,《新民丛报》第 11号,1902年 7月。,他认为即使说“命”,那也应该是个人自身的力量可以左右的。
与《子墨子学说》相比,梁启超在《墨子学案》里,对“天志”和“明鬼论”的缺陷给予更多的批评,只有“非命”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仍然被给予较高评价。关于“明鬼论”,梁启超再也没有表现出如《子墨子学说》中那样的执着,而只是断言其为太古的遗物而已,没有要将它跟宗教连在一起来应用。而且,此处梁启超提到孔子的大同主义的价值,将墨子的兼爱主义与大同主义作比,指出虽然它们的理论方法相同,可孔子的大同主义并不要求立刻实行而必须经过各个阶段逐渐进化。兼爱主义不会接受别的主张,这点被视为与孔子的不同之处,这样兼爱就被降低在大同主义之下了。
其实,《墨子学案》的重点与《子墨子学说》相比有很大的变动。在《墨子学案》里梁启超大大引进西方学术术语,阐释墨子的经济学、论理学、科学等,但没有继续探究其宗教思想,反而再次批评钜子制度以及尚同社会,指出它平等但不自由,像俄国的劳农政府。也就是说,此时梁启超更加关注近代社会的结构,把民约论也带进来,按照近代社会的发展,重新描述墨子的社会组织及其程度。
“墨家既以天的意志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而极敬虔以事之,因此创为一种宗教。其性质与基督教最相逼近,其所以能有绝大之牺牲精神者全恃此。”④《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 130页 -第 131页。在相互间隔十多年的《子墨子学说》和《墨子学案》两篇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梁启超如何应用墨子:要么使之成为其对待死生观的学理资源,要么使之与近代科学结合显示其学术价值。而且梁启超无论怎样处理,都很认同庄子的“天下”篇为最好的墨子论。梁启超认为墨子的做法虽然不免极端,但墨子的精神还是可贵的。并也与民约论做对照,指出墨子不免忽略了个人权利、思想自由。“墨家只承认社会,不承认个人。据彼宗所见,则个人惟以‘组成社会一分子’之资格而存在耳。离却社会,则其存在更无何等意义。”①《先秦政治思想史》,第 131页,第 162-163页。梁启超提到章太炎所言之“墨学若行,一定闹到教会专制,杀人流血”,就说太过②《墨子学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 30页。,可说墨子尚贤,而最贤的是钜子,钜子又是墨学的优秀者,所以墨学若组织社会一定是一种教会专制政治,这是章太炎反对墨子的地方,梁启超也认同此观点。探讨死生观的时候,梁启超之所以关注墨子,是因为墨子所具有的宗教性,但其宗教性却是需要由梁启超来补足或否定的。尤其是“宗教”对社会和人所带来的负面因素,梁启超始终很警惕。因而梁启超就断言,所谓宗教不仅仅意味着灵界的信仰,墨家虽有《天志》、《明鬼》等论说,但从来没有提过极乐、来世等事,因而与基督教、回教等那些宗教性质不同。把墨家视为宗教者,主要指墨家的主张带有宗教性③《先秦政治思想史》,第 131页,第 162-163页。。梁启超明确把墨家与宗教做了区分,而最后提出的就是墨子的人格魅力,墨子信徒都那样能牺牲自己,是墨子的人格感化力使然。对墨子内在的精神,梁启超表示赞叹,但他对墨子的灵魂观没有再进行加工及与其它宗教放在一起讨论。
四、从“鬼魂”到“精神”领域
《新民丛报》上所提到的内容中,笔者特别关注的是《新民丛报》逐渐增加跟精神修养和心理学有关的论说。特别是它采录杂志《人性》上所登载的文章,值得注意④咀雪:《论信仰》,《新民丛报》第 3年第 24号,1906年 1月。。在《太阳》和《中央公论》等日本综合杂志势头很盛的时候,1905年 4月,杂志《人性》以提倡“依据自然科学上的知识,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我国唯一的学术杂志”⑤《人性发刊の趣旨》,《人性》第 1卷第 1号,1905年 4月。而创刊。主编富士川游在德国修医学,这份杂志也以德国杂志《政治人类学》为典范,从生物学、医学的角度来讨论人性。《人性》的宗旨比其它综合杂志更具专业性,是一个独特的存在⑥关于《人性》,参见松原洋子:《富士川游と杂志 <人性 >》,《<人性 >解说·总目次·索引》,东京:不二出版,2001年版。。“攻研人类的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历史是文化史的目的”⑦富士川游:《人性》,《人性》第 1卷第 1号,1905年 4月。,也就是说“人性”具有明显的“文化”的意识。在梁启超、杨度、蒋观云等《新民丛报》同人探讨死生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新民丛报》注意到这份杂志,似乎也走向与“文明”不同的探究人本身的“精神文化”的方向了。并且也可以说,这还显示了“宗教”被带进来以后,不断地展现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交涉的明治学问的一个过程⑧参见林淳、矶前顺一:《近代日本と宗教学·序文》,《季刊日本思想史》第 72号,2008年;矶前顺一:《<日本の宗教学 >再考——学说史から学问史へ》,《季刊日本思想史》第 72号,2008年。。
在此笔者要关注的是“精神”这个词。现代汉语中,“精神”有两种发音,即“jīngshén”和“jīngshen”,前者是从日语引进来的属于心理学范畴的学术术语,即现代汉语“精神”的意思,后者是元气、志气的意思⑨《中国语大辞典》,大东文化大学中国语大辞典编纂室编,东京:角川书店,1994年版。。不过,“精”在古代汉语中即有灵魂、气、神之类的意思。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后,笔者认为,他所用的多半是前者的意思,即从日本引进过来的科学术语,当要表示后者的时候,梁启超则爱用“元气”这个词。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个词的演变,不难看到,“魂”字也跟“精神”一词一样走过同样的路线。根据《说文解字注》,“鬼”代表一个总称,就是人死了之后要回归的某种存在。如果再具体地进行分别,就有“魂”、“魄”等名称,比如“魂”是阳气,“魄”是阴神,而实质上都是属于“鬼”一类的东西。但梁启超以及革命人士所用的“魂”还带有精神性的意思,梁启超把“魂”也提升到人的内在精神领域,如“中国魂”所表明的那样,“魂”被带进新民精神的启蒙中去了。
关于“精神”,笔者还要进一步指出,梁启超原来以“精神”和佛说的羯摩、进化论的遗传性为同义,作为“不死”的东西而使用⑩中国之新民:《余之死生观》,《新民丛报》第 3年第 12号,1905年 1月。。对梁启超来说,“不死”的东西应该是如同佛教的教理那样,具备究理的禀性。在这一意义上,梁启超所说的“精神”充分带有科学的性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起初梁启超被蒋观云指出《余之死生观》中没有谈到“无我”,但后来梁启超在《佛教心理学浅测》中提到“无我”,并使得心理学和佛学联结起来⑪《佛教心理学浅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八》。。梁启超解说五蕴皆空的道理就是“无我”的道理,用这“无我”脱出无常的苦恼达到“清净轻安”的状态,是“无我”的宗旨,这也促使人去学习高深精密的心理学①森纪子指出梁启超用五蕴皆空解释"无我",这似乎接近于姊崎正治的《根本佛教》和木村泰贤的《原始佛教思想》这两部著作的思路。森纪子:《梁启超の佛学と日本》,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版。。在此,“无我”与高度的“精神文化”得到联系,梁启超终于用心理学的学问提出“无我”了,这表明梁启超在撰写《余之死生观》的当时,对于西方和日本的宗教,以及对于“无我”抱有深刻的警惕性。此后,借用心理学这样的西方科学的学问谈“无我”,同时也开始谈及“精神文化”的领域了。夏曾佑在《新民丛报》上所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原》中,把孔子和墨子的鬼神观做比较,指出墨子承认鬼神以使得轮回存在,这导致轻生死的路线,夏对此给予批评,并强调宗教确是需要个人修养②别士:《中国社会之原》,《新民丛报》第 34号,1903年 6月。。梁启超创造“新民”,意识到“有我”的重要而没有轻易谈“无我”,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原来梁启超强烈地认识到西方宗教的教义和格致学互不相容,与此相比,佛教的教义则达到科学的地步。于是如上文所说,梁启超虽然提倡佛教,但也声明不谈宗教学③中国之新民:《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新民丛报》第 19号,1902年 10月。。要说宗教学,就应该谈各宗教的好坏。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至诚、信仰。只要有至诚的信仰,没有佛教也可以。对梁启超来说,“宗教”完全不是科学的,也不足信任。因而讨论宗教上的事没有什么意义,个人的信仰内容比“宗教”更为重要。梁启超也有意识到“宗教”,在面对佛教教理时,就承认佛教比其他宗教更具有科学性。但对于“宗教”的佛教所谈的“无我”,梁启超还是尽量要将其作为“我”和世间的联结点对待。对于有可能会联系到迷信的“宗教”,梁启超很警惕,直到最后得到“心理学”的后盾,才开始讨论和展示“无我”。
由此可见,梁启超很讲究“我”的存在,也看到“宗教”谈到了中国经学没涉及的死后世界,甚至提到“灵魂”的观念,因而认为这是他们的特征和优势,但追究其理的是佛教而不是西方的宗教。于是梁启超试图依靠西方科学接近“无我”,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在梁启超那里最初也被放在“不死”的领域,之后则被放置在东西方文化的视角上,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重新得到评价。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提到的“东西文化调和”论那样,梁启超认识到中国文化即是包括其“精神”的。在梁启超那里,“精神”从“不死”的领域升华到“文化”的领域,随之,孔子的“毋我”和佛教的“无我”也被当作同样描述超越自我的精神文化而成为东方文化的核心④《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对于道家,梁启超本来由于其厌世而消极地看待,但后来也作为追究“高尚的精神文化”重新给予评价⑤《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 107页 -第 108页。。
五、在群治和个人之间
梁启超刚结识章太炎的时候,章向梁质问康有为的宗旨,梁启超回答是变法维新和创立孔教,章就说变法维新为当时的急务,但只尊孔教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⑥冯 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 14章 (<《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66页。。在此该注意的是,作为跟梁启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如同抵抗“梁启超路线”一般,章太炎展开自己的言说。章太炎很早就在《清议报》发表《儒术真论》,他要彻底地破除天和上帝主宰人间的观念。他也提到西方天文学,但在他看来,天文学所谈到的太阳、星球、地球是各自都有自己的世界的,太阳是实物,天和上帝则是人所想象的东西而已,因而人和太阳有关系,而不是人和天或上帝有什么关系。在章来看,佛教的轮回、因果也是自己的循环,“佛氏之约,不得伺诸天鬼神穷理尽性。”⑦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 25册,1899年 8月。章太炎对人被主宰表示极大的警惕性,还批评迷信,引用荀子的话,指出天星的运行与政治无关⑧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 31册,1899年 10月。,佛教虽然有一整套因果报应的理论,但这也是跟天无关的,而是“我”和“你”的直接关系⑨章氏学:《儒术真论》,《清议报》第 32册,1899年 12月。。这是章太炎对“公理”的不信⑩太炎:《四或论》,《民报》第 22号,1908年 7月。。但因为梁启超注重对群治的效用、对“新民”的道德,所以重视天人感应,并期待天对人或群治的功能,而没有试图要对中国的“天”提出疑问,他宁肯给“天”存在的中国文化重新确认和评价,而认为不是像“天然”那样让它随意发展,应该由我方来主动地掌握它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梁启超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要重新建构历史,或者不如说在各国帝国主义角逐之中,梁启超深刻地探讨如何引导中国的走向并为中国人提出适应当下时代的文化。在该过程中,梁启超讲究“新民”。可章太炎的视角则直接针对人的个体本身,不管是“天”还是“上帝”或“公理”,章太炎对人所设定的东西根本不信任。对于个人被这些东西所压迫的状况,章太炎表示强烈的抵抗。由对各个存在的讲究出发,章太炎将佛教和庄子融合在一起展开“齐物论”。章太炎充分意识到个人之间的差别、个人的存在。章太炎所谈的“不齐”不仅在于个人之间的不齐,其内涵还包括国家、文化的差异。引入佛学而解释齐物论,也有显示西方所没有的文化体系的用意在内。因而章太炎的齐物论所针对的是“文野之见”:“文野之见,尤不易除,夫灭国者,假是为名,此是梼杌、穷奇之志尔”,“故应物之论,以齐文野为穷极。”①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第 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101页,第 118页,第 118页,第120页。关于轮回,章太炎讲究的是是否“自主”,“佛法所说轮回,异生唯是分段,生死不自主。圣者乃有变易,生死得自主故。”②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第 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101页,第 118页,第 118页,第120页。章太炎解释中国古代圣人也理解佛教的轮回和因果报应的道理是相通的,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③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第 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101页,第 118页,第 118页,第120页。。章并且说,佛教的涅槃以排除任何欲望而求摆脱烦恼,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齐物则站在一般人的常情,适于民意,“以百姓心为心”④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第 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 101页,第 118页,第 118页,第120页。。
实际上,梁启超认同章太炎对于庄子的解读。梁讨论庄子的时候,全部采用章的解说,如说“庄子本一情感极强之人,而有更强之意志以为之节制,所谓能‘自事其心’也。”⑤《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第 19页。但梁启超自认是报人,因而认为自己应该引导舆论:“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治之天职者也”⑥《敬告我同业者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 37页。,自觉地表达国民的“公意”。以“公意”为活动的基础,这即是用报业来教导“新民”的梁启超的视点。梁启超强烈地主张现在是培养民智、民德、民力的阶段,如果从读者的立场来看,这也许显得带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梁启超也需要解释新民说不是跟政府说的而是针对国民说的⑦《答飞生》,《饮冰室自由书》,《新民丛报》第 40·41号,1903年 11月。。梁启超自己设定“新民”和“公意”,作为报人试图建构一种舆论,因而不是报人的章太炎感到梁启超那里“公意”占更大比重,而看不到对于个人的重视。作为报人以及变法引导者的梁启超,通过“传播文明三利器”,不管是塑造“中国魂”还是创造“新民”,这种“启蒙”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确是不可避免地具有控制个人的方面,章太炎对此作出敏感的反应。可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还没达到讨论个人的阶段。梁启超的工作首先就是从建构“新民”开始的。因而比如后来围绕“非宗教同盟”,梁虽然着重于“公意”,但宗教意识所关联的“群众”与梁期待建设的“新民”在梁那里被有意识地加以分别。梁启超对于个人的观念可以在其“新民”理念中找到蛛丝马迹,但“新民”尚不能形成“宗教”所关联的“群众”。在这些概念的缝隙之间,似乎可以察觉出梁启超当时在“个人”与“新民”的理念之间乃是经过调整而有所抉择的。
六、从“宗教”转向本土文化
康有为把西方文明的发达根源归结于宗教,借此把孔子抬高到耶稣那样的地位,《孔子改制考》就体现了康有为的意图。其实,依赖宗教加强群治的水平,如上所说这是梁启超也具有的,章太炎也借用宗教来推动革命,可梁启超站在启动人民的立场,更要求推动个人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尚武充斥的时代中,梁很期待信仰、精神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他向来所欣赏的任侠风气也更加得到青睐。在考虑如何能够使得民众个人敢于牺牲的时候,他认为需要建立一种能够足够信任的死生观。因而梁启超开始关注宗教,尤其是宗教的死生观。梁启超认为佛家学说最能得到世界诸哲的信仰,把不厌世的因果报应和国家建设结合在一起⑧《国家运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二》。,并关注更古老的中国思想。
梁启超对宗教的评价标准在于它给群治带来多少贡献,因此他提到佛教。但如姊崎正治在与梁启超的交往中①石关敬三、红野敏郎编:《大西祝·几子书简集》,二·2·五 1899年版,东京:教文馆,1993年版,第 305页。矶前顺一、深泽英隆编:《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知识人と宗教姊崎正治の轨迹》,东京:东京堂出版,2002年版,第 45页、第 316页。,指出梁启超倾向于尽量统一地看待佛教和儒家②石关敬三、红野敏郎编:《大西祝·几子书简集》,二·2·五 1899年版,东京:教文馆,1993年版,第 305页。,梁不只是特别提出佛教,还要与儒教并列探讨。这是在梁启超解读墨子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的,要活用墨子,还需要用儒学或科学来补充其精神。不管如何,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宗教有不少优点可以用来发展群治。从宗教思想来看,中国古代宗教都切近人事,专门讲现世的事,不讲来生,而且没有西方那样属于特别阶级的宗教机关和僧侣。在中国古代,政治和宗教都是为了处理人间事务,君主和教主都具有同样的职责。设立天神创立宗教,很快就成为非常普遍的习俗,没有西方那样神和人是完全不同种类的观念。在中国,神和人的界限很模糊。梁启超谈到更古老的中国宗教,即孔子谈“天地”之前的时代,那时只谈到“天”,“天”的威力广大,深入人心,能让人产生敬畏之心,这样有助于维持群治③《志三代宗教礼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九》,第 3页。。梁启超经常谈到汉代儒家独尊,诸子学问被排斥,导致中国思想学问自由的局面退步,可对梁启超来说,“天”还是离不开“人”。诸子百家有“天命”(孔子)、“天志”(墨子)、“天道”(老子)、“天和”、“天德”(庄子),汉代董仲舒提倡“天人相关”,到了宋学,则提出“天人合一”。“天”本身有多层性,梁启超在此追溯到比提出“天人合一”的宋学更早的上古时代,从那里出发把“天人合一”说带进来给予评价。
梁启超在 1901年的文章《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把欧洲和中国做比较,指出中国古代思想是“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对于天而负责任。”近代欧洲是“帝王及其它统治权,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统治者对于民而负责任。”④中国之新民:《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新民丛报》第 10号,1902年 6月。跟西方相比,中国不是阶层社会;关于信仰,因为中国是“非宗教国家”,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之争;所以梁启超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参政问题和民族建国⑤中国之新民:《论自由》,《新民说七》,《新民丛报》第 7号,1902年 5月。。但当下是“武装和平”,梁启超所看到的是其他国家对尚武精神的推崇。梁启超对世界主义和大同思想有助于推广仁德博爱给予评价,可在当下的世界中,还是不得不注意到基督教的好战之风以及佛教轻死生的观念⑥中国之新民:《论尚武》,《新民说十九》,《新民丛报》第 28号,1903年 3月。。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连载“新民说”,也认为对“新民”的群治来说,佛教有好处。但是在日本社会和各国走向军事之路的时候,“死生观”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如何对待“死”的问题出发,考虑到本国在世界形势中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对有利于群治的功绩和名誉观念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西方的“宗教”也罢,日本的“宗教”也罢,在其背后,帝国主义忽隐忽现,并且“宗教”这一概念本身很难与讲究天、人、道的中国思想相对应,梁启超以及《新民丛报》同人十分清楚这一点。在探讨的过程中,蒋观云走向道家,梁启超提出“天人合一”,试图把“宗教”用儒家、先秦诸子、佛教等加以阐释,而使之作为与“宗教”对抗的文化根基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他们看到眼前的“宗教”那里没有能让他们首肯的文化。
在明治日本,“宗教”被带进来了,明治政府毕竟把佛教和基督教归入“宗教”而没有把神道归于“宗教”的范畴。“国家神道”带着宗教和道德两方面的元素被编入国家体制。于是神道国教化被推行。与此同时,帝国大学设立了“宗教学”,个人的信仰问题就在带有官学性的学问体制内,与“民间信仰”开始隔绝⑦池上良正:《宗教学のなかの民俗·民众宗教研究》,《季刊日本思想史》第 72号,2008年。。
“宗教”与教育或道德之间展开交锋、交错,《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原来认为西方用宗教担任道德教育,意识到能与此相对应的日本文化而撰写了《武士道》。上文所说的宗教和教育之间的论争是在佛教和基督教被纳入明治国家体制中之后展开的。实际上新渡户稻造一方面针对欧美读者写出了《武士道》,显示日本也有能够与“宗教”媲美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殖民地政策学者,站在给日本殖民地统治者提出建议的立场,从事作为“东西文明的媒介者”的“文明”政策⑧参见酒井哲也:《近代日本の国际秩序论》,东京:岩波书店,2007年版。。此外,大隈重信也一方面谈“东西文明的调和”,另一方面实行被梁启超所严厉批评的“大隈主义”,即推行日本殖民主义政策。
在日本,江户的泰平时期,国学、皇国思想有所发展,明治新政府把它政治化。“尚武”被宣传,其价值观和死生观都被塑造以感染国民,在文明的矛盾日益膨胀的状态之下,“尚武”很容易地得到普及。明治国家用“祈战死”或“日本魂”等风潮掩饰国民该面对的“死”。他们使得“死”和国家、天皇结合而让国民承认,这背后有神道得到优遇的明治体制的存在。为了配合信仰自由的近代体制,在明治宪法之下,神道、佛教和基督教都被当作宗教,但之前,神社神道不是作为“宗教”而是“祭祀”得到独立的地位,参与成为国家权威的精神基础①岛 园进:《日本における〈宗教〉概念の形成——井上哲次郎のキリスト教批判をめぐって——》,山折哲雄、长田俊树编:《日本人はキリスト教をどのように受容したか》,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ンター,1998年版。。在这样的国家体制影响下的“死生观”充斥的日本,梁启超和其同人看到了日本的尚武和殖民主义政策,也因为看破他们的掩饰,所以对于本来与这些政策相关联的“死生”问题,梁启超和同人各自展开探讨。在与明治日本同样的言论空间中,梁启超和同人展开活动,亲眼看到“文明”的“尚武”和其过度的行为,却完全看不到其背后能让他们首肯的“文明”价值。因而如上文所说,梁启超试图精心地剖析佛教和墨学的教义而探究该如何对待列强的轻死行为,面对死生问题。梁启超在明治日本,在他自己的自由空间之中提出佛教的问题,追问“不死”的“宗教”到底为何,于是使得自己的问题意识从“不死”演变到“精神文化”的发展。无论如何,梁启超的任务是适应时代的新民文化建构。在明治政府企图设定宗教的轮廓下,梁启超则在自己的杂志上很自由地探讨“死生观”和“宗教”。欧美政治家有宗教的思想基础,虽然不好说实际上他们的宗教信仰到底给政治和社会活动带来多少影响,但在梁启超看来,“宗教”这一西方近代术语有时作为支撑着克林威尔、贞德、玛志尼等英雄的精神动力而为他所接受,有时也被当作相当于阳明学和禅宗、作为提高所谓“私德”的工具而得到提倡。梁启超所用的“宗教”是至诚即是一种信仰,他同时还注意到王学和儒学,提出了精神文化②参见拙文《梁启超对日本近代志士精神的探究与消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 2期。。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使今日世界而已达文明之极点也,则人人有自治力,诚无待于宗教”③中国之新民:《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新民丛报》第 19号,1902年 10月。这样的梁启超的认识。
不管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章太炎,由于基本上他们具有以经书为中心的传统教养,所以他们关于西方“宗教”的讨论仍是与经书相纠缠,并对迷信采取相当严格的态度。1922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在此书中梁启超谈及中国宗教,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一以贯之地保持跟宗教的距离。虽然梁启超在宗教那里看到很积极的意义,但认为“中国土产里没有宗教”。因而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宗教史即主要指外来宗教。他把佛教也归入外来宗教。道教虽然产生于中国本土,但梁启超很严厉地看待并批评其影响力,说他们扰乱社会。于是与其注意西方宗教或外来宗教如何进入中国文化里,不如表彰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梁启超对讨论中国宗教时用一神教或多神教这个说法也表示反对,所谓“名词颇不适当”。他还在“宗教”那里看到对异教徒的排挤,而中国则是“有许多庙里,孔子、关羽、观音、太上老君同在一个神龛上”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 143页。。虽然梁启超对道教采取很严厉的态度,但对民间的信仰则很积极地认同其价值,如屈原、关羽等人作为神受祀,也认为如果考察其文化背景,就会成为很精彩的宗教史的一部分。他还从七夕、中秋节等节日里看出跟西方宗教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价值。梁启超虽然没用“民俗”文化这个词,但可以说,从梁启超对西方“宗教”的关注演变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挖掘和重新评价,这背后有“宗教”无法概括的中国文化的存在。
余 论
梁启超论佛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脉重要的伏流,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学家以及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清末新学者没有与佛教无关的,梁启超本身也喜欢谈佛教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81页。。可另一方面,梁启超本身在输入新知识的过程中,从最初起一直没有把“宗教”作为主题,而是与其保持距离。在建构“新民”的过程中,在梁来看,“宗教”似乎也会有助于形成“新民”精神,但梁启超始终在摸索可以替代“宗教”的精神依据。实际上,笔者认为这还意味着梁启超对当时文明诸国的文明正当化的一个反抗。身处明治日本的梁启超,亲眼看到明治政府对于大众推行尚武和殖民地主义政策并随之形成的群众心理,也无法认同其带有“宗教”臭味的思潮。在这一点上,周作人也许同样如此。周作人说“中国决不是无宗教国”,批评类似萨满教的野蛮事件①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知堂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本来对萨满那样的“宗教”抱有批评的态度,也看到群众那里存在着由大众心理推动的类似于“宗教”的东西,并对此具有深刻的不信。关于周作人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批评已有一些研究,不管是否反宗教,他对被某种目的引导而推行的运动抱有不信任感②主要参见尾崎文昭:《陈独秀と别れるに至った周作人——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の中での冲突を中心に》,《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35辑,1983年。。这也跟梁启超一样,在日本的所谓“宗教”的性质成为这一看法的根据。梁启超很警惕地看到,既然“宗教”与“迷信”相联系,群众就会很容易地被引到社会风潮的某个方向。日本幕末志士、武士道以及所谓“日本精神”,都被明治国家向同一个方向塑造,梁启超亲身体会到,这就是相当于群众被某种权力所盲动的“迷信”。对于这种“宗教”现象,同样在明治日本时期的英国研究者 Chamberlain③B 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英国日本研究专家。1973年赴日,在海军兵学寮作英文教师,1886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师。1891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位外籍名誉教师。主要从事日语(包括阿伊努语、琉球语)研究和日本文化的介绍,翻译《古事记》,也推动日语罗马字化运动。也关注近代日本社会所产生的“新宗教”动向。周作人最后也认识到,只能从“宗教”入手了解日本文化,这都和梁启超所了解的当时日本的现状相类似。用某种权力所塑造的文化只能用宗教来表达,这是梁启超所看到的。梁启超和周作人不仅理解当时的民族主义或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更慎重地看到推动“运动”的群众心理,或者是他们对群众心理本身抱有不信之感,不管其目的为何。因而,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虽然梁启超对以往的基督教表示批评的态度,但也明确地表示“非宗教同盟”绝不应该出现培养信徒等行为,给他们提出警告。梁启超不是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而是提示人各自具有“信仰”是有意义的,并认为这才是讨论“宗教”时最有价值的。也即梁把以个人为主体的“信仰”作为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梁在“新民”之后对个人的进一步要求。
梁启超到最后一直没有缩短跟宗教的距离。他要用自己的方法保护中国独有的文化,找出其价值。但同时可以说,对于中国古来的死生观,梁启超只是把它当作迷信来对待,他的思路就从迷信飞跃到“宗教”了,其间所存在的“民间”梁启超基本上不怎么理会。中国古代宗教观、死的世界往往跟祖先联系,但梁启超在推动变法时,往往对以一族为主的观念给予否定,要建立“新民”,需要注重社会上的意义。跟下一代相比,梁启超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属于跟“民间”对话的阶层。但不管如何,梁启超从变法运动时期起,就把媒体这一近代文化带进来,精心努力挖掘和传播知识,并使之普及,这是作为“近代”文化的先驱所具有的革新性的贡献。打破阶层、国界的梁启超的编撰工作,成功地获得了很多读者。于是梁启超的工作是,针对他自己所设定的新时代的中国人即“新民”,如何去建构兼有民力、民智、民德的文化。同时也把自身所处的明治日本的体验穿插其中,对于“尚武”、“死生观”以及“宗教”应有的内容重新追问和探讨。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梁启超还逐渐地发现在“迷信”、“宗教”、“科学”等术语交错之下,无法用它们来涵盖的扎根于民间的信仰文化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这些东西后来会被编入“宗教”或“民俗学”的学问范畴里。梁启超虽信赖“科学”,但经过“科学”之后,如同关注民间的祭祀活动那样,梁启超开始注视到跟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宗教”、“精神”文化的价值。在日本,在被称为“时代之闭塞”的时期,尼采受到明治文坛的瞩目,“个人”这一概念被探求;鲁迅就切入此处,将以“人”为根基的个人精神作为文明的真髓进行探究,追问文明。鲁迅与其说是否定迷信,不如说是更加批评“伪士”,同时他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行为进一步展开批评④以上主要参见伊藤虎丸:《鲁迅と日本人》,东京:朝日新闻出版社,1983年版;《初期鲁迅の宗教观——科学と<迷信>》,《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41集,1989年。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 7期,后收于《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使得文明批评发展到个人的“人”的地步;同时挖掘民间文化并与之展开交流。这些都是在皇权覆没了之后,由鲁迅、周作人等下一代知识分子进一步展开的追究。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5-0076-12
*本文是在 2009年 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全国博士论坛上所发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吉田薰,日本女子大学学术研究员。
[责任编辑:翁惠明]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