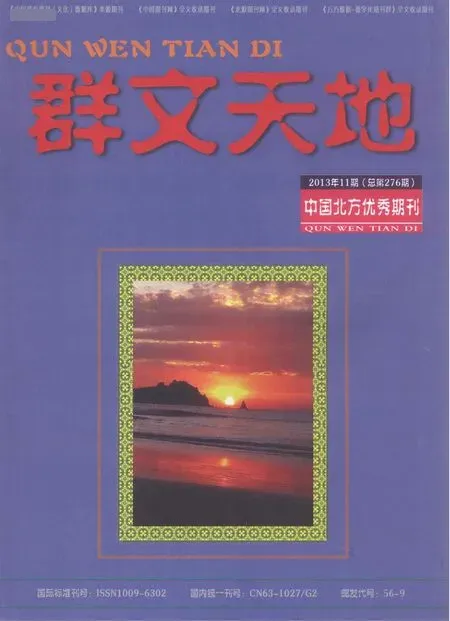安多藏戏“南木特”剧种的形成和特征
■阿罗·仁青杰博
雪域安多藏区有两大藏传佛教名刹,这就是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拉卜楞寺和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隆务寺。这里藏传佛教文化十分发达,尤以藏传佛教学者云集而闻名遐迩,早已形成藏族文化比较发达的文化名城。这两座寺院虽属两省管辖,但地理毗连、宗教文化联系又十分紧密,论辩著学术活动从未间断。二寺有夏日仓活佛和嘉木洋活佛系统的传承,佛殿寺宇庄严辉煌,鼎盛时期二寺僧众达七千余人,学者辈出,成为安多藏传佛教文化的中心地带。公元 1690—1720和公元1780—1823年之间,分别在隆务寺和拉卜楞寺开始首演藏戏剧种,使藏戏在安多地区得到发展,并逐步形成“南木特”剧种演出的独特内容、形成程序,成为安多藏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南木特”剧的初始阶段
1、大成就者嘎旦嘉措的道歌音调成为藏戏“南木特”(意为史传)剧种的先声
隆务寺初建于藏历第六个甲子之初,即在唐东杰布诞生之前的公元1370年(藏甲子铁狗年),开始这座寺院为“隆务仓”。后来从卫藏地区向安多地区传入佛教,随着佛教的兴旺有一位高僧喇嘛三丹仁钦建成隆务寺。开始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在夏日仓一世嘎旦嘉措(1607—1677年)时改宗格鲁派,并建成大经堂。在夏日仓大师30岁时建成显宗经院,特别是他的《嘎旦道歌》既是诗歌巨作又是藏族“南木特”剧的先声之作。因为道歌的内容主要结合佛教典籍,除了针对学僧,语句通俗易懂之外,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易记易唱,集民俗、宗教、喜恶、因果、格言和训诫于一体,将人生舍取、人世正误等用诗歌和谚语相结合的手法创作成赏心悦目的篇章,很快在热贡隆务地区的僧侣群众口诵心记,得到普及。因此,一些宗教职业者和嘎旦嘉措的许多亲传子弟包括嘎旦嘉措本人曾在广大民众中高唱道歌,将深奥的佛教经典内容用易理解的例子,深入到学僧和民众的心田中去,成为一种崭新的传教方式。虽然尚不能确切指出何种舞曲为何种道歌音调所形成,但现在热贡地区民间有一种区别于其他民间音乐的“道歌音调”的确存在,特别在一些吉庆的日子里,热贡地区各个村落的男女老幼聚会一起,齐声吟唱《米拉十万道歌》、《嘎旦道歌》和《夏嘎巴十万道歌》,并作为一种古老的习俗被保存下来。当时产生大量道歌的同时,以隆务寺主持嘎旦嘉措为中心的僧侣文人们不仅在民间普及了道歌的曲调,而且也成为僧侣们所自觉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后便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呓”的说唱艺术形式,寺僧们用以反映他们生活中的苦乐,或者将所闻当作笑料,甚至加以讽刺。总之,这种说唱艺术形式是从道歌中演变而来则是无疑的。从此,隆务寺有了道歌,由嘎旦嘉措开创的宗教生活中的道歌这样一种崭新的说教内容,在他身后代辈传承也依然如此。不仅如此,寺僧们并不满足于只演唱《嘎旦道歌》,他们还以道歌的音调演唱佛教本生传、格言、诗词、高僧传、佛教故事等,在一定时期内,这座寺院中形成了“呓”和道歌之间的文艺演唱形式。
在这一期间,有些僧人曾到西藏各大寺院深造佛学之后又返回隆务寺,他们在隆务寺一面从事论辩著活动,另一方面又将他们在西藏看到的藏戏的原型“阿姐拉姆”和宫廷音乐中的各种音调带回隆务寺,借以传播佛教故事。他们根据在西藏看到听到的藏戏剧种“阿姐拉姆”的演唱方法,在隆务寺一年一度的“夏季闭修”活动之后,形成一种举行吉庆活动的新习俗,在吉庆活动中不仅演唱道歌佛经,还兴起各种嬉耍,成为“亚顿”的节日。到这个时候,《嘎旦道歌》才真正成为藏戏“南木特”剧曲调的先声,证明了《嘎旦道歌》的音调已成为安多藏族戏剧最主要的基础音乐这一特点。
2、从“夏庆”到“亚泽”是安多藏戏“南木特”剧的雏形
我们仅从字面理解“夏庆”一词的含义,除了“夏日的吉庆”之外别无解释,从隆务寺将“夏庆”作为一个重大节日的历史看,也只有一个结论,这就是该寺每年农历6月15日到8月1日之间寺僧必须遵循的必修功课,即“夏日闭修”。时期内,连续九昼夜绝大多数寺僧停止一切活动,并告示四周,在“夏日闭修”的主要内容是佛陀上座部的修行,将其称为“承认三事”(三事指长净事、坐夏事和开禁事),自然包含了佛事的“长净”和“开禁”,实际上是格鲁派僧侣戒律的一种。其中规定了僧侣应舍弃的内容,诸如时间七七四十九天,地点除寺院外不得擅离一步,修行上坚守修技事,用一种严密而又单调的修技方式打发日月,思维活动不能旁骛,直身打坐之故使身体日渐消瘦。所以,一旦结束这种长时间苦读与修技活动后,寺僧们便和自己的学友为伴自发地加以庆贺。与上同时,寺院总管便统一安排寺僧的夏庆活动,寺院除了让寺僧们吃饱喝足外,还让他们到寺院附近的森林或草甸中自由吃喝玩乐,使他们尽情享受高原夏日愉悦。所谓“夏庆”一词便由此而生。当时,这座寺院的佛堂规模日渐宏阔,经院制度也日趋完善,夏日仓二世阿旺承勤嘉措(1678—1739年)年满20岁的火牛年(1697年),这位活佛到拉萨哲蚌寺时,五世达赖喇嘛将西藏的“阿姐拉姆”演出从佛门中分出来单独发展藏戏,并在艺术形式上广泛吸收民间艺术表演方法,使西藏藏戏表演艺术形式完善丰富起来。“阿姐拉姆”更上了一层楼,在哲蚌寺一年一度的“雪顿”节期间,西藏各地藏戏剧团从四面八方赶来拉萨,人们会聚一堂,各显其能,使藏戏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良好阶段。以夏日仓二世活佛为首的隆务寺部分僧众不仅加入到哲蚌、甘丹、色拉三大寺院的僧伽中苦修佛事,还由于他们寄居的主要处所就在哲蚌寺的缘故,有机会观看每年“雪顿”节演出“阿姐拉姆”剧的盛况,“阿姐拉姆”剧的演出状况和艺术表演方法也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他们返回隆务寺以后,每到“雪顿”节和“夏庆”的时刻,便有了演出“阿姐拉姆”剧的强烈愿望,“夏庆”时期僧侣从一开始的口唱道歌,发展到身段表演的歌舞结合。这种“舞”已不再是民间舞蹈形式,而是僧侣们以反映世俗生活或带有深厚佛教色彩的舞蹈动作被创作出来。尽管这样,但一种自成体系的台步都难以产生。其原因是:从寺院中产生的“舞”、“呓”和“道歌”,从字面意义讲虽有很大区别,但实际上与民间村落中流行的“舞”、“呓”和“道歌”相比较,在形式和内容,音调和表演方法,都找不出多大差别来,内容上受到佛教教义的很大束缚,“舞”、“蹈”、“呓”在寺院长期没有更大的进展。所以,“夏庆”中的唱道歌与舞蹈的方向虽有所发展,但由于当时社会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寺僧中有较高文化造诣又对佛学有所理解的部分僧侣文人开始了对“夏庆”活动内容的改编。这些僧侣文人由于大多曾在西藏各大寺院游学,他们依照《嘎旦道歌》的音调,吸收西藏“阿姐拉姆”剧的表演方法,将宫廷音乐和民间舞步杂揉到“夏庆”艺术表演程序中,并且将藏族历史上高僧大德们的故事、佛本生故事,以及《如意宝树史》中的故事情节加以编选,用道歌的音调吟唱,用“舞”的形式表现许多节目。虽然在单一道歌音调中延伸出的其他音调年复一年地变化着,但在原来“阿姐拉姆”和宫廷音乐的表演方法方面却没有多大发展,仍然停留在“夏庆”游戏的水平上。尽管这样,我们认为无论何种艺术形式,都是从无到有、由浅到深、从不完整到完整的,这一切不仅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相联系,而且又与在实践中及以繁荣和发展的一般艺术形式相联系。在道歌的多种音调中演变出“萨协拉姆”的表演方式,这或许是从西藏传来的歌舞或宫廷音乐的表演中逐渐演变而来的。《大地仙女》的演出者和编导者多是曾在西藏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伽中经过学习而返回隆务寺的僧人,由于这一新的表演方式十分生动活泼,使许多寺僧为之倾心,在每年的“夏庆”活动中演出《大地仙女》的僧侣人数由40—100人不等,阵容十分庞大,但由于受到方言土语的制约,从《嘎旦道歌》的音调到《大地仙女》的声腔转换往往约定成而由寺僧们自行编撰的。
随着隆务寺文化生活的日渐丰富,寺僧们受夏日闭修结束的夏庆游戏的影响日渐深入,隆务寺领属的支寺和子寺也日渐增多,政教和经济实力也日渐雄厚,寺僧们已不满足于夏庆游戏。夏日仓二世活佛55岁时,即公元1732年,藏历水鼠年,隆务寺各个属寺的僧众集中到隆务寺开始举行“隆务大法会”。于藏历木虎年即公元1734年隆务寺新建密宗经院,规模进一步扩大,从此,每年举行隆务大法会的各种仪轨,除开始跳护法舞之外,寺僧们视“夏庆”和“神舞”为重大的喜庆节日。“神舞”是藏传佛教寺院的一次重大佛事活动,“夏庆”则是西藏“雪顿节”即“亚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大活动集寺僧们的苦乐与其中,热贡地区的大小寺院从此都开始加入“夏庆”活动。隆务寺也正式选定后山的一块草坪作为每年“夏庆”活动的具体地,从此,隆务寺“夏庆”活动则成为热贡上中下三部所有寺院的“夏庆”活动。当时有许多从西藏返回隆务地区的僧人,他们在西藏聆听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特别是经常模仿卫藏《阿姐拉姆》剧的演出动作及其相近的表演方式,不仅使隆务寺的“夏庆”游戏更加丰富,而且仍不满足于“夏庆”游戏,不谋而合地酿演出“阿姐拉姆”剧。年老的僧人们认为“阿姐拉姆”剧的演出方式好是好,但在寺院演出又不大适宜,他们引经据典,提出了上演史传剧目的主张。从此,将“夏庆”中吃喝玩乐的活动称为“夏嬉”,代替“夏庆”名称。后来“夏嬉”活动中的吃喝风俗渐衰而喜庆节日的内容加大,将上述的演出活动又统称为演“南木特”,将高僧大德的传记用道歌音调演唱,并应用民间舞蹈演出《大地仙女》舞,还有说唱艺术等,统归于“夏嬉”的范畴内,使以前道歌音调的种子,生出歌舞的苗子,翻开安多藏戏史的第一页,第12个藏甲子之间形成了安多藏戏的“南木特”(史传)剧目。
3、从“夏嬉”到“南木特”剧的剧本出现
第11个藏甲子铁马年即公元1630年,夏日仓一世活佛时期,隆务寺建成显宗经院后不久,就完成了“嘎旦道歌”的编纂工作,“道歌”音调在寺僧中普及的过渡期便是为“南木特”剧种做奠基的时期;从夏日仓二世20岁时即第12个藏甲子火牛年(公元1697年),到拉萨晋见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和四世班禅洛桑叶榭,到他57岁木虎年(1734)隆务寺建成密宗经院期间,“南木特”剧种开始发端,只是“夏嬉”一词不能替代“南木特”剧目的内容和形式。当时所谓的“夏嬉”指各种游戏的总称,“南木特”剧的演出是“夏嬉”活动中重要演出部分,对“南木特”一词略作考证的话,从字面意义上讲,指的是正人君子的事迹、经历、言行,或者从历史人物传记中摘录韵文体部分加以演唱,诸如“阿姐拉姆”剧中的“南木特”部分,上述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在安多藏语中称为“南木特”剧目。细加分析,安多藏人对这类戏剧并不称为《阿姐仙女》,所谓“南木特”,这里指的是戏剧开始演出时的剧本即《阿姐拉姆》的八大剧本:《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传》、《卓哇桑姆传》、《智美更登传》、《法王诺桑传》、《班马俄本传》、《苏吉尼玛传》、《昂萨姑娘传》、《端约端珠传》,从整个藏区所共有的这八大剧本题目的最后一个字“史传”可以看出来,而且藏语中也称演出这些剧本为“演史传剧”。“夏嬉”活动中跳的史传剧目也以上述八大剧本为依据,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历史上正人君子的事迹言行,所以,无论从名从实都有称之为“南木特”(史传)剧目无疑。“夏嬉”活动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加进佛语、佛本生传、大德僧的业绩等,并成为“夏嬉”活动的重要内容。其他的娱乐活动也只能在“南木特”剧的演出中间穿插进行,而且,音乐以道歌声调和“大地仙女”的演出方式为主,成为僧侣们“坐夏”之后的大型喜庆活动“夏嬉”主要内容。所以,将“夏嬉”活动内容变成演“南木特”剧目,主要在夏日仓二世的晚年。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除《法王诺桑传》选段外,其他未作统一规定。
夏日仓三世更敦承烈热杰,(1740—1794年)主持隆务寺期间,寺院规模更加宏阔,在第13个藏甲子水蛇年即公元1773年建成时轮经院“密咒宏大洲”。在他49岁时即藏历火马年(公元1786年)继承夏日仓二世的遗愿,到西藏晋见达赖喇嘛坚白嘉措,并长期在拉萨驻足,回到隆务寺后大兴佛事,在僧俗民众中宣讲《嘎旦道歌》和《嘎旦全集》,这在热贡上中下地区又一次掀起了演唱道歌的热潮。同时,又经隆务寺请来《甘珠尔经》、《丹珠尔经》等许多佛教经典,让热贡地区的画师画出以《嘎旦传记》为内容的许多唐卡(藏式卷轴画),又掀起了一次赞颂夏日仓一世活佛生前业绩的热潮。也在这一时期,隆务寺正式建立演出“南木特”剧的班子,使这一戏剧事业成为该寺每年的重要佛事活动而固定下来。
无论戏剧,还是小说、诗歌任何一种文艺形式,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依据社会的各种有利因素得到发展的。史传剧目也是从无到有,在不同时期根据社会和这座寺院的发展变化而出现专事藏戏的班子的,应该说这也是藏族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隆务寺显宗经院“思闻洲”下设的戏剧班子从担负起每年演出“南木特”剧的任务以来,不断总结经验,创造性地不断对安多这一藏戏剧种进行改革和创新,对剧本不断加工完善,对剧本情节也继续加工整理,使之较前更加完备、宏大,特具安多地区特色和民间特色。并以当地方言为基础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之成为规模具备而内容深刻的当代“南木特”剧目的艺术演出形式。
4、安多拉卜楞寺“南木特”剧的形成发展概述
名闻遐迩的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甘肃拉卜楞寺,于第12个藏甲子火牛年(公元1709年)由嘉木洋·协白多杰阿旺宗哲创建,一直成为安多地区政教合一的一座名刹。嘉木洋二世久买旺布(1728—1791年)时期使这座寺院的文化体系更加完善,为了使论辩著的成才之道更为光大特创,立“七月经院”,使僧众在佛学的论辩方面能够入门,并于农历7月初8跳“鹿舞”。其他又根据久买旺布的指令,光唐三世关确丹贝忠美(1762—1823年)将《米拉日巴及其道歌》中关于“猎人猎犬归依米拉日巴”的情节改编成“鹿舞”上演。由于被称作《猎户宫布多杰》的这种“鹿舞”与通常意义上的舞蹈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都有很大区别,超越了藏族舞蹈的内涵。这一剧本中出现的情节、人物性格、以及舞蹈动作等显得十分丰富,已经冲破了过去仅以手舞足蹈的局限,歌舞剧三位一体而融入固定唱腔,已有剧的形式,超出了舞的限制,也超出了以面具、法器、手印为禳灾消祸而出现的那种哑剧形式,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还有很高的讽喻。娱乐表演,成为这座寺院“南木特”剧的一种最早形式。随着这座寺院“七月禅院”的不断壮大,“鹿舞”渐变为《猎户官布多杰传》,使之从通常的护法跳神中分解出来,它的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系而成为僧俗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演出形式。其后,这一演出中又加入“丑角”和“狮舞”等非护法神形象的一些新的角色,使“舞”和“蹈”的动律更明朗化。同时,出现大小宫布多杰和猎犬之间的既相亲近又相矛盾的关系跌宕起伏,戏剧色彩较前更加浓烈。具体细分为这样几幕:(1)安宅;(2) 米拉修禅;(3)“鹿舞”;(4)猎犬之舞;(5)宫布多杰之舞;(6)米拉说法。一般分为这样六场,包含了原始的一整套舞蹈内容。一年一度的“七月法会”也像“祈愿大法会”那样规模盛大,成为这座寺院的一项重大佛事活动。上述的表演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光唐丹贝中美创编的《猎户宫布多杰》也从“舞”的形式转变为“南木特”剧的根本性基础了。
公元1946年,在第五世嘉木洋活佛丹贝坚赞(1916—1947年)的敦促下,由浪论·嘎桑莱谢嘉措主持编导的《松赞干布传》在拉卜楞寺正式演出,这是将拉卜楞地区的民间歌舞、寺院神舞和内地京剧艺术、西藏“阿姐拉姆”剧等文艺形式结合而成的第一出藏戏剧目,也是这座寺院名副其实的戏剧节目。
公元1955年,这座寺院又上演《坚定的信仰》,之后,又由密宗禅院演出《智美更登传》,较之以前上演的“南木特”剧目,情节方面虽然和同仁隆务寺的“南木特”剧有雷同,但音乐和台步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念和唱的方面虽然与道歌和民间音乐也有较大区别,但将方言和台词表达方式、台步舞步以及程序等集中了名家的优点,安多地区的群众看了以后感到浑然一体,更加符合安多地区的乡俗民情,地方特色更加浓厚。
随着拉卜楞寺在安多地区藏传佛教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藏戏剧目也在安多地区各大小寺院中盛行起来。各地的生活习俗和宗教实际以及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艺术形式,使“南木特”剧目更加蓬勃发展起来。上演的剧目有《猎户宫布多杰》、《文成公主》、《牟尼赞普》、《赤松德赞》、《阿豆拉姆》、《罗摩衍那》、《坚定的信仰》、《青年达美》等一批新编创的剧目。这些剧目在四川、青海和甘肃等的安多藏语系的寺院中热闹上演,并根据各地实际和艺术表演形式,使这种演出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地。细加分析,这也有力地推动了藏族戏剧事业的向前迈进和发展。
但是现在拉卜楞地区各寺院中所演出的“南木特”剧目早就超越了以前的藏戏规范,在台步、唱腔和音乐方面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很多地方模仿别的民族的戏剧艺术形式,特别是手势台步方面很像京剧的表演,尤其在乐器配备方面,使人有一种这是不是“汉族戏剧呢”的感觉,是否将过去寺院的一整套表演形式加以改变了的想法。但无论怎样,藏戏“南木特”剧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拉卜楞寺仍然为这种戏剧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南木特”剧的表演方式及其艺术特征
“南木特”剧一开始是与佛教内容相联系而产生的一种戏剧艺术,它的表演程序和方法也会有一定的佛教色彩。而且与西藏、康巴地区流行的“阿姐拉姆”戏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趋向,继承了千百年来藏传佛教的习俗及其优秀成分。尽管拉卜楞寺和隆务寺演出的“南木特”剧在表演程式和方法方面有所侧重,但其演出的目的则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将佛陀语录和佛教故事以生动活泼的舞台形象向众生加以喻示和传播。佛教徒并没有将这种表演列入艺术之列,只是将它看作是将深奥的佛教教义通过比喻性的表演而引导民众潜心向佛的一种方法而已。这也是这两座寺院及其周围的僧俗民众所谓“向南木特剧膜拜”之说的真正含义。这也正是僧俗群众以身语意全身心地崇拜藏戏“南木特”剧内容的原因所在。由此可以看出,艺术作为表现宗教观念、藏族文化与宗教内容密不可分的历史原因。
1、隆务寺“南木特”剧的开场戏——献祭仪式
隆务寺演出“南木特”剧的序幕除演出形式之外,在内容上与西藏“雅隆扎西雪巴”演出的“猎户诵”的场次相近。譬如,剧中的“阿嘉”角色与“阿姐拉姆”剧中的“嘉鲁”角色相似;“南木特”剧目中的“特金刚杵”们(前述《大地仙女》剧中角色)虽从装扮方面命名,而实际上与“南木特”剧种的仙女或五佛相似;“亚泽阿哇”角色的形象既是“夏嬉”活动中出现的新名词,也是由于安多藏语中称“阿爸”为“阿哇”的原故,是喜庆活动的总管而命名的。总之,“南木特”剧中的这种序幕来自以前的“夏庆”和“夏嬉”活动,这一场次与猎户诵的关系将在后面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南木特”剧的演出和“阿姐拉姆”剧的演出一样,得到了从广场演出到剧院演出的过程。为上所述,从“坐夏”活动的最后一天即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便在隆务寺广场作首场演出,实际上是为以后几天的真正演出做准备。三十日即在寺院靠山的一处固定草滩上进行演出,当地民间称作“上山岗”,实际上表示寺僧们完成坐夏的佛事活动后,必须到数里之外游方的戒律规定。这一天隆务寺的大多数寺僧们已经圆满完成了三事深修,由历届夏日仓活佛和长老们率领僧众在出现黎明的曙光时即到达场地,隆务寺全体僧众和热贡地区35座佛寺,18处静房的僧人,共同参加坐夏修炼后的吉庆活动,并在庆典中观看“南木特”剧的演出。首先由全体演员向夏日仓活佛、其他各位活佛以及长老们敬献哈达和礼品;再由隆务寺显宗经院领属的“七月经院”主持等心语意三僧敬献袈裟和献祭祝祷的“曼智”(献祭时的祭器及祷词),又由“夏嬉阿哇”(主演和演员一身二任)和阿嘉(与“阿姐拉姆”剧中的嘉鲁相似)等四僧为首向金刚持佛行膜拜礼之后,演出便正式开始。
2、“南木特”剧的人物造型方法及其特征
由于藏族“南木特”剧是随着宗教文化内容的发展而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它的内容到形式都保留了许多佛教的内容。寺院中的壁画、泥塑等人物的形象和姿态,手印和穿着,神祗螭(泛指三界神灵)三种形象以及慈目、忿真诸相造型,还有跳“羌姆”舞中的诸多舞者形象等,都被“南木特”剧目所吸纳。历代的艺术家们进行创作和追求,在进行比较和整理的过程中,在表演方式上加入许多丰富的宗教文化内容,也吸收了许多表演方式。诸如骑马射箭、秋收打猎等动作也做了必要的添加,也反映了藏族现实的社会生活。其中的神话、幻想和实际,喜怒哀乐、真善美等等,都以现实生活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和提炼,使戏剧形象具备丰富的表现力。民间舞蹈和歌曲、遍及安多藏区的情歌或野曲、法舞面具和寺院艺术、民间游戏和敬神仪式等,都有符合民俗的待人接物的礼仪,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中有一定的表现,凡此种种,都被吸收到戏剧艺术中加以表演。这也是独具特色的藏族传统文化在藏戏中的体现,使这种表演具有了民族性、传统性和文化艺术性,这许多表演内容和手法为藏族“南木特”剧的造型艺术所吸收,使表演明快而集中,并被保留下来。在安多藏戏剧目中常见的最基本表演方法和技能如面部表情、扮相、手印、台步等内容繁多,但最主要的在步法和身法:即被称为“大象驮货物”、“婆罗门陨石”的身腰技能;被称为“天空的盘旋”、“湖泊滨”的各种步法;眼力所及于舞步的各种眼法,舞者的添接和心愿加于周围除反映人物内心世界之外,还有一些细节,与“南木特”剧目的演出无关。另外,表演手法中的“老鸹解馋”、“绊行”、“跳跃”、“阵舞”“神舞”、“螭舞”、“军舞”、“马舞”和“燕舞”等都很盛行,并形成“天鹅饶湖”、“雄鹰降富”、“吉祥双临”和“碎步引导”等技法,多在“南木特”剧目的“献哈达”、“坚定的信仰”、“威镇”、“大尊崇礼”、“持金刚”等蕴含了神佛、护法的手印,所表示的内容各有所指,如前所述。隆务寺在演出“南木特”剧目时的序幕献祭仪式中的“镇地安宅”一场时,有许多不同的手法表演需要了解。在表现喜悦心境时有“吉祥连环”和“雪山之境”等许多欢快的表演,一般都在接近尾声时演出的。总之,在演出安多藏戏剧目中,无论出场人物或男或女,总体上分男步和女步之别。男步如国王、大臣、武将、老人、力士、弱者、鬼神和坏人等都有各自的步法和手法,他们亮相时身法也各有不同,这是“南木特”剧种所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女步如空行度母、仙女、螭女、魔女、王后、浪女、老妇、美女和少女等有很多角色,在戏剧人物造型方面有各种不同的表演方式,其所共有的步法、身法和手法则是“史传”剧目人物造型的基础,也是“南木特”剧种最基本的表演特色。
三、“南木特”剧的服装道具、面具、场记及其配器
任何民族的传统戏剧都具有本民族特色,表现在服装道具、面具、场记和配器等,其所表现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所表示的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影响下的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上层建筑也各具特色。藏族地区分为三大方言区,安多方言区的藏戏也因这一地区人们的所好、历史条件、自然景观等因素,所造成的服饰打扮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南木特”剧中的服饰道具等也表示了各自不同的内涵。
1、“南木特”剧的服装道具
与艺术相联系的任何事物都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性质的反映,戏剧的服装道具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兴衰也有很大关系。“南木特”剧的服装道具的样式颜色在本民族服饰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剧情和人物身份来制作戏剧服饰。戏剧本身的特点和继承传统也是不同的戏剧流派所应遵循的规律,所以在服装道具方面也表现出“南木特”剧目的特色。
安多藏戏“南木特”剧种的人物服装道具,分述如下:
(1)夏嬉阿哇——冠戴之上镶以宝饰,黄缎上衣墨绿色上袍,水獭皮边沿以各式金线绣出花纹,腰系五色腰带,表示了千户之上的权势。佩戴象牙耳环,腰系印章袋和小刀,手中持五色绳表示了高于所有演员之上的权威。
(2)阿嘉——头戴普通百姓常戴的一种佩带束起发鬓,佩银耳环,白色上衣,百姓服束以三色腰带,佩带一柄镶金因的长刀,足穿一双百姓鞋,手持木棍,一看便知是普通百姓家中的一位家长模样。
(3)金刚舞者——头戴发牌、红黄色缎子的上衣,彩虹花纹的长袍下摆,足登彩虹花纹的长靴,手持剑、斧、弓、箭和铁索,给人以一群严厉的女神从天而降的感觉。
(4)密咒师——密咒经王的黑色帽沿下,黑色绸匠遮晾,在黑红色的氆氇长袍上印有忿怒面相的龟背八卦图,项间戴一串骷髅串珠。腰系细绳,前心和后心服饰有四处火焰腾跳的花纹,穿云纹的坎肩,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头盖骨的钵,以“黑旋风”式的舞姿登场,腿作颤抖状,表现出降敌的姿态。
(5)温巴(即猎户)——束起长发鬓,短发自然垂下,直至额头,穿豹皮上衣,着紫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腿挽到大腿部,足登无腰鞋,一柄喷出火焰的剑记做英雄的标志。显示出一副十八般武艺在身的扮相。
(6)拉姆(即仙女)——用绸带和丝线装饰发鬓,戴五佛发牌,头饰从假发以至垂悬于腰间,在各色花纹的软缎上衣之上镶以珠宝等串珠,下身裤筒彩虹状图案裹身,给人以上界供奉仙女下凡之感。
(7)宫布多杰——面带紫红色面具恰似安多牧民的面庞,黄羊皮翻领上衣,腰悬长刀,手持抛石索和弓箭,露出肩膀,表现出牧区猎户的样子。
另在演出中还有国王、王妃、大臣、士兵、波罗门夫妇、宫廷侍从等人物的服饰打扮道具等则根据剧情制作,将领扮相似乎是参照藏式卷轴画中的地方神或土地神的形象装扮的。反面人物的服装道具要怎样难看就怎样打扮,没有硬行的规定。
2、“南木特”剧的面具
藏族的面具制作工艺由来已久,是原始艺术文化的一个分支。后来在反映佛教丰富多彩的造型中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具,譬如跳“羌姆”舞的面具则是根据有关佛教的内容而制作的。藏戏“南木特”剧的面具则完全根据跳“羌姆”舞人物的面具演变而来,这在“南木特”剧中的骷髅面具、小丑、犬、鹿、虎、豹、熊以及慈面、忿怒面具中可以得到证明。就连安多“南木特”剧所独有的大小宫布多杰的面具也是在跳“羌姆”舞面具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南木特”剧不同于“阿姐拉姆”剧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戏剧人物不再戴面具,而是直接在局部用油彩化装的。上述的骷髅舞则从跳“羌姆”舞中照搬过来,这在表演方式上得到证明。直到今天,安多地区的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中仍然活跃着跳“羌姆”舞中的骷髅舞、小丑、宫布多杰和鹿犬舞蹈,更能说明问题。
3、“南木特”剧的场记
戏剧舞台是演员演出戏剧节目的场所,藏戏“南木特”剧的演出中,用白布将演出场所分隔成前后两部分,前面部分演出,后面部分又分割成几处布帐,演员们用以换装、化装、休息和取道具等,除后面部分外其余三面环形都可以观看节目。“南木特”剧的演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广场演出而没有真正的舞台。为了在演出中反映一定的背景,在舞台布景方面也想了不少办法,一般将现实生活与文化艺术实际相结合以体现剧情来布景的。有时也采用藏族文化艺术生活中的夸张手法,或者采用传统的浪漫主义的各种方法直接用于舞台布景。譬如天宫布景则用白灰在演出场所画出祥云图,同样以水纹表现湖泊、山尖表示山脉,还有佛堂等。为了表示往来于地下龙宫的情景,演员们以一条线为界,以那些参与演出的场记人员为主,用写实和写虚的手法加以表示,并说明按“平、起、文、武”分别将演出场所列为四等份。根据与佛教内容相关的台词、台步、音乐等进入“平”的范围演出;根据国王等政事为内容的演出则进入“文”的范围,并在演出场所的中央进行表演;舞蹈表演进入“起”的范围,包括庆典、吉祥歌舞等均入“起”场;“武”指战场、军列行进等场合。总之,将演出场所分为四等份也仅是布景意向,并没有绝对限制或加以固定不变。在戏剧之前的歌舞演出中就有所谓“平、起、文、武”,直至《智美更登传》的演出都是如此之说。这也是当天演出“南木特”剧时,师承古老的文化艺术活动并表示了将演出场地视作福泽圆满之地而加以变幻的一种做法而已,实际上意向性地表示剧中主人公智美更登王的事迹就蕴含了“平起文武”等四项内容。以后随着表演艺术的不断完善,在布景方面又创造性地想了各种办法。譬如在幕布上方悬垂一匹蓝色的布料,从地面的角度看,风吹起来似有水纹的波动,周围插上松树枝和花草,表示水边的松林,如《诺桑王传》中的渔民隐蔽在松树中窥视意乐仙女及其随从侍女们洗浴就用了这样的布景。总之,在“南木特”剧的演出中,舞台布景有农牧区所共有的景观,也有各个地方的许多不同景观。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戏剧布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仅仅局限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联系的眼前场景,寓意的、引发人们内心联想的布景,也在舞美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中向虚实结合的方向发展,成为戏剧表演中不可或缺的、富有表现力的基本组成部分。
4、“南木特”剧的器乐配置
安多藏戏“南木特”剧一开始除了道歌和唱腔外,并没有配器。后来受到西藏“阿姐拉姆”剧的演出影响,才开始运用鼓钹加以烘托气氛,使“南木特”剧的演出有了配器,而且依然以鼓钹打击乐器为主。
在长期的藏戏发展过程中,各类民间器乐演奏被吸收为“南木特”剧的演奏音乐,并增加了许多器乐。总之,“南木特”剧的器乐配置是在民间器乐演奏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藏戏的音乐一般分为板腔乐、舞蹈乐和中间乐三部分组成。板腔乐是“南木特”剧的主体音乐,这一音乐的形式、组成都自己的特色,是戏剧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具体体现和悲欢离合等情感的反映。这种依据剧中人物内外部形象而唱的板腔音乐是在多种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加以改编而来,具有优美动听的显著特点,满足了“南木特”剧的表演需要。这种音乐又可细分为戏剧性腔调、柔情性歌舞调、述事性腔调、说唱结合的腔调、道歌体和欢快体调、悲调和法调等,几乎囊括了“南木特”剧的所有音乐腔调。舞蹈乐是在“南木特”剧演出中用于喜庆、吉祥如意的场面演奏的音乐。这种音乐又可细分为自由式和规定式两种:前者由演员因地制宜地掌握快慢急缓,是表演技能和唱腔紧密结合的一种唱法,以表现演员内心情感和外貌形态的辅助音乐,在演出中是一种高难度的音乐;规定音乐在“南木特”剧的演出中应用也比较广泛,由规定的器乐配以规定的舞台动作,也是“南木特”剧的一大特色。第三种即中间音乐,是在演员上场、下场和换幕布时演奏的音乐。安多藏戏中多选用这一地区民间小调作为“南木特”剧的中间音乐,如《一位好神职》、《阿妈啦》、《雪山上的花朵》等视剧目的内容而加以演奏,这也可以看作是“南木特”剧音乐的一大特色。
藏戏“阿姐拉姆”剧和“南木特”剧最初只有鼓钹器乐伴奏,随着各个时代戏剧事业的发展与周邻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并吸收了一些共同的和独特的器乐应用于“南木特”剧目中。拉卜楞寺曾有过乐队,有藏族传统器乐龙头琴、鼓钹、笛、大喇叭、笙和手鼓等,他们演奏的中间音乐有从祖国内地传来的《万年欢》和《五台山佛乐》等。根据本民族文化创作的音乐有《旦本正上师》、《珍惜的雨丝》、《时兴》和《多谢》等许多乐曲。公元1946年该寺上演“南木特”剧目《松赞干布》时,开始将上述曲目和乐器应用于戏剧音乐中了,成为“南木特”剧目器乐配置的开端。
四、与“史传”剧目相关的几点深微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只知道传统藏戏只有“阿姐拉姆”剧,并发表过各种论点。但凡是对藏族文化深入研究的人都会发现,不能将藏戏艺术认为只有西藏的“阿姐拉姆”剧一种剧种形式和表演手段。这仅从内容和名称分析也可得出要点,光唐·元丹嘉措曾经也指出:
五大门类分支系,
十六范畴如珠玑。
引得众生作教化,
普天同庆是戏剧。
此外所说“五大门类”指:(1)提出问题的门类;(2)回答问题的门类;(3)商讨后得出决定性的语言精华;(4)被揭露而不能忍耐之状;(5)发生怀疑之后费很多口舌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定论,换言之,就是提出矛盾,解决矛盾,情节跌宕起落,最后得出结果的一般戏剧环节就是如此。所谓“十六范畴”指:入戏到结局的各个发展支系情节,诸如明晰的起因和形成定论,揭开疑点和做出结论,近处描叙和全面展开,亮出优点和含蓄隐喻,以及欢快语言等,藏戏十六范畴或称三十六范畴。另外还论及美化支系、环节支系和其他联接支系等,凡此种种在舞台形象方面表现怒相、威严相、惊奇相等,根据故事情节,前后联结,演员通过身段和语言加以体验表演方法。在身段和语言方面前贤们已做了许多精辟的回答,主要以引观众,使观众喜闻乐见为戏剧范畴的通常原理,所以,藏族许多学者在藏族文化的十大学科(即大五明和小五明)的“歌舞戏剧”学科中已经做过论述。尊者次成木仁钦曾经指出:“根据前贤的以语言分解之法,可根据不同的语言中相近语汇组成曲调念白和表演”。如果将各种身段姿态和各种音乐唱腔,各种语汇构成韵白,散白和韵散混合的言词配以音乐来完成一个故事情节,可称为“戏剧”的话,将藏族传统戏剧仅指“阿姐拉姆”剧一种则范围太小,与戏剧的定义范畴相背离。有人将西藏地区流行的“阿姐拉姆”剧看成是藏族唯一的传统剧种,这是对藏族文化历史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一种错误观点,譬如藏传佛教最早从印度传入藏族地区,释迦牟尼出身于印度,教义也是佛陀的教义,藏传佛教经典也不仅仅是单纯藏族文化而来,但藏传佛教毕竟是具有青藏高原文化的佛教流派,同源异流,都是一个道理。
总之,文化是没有民族和国家界限的,都能为全人类所接受。无论何种民族一开始,文化并不受时空界限的限制,都是相辅相成、触类旁通的,这一点已被人类的历史所证实。或谓“藏区”一词的含义仅指西藏,其他诸如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被看成是一般藏区或者仅有藏族,由于这种糊涂观念和认识,只将西藏自治区的“阿姐拉姆”剧看成是唯一代表藏族戏剧的剧种,将西藏文化看成是藏族文化,而安多、康巴文化就不是藏族文化,文字也只能叫作西藏文,而不是安多文和康巴文了,这是主观臆断的一种认识。
现在研究藏族戏剧的一批汉藏学者近年来发表了各种研究论文,对藏族传统戏剧统称为“藏戏”,又根据各地方言之不同命名者,或根据演出中所戴面具之不同等,将藏戏传统剧目又细分为许多剧种。如按方言分类者有西藏藏戏、安多藏戏和康巴藏戏等;按不同的表演方式分类者有白面具藏戏、蓝面具藏戏,以及昌都戏、安多戏、门巴戏、德格戏、木牙戏、嘉戎戏等。笔者以为根据地名、方言和面具对藏戏加以分类则毫无必要,在安多藏区的大多数地方所盛行的藏戏是从拉卜楞寺和隆务寺发展起来的“南木特”剧目,从西藏和康巴地区发展起来的藏戏初由“阿姐拉姆”剧而来,除了对嘉戎、德格和门巴演出的戏剧进行调查和发掘之外,西藏地区的藏戏可称之为“阿姐拉姆”剧,安多地区的藏戏则称为“南木特”剧比较合适。因为流行于安多藏区的戏剧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这地区约定成俗为“南木特”这一名词,这一剧种最初从拉卜楞寺和隆务寺发展而来,现在安多藏区有许多表演形式,犹如一棵树上开出百朵鲜花一样,“南木特”剧目则是安多藏戏的生命线。有人将“南木特”剧又分为“甘南藏戏”和“黄南藏戏”,这种以地名分类的做法是多此一举,没有实际意义而徒劳无益。同样,在西藏和康巴藏区流行的戏剧的生命线则是“阿姐拉姆”剧,它无论语言、地方特色,都是枝繁叶茂,我们稍事调查便可以从中得到证明,个别戏剧虽然互相有点区别,但它的渊源仍然是“阿姐拉姆”剧而不是别的什么,将它们统称为“阿姐拉姆”剧则是毫无疑义的。总之,藏语意义上的“戏剧”二字的含义是:“剧”指情节的跌落起伏艺术,“戏”指的是美丽、英俊、丑恶等三种身段表演;以及强弱、谈笑和恐吓等三种语言艺术;怜悯、威严与平和等心理表演艺术等,依据这样九种表演艺术加以体验,这两部分谓之“戏剧”。藏族戏剧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具备许多民族特色,有话剧、仙女剧、史传剧、歌剧、曲艺剧等许多剧种,这些剧种在各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是从无到有的发展史。
二十世纪80年代后,“南木特”剧在安多藏区重新得到发展的同时,西藏的一个“阿姐拉姆”剧团专程到热贡地区做了演出,他们在看了当地的业余剧团演出“南木特”剧后,提出了“这不是藏戏”的议论。实际上他们以“阿姐拉姆”剧的标准衡量藏戏,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南木特”剧不是“阿姐拉姆”剧。当然,这也是没有将藏戏和“阿姐拉姆”剧的整体和个体以及内容未细加区别的一种观点。正如西藏地区的人民群众对“阿姐拉姆”剧所喜闻乐见的那样,安多地区的人民群众对“南木特”剧也是喜闻乐见的。如果将藏戏仅仅局限于“阿姐拉姆”剧一个剧种的话,那么对“藏族”这个名词在文化上要做新的解释,只要是藏戏,就必须是“阿姐拉姆”剧,只能承认藏族除了“阿姐拉姆”剧就没有别的剧种了。正如藏族文化的源流是从西藏开始的这一点得到证明一样,藏传佛教的“后宏期”却从安多地区向西藏传播文化并对藏族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在西藏、安多和西康这样三大方言区中,如果将安多藏区的范围和人口占整个藏族三分之一的地区产生的这样有广泛影响的“南木特”剧认为不是藏戏的话,那么“阿姐拉姆”剧怎么就能肯定是藏戏呢?正如“南木特”剧不是“阿姐拉姆”剧一样,安多区藏戏喜欢上演“南木特”剧而不愿演出“阿姐拉姆”剧,如果仅仅根据这一点不承认“南木特”剧为藏戏剧种的话,那么“阿姐拉姆”剧也仅是西藏地区的一种演出方式而不能称作藏戏了。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对安多和西藏、西康的艺术体系没能得到一个认真调查的机会,加上各地区间相距甚远等原因,藏戏界对各地的戏剧很少有史料记载,发展也很不平衡,这点在《音乐之典》中曾指出过:
西藏有藏戏,
戏区全体知;
周边藏区中,
甚少知此事。
这是指十三世纪以前整个藏族地区的戏剧发展情形,而进入十八世纪以后,整个藏族地区还未出现一个统一的戏剧和戏剧理论,西藏、安多和西康三大方言区各行其是,实在令人可叹!同样,对流行于安多藏区的“南木特”剧,从理论到演出方式,戏剧内容等除个别专业人员外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只注重于日常的戏剧演出,而对于藏族地区的戏剧文化事业没有深入了解和全面评估,长期以来“南木特”剧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在没有认真分析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认为“模仿了其他民族戏剧”、“是一种歌舞剧”等等,连起码的戏剧常识都不懂,实则是一件羞耻事。
在《藏族南木特总论》一文中,我们曾指出,总起来说藏族戏剧可分为话剧、阿姐拉姆剧、南木特剧、歌剧、歌舞剧等多种剧种。其中:“南木特”剧在整个藏区三分之一的方言区流行,“南木特”剧也是藏戏的一个主要剧种之一,正如对“阿姐拉姆”剧冠以“藏族阿姐拉姆”剧一样,“南木特”剧也可冠以“藏族南木特”剧的名称。西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叫《藏剧阿姐拉姆剧剧本》的书中编选了《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传》、《郎萨姑娘传》、《智美更登王子传》、《卓哇桑姆传》、《苏吉尼玛传》、《端约端珠传》、《白玛俄本传》、《法王诺桑传》等八种传记本。这八大传纪本并非仅由“阿姐拉姆”剧演出,“南木特”剧的舞台上也长期进行过多次演出,这不仅在“南木特”剧的发展历史中得到证明,而且也是“南木特”剧的主要演出剧本,如果细加推敲,从藏戏剧本和藏族“阿姐拉姆”剧的剧本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藏族文化中的大五明和小五明中的戏剧学也不能仅仅用“阿姐拉姆”剧取而代之。同样的道理,对藏族戏剧文化事业进行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为藏戏事业发扬光大而做出不懈努力的同时,对兴起于安多藏区的“南木特”剧也应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最终做出结论,为使藏族戏剧的理论更加完善并形成体系而做出努力,这是藏族戏剧理论界所肩负的一项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