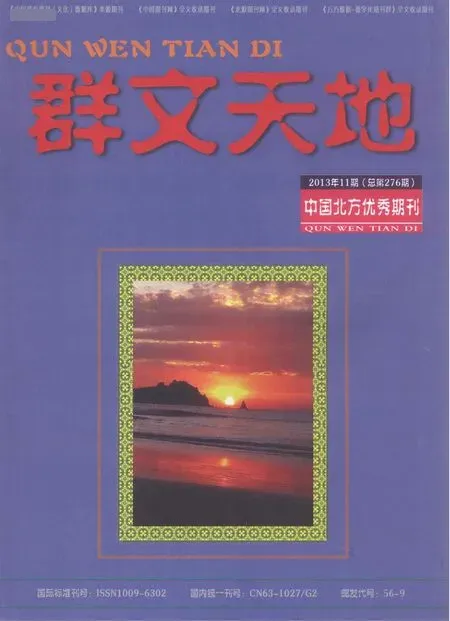“花儿”古今谈
■ 亚 雄
“花儿”是流行三陇、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民歌。“花儿”的另一名称叫作“少年”。民歌属于民间文学研究范围,现在全国各地,在有关部门组织领导下,均有了民间文艺研究会或民间文艺协会的组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风格的民间歌曲,浩如烟海,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的音乐遗产,单就一九七九年来说,我国音乐工作者,深入各地,采集民间歌曲,约有十余万首,将要出版题名《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巨著,成为洋洋大观。
“花儿”的研究,不算过去的成果,近两三年来,歌唱“花儿”最盛行的地区,如临夏、康乐、西宁、宁夏等地,由文化、民研部门出版的“花儿”选集之类,丰富多采,传诵一时。
按“花儿”流行的地域来分,有三个体系:即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与“陇中花儿”。
河湟体系:河指黄河,湟指湟水,就是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沿河上下及其附近地区流行的“花儿”,都叫作“河湟花儿”。这个地域,包括甘肃的临夏、永靖、东乡、和政、广河、康乐、皋兰、榆中等地;青海的民和、乐都、湟中、湟源、互助、大通、循化、化隆等地;宁夏的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地。河西走廊的“花儿”,也属这一体系。区域辽阔,三个体系中它是首屈一指。这种绮丽婉转的山歌,演唱者无论是汉、回、藏、土、撒拉、保安、东乡、裕固各民族,都是使用汉语。歌词的基调是四句,有的唱五句、六句、八句不等,这是它的变格。
洮岷体系:三句者叫作“单套”,六句者叫作“双套”,甚至有唱八句者是其变格。洮岷“花儿”又分南路、北路。南路包括岷县、卓尼等地,北路包括康乐、临泽、临洮、渭源等地。
陇中体系:一首四句,分为两段。流行地区是庄浪、静宁、武山、甘谷、清水、秦安、陇西、定西、通渭、会宁等地。陇中“花儿”和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区别很大。历来研究“花儿”者,把它排除在“花儿”之外,不认为它是“花儿”。但这一区域的群众,把它称为“花儿”。把漫“花儿”叫作“喝花儿”、“叫花儿”。三个流派的提法,值得“花儿”研究者参考。
“花儿”盛行各地的主要据点,每年均有“花儿”会的定期举行。这种“花儿”会,既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聚会,也是访亲会友的场所。当初以庙会形式兴起,后来也起了物资交流作用。这些“花儿”会,都是在农忙间隙举行。甘、青两省的“花儿”会,按地方季节,先后在每年农历四、五、六、七月选定会期。著名“花儿”会有:康乐六月初一至六日的莲花山;岷县五月十七日的二郎山;西大寨五月二十三日的大庙滩;临潭郊区六月二十四日的雷祖山和四月初八的松鸣岩、吊滩;永靖四月十五日的炳灵寺;民和五月初五的峡门,六月初六的七里寺;互助六月初六的五峰山庙会,六月十五日的丹麻庙会;乐都六月十五日的瞿昙寺庙会;大通六月初四至六日的老爷山庙会,郭莽寺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六月十四、十五日庙会。“花儿”会相沿既久,热闹非常。尤以莲花山的六月初六最为驰名。在十年浩劫中,各地封山禁歌,现在“花儿”得到了解放,“花儿”会亦恢复昔日的繁荣。
“花儿”是劳动人民所创造,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心声。“花儿”的地理分布、历史源流、歌唱方式及其内容等,实不仅是民间文艺的宝库,而且又是研究民族学(包括民风、仪苑、道德、制度)、历史学、语言学的极为丰富的辅助材料。
“花儿”开创的年代,当在盛唐,距今约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盛唐为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诗歌至唐,大量模仿西北边疆少族民族的音乐形式和文学形式,这种风气的开创者,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征歌选舞,祟尚伊凉。驻节伊凉等地的使臣,不断地进奉伊凉诸曲。伊凉诸曲最短小者只有三、五句,那便是山歌“花儿”的文学形式和音乐形式。李隆基模仿西凉的积习和流风而见于诗歌。五言、六言、七言诗,固然是继承齐梁体,而绝句诗只有四句;词在唐代,已开长短句之源,这都是接近于“花儿”的音乐形式和文学形式。“花儿”在西北边疆的流风遗俗,不见于记载,而反映到中原内地,诗歌词曲受西凉的影响,则班班可考。
“花儿”这种音乐形式,在西北边疆,唐、宋、元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当地民族语言来演唱,并不是以汉语演唱“花儿”。“花儿”这个汉语名称,我估计当在明代大量移民西北边疆以后才有之。因为大量移民充边,汉人才成了多数。汉语也就普遍流行开了。这时候“花儿”流行的重心,渐渐地由河西走廊移至河湟、洮岷、甘宁边区一带。汉语演唱“花儿”也就普遍流行起来。时至今日,不论是汉、藏、回、撒拉、土族、裕固、东乡、保安等族,漫起“花儿”,汉语中夹杂着少数民族语言,现在有一种被称为“风搅”的唱法,便是“花儿”语言演变的残留痕迹。宋、元之际,内地也有人模仿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山歌形式来歌唱,叫作“叶儿”,这个名称来自内地。“花儿”的汉语名称,则出现在“花儿”盛行的当地。由“花儿”到“叶儿”,自然有一个演变过程。
到了清代,在上述“花儿”的盛行地域,“花儿”成了家喻户晓的时兴歌曲。我在研究“花儿”过程中,曾经翻阅过一些地方志和名人诗文集。在吴镇的《松花庵集》中,检出“花儿”这一名词,当是“花儿”最先见之典籍者。吴镇《忆临洮》诗等九首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句子。“‘番’女亦风流”句,不仅表现“花儿”习见于藏民之歌唱,而且他们的歌唱语言,必是使用汉语。吴镇的诗句,对我的浅陋见解便是佐证。
“花儿”体系、流派之间,出现了“花儿”的“令”这一新生事物。“花儿”之有“令”,我估计当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令”代表体系、流派之间的特色,遂有“河州令”、“东峡令”、“撒拉令”、“红花令”、“大眼睛令”、“扎刀令”等许多名称,到现在已超过百种。
“花儿”富有生命力,也富于感染力,形象思维之美,历千古而益彰。时至今日,又进入了一个灿烂光辉的历史时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上,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近来驰誉艺坛,声扬四海的舞剧《丝路花雨》,是从敦煌艺术中吸取营养,进行艺术概括和意匠经营,从而创造出轰动一时的典型化艺术形象,这是舞剧创新的良好典范。人们知道,新兴的甘肃地方剧“陇剧”,是由陇东“道情”提炼发展起来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利用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而产生的。“花儿”的发展和运用前途,无疑是光明的。推陈出新,它必将跻登于舞台艺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