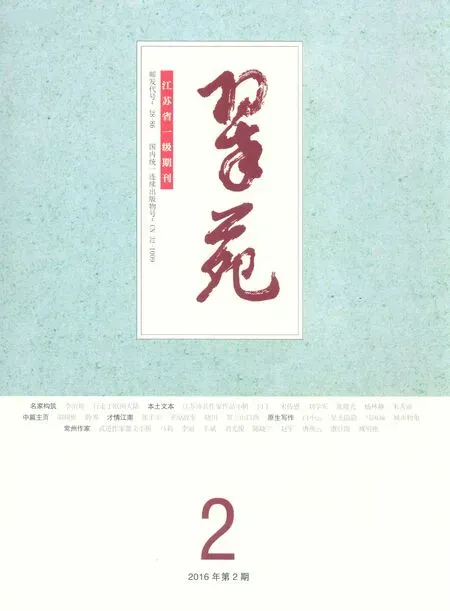游荡在身体深处的往事
■高维生
游荡在身体深处的往事
■高维生
最后的秋天
北方的秋天,除了储存白菜、土豆和过冬的蔬菜,还要准备大量的燃料,以备度过漫长的冬天。
北方住的房是带防寒棚的,这样有利于保暖,躲过寒冷的日子。大院的多数人家趁天气暖和,打一锅浆糊,把牛皮纸或报纸裁成宽条,用写美术字的板刷,从顶刷到底,然后贴到窗框缝上。到了冬天,再强烈的风,也钻不进屋子里来了。有的家干脆做一个窗板,到晚上挡住窗子,白天再卸下来。我家的防寒棚,自从搬进来住就没上过锯末。冬天的时候,炕烧得烫人,到了后半夜,风扑棱翅膀,自上往下扎,温度降得快。父亲说:“明年一定在防寒棚多上些锯末。”
秋天时,父亲托人在市木材公司买了十几麻袋锯末,运来就堆在院子中。那几天,院子堆满了装着锯末的麻袋,空间变小了,走路困难,不时被麻袋刮住。星期天都在家休息,前一天夜晚,一家人商量好了,第二天把锯末上到二层棚里。
我们家兄妹四个,就我是男孩子,上房掀瓦的事,体力较重的活自然是我的事了。家里没梯子,只好先爬上院子的板障子,在烟囱那儿上房。房檐光滑没东西可抓,前面竖着烟囱,我抠住烟囱的棱角,一点点地向上攀。
我扶着烟囱,终于登上去了,小心地往上走。红色的机制瓦,排列齐整,每迈一步都得注意,踩空了人陷下去不说,瓦碎了得四邻八舍找。瓦直接搭在木方子上,掀开瓦露出了二层棚。里面黑洞洞的,钻出一股说不清的气味;一阵响动声,老鼠忽地一下跑散了。我说不清楚,这么高的地方,老鼠怎么爬上去的。怪不得夜里静下来,迷迷糊糊中,就听到棚顶有喀哧喀哧的啃东西声,听起来吓人。在黑暗中,总觉得一双眼睛在观望,我害怕地蒙上被子。我真想抱上一只猫,放它在这里住几天,把老鼠消灭干净。揭开瓦,一块块地放在一边,阳光投在二层棚里,光柱中飘浮浑浊的灰尘。我解下腰间的绳子放下去,妹妹们把装好锯末的麻袋系上,我慢慢地拉上来。麻袋装上锯末变得沉重。绳子是粗麻纺的,往上拉的时候,锉刀一样,时间一长,皮肤火辣辣地疼。一趟趟地拽,锯末倒进二层棚,我还要钻进去摊开锯末,铺得均匀。
我累得胳膊像断了,手掌磨得生疼,风吹在身上,脸上的汗水还是不住地淌。我爬上了人字形的屋脊,骑在上面,放眼望大院的情景。后园外的菜地,秋白菜绽开笑意,迎接阳光的祝福。菜地边的泵房马达轰鸣,水渠里流水环绕菜地。屋顶的稻草上,乱蓬蓬地长几棵小草。草绳横一道竖一道,编成方格形状,罩在稻草上。看泵房的中年妇女,穿着靴子,扛着铁锹,沿垅台察看放水的情况。我家后园的两棵杨树,中间系一根绳子,上面晒着棉被,杨树下有了几片枯黄的落叶。
大院中飘来小提琴的乐曲声,琴声哀怨,诉说人间的不平,透一丝丝凄凉。马老师的女儿在拉小提琴,她拉的是《白毛女》中的选曲《北风吹》。马老师的女儿,大我一年级,却懂事多了。她很少和我们满院子疯跑,只要一有空闲就站在院子中,面前摆上乐谱架,一遍遍地练着小提琴。她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中,似乎对外面的事情毫不关心。我们在胡同中大喊大叫,跑来跑去,玩“藏猫虎”的游戏。
我手遮在额前,迎着阳光望去。邻居小秋和我是同学,她穿一件衬衣正在洗头。小方凳上放着铜盆,长发浸在水中,湿淋淋的头发使她更漂亮了。她家的铜盆我看过,有很多年月了,铜盆裂了一条缝,被穿街过巷、锔锅锔碗的匠人锔过。小秋性格内向,我们是同班,在学校从不说话,不认识似的。回到大院,作业不明白、记不清楚就找她去问。想偷懒时,便等小秋做好了作业,借来她的本子抄一遍。
风比下面大,我坐在那儿休息,不大的工夫汗就消去了。麻袋里的锯末全部上到二层棚里,瓦重新摆好。我在屋顶站了起来,看到大院的全景,别的人家屋顶上,有的扔不少石块,有孩子踢到上面的踺子,还有丢弃的旧鞋……
一条条胡同,纵横错落有致,构成大院往来的小路。星期天大院的人明显多了,说话声和出出进进的人,给大院带来了一片生机。已近中午,我家的烟囱也冒出了烟,敞开的窗子,飘出炒菜的香味。
干了一上午的活,身子酸疼,肚子里饿得直叫。
一群大雁,排着整齐的阵形,从我头顶的天空飞过。它们向温暖的南方飞去,躲过寒冷的冬天。我的目光追随远去的黑点,那是大雁最后的一滴痕迹。
这是秋天不多的、天气晴朗的日子。
老山东
山东人以意气、豪爽而名闻于天下,而大院的老山东以脾气倔犟、善骂街,在那片出了名的。
老山东的叫骂有滋有味,在这熟悉的声音中,大杂院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这天一大早,老山东又骂开了,夜晚不知谁故意发坏,把一小堆垃圾倒进他的苞米地里。老山东的老家在鲁西南,闯荡东北多年,还是操着浓重的家乡话。他的许多话,小孩子都学,觉得挺好玩。
老山东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飞,跺得地咚咚响。他的骂声,在整个大院炸开,每家每户都能听到。有人说,谁这么缺德,惹这个倔老头子干嘛。孤老头领着姑娘过就够可怜的了,不帮助人家,还欺负人家。女人忙着手中的活,丈夫等着吃饭,孩子准备上学。老山东的骂,声音大,没回音,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他心中的愤怒发泄完了,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划了一个句号。
老山东的女儿凤春和我是同学,长得白净,剪着运动头,很少见她扎辫子。她母亲因病死得早,小小年纪过早地失去了母爱,打从记事,父亲是她生命中的惟一。她的性格中,更多地接受了父亲的遗传。在学校从不欺负别人,一旦受到了伤害,她会玩命地还击。我们那个大院,原来是剧团的宿舍,后来进出的人家多了,变成了大杂院。老山东是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没任何生存保证,看老天爷的脸色,靠一辆手推车,养家糊口。他漂泊到这座城市,无亲无故,凭着良心、力气生活,时刻应付千变万化的生活,准备反击侵犯的对手。凤春和我们一般大小,却是大院最懂事的孩子。她过早地走进锅碗瓢盆的天地,操持家务,侍候辛劳的父亲。
下午一般情况下,学校不上课。凤春生着大灶膛,把苞米馇子下锅,开锅后,慢慢地熬着。苞米馇子硬不易烂,必须熬几个小时,等到晚上父亲回来,就可以吃热饭了,不必拖着疲劳的身体再动手了。凤春家住的是偏房,大院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她家坐西朝东,在角落中,但她家院子前有一大块空地。春天早晚有空闲,老山东就整理沉静了一冬的土地,泥土散发潮湿的气息,土地留下了铁锹的锹印。垅备得笔直,梳理得干净。他还抽空修绑铁蒺藜,隔开大院和空地,孩子们到了这儿变得小心,怕那倒刺的铁尖划破皮肤。雨后的一天,刮着湿润的春风,播下了苞米种子。老山东为了生计,天天早出晚归,阴天下雨实在出不去,才休一休。大多时间是凤春一人在家,她拿个板凳,坐在苞米地边上看书,一抬头就能望到灶膛里的火。
放学的路上,偶尔碰到老山东和他的伙伴们,几辆车排成一列,上面拉着铺地下自来水管线的铁管,要不就是水泥电线杆子。夏天的热气,扑在身上毒辣,老山东花白的头发滚出豆粒样的汗珠,滴落下来。套带勒在肩头,他前倾着身子,穿着打补丁的黄胶鞋,蹬足了每一步。老山东看着从学校大门走出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不和我说话,而我们不明事理,观望负重的车队,缓慢地穿过街道,一步步地朝前走。
放暑假的前几天,大院的空气紧张,学校发通知书的那天最难熬,考试成绩差的同学,不知如何回家交待。轻则挨骂,重则躲不过一顿胖揍。孩子的天性永远改不了,离学校不远,有一处建筑工地,我和同学们看着建筑工人干活,忘记了成绩一事。搅拌机欢快的歌唱,升降机上下升降,运送着砖和拌好的泥灰。戴安全帽的工人,一边干活,不时地和伙伴开粗俗的玩笑。我们站在一旁观看,觉得很有意思。
夏日天长,暮色中的空地一片葱绿,苞米发出奇妙的香味,蜻蜓、蚊子围苞米地转悠。苞米上的缨络,指向暗下来的天空。白天趁老山东不在家,在他家的苞米地附近逮蜻蜓。低飞的蜻蜓,好像一挥手就能抓住。我停住脚,举起右手,竖起大拇指,口中念经一般地叨念:“蜻蜓,蜻蜓落落,叮当打锣!”偶尔有一只蜻蜓落在大拇指上,我伸出食指,抓住它毛绒绒的细腿。蜻蜓扇着薄翅,想挣脱我的手,重新回到天空。我仔细地观察,昆虫界的“飞行员”,亮晶晶的眼睛,有树叶纹络般的、透明的翅膀。它不住闲地为人类除害,消灭蚊虫,却善良地落入孩子恶作剧的陷阱。残酷的游戏,我在童年时做过。傍晚时分,各家各户敞开的门,传出勺子碰碗的响声,骂孩子学习不争气的声音,不时从邻居家传出,我惴惴不安,等待父母的训斥。一声尖锐的哭叫,划破了黄昏的大院。老山东的咒骂,夹杂凤春的哭喊,在黄昏中回响。老山东因为她考试没考好,一边打,祖宗三代地骂。他刚刚干活回来,手推车还没放好,腰上别着擦汗的毛巾,衣服没来得及更换,抽出车上的粗绳子,没头没脑地打开了。邻居们没有过去劝他的,知道劝也不管用,老山东的倔劲上来,弄不准给你两下子。凤春被抽得抱着脑袋,不敢动半步,绳子在空中扭动,打在皮肤上啪啪作响,出现了一条条红檩子。老山东打累了,骂够了,把揉皱的通知书,撕得粉碎,狠狠地扬进了苞米地。凤春抽泣着,忍耐了一会儿,走进屋里,打来一盆清水,放到父亲的身边。打也好,骂也好,他们父女俩相依偎命,谁都离不开谁。凤春抹着泪在院子支好方桌,端上煮好的饭菜。老山东一脸阴云,天很快黑了下来,大院子有的人家,吃完晚饭出来纳凉了。
童年的暑假,往往是在这不和谐的声音中开始的。
第二天清晨,老山东又骂街了。夜里老山东痛打女儿的暴行,激起了愤怒。人们觉得孩子应该教育,打是对的,可不能没死没活地打。如果稍一失手,姑娘一生就毁了,多亏还是亲生的女儿。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大多是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一些反法西斯的影片。地下游击队的战士,接头、碰面、分手,总说一句话“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有人模仿电影中的台词,把对老山东做法的不满发泄出来,在他家的山墙上,用黑木炭歪歪扭扭地写下了:“消灭老山东,自由属于凤春!”几个大字,并在地上浇了一泡尿。一夜过去了,地上尿的痕迹,仍然醒目。对这样的革命行动,老山东气得须眉倒竖,一盆水奋力地泼上去了。水湿的炭字没冲洗掉,更加清晰。这一行字,还是凤春一点点地擦去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老山东的苞米丰收了。他挥舞手中的镰刀,在哗哗的响动声中,苞米秸一稞稞倒伏下去。留下的茬子,还抓住土地。他让凤春把同学请来,在他家小炉子上烧苞米吃。扒掉叶子的鲜苞米,嫩嫩地散着香味。在苞米的一端,插上一根粗铁丝,不停地在小火上转,免得烤糊。老山东不住地忙碌,给我们挑棒粒饱满、没虫子眼的苞米,帮着插上铁丝。他流露出孩子般的真诚,动情地唠起了遥远的鲁西南。他老家的庄前有一条河,他曾和伙伴们在河中捉鱼,戏水,光屁股在河滩上追逐,河两岸是无边无际的青纱帐……老山东的讲述梦一般,他的眼睛中,见不到往日的严厉,有了一层柔静的水湿。
秋天就那样过去了。
冬天里的空地荒废着,一场大雪覆盖了土地。几只觅食的鸟儿,留下花纹似的脚印。老山东的家,白天很少见到阳光,在他家的墙角,时常刮起一阵旋涡似的风。树叶,草棍,废纸,破塑料布在风涡中旋动,从地面上升起。寒假时凤春躲在家中,我总看到她读书。
第二年的春天,老山东的家搬走了。他家的房子被扒掉,那地方准备盖一幢新房。不久凤春转学,不在我们学校念书了。同学之间断了音信,几年后,偶然听到她考上延边大学。再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城市。
鸟笼
星期天的早饭后,我提着一桶脏水,向大门外走,没等推门,门却被推开了。来的是一位陌生的小伙子,高大的个子,一双眼睛神彩飞扬,穿着洗得泛白的工作服,脚蹬白球鞋。他从来没来过,我们互相不认识,他热情地问到:“这是高叔家吗?”我一听是找我爸爸,桶放到地上,“他在屋里看书呢。”
我忙引路,把客人领进父亲的房间。
我倒脏水回来时,屋子传出笑声。爸爸叫我进去,向我介绍说:“这是罗大爷家的哥哥,你得叫义春哥。”我看着一脸笑容的他,紧张地叫一声:“哥哥。”义春哥高兴地把我拉进怀中,我感到他的力量是那么的大,小山一样稳牢。
罗大爷我见过,身体精瘦,说话有力气。我爸爸和罗大爷的交往,是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去朝阳川酒厂采访,写出了《古老酒厂换新貌》,刊登在《红旗》杂志上,文章在自治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罗大爷是一厂之长,他们的交往从那时开始,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听爸爸说过罗大爷家人的情况,知道有个义春哥,直到今天才见面。
秋天的阳光,从敞开的窗子流进,在砖地投下一片光亮。义春哥拿着我的手,不停地拍打他的另一只手,一边和我爸爸说着,星期天去市木材公司,给我家买烧材的事。天气一天天转凉,烧材,煤炭,白菜,腌菜,只有充足的冬前准备,才能度过冬天。我年龄小,去买烧材大人不放心,爸爸忙于工作,只好求助义春哥。
义春哥提出带我去同学家玩,爸爸同意了,并嘱我早些回来。义春哥拉着我的手,走出了家门,义春哥比我高出一大截,我的头刚到他的肩膀,我感到自豪,想到平时欺负我的人,见到义春哥的形象,再想占便宜,一定要先琢磨琢磨。
义春哥领我去了同学家。徐才和他同班是最好的朋友,两人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学习委员。徐才的家就在学校的马路对面,是一排旧房子。大块的青瓦,夹杂几块红瓦。院子的一段是碎砖围成的半人高的墙,另一段是木板子夹成道板障子,空地上种着一垅垅青菜,几只鸡在地边不停地啄食。徐才家一进门就是外屋地,锅台的一侧是吊挂的碗橱,锅盖是铝锅盖,风匣陈旧,上面放一盒火柴,屋子里有一股饭味。他家的孩子多,有几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都说:“义春哥来了。”
徐才和义春哥个头差不多,他的胡髭比义春哥的黑,说话的声音,比义春哥浑厚。义春哥把我介绍给徐才,他摸着我的脑袋:“小伙子够精神的。”我坐在炕沿上,打量生疏的屋子,墙中央贴着毛主席的标准像,旁边挂的镜框,镶满不一的黑白相片。有的手拿红宝书,有的戴着很大的像章,也有穿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窗台摆着新扎的滚鸟的笼子。一缕阳光投在鸟笼上,把高粱秸涂上訑色,宽敞的笼中,还没印下鸟儿的脚痕。
义春哥和徐才唠嗑,说着学校的事情和下个星期天,让他一起去给我家买烧材的事。而我却被鸟笼吸引住了。徐才见我喜爱样子说:“过几天叫我弟弟给你扎一个,下雪的时候,挂在院子的树杈上就行了。”
每天放学,我路过徐才家,总是走得很慢,向他家的窗子里眺望。一是想看到义春哥的身影,再就是想看给没给我扎鸟笼子。
我盼望星期天快一点到来,和义春哥去市木材公司买烧材。中午放学,我看到义春哥趴在徐才家的矮墙上,向马路张望。我贴着墙跟走过去:“义春哥。”他看到了我说:“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星期天早一点到徐才家,从这儿走。”我想了想:“不借推车了?”义春哥笑了笑,替我整了一整书包带:“用徐才家的就行了。”
我和义春哥分手,没好意思问鸟笼子的事。
星期天我起得早,胡乱地吃了一口饭,跑到徐才家。义春哥和徐才在给推车的轮胎打气,他吭哧吭哧地压气管子。义春哥穿着工作服,宽阔的肩紧撑着衣服,透出青春的活力。
“义春哥。 ”
“来了。 ”
徐才说,我们走吧。
义春哥让我坐在空车上,推着我走出徐才家的院子。星期天的马路,人不多,秋天是每个家庭最忙的时候,这是入冬前的准备阶段。义春哥和徐才说着话,没有走大路,而是走小路。这条路是近路,但要穿过一座吊桥,平时人走上去颤悠悠,桥头竖两根半米左右高的钢轨,为的是防止推车的通过。这桥主要是为了上下班方便,免去绕道而临时搭建的。吊桥是由钢丝绳和木板搭成,人走在上面,稍一用力就摆动,如果盯住桥下的河水,就有头晕目眩的感觉。
马路的尽头是沙土路,远远能看到河堤,扑过来的风,漫着水湿气。吊桥上来往的人和自行车,像剪影在移动。越走坡越陡,我明显地感到车子在攀升,义春哥在用力,徐才伸过手,两人合力地往前推。我看到河水,秋天是布尔哈通河浪漫的季节,河水广阔,如手法熟练的绘画大师,挥动苦艾的画笔,用大地的调色盘,蘸河水的颜色,在两岸留下了质朴的画面。
吊桥的桥口出入不便利,需要单个人通过,两根钢轨障碍人们的顺利通行。义春哥让我从车上下来。他和徐才竖起车子,在一二的号子声中抬过钢轨。推车一落到桥板时,整个吊桥都在晃动。车子在桥上尽可能地靠边,给过往的人和自行车让路,河水清澈,泛着阳光的碎片,车轮踏着水的旋律从桥上穿过。
下了吊桥不远处,就是市木材公司。木材公司像巨大的贮木厂,偌大的厂子堆积各种圆木,搭得高高的板材垛,散着木质的清香。“严禁烟火,人人有责。”白底红字的牌子,非常醒目,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卖烧材的地方是在锯木车间,露天的厂房,四面透风,是木杆和板子搭建而成的。车间中是一台大型的电锯,操做工人的手中,有一个带铁钩的长杆子,钩动运来的圆木,送上电锯的台子。电锯的前方,是长长的输送带,电锯锯下来的板皮和边角料,不断地通过输送带,被送入前方。买烧柴的人站在两旁,盯着输送带上的废料,捡出松木、椴木,树皮少、没有树疙瘩的边材。这样的木柴,回家劈时省力又好摆放。
义春哥和徐才随着输送带不停地转动,捡出来的木柴丢到一边,我就从地上再抱到推车里。电锯工作起来,噪音大,尖锐的钢齿,吞噬圆木的吱吱声,飞溅的木屑,在电锯前攒起小山般的锯末。操作工人,两人之间不停地打手势,身上的围裙,扑满了锯末。
我两头来回地跑,身上冒出了汗,脱掉外衣,只穿一件背心。徐才看我忙乎的样子,对义春哥说:“还挺能干的。”
我的脚步,随时间的流过变得沉重,怀中抱的木材,一趟趟地渐少。
一只鸟儿,在天空飞过。望着远去的鸟儿,想到徐才让他弟弟扎鸟笼的事来了,我看了他背后一眼。
秋一天天深了,风徒步在北方的大地上漂泊。我家后园的杨树,枝桠上的叶子,落得差不多光了,有几片枯叶在风中挣扎,维系树杆的茎枯萎了。障子根积树叶,乱草,刮来的破塑料布和纸片。到了夜里,风更猛烈,风沙打得玻璃啪啪作响,发出呜呜的怪叫。一夜的风,送来了冬的信息,用不了多久,初雪就会降临。
义春哥偶尔来我家,问有没有活要帮助做。放学路过徐才家,我常看到义春哥,他招呼我到徐才家玩一会儿。一天进了徐才家,看到炕上放着扎好大框的鸟笼,义春哥说:“这是给你扎的鸟笼,下雪后,你就能滚鸟儿了。”高粱秸扎的鸟笼,有了雏型,门、窗和竹栅栏没有上。炕上铺一块黄帆布,堆一大抱高粱秸,削得一般粗细的竹签,一把磨得锋利的电工刀丢在一旁。我仔细地研究鸟笼的框架结构,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亲手扎。
那天我放学回家,进了家门妈妈就说:“你义春哥,把鸟笼子给你扛来,让他留下吃饭也不吃,急忙忙地回家了。”我把书包丢下,推得门砰砰的响,我看到炕上的鸟笼,精致的门窗,漂亮的翻板,抚摸光滑的秸杆,似乎听到鸟儿欢快的鸣叫。
夜里没风,炕烧得烫手,躺在热被窝里,我很快地睡去。梦中落了第一场雪,雪掩盖了大地,新鸟笼挂在杨树上,翻板上绑着金灿灿的谷穗,布下了一个美丽的陷阱。
天亮时,窗外的天空还是灰朦朦的。
高维生,吉林人,满族。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季节的心事》、《俎豆》、《东北家谱》、《酒神的夜宴》、《午夜功课》、《有一种生活叫品味》、《纸上的声音》。从1988年开始,在《散文》、《天涯》、《作品》、《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