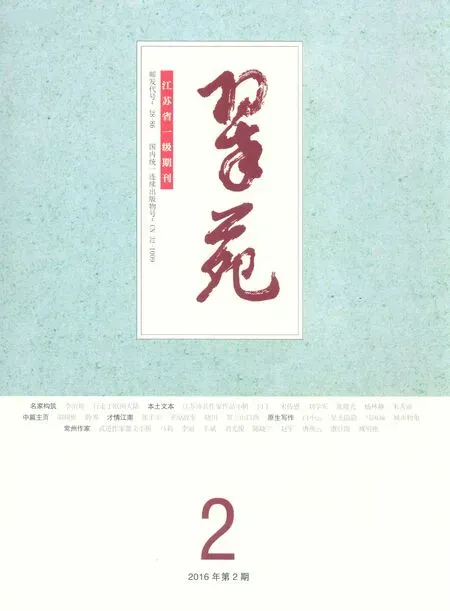她在水塘冒身张望
■许 侃
她在水塘冒身张望
■许 侃
在我读书的沙塘街小学,最漂亮的女生王倩有三个哥哥。
这一家子非常有意思,他们的母亲长得很美,个头高,身材修长挺拔,年轻时一定是个风流美人,却嫁了一个武大郎似的丈夫,个头比妻子矮,脸上的褶子多得像一团抹布,最显著的是额头上有三道竖直的伤疤,绰号叫“砍三刀”。他们的儿女却一个个禀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都长得有棱有角,有模有样,眉眼间流露出一股不让人的英气。这兄妹四人,虽然未必都像他们的母亲,但是没有一个长得像他们的父亲,那是肯定的。
王倩跟我是同学,但是常到我们家来玩的却是王倩的小哥王仪,王仪是我三哥的同学,他俩好得就差割头相换,整天凑在一起。王仪长得比他妹妹还有型,用今天的话来说,真是帅呆了酷毙了!那时不说帅不说酷,那时说嗲,我们说王仪长得真嗲!王仪是沙塘街中学文艺宣传队的。学校“五一联欢晚会”演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常青指路》一折,饰男主角的就是他。王仪饰演洪常青,我三哥饰演洪常青的通信员小庞。当吴清华搭着洪常青的肩膀翘起后腿,我三哥饰演的小庞单腿跪地,在他们后面摆一个手指前方的造型。吴清华肥大的裤管让人浮想联翩……我之所以记得这些事,是因为王仪来我家玩的时候,我听见他跟我三哥讨论:当洪常青手指前方的时候,小庞是不是看见了吴清华裤管里的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我三哥指天发誓,什么也没有看到。可是王仪还是不相信。
“你小子,你没看到,能做那梦?”
我不知道我三哥做了什么梦,只是看见三哥的脸红了起来。他好像吞钩的鱼越是急于摆脱,越是钩得牢了。王仪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亏了,我这男一号亏了。还不如你演小庞。下回我要跟你换换。”
“行啊!”三哥巴不能地答应。
“一言为定。”两个大男孩摆出男子汉派头来击掌。其实他们也知道这绝不是两人私下交易可以实现的事。
“哎——还有。”王仪又说。“下回我洗裤头你也要给我放哨。”
“好说。”三哥答应。我却如堕五里雾中,洗裤头?三哥连块手绢都不洗,什么时候洗过裤头?还要放哨?
洗裤头的奥秘我也懂得的时候,王仪洗裤头已经用不着人放哨了。因为那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洗衣的事,一般家里都是母亲承担的,男孩子长大成人第一次感到害羞的时候,他就把裤头藏了起来,不让母亲找到。
王仪的母亲是我们街上被人议论最多的女人,大家都知道她叫桂花。名叫桂花的女人其实早就想死,死了几次没有死成。一次是上吊,绳子已经挂上了,却被从学校回来取红领巾的王倩碰上了,王倩哭着把母亲踢倒的凳子又扶正了。这样一来,桂花就死不掉了。又一次还是上吊,被她的丈夫发现了,砍三刀把她解救了下来,搧了她几个嘴巴把她又打醒了。
王仪的母亲桂花死没死成,脖子里常常有两道暗红色的淤渍,大家都说那是被上吊的绳子勒的。我们街上后来出了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也这样说。其实不是,王仪的母亲桂花会刮莎,有个头痛脑热的不去医院,自己用手在脑门上或者脖子上反复来回这么揪,这么刮,直到刮出血痕,感冒也就好了。在我的印象中,王仪的母亲桂花是个奇怪的女人,她的身体散发出一种魅人的气味,甜丝丝的,有点儿香又似乎是臭。她老是爱感冒,动不动就刮莎,一刮就刮出两道暗红色的淤伤,让人以为她又上了一回吊,又被上吊的绳子弄出了伤痕。
他们家的事说起来真是一部书。有些事我们小的时候并不真明白,是后来想明白的。桂花为什么以那么美的姿色嫁给了“砍三刀”那样的男人,这个迷永远没有人为我们解开了。我们所知道的是,一开始他们家的生活还是蛮甜蜜的。后来闹到桂花上吊请死,转折点出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街上后来成名的作家说,都是因为他们夫妇一次做爱后,砍三刀喝了一碗凉水。这碗凉水引起肚子痛,叫做桂花的女人错请了一个医生的儿子来看病,这个儿子不懂医术,胡乱抄了一份他老子的药方,让砍三刀泻得一塌糊涂,从此男性的功能就丧失掉了。后来,那个医生的纨绔儿子竟然将叫做桂花的女人弄到了手。
这是不能全信的。我们沙塘街是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老郝,老郝也有一个宝贝儿子小郝。这个宝贝儿子既然人称“宝贝”,为人处世总有一些乖张的地方。他去给砍三刀治病老郝是同意的,既然能够出诊,也不至于连一张泻药的药方也看不懂。问题是,他的“宝贝”脾气上来了。他看见那个来延医的女人桂花长得唇红齿白,心里就想世上哪个男人有如此艳福,消受此等尤物。及至到了砍三刀家一看,卧床的竟是一个獐头鼠目之辈,心里不禁大为抱憾。毛病又是为性爱而起,他的心气就乖张起来。他原拟好了一张温中补阳的处方,却没有给砍三刀的女人桂花,另抄了一份泻药处方,让砍三刀永远失去了作为一个漂亮女人的丈夫所能享有的快乐。
小郝断送了砍三刀作为男人的幸福生活,并没有自己去填补空白。生活的逻辑往往并不像小说家编的那么有条有理,严丝合缝。在那个漂亮女人不甘寂寞的情爱生活中再也没有小郝什么事。而老郝知道了儿子开的药方,大为震怒,从此绝了让小郝子承父业的念头。
说句笑话,夫妻之间如果失去了性的交战,那么就会转换为语言的交战,乃至于肢体的交战。这条定律适用的取值范围从男女结婚之日起至65岁。因人而异,可以适当变化,最低值应不低于45岁。而在王仪的父母之间,这条定律开始起作用的时间是35岁,正是引起剧烈变化的关头。所以王仪他们兄妹从懂事不久开始,见惯的就是家庭矛盾的激烈冲突。
桂花常常莫名其妙地失踪一小会乃至几小时,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冒出来。砍三刀当然明白这种失踪的意义。尤其是当他作为男性成为一个废物之后,这种失踪的意义就更为暧昧而确定。他无数次的哀求甚至下跪请妻子为他保持贞节,在得到保证又遭背弃的反复蹂躏中,他们有时冷战,有时大闹。一次,砍三刀绝望中失去理性,冲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对着自己的脑门连砍三刀。这个小个子男人是孱弱的,他要是足够刚烈的话,就绝不会对自己下刀子,而是寻着仇家和冤家去了。他要是足够刚烈的话,就不会是不轻不重的砍,而是直接抹了脖子。他这三刀把自己砍得鲜血淋漓,却不会死,徒然在沙塘街上留下了一个笑柄。
父母是这样的不堪,然而儿女们却都是好样的。
小时候,我们在街上有时候听见邻居们说笑话,一个说:“老王人怂,养得儿女却个个顶笼。”
另一个说:“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人怂,才不怂,才另有所怂吧?”
这一串绕口令式的谜语听得我们晕头转向,说话的邻居们却哈哈大笑起来,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说这话的时候是绝不可能有王仪在场的。他会当场叫你好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然而,这些人却喜欢让王倩零星听到一些。由此可见世道人心的卑劣和怯懦。
这种时候王倩只有装着没听见,或没听懂。她也不敢回家对哥哥们说,她怕他们闯祸。王家的三个兄弟不仅相貌不似乃父,连性格也是迥然不同的。老大沉稳,老二内秀,老三王仪聪明刚烈,好像艳阳天放响的一只二踢脚炮仗。他们与乃父砍三刀那种委琐的令人耻笑的作风判若泾渭。
王仪既然是我三哥的死党密友,我们对王仪的了解最深,就说王仪。王仪胆子大,一次我们上山去玩,三哥踩塌了地面下朽坏的棺木,一下子掉进了一个坑里,爬上来连声说吓死人吓死人,那下面好像有骷髅。我们看着三哥,连他的身体都不敢挨近了。王仪把三哥拉上来之后,却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扑通一声就跳了下去。他扒拉扒拉,把坑口扩大了一些,从下面捞出来一个白森森的死人头盖骨,拉出战场上的英雄扔手雷的姿势,朝我们中间扔过来,吓得我们几个孩子嗷地一声炸开了。还有一次,我们到沙塘街年事最高的毛爷爷家去玩,他们家的一个特点是后房檐下放着一口厚皮棺材,那是我们街上有名的孝子毛大顺提前为他父亲准备下的。王仪和三哥打赌,谁敢跳进棺材里躺下,谁就是英雄好汉。那年代“英雄好汉”四个字对男孩子有很大的诱惑,无须任何物质奖励,人们为这四个字就干出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打着到毛爷爷家去玩的幌子,把那口棺材里里外外侦查清楚了,换一天,趁着毛爷爷到公园里溜鸟,三哥和王仪两人偷偷潜入毛爷爷家的后院,抬开了棺材盖。看着漆着红口的黑皮棺材,三哥怕了,说:“我不干。 ”
王仪身手矫健地一翻身就跃进了棺材。听三哥说,他在棺材里放平了身体,伸手蹬腿,快活得手舞足蹈,嘴里嚷嚷着好大好宽敞。他还让三哥把棺材盖给他合上,三哥一个人抬不动棺材盖,也不愿意把他盖上。如果把他盖上了,剩下他一个人他会害怕的。三哥说:
“你出来吧。叫毛爷爷看见可不得了。”
毛爷爷长得人高马大,如果知道有人抢他的先睡了棺材,不知道生起气来会怎样呢。
王仪敢睡棺材,这件事给我们震动不小。他对死亡的无所畏惧是不是继承了他母亲的生死观呢?
桂花在两次上吊不死之后,不想出现她的丈夫“砍三刀”自砍三刀未死的情形,那太叫人笑话了。之所以上吊不死,有人说是因为她老是刮痧,阎王爷账下的牛头马面也被她哄骗了,看见她脖子里有了暗红色的淤渍,以为她又是刮痧,就不收她。她第三次自杀选择了跳进沙塘的办法,她就一下子死掉了。
我们小的时候,沙塘街的大人吓唬孩子夏天不要到沙塘里游泳,就说沙塘里有水鬼。作为证据之一,他们会说:“桂花,那个女人你们知道啵?喏,跳到沙塘里死掉了。”这个说法的震撼力太强了,所以有相当一些年头,沙塘里那么清的水竟然没有孩子游泳。
桂花死后,砍三刀一人领着四个子女生活。这四个子女在外人看来,他们与砍三刀的血源关系是可疑的。但是,砍三刀从来没有这种疑虑,砍三刀的子女也从来没有这种疑虑。他们这一家人在桂花死后的日子里表现出来的亲情和勇气,获得了爱挑剔的沙塘街人们的认可和尊敬。
粮食永远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对于一个有着三个如狼似虎的大小伙子的家庭,每月每人28斤的粮食定量好像一个咒语,催着一家之长发了疯似的为粮食挣命。我家也是缺粮户,我记得父亲常常在星期日的早晨天不亮就骑车出门了,有时候到傍晚才回来,带回来一小口袋粮食。砍三刀一次上我们家来,向父亲讨教搞粮食的办法。父亲说,到乡下找农民家去买高价粮呗,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砍三刀便约我父亲明天带上他一块去。
我父亲带着砍三刀去乡下买粮食的那天,我母亲整天在家里坐卧不宁,她老是觉得今天父亲下乡买粮会不大顺利。按说两个人行动,彼此有个帮靠。但是,有些事情人多反而不好,人多目标大,过关卡的时候更容易被人注意。果然,那天他们买了粮食回来在经过采石镇时被检查站拦截了。我父亲说,他们原打算趁着夏日午后的炎热,利用检查人员昏昏欲睡的空子,悄悄地溜过马路。没想到路旁设在一处高地的检查房子里还是传来一声:“站住!”正巧这时有一辆农用卡车冒着黑烟从马路正中驶过,隔断了检查人员的视线,我父亲压低嗓门呐喊一声:“冲!”打算裹在农用卡车的身后冲过这个鬼门关,如果他们跑远了,检查人员也没看清他们带的是什么东西,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这关键时刻,砍三刀手忙脚乱,不知怎么狠命一蹬,自行车链条掉了。他朝我父亲大声喊道:“完啦,完啦。 ”
我父亲打算陪着他停下来。砍三刀忽又喊道:“老许你跑吧!”我父亲知道留下来无益,只好一个人下死命狂奔,远远地听见身后检查人员咋唬道:“嘿,你跑,叫你跑。逮了母的还能跑了公的?”我父亲心里捏了一把冷汗,要是砍三刀供出我父亲的单位姓名,这麻烦就大啦。
可是砍三刀矢口否认他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他说他与前面那骑车的根本不认识,那人的口袋装得支棱八茬的不可能是粮食。接下来他就点头哈腰地向检查人员赔罪、解释,说农用卡车声音太吵了,没听见检查员叫他“站住!”又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说家里孩子多,嘴糊不住,买点儿高价粮绝不是投机倒把,是给孩子们糊嘴的。那时候社会管制虽严,风气还是好的,人讲道理。如果真是这么回事,也不是绝不通融。粮食要留下,回单位打证明,如果能拿回来证明,粮食还可以发还。
可怜砍三刀和我父亲一样都是早晨喝了碗稀粥就出发了,到这时没有吃上一粒米。我父亲回到家里,还有母亲将熬好的绿豆汤送上去。可怜砍三刀就惨了,粮食被没收了,要打证明才能领回来。这事别人帮不上忙。砍三刀顶着大太阳骑着自行车疯了一般回到城市找人。星期日单位不上班,砍三刀找到他们锅炉厂革委会主任家里,说了半天,让主任相信了他的话,给他写了证明,又让他找干事小张到办公室盖章,砍三刀又找到小张家里,央告他帮个忙,陪他到办公室跑一趟。小张见有主任的字条,虽然满心的不情愿,还是照办了。忙了一圈,砍三刀再回到采石镇上领粮食,等到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这天夜里,王仪忽然梆梆梆地敲我们家门,敲得很急。他说他爸爸昏过去了。我父亲急忙披衣下床,让母亲端一碗绿豆汤随后就来,他自己连忙跑到王家,只见王家兄妹乱作一锅粥,把倒在桌前仿佛瘦小了一号的他们的父亲围在中间。王倩一声声叫爸,哭得泪人儿似的。
砍三刀是急火攻心,又累又怕,中了暑了。前时全凭一口气顶着,此时人粮到家,一松气,就昏过去了。我父亲对失了主意的一群孩子说:“快,送医院。还等什么。”说完背起砍三刀就走。
砍三刀出院后和我父亲成了好友。
夏天的晚上,沙塘街的人们喜欢搬出凉床来在街道的树下趁凉。父亲跟砍三刀下象棋,拉呱。父亲说,早年间东北山里人家来了客人,寒冬腊月只有一铺大炕。家里姑娘大了,客人不能撵走,怎么办呢?一铺睡吧。但是第二天早起,主人必要从门外取来一瓢凉水,请客人一气喝下。如果客人是规矩的,凉水喝完就完了。如果客人夜晚做下偷鸡摸狗的事,这一碗凉水喝下去终生阳具不起。
砍三刀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嗨!我要是早一点听到你这个故事就好了。谁也没有逼我喝凉水,我自己口渴,爬起来咕咚咕咚喝了一气。”
我父亲说:“咱们南方地暖,就算喝了凉水也不至于怎么样。”
砍三刀说:“谁说不是呢。要不是又叫小郝那个小王八蛋给我下了泻药,也许肚子疼几天就好了。”
我父亲说:“唉,不提那些了。”
砍三刀并不因为触到了他的隐私而黯然,看见我父亲懊悔失言,脸上故意露出明亮的神色,说:“不妨事。反正桂花死都死了。这些事早就无所谓了。 ”
王仪睡过毛爷爷的棺材以后,不久出了一连串怪事。首先毛爷爷像发现有人跟他争棺材似的,忙不迭死了。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爷子,虽然年事已高,一向架个鸟笼,红光满面从沙塘街走过,活得有劲得很。那时节养鸟被视为八旗子弟的没落习气,但是毛爷爷不怕,他家从他父亲起就干铁路,毛爷爷从铁路上退休,儿子毛大顺和孙子毛小毛又接了班干铁路。一家世代铁路工人,这在当时被视为最红的成分。可是,毛爷爷说死就死了。中午喂鸟的时候,一只黄猫在门口虎视眈眈的,毛爷爷拿起一把扒炉灰的铲子赶过去打那只猫,脚下拌了一跤,跌得并不重。毛爷爷自己爬起来,拧了拧脖子,好像没什么事,照常午睡去了。没想到一觉睡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毛家声势浩大的出殡之后,王仪就开始不断地做恶梦。他有时梦见他的母亲桂花从沙塘里冒出半个身体笑模笑样地向他招手。有时梦见毛爷爷手执炉灰铲子追赶那只黄猫,黄猫一跃跳进自己怀里,他怎么扔也扔不掉,只好拼命地跑,不知道毛爷爷是追黄猫还是追自己。王仪跟三哥说梦的时候失了往常的笑容,脸子惨白。他在舞台上演洪常青时常忘词儿,老师训斥了几次,终于不让他演了,连小庞也不让他演。我三哥并没有顺势晋级成为主角。既然王仪不演了,他留在宣传队老是当那个 “往女人裤裆里一指”(王仪跟我哥戏谑时的笑语)的小庞也没有多大意思。正好宣传队要进新人,三哥就跟王仪一块退出来了。
这年夏天,下了一场冰雹。鸡蛋大的冰疙瘩把王仪家的屋瓦都砸坏了。晚上下雨,王家就漏得不行。第二天王仪上到屋顶换瓦,揭掉砸坏的瓦块,从屋顶上看到了自家屋里的情形。王仪说,他看到了父母亲睡的大床,那一瞬间,与在家里看到大床产生的感觉完全不同。多年以后,我回想王仪跟三哥说这话时的表情,我判断他隐去了许多话没有说出来。那时王仪大概有十六七岁,有点懂事了,沙塘街上关于他父母的风言风语大概他也听说了一点儿。我猜想,王仪这时的心里是不是发生了一种窥破人生真相的惊悚?
砍三刀在房子底下问儿子磨蹭什么?王仪把屋瓦盖好,就顺着砍三刀扶着的木梯下来了。从此王仪的性格变化很大。他再也不是那个饰演洪常青角色的阳光男孩,他的性格变得敏感、紧张,防卫性很强。即使跟我三哥这样的老朋友在一起,也常常显得抑郁寡欢。
这年秋天,王仪在家门口拾到一枚铜钱。铜钱并不稀奇,我想也许是他妹妹王倩找来做毽子,弄丢了的。可是,王仪却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这是我妈妈丢下来给我的。”
三哥说:“怎么可能?一个铜板!你妈要丢起码也要丢一块银元吧。”
王仪尖锐地盯了我三哥一眼,把我三哥脸上的笑容凝结住了。我三哥马上意识到调侃得不是地方,在有关他母亲的话题上,王仪接受不了任何玩笑,哪怕最温和的一句白话。
王仪从我三哥的脸上读到友谊的真诚,他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跟你说你也不懂。”
学校召开秋季运动会。一百米跑是王仪保持学校记录的项目。这一年王仪不想参加了。可是班主任老师说,除非你能说出来让人信服的理由,否则,为了集体的荣誉你必须得跑。
王仪在运动场上,是全校女生瞩目的焦点。如果王仪不参加运动会,确实太让人遗憾了。他那匀称的体型,敏捷的身手,加上漂亮的有些女性特征的脸,太让人心热了。他的眼睫毛又长又浓,眨眼之间好像有蝴蝶翩翩飞动的阴影在眼睛里闪动。
王仪上场了,他穿着背心短裤,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发令枪响,王仪像一只脚细身轻的小鹿猛地冲了出去,然而他还没有冲到十米,便一下子扑倒了。他的身体几乎平行地冲向炉渣铺成的灰色跑道,向前滑行了好几米。全场一阵惊呼。
我三哥陪着王仪在校医务室进行了简单的伤口处理,手肘膝盖处抹了大片的红汞药水。然后,一瘸一拐地回家了。
这件事和王仪的死也许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王仪的病症确实是从这件事之后显现出来了。他开始持续发低烧,脸上的红晕就像我们沙塘街在夏天的傍晚时常出现的斑斓晚霞,又像傍晚时分被晚霞的红光照亮的沙塘水面。他和我三哥站在沙塘沿上,注视着无数的蝙蝠煽动着黑色的翅膀在透明的空气里一剪一剪地翻飞,他说:“三宝,来世我们还做朋友。”
我三哥搡了他一掌,说:“去你的,开什么玩笑。”
王仪说:“真的,我又做梦了。我觉得我妈要招我去了。 ”
我三哥捉住王仪的肩膀说:“你别吓人,王仪。你看着我,看着我。”
王仪把脸别过去,我三哥扳着他的肩膀,他不肯正视我三哥的眼睛。
砍三刀带儿子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了一个病名。我记得那时候反复听他们述说的两个字叫做:肝大。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三哥说,一个人运动过度缺少糖吃,就容易得这种毛病。我至今不知道三哥学来的说法是不是有点道理。王仪的肝大,用我现在的知识理解大概应该叫做肝炎。按说以王仪那样年轻,得了肝炎也不至于很快死掉。所以,王仪的病或者是肝癌也不一定,因为他最后的日子肚子鼓得像临盆的产妇一般。我从那时起又知道了一个医学名词,叫肝腹水。
王仪没有过上他的18岁生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天我发现三哥一个人坐在沙塘沿默默地流泪。三哥要是受了委屈从来都是大吵大嚷地哭嚎,看见他那样默默流泪的样子真吓人。我陡然升起一种担忧,怕他被沙塘里冒出来的水鬼拽到水里去。所以,我就躲在煤厂贮存煤基的棚子里,从板壁的罅隙间一直偷偷观察着三哥。煤基厂外就是沙塘沿,距水一米多高,有一条被钓鱼人踩出的小路,还有一棵枯萎了的杂树。三哥就坐在树前,不停地挥动胳膊用手背擦试眼泪。我看见他的手背被泪水浸得又红又亮。我一直偷偷地看着,直到看见他终于站起身来走回家去。
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自己躲在堆满蜂窝煤基的板棚里窥视三哥的情景,仿佛又体味到三哥当时心里的伤痛。这件事我从未向三哥提起,怕勾起他的伤心事。这也许只是一个托词,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不敢面对那样一个时刻我们彼此脸上会出现的表情。我的父亲和“砍三刀”也故去多年了,我知道他们两人相交甚契,想多回忆一些细节,在此文中渲染铺陈一下,竟捉襟见肘,资料匮乏。最多出现在记忆中的情景也就是一张凉床子,放在泼了水去暑的空地上,两人犄角相坐,中间置一棋盘,头顶是白杨树阔大的树冠,给夏夜的星空锯出边缘。而占居大半个凉床子的主角却是尚未成年的小孩子们……
王仪死前还有一些异样的事情,那段时间我们听到的鬼故事特别多。什么无头的裸体女人走在围墙上啦,什么有人在坟堆里走呀走呀总是走不出来啦,我记得王仪总是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尽管有时吓得脸色发青,还是对讲故事的人说:再讲一个,再讲一个。讲故事的有我大哥,还有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邻居。
这个邻居后来成了著名作家。
许春善,笔名许侃。安徽省作协会员。高级经济师。 曾在《雨花》、《安徽文学》、《厦门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十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