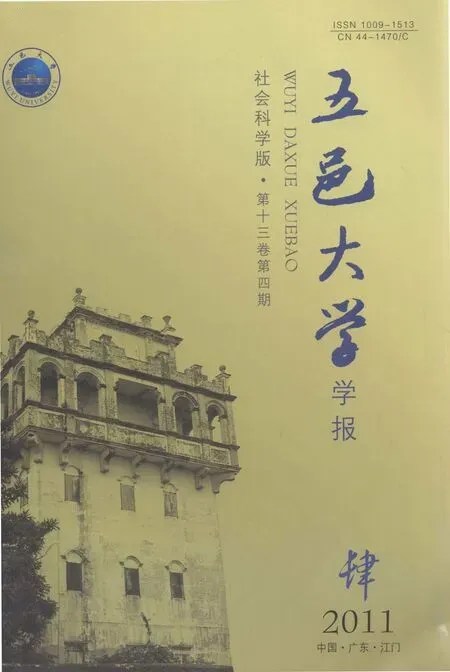六朝论体文的诗意性言说
杨朝蕾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六朝论体文的诗意性言说
杨朝蕾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六朝时期达到繁盛。六朝论体文采用隐喻式、造境式、抒怀式等言说方式,表现出其可以 “比”、“兴”、“怨”的诗性特征,与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直接形成它的诗性精神。
六朝论体文;诗意性;言说方式
作为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的论体文,经过先秦的孕育、两汉的发展之后,在六朝时期渐趋繁盛。其时,作论与著子、史同为 “立言”的方式。就文体而言,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的第三大文体。六朝论体文,是当时理性精神的产物,但在其理性中又涵泳着诗性。这种逻辑性与诗意性的融合,在文本形式或话语方式上表现为用诗性之 “言”承载玄远之 “思”。六朝论体文家专注于对宇宙人事的诗性感悟,专注于对这种感悟的诗性表达,并不着意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的逻辑推演。这种思维特征使得六朝论体文走上一条与西方论著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其诗意性言说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诗性思维特征。
一、论可以 “比”:隐喻式言说
诗可以比,比即比喻。东汉郑众称之为 “比者,比方于物也”[1]。朱熹进而论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2]也就是用两种事物间的相似处打比方。论体文中亦有 “比”,多称为 “譬”,亦为比喻。冯友兰认为: “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1]11这道出了古人表达思想的独特方式。季广茂在其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中写道:“隐喻不仅能折射出人类诗性智慧的光辉,也能揭示出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的哲学睿智;不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桥梁,也是人类认知自身发展的途径。”这强调了隐喻的深远意义。论体文中,隐喻的运用,既使文字简洁洞彻直指思想内涵,又使思想不粘滞于文字不死于句下。
六朝已远离产生巫术与神话的时代,但当时文士对隐喻思维中 “互渗”现象所带来的奇特效果仍然甚为着迷,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摆脱理性的羁绊和超越按部就班的逻辑过程,使看起来完全不相同的两个概念、两种现象或两类形象瞬间建立联系,并生发出新的意义来。对于六朝论家而言,隐喻与其说是其出于形象表达需要所自觉运用的一种文学修辞方法,不如说是其出于抽象、概括、省略等需要而进行的逻辑思维的不自觉的或 “无意识的”前提。隐喻在给语言表达带来多种途径的可能时也给思维本身带来多种途径和方向,它使思维脱离了已有的规范和轨道,凭借着 “灵感”、凭借着残留的印象、凭借着那些难以言说的感悟翱翔。
一般而言,隐喻可分为常规隐喻与创新隐喻两类。常规隐喻体现的是一定语言使用群体文化和经验的积淀,其形式的源域是人们熟悉的、具体的事物;创新隐喻则指创造相似性隐喻,是隐喻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体现,其产生依赖创造者基于自身经验的新感受。六朝论体文中所采用的隐喻式言说既有常规隐喻,也有创新隐喻。
形影之喻就是一个早在先秦即已使用的常规隐喻。《韩非子·功名》曰:“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4]这以形影喻名实。六朝文士亦将其用到论体文中,韩伯 《辩谦论》曰:“夫有所贵,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谦焉。譬影响之与形声,相与而立。”[5]1431是以形影喻美与谦之关系。欧阳建《言尽意论》曰:“名遂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5]1152又以形影喻言意。
形神之争是汉魏六朝的重要论题,东汉桓谭提出著名的烛火之喻,指出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气索而死,如火著之俱尽矣”[6]30,以此说明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后来,王充在《论衡·论鬼》中进一步论述:“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7]东晋慧远 《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五》中的问者提出:“法令本异,则异气数合,合则同化,亦为神之处形,犹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毁必灭,形离则神散而罔寄,木朽则火寂而靡托。”此当承桓谭与王充而来。针对这个问题,慧远结合现实中常见的薪经过燃烧成为灰烬,但火却从此薪传到彼薪、永不熄灭的现象,来证明人的形体消灭了,“神”也从这一形体传到另一形体,永恒不灭,“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6]32。在慧远之后,郑鲜之也以薪火之喻来证明神不灭,却是从另一个角度。他认为:“夫火因薪则有火,无薪则无火,薪虽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为用耳。若待薪然后有火,则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阳,阳为火极,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资,亦犹此矣。”[6]29很明显,他以火理象征事物本质,而薪火只是火的现象,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所以并不易于为人所接受。
南朝陈朱世卿 《法性自然论》:“譬如温风转华,寒飙飘雪,有委溲粪之下,有累玉阶之上,风飙无心于厚薄,而华霰有秽净之殊途,天道无心于爱憎,而性命有穷通之异术。”很显然此喻受范缜树花之喻的影响。《梁书》卷四十八载,萧子良曾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8]但值得注意的是,朱世卿并没有照搬范缜之喻,而是加以拓展,将喻体扩展为花与雪。
由此可见,六朝论体文虽袭用了前人的常规隐喻,却赋予其新的内涵,体现出当时文士的创新精神。诚如钱钟书所言:“比喻有两柄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边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 (denotatum)同而旨 (significatum)则易;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9]
六朝论体文中的创新隐喻则指那些更具诗性特征、更注重形象性的隐喻。如释慧观 《因缘无性后论》:“积滞皆倾,等秋风之落叶;繁疑并散,譬春日之销冰。”释慧通 《驳顾欢 〈夷夏论〉》:“正道难毁,邪理易退,譬如轻羽在高,遇风则飞;细石在谷,逢流在转。唯泰山不为飘风所动,磐石不为疾流所回,是以梅李见霜而落叶,松柏岁寒之不凋。”此中既富有易感知的形象,如秋风、落叶、春日、销冰、轻羽、细石、泰山、飘风、磐石、梅李、松柏等,又不乏专业化的抽象的术语,如积滞、繁疑、正道、邪理等,这种隐喻式言说方式,既解决了理论的形象性,又解决了理论的规定性。
隐喻式言说之所以成为六朝论体文的重要话语方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因为这种方式能够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多种涵义。无论如何,语言符号的直接传导能力是极有限的,符号与所表达内容的对应既限制了符号本身,也框定了其内涵。在以逻辑思辨为主要言说方式的论体文中,运用解析手段是为了捕捉对象的内核,因此论证的指向往往凝聚于某个点上,而这个点往往是不可再分解的原点。隐喻式言说方式则常常打破框框,在不同的符号与意义之间架起桥梁,建立各种通道。其功能中含有弹性和张力,使得隐喻所表达的含义不只是集中在一个点上,不只有单一的解释。它在论证对象周围划了一个有弹性的范围,从而不使所表达的一切都固定下来或凝聚下来,只是诱导和暗示,引导人们进入一个面,一个空间,使读者在这个范围中可依据个人的气质秉性、人生体验等等方面作为理解的基础而有接受的选择、有再阐释的选择,似乎也给各种不同类型的读者开辟了通往彼岸的不同的道路。隐喻的价值并非彻底说明对象,而是引导读者发挥其联想与想象,以共同走完这论证的过程,为其开拓了进入论证对象的多重路径,搭起了联系的桥梁。因为只有隐喻在建立大跨度的桥梁时不需要事先筑起一些坚实的逻辑的桥墩。[11]
其次,六朝论家多为诗人,受诗之熏染日深,对诗的隐喻表达方式驾轻就熟,这种言说方式所带来的效果往往超出论者的预期效果,引起深远影响。上文所言范缜的树花之喻即为其一例。因此,在论体文中运用诗性言说方式实为其习惯的延伸,或者说论者在论体文创作时,也期待语词的审美效果而不是期待某种确实不移的、准确的理论表达。虽说擅长创作论体文的文士皆有一种追究事物与现象底里的还原冲动,但是擅长于运用隐喻的论者与长于知性解析或理性建构的论者是不同的,他们希望那种抽象的理论能被还原成生动的形象,因为他们觉得形象所激起的视觉或其他感觉效果较之逻辑论证更具说服力。换言之,离开形象的抽象理性的内在力量并未为六朝某些论家所真正了解,所以隐喻式形象成为传送意义的首任之选。
再次,六朝论者在选择喻体时常常倾向于用某些前人提炼过的具有一定意义指向的形象,这样可以避免因生僻而产生歧义和心理疑窦。上文所举的那些常规隐喻即如此:选用 “形影”、“烛火”、“树花”来作喻体,不但精彩,而且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人们在接受它们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当然,一旦作为喻体,其涵义与原作的意义不尽相同,上下文的变迁使其在原来的意义上延伸出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倘若孤立地存在就会显得单薄,可是当它们以旧有的意义作衬托,其背景会深宏阔大起来,故在六朝论体文中的形象隐喻中可以发现,作为喻体的材料来源往往出自前人论作所构造的形象而非论家直接从生活和自身经验中提取,这样就增强了隐喻式论说的文化意味。
二、论可以 “兴”:造境式言说
兴,是指古代诗歌创作中自觉协调心物关系,孕育、熔铸艺术形象的构思方法或思维方式。郑众称:“兴者,托事于物也。”[1]610孔颖达曰: “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发起己心。诗文皆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体也。”[12]二者均强调了诗歌中事与物的关系。可见,“兴”就是用一定的物象或情境表现某种特殊的情感、思想的方法,是联系 “意”与 “境”的桥梁。
古人甚为强调意境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司空图曰:“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13]王国维则强调所有文学作品皆要有意境:“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撼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一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14]又将意境分为“造境”和 “写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15]可见,写境,贴近现实,契合自然,是一种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形态;造境,则为虚构之境,充满激情和愿望,本之自然却又超乎自然。
如前文所言,六朝论家大多为诗人,将诗歌创作的手法用于论体文创作也未必是有意而为之。通览留存下来的六朝论体文作品,亦不乏造境之美文。阮籍的 《达庄论》开端写道:
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坌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洲。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16]
阮籍推重庄子的 “寥廓之谈”,发而为论,自然更多寥廓之气、恢宏之貌。此处的 “先生”明显带有 《庄子》中 “真人”的风采,他游于天地之间,无拘无束,优游任性,委运自然,是其在内心刻画的理想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而这种自然情境的创设,以写意的笔法,勾勒出与心之所契合处,笔到而神会,别有一番境界,显然表现了阮籍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也就是说,当社会实际秩序的建构欲望落空之后,备尝生命沉沦的阮籍需要用这种造境的方式进行自我拯救,需要在另外一个空间建构一套秩序来满足内心 “立”的欲望。
阮籍 《达庄论》中所造之境纯为虚构,是其为自己的理想化身 “先生”营造的一个优游自若的生存空间,是理想化的境界,与现实相距甚远。仲长统 《乐志论》中所造之境则在虚构之中遵循 “自然之法则”,“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其文曰: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 《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人帝王之门哉![17]1644
文章描绘了一个超然于一切的世界:环境优美,生活自足,全家老少,其乐融融,逍遥于天地,得全于乱世,表现了仲长统试图超越现实而神游于精神世界的心情。这种境界更让人神往,因其与人世生活相距不远,可以不改变日常生活状态,而又在精神上超脱于现实。至梁代萧绎 《全德志论》却是为其政治意图而造境:
物我俱忘,无贬廊庙之器;动寂同遣,何累经纶之才。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但使良园广宅,面水带山,饶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鱼鸟。九月肃霜,时飨田畯;三春捧茧,乍酬蚕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击西缶。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若此,众君子可谓得之矣。[10]187
文中虚构的情境悠闲自得,此乃萧绎为其臣子创设的理想生活状况,其用心显而易见,即让他们全身为贵,忘怀忧苦,不必关心民生与国家之兴亡,而他作为君主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通过以上文例不难发现,在作品所造之境中充溢着作者的 “意”。“意”是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体悟,兼具感性与理性的因素,它融于作品所造之境中的所有组成部分——人、事、景,使之成为主体化、心灵化、审美化的世界;而 “意”又是理性的、后天的,它一方面来自外在世界向主体的呈现,一方面来自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评价。论家在作论之前,先有 “意”蕴含于胸,然后造境言之,“意”在心中,境亦由心造。相传为王昌龄所作的《诗格》中 “诗有三格”一条曰:“诗有三格:……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也就是说,作者从感受出发,为情感、思想寻找恰当的表现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心入于境,神会于物”,作者创造一种能够表现其情志思想的,由主观选择、改造、虚拟的境界。
六朝论体文因造境而使其所言之理变成含蓄而深远的 “境”中之理,所造之 “境”又因蕴含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而具有了诗境的韵味悠长。造境强调刻意经营,讲究 “意新语工”,师法自然,但不是对自然的逼真描绘,而是力求将隐含在形、色中的气、道、理、情、神等内在的本质的东西生动地表现出来。从此角度言,论体文中的造境式言说与诗歌创作技法 “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论可以 “怨”:抒怀式言说
孔子在 《论语·阳货》中提出了非常有名的论诗之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 “怨”被孔安国解释为 “怨刺上政”。《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钱穆认为:“故学诗,通可以群,穷可以怨……学于诗者可以怨,虽怨不失性情之正”。[18]也就是说,诗歌可以抒发、舒散怨恨、哀怨等情绪,其包含有和谐人际关系和批评时政等意思。就此而言,六朝论体文不仅与诗歌有着外形上的相似,其内质也是相同的。诗人是发愤而作诗,论家又何尝不是发愤而作论?孔子若不是四处传道四处碰壁,何来 “诗可以怨”之论?司马迁若不是惨遭奇耻大辱,又何来 “发愤著书”之说?六朝论家与其说是在立论辩理,倒不如说是在抒情言志,是故其文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和个性特征,与西方那种康德式的长篇巨制和黑格尔式的缜密周严大异其趣。六朝论体文的抒怀式言说是其诗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其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六朝论坛巨子嵇康之论虽以思辨见长,却并不能遮掩或取代其贯穿首尾的诗人激情,他把心性的自然演化为行文的自然,尽性而作,丝毫不顾及其后果。《管蔡论》是一篇颇有胆识的文章,为被史家视为 “凶逆”的管蔡翻案。该文立论大胆,分析全面,完全无视 “其时役役司马门下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谈也”[19]。至于其遭杀身之祸是否源于此,另当别论,但其 “想说就说”的特点还是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其文中所说的 “越名教而任自然”,“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20]262,更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经典。其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懑皆借论而发,由其文亦可感受到其 “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有好尽之累”、“疵衅日兴”[20]119的个性。
虽说出家人四大皆空,但在佛法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面对来自桓玄的质疑、何无忌的责难,东晋高僧慧远 “深惧大法之将沦”,忧心似焚,着急、焦虑、担忧、强烈的责任感交织在一起,难以遏制,自然流露于其 《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字里行间:“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义存于此!义存于此!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5]1769慧远将这些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以理性思辩为特色的论文充满浓厚的情感意味。
受儒学浸染甚深的范晔,在其 《后汉书》史论中极力推崇儒家忠义节气之士,对他们的遭际感愤不已,也借此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情感的大河时而气势奔腾,时而潜滋暗涌,所以其史论感情充沛,跌宕起伏,回荡着悲怆的旋律。《南史·范晔传》指出:“(晔)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 《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21]可谓一语道破范晔之心事。
《党锢传》为东汉气节之士的荟萃名篇,范晔在 《范滂传论》中写道: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7]2207
其悲壮感慨,可泣鬼神!子伏其义而母劝其死,在亲情与道义面前,深明大义的母亲不得不舍却自己的儿子,看似与人情相悖,实则益发突出其节气,有其母方有其子也。王鸣盛论曰:“滂母以其子与李、杜同祸为幸,皇甫规以不得与党锢为耻,光武、明、章尊儒劝学,其效乃尔,得蔚宗论赞,以悲凉激壮之笔出之,足以廉顽立儒。”[22]其对此感触颇深。
“比”、“兴”、“怨”的诗意性言说方式,使六朝论体文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言说方式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直接影响到论体文的内容。在这种有限的字句、简洁优美的形式之中,哪有雄辩和宏论的用武之地?因此六朝论家不得不将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浓缩于咫尺之间。在这样一种极其有限的词语空间,根本无法展开其弘廓的演绎和深邃的抽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六朝论家根本无意去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他们习惯于随意发论,注重意会,吉光片羽,简要自然,与西方文论的思辩性、系统性、规范性、明晰性等特征更是大异其旨。更为重要的是,六朝论家作论的目的是要求爱智 (哲学)者 “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3]9,不仅是认知的、思辩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层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六朝论体文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1]郑玄.周礼注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10.
[2]朱熹.诗集传 [M].北京:中华书局,1958:4.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52.
[5]严可均.全晋文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道宣.广弘明集 [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黄晖.论衡校释 [M].北京:中华书局,2006:875.
[8]姚思廉.梁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3:665.
[9]钱钟书.管锥篇 [M]..北京:中华书局,1979:39.
[10]严可均.全梁文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蒋原伦,潘凯雄.文学批评与文本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8.
[12]毛诗正义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13]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 [C]//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17.
[14]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 [C].//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493.
[15]王国维.人间词话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1.
[16]陈伯君.阮籍集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7:133.
[17]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44.
[18]钱穆.论语新解 [M]..北京:三联书店,2002:451.
[19]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 [M].殷孟伦,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92.
[20]戴明扬.嵇康集校注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62-263.
[21]李延寿.南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5:849.
[2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06.
On the Poetic Features of Argumentation Essays of the Six-Dynasty Period
(by YANG Zhao-lei)
The argumentation essay is a major genre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which flourished in the Six-Dynasty period.Such essays in this period adopted such approaches as metaphor,context-building and lyric expression to show poetic features like metaphor and simile,allegory,and complaint.The essays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correspondence with poetry and developed their poetic spirit.
argumentation essays in the Six-Dynasty period;poetic nature;expression modes
I207.2
A
1009-1513(2011)04-0061-05
2011-08-3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魏晋子书流派及其文学价值研究”(批准号:07BZW023)的阶段性成果。
杨朝蕾 (1977—),女,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文研究。
[责任编辑 文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