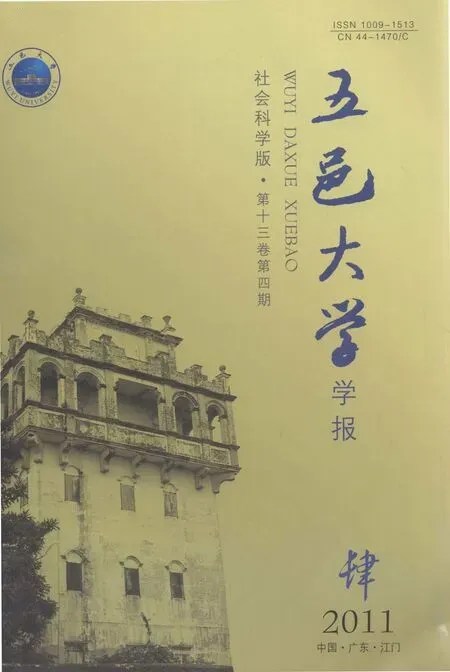张抗抗:启蒙心态、自审意识与童话情结
孙祖娟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张抗抗:启蒙心态、自审意识与童话情结
孙祖娟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张抗抗的创作,呈现出一贯的政治关心欲望。她以强烈的启蒙心态进入文学,逐步凸显以及加深其自审意识,表达其对社会与人生的积极关注和干预,同时自然地融入对童话的喜爱与重新编码。而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作者感知社会的独特视角与艺术表现能力。
张抗抗;启蒙心态;自审意识;童话情结
张抗抗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在数波文学潮流中,她不断有新作面世,从早期的 《分界线》到新时期初的 《北极光》、《爱的权利》到 《隐形伴侣》再到后来的 《作女》、 《赤彤丹朱》、 《情爱画廊》、《集体记忆》等,变化愈趋自如,手法日臻圆熟,影响越发深远。除了小说,她也创作出大量散文。她的作品,既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感性的情趣,深受读者喜爱。
纵观张抗抗长达近40年的创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自身的成熟与改变,看到她创作的不断发展与超越,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一些属于她个人的特征与 “症候”。
一、启蒙心态
张抗抗虽说有很好的写作天赋,但为了改变命运而写作也是重要的动力。就人生经历来看,不甘于平庸、不甘于被某些外来的影响击垮 (如家庭受政治运动的冲击),恐怕是她最初的创作契机。她出生于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是报社的主编,母亲是教师,还有关爱她的外婆。她天资聪明伶俐,读书好,爱写作,曾经是时代的宠儿。家庭的文化气息、父辈的教育及童年的幸福经历,奠定了她最初的人生观:勇于追求,积极进取,有着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与良好的人文素质。这些特点在其创作中有着明确的表现,诚如戴锦华所说,她 “执著于一种作家作为社会的良知、人民的代言、不畏权势的秉笔直书者的角色,并以其作为自己别无选择的责任”[1]。因之,张抗抗的创作总是积极追求和紧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这种心态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启蒙意识。
启蒙本来是个庞杂的概念,张光芒就当代启蒙文学思潮作了几十万字的论述。在此借书中董建序的定义:广义的 “启蒙”,是指一切唯客观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动,是指人类思想史上与当前现实中一切反封闭、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总之一句话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运动与文化精神。[2]借此评价张抗抗的创作精神,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启蒙心态:在社会的参与中体现出的以良知与责任为主的创作心态。
这种创作心态在张抗抗的知青小说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张抗抗有许多写老三届的作品。老三届指的是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张抗抗正是1966年初中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学生参与大批判,加入红卫兵,然后 “上山下乡”,他们当时多是渴望做英雄的年青人。父亲的 “历史问题”,曾让张抗抗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3]19后来,她对自己进行了反省: “我的家庭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使我既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仗义执言的精神。”[3]25虽然自己积极争取入团,一次次写申请,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之门外。她一方面不相信父亲是坏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挖空心思批判父亲以便显示自己的觉悟,这种两面人的难堪在她内心留下深深的创伤与屈辱。也就是这些人生经历,成为了她后来主动反思与批判 “文革”的内在原动力。
张抗抗早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是单纯的女青年,“相信一切报上的宣传和书本上的话,崇拜一切有识之士,对当时所有的 ‘革命理论’全盘接受并深信不疑”[4]。 《北极光》里陆芩芩对爱情的寻找,其实也就是在找精神的偶像,她对主流英雄人物是有着莫名崇拜的心理的。同样因为崇拜,《隐形伴侣》中的肖潇才爱上了陈旭这个有野心胆识、有智慧能力的时代英雄。尽管崇拜遮蔽了肖潇的双眼,但肖潇的选择从其初心而言,却是英雄情结使然。所以在张抗抗早期 《爱的权利》等文本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单纯、透明的,她们一方面有自己的好恶是非观,另一方面又崇拜、依附强势的男性。张抗抗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出她对社会主流的肯定,对英雄的呼唤,并试图以这些人物的行为和性格,来对比性地显示出她对当下社会现象尤其是精神滑落的不满和担忧。她认为当下社会的人们不应该为金钱拜倒,不应该对美的东西麻木不仁。她所表明的正是她鲜明的是非观和政治立场,只是在小说中这一意识经常性地遭到遮蔽而已。
对 “极左”思潮的批判、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以及对真善美的渴求、对科学民主的拥戴、对爱的权利的呼唤,这是张抗抗早期作品的主旋律,她试图以此对读者进行精神启蒙。张抗抗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具有 “启蒙者”姿态的男性知识者形象,他们的人生经历往往伴随着坎坷与苦难,大都在政治迫害中沉浮与挣扎,但依然信仰不灭、理想远大、意志坚韧而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形象高大,让人仰视,尤其是对女性。 “启蒙者”形象的出现,主要是社会氛围与时代文化思潮所致。由于新时期时代文化语境的变化, “主体性”意识与 “新启蒙”精神日益具有了合法性。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普遍关注具有精神内核的形而上领域,重视民族国家和改革开放等时代性主题,具有启蒙意义的宏大叙事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潮。张抗抗自己就说:“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新时期以来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这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5]因此作为女性的张抗抗,选择宏大的启蒙话语叙事,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此外,张抗抗自身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道路的选择也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
由于父母的问题,张抗抗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牵连。尽管产生了自卑与焦虑,但她与家人都还是渴望进入社会的正常秩序。在“爸爸的老问题加上妈妈的新问题,我眼前一片漆黑”的状态下。她不满于在外婆家附近的插队,“但我已无法安于一隅,我内心的骚动无法停止——外面的世界,遥远的北国,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也许是为了文学,也许是为了革命,也许是为了爱情,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反正我一定要到远方去,去开拓自己的未来”[3]35。这里,既有对现实的逃避,更有对命运的抗争,还有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由此彰显出张抗抗隐忍、坚毅、自强而独立的性格特征。而这种独立、抗争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姿态,从内在实质上说与时代精神有着一致的脉动,这也成为她日后在文学创作中选择启蒙性话语和时代性主题的心理动因。
在北大荒的8年,张抗抗经历了短暂却痛苦的结婚、生子、离婚过程,然后是漫长而孤寂的写作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父母亲都始终支持她,尽管她曾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也许当初还带着某种委屈与怨恨漠然地走向北大荒。从这一点看,张抗抗又是幸运的。事实上,在她的成长经历中,亲人的鼓励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环。譬如 《分界线》的命名,就是她与父亲反复讨论的结果。 《隐形伴侣》中,从肖潇父亲对于陈旭的看法、肖潇回杭州后不敢去见自己的母亲等细节中,都可以窥见张抗抗当时的心境以及父母亲形象的隐形参与。
张抗抗最早产生一定影响的小说 《分界线》,就是在积极入世精神鼓舞下的产物。对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这样评价:“《分界线》严格地说并不是文学,而是某种概念的诠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和传声筒。”[3]188而这一说法,也佐证了作者欲为社会精神启蒙的主观创作意图。
二、自审意识
从张抗抗的创作实践看,她无疑是个主流文学作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然而她的成长经历又显见她长期并不被主流意识所接纳,只是一个处于边缘叙事身份的作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她有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她的成长却不断受阻。这样就形成一种悖论:越是被主流排拒,越是想融进主流。所以,张抗抗的作品便顽强地呈现出一种宏大叙事的文本策略,一种对社会、对政治的超出性别的异样关注。她早期的一些列作品所追求的宏大叙事、主流意识、启蒙心态、英雄情结等,无不带有这一人生经历的心理胎记。但随着岁月的流迁、人事的更迭、潮流的兴替,早先的愤激已被中年的理性所抚平,这促使她从意识形态沉重的说教中走了出来。她不断地检视自己过去的脚印,也不断地反思与修正自己的精神世界。正是因为她的强烈自审意识,她总能不断地尝试对自己的表达做出改变。张抗抗早期涉及知青生活的作品 《白罂粟》等,就在倾诉苦难的同时表述出追溯苦难来源的愿望,并对知青中受极 “左”思潮毒害甚深的另一类人做出表层的分析。到了《隐形伴侣》,她便试图从人内心自审的视角,来表现知青扭曲的人生轨迹,揭示其思想意识根源,并探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也因此被公认为是有 “思想激情”、“群体意识很强”的作家[6]。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的中篇小说 《永不忏悔》,以及至90年代的 《沙暴》、《残忍》等,张抗抗执着于揭示知青自身弱点和缺陷,检讨上山下乡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为自身 “诊病疗伤”。而 《情爱画廊》及后来的 《作女》等不仅显示出了作者一贯的对人性的关注,也将曾经被遮蔽的女性意识展示出来。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重要时期或者文学思想变迁的潮汐里,张抗抗总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使人们对她刮目相看。新世纪以来,张抗抗又出版了《黄罂粟》、《请带我走》、《鸟善走还是善飞》等中短篇小说集,其中 《集体记忆》、《面果子树》等篇目甚为评论家和读者所肯定,成为她具有强烈反省意识与批判精神的代表作。
什么是自审?张抗抗在 《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中将其定义为:自审是对罪恶的认识,是经历了非人化到神话最后回到人化的 “怪圈”之后自我的重新获得和确立。[7]141她非常重视的是人性的内省。正因为作家所具有的自审意识,她才能够去对自己的过去做深入的检视,对自己的创作甚至人生进行深刻的内省。生活的波折带给张抗抗的,不光是苦难的记忆,同时也有理性的沉淀;而这种理性沉淀,又给其作品精神理念、叙事风格和文化意识带来一系列转变。张抗抗的自审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自身的反省。女性作家的自审意识,并不始自张抗抗,它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即使在与张抗抗大体同时代的作家里,张洁、铁凝、王安忆、残雪等,也不乏对人自身、人本质的深层反思和自省。她们既对男权文化中心进行反叛与颠覆,同时也以自审的姿态对女性自身的文化病态进行冷峻审视与批判。张抗抗的 《隐形伴侣》有着准自传的色彩。在 《隐形伴侣》中,肖潇与作者有着诸多的相同之处,都曾单纯幼稚、盲目崇拜。张抗抗借助肖潇这个人物反省了自己在那段岁月的浅薄与荒唐,但作者不是简单地对人物做道德的抨击,而是将其置身于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去进行反思,去思考人性呈现中的显与隐、善与恶,去发现那个在挣扎与抗争着的绝望与恐惧的 “隐形伴侣”,去审视人性是如何被显在的社会语境与潜在的集体无意识一起绞杀的。这种批判性的内审,无疑具有知性的深刻和人性的震撼。张抗抗小说中人物的自省,既表现了作家的自审,也表现了对社会的严重关切和对灵魂的细致剖析。如 《月亮归来》中,一个返城知青目睹一群可爱的小鸭子在一个公园水塘里一只只地消失,悲情的场面使他痛苦地回忆起往事,反省 “文革”和 “上山下乡”在“大跃进”之后是如何破坏环境的。人物的忏悔和歉疚,其实就是作家心灵的共鸣与悸动,在那些捕杀鸟兽的人群里,不是很容易见到作者的身影么?
其次是对老三届的反省。张抗抗一直关注思考着昔日的 “老三届”,以及他们每一个特殊个体的生存状态。[8]在改革大潮中,一些做着英雄梦的人被时代磨砺成平庸,有的仅仅满足于端一个铁饭碗,有的则迷失了自我,或挖空心思去赚钱,或堕落成贪官,享受着腐败带来的利益。他们的自我怎样觉醒,健康的人格怎样锻造?同样是作家非常关注的。《残忍》、《沙暴》就是探讨了这样的主题。《沙暴》里的知青辛建生,他的重新拿起猎枪的决定,最终标明他的内心抵抗在强大的外部物欲面前是何等的脆弱。这其实不是道德的颓败、人性的堕落,更是人与环境之关系的纠结。诚如作者所言:“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被人的欲望所支配所奴役所改变着,这便是人类的灾难之源。”[7]155作者的自审不仅是在审视自己,更是在此基础上反思人类的行为,这实际上有些终极关怀的意义了。“老三届”的上山下乡作为那个红色年代的重要事件,它所指涉的几乎关联着社会政治的各个领域,它曾牵动的几乎集中了 “文革”时期的千家万户的神经,对它的反省和评价注定是无法回避的。张抗抗没有回避,而是积极地以笔为刀,深入解剖。她不仅用多部小说来进行反思,也在许多序言、访谈里,直接地发表她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看法。尽管回忆往事是痛苦的,但人终究要正视自己。
再次是对红色追求的反省。《赤彤丹朱》“那四个红色的汉字垂叠交错,相互勾连又彼此挤压,从红字的缝隙中,产生出多少无声无色无形无状的故事,故事被历史沉重的驮起,化作了一首哀婉悲凉的红色变奏曲”[7]153。作者通过张恺之与朱小玲的经历,反思人们对革命的理解与追求。这本来是张抗抗耳熟能详的爸爸妈妈的故事,但它的写作却与新历史主义不期而遇,于是张抗抗通过个人对历史的感知,解构了关于红色的神话。这部作品肯定理想,反思理想,追问了理想主义的阴暗面,成为张抗抗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集体记忆》也是这种反省的延续,为什么澹城的人集体失忆?它也是对历史与记忆、历史与民族中的权力、政治的反思。
启蒙心态仍在,自审意识却不断深入,张抗抗的叙事亦从全知视角转向有限视角,但其文本的内涵却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力度。
三、童话情结
在当代女作家的创作中,带有童话色彩的并不少,但顽强并一贯地显示出对童话兴趣的并不多见,张抗抗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由其对童话的厚爱,催生出她类似童话情结的情感因素,并在其文本中自然呈现、水乳交融,这成为她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特性。
这种童话情结,首先来自张抗抗对于童话的喜爱。张抗抗母亲就曾经是一名童话作家,还是在她的孩提时代,母亲最先给予她的文化因子就是讲述诸如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丑小鸭》等外国童话,用童话去滋润她的心田,童话给了她一种永恒的精神气质。张抗抗自己也说,她是被童话 “养成”的,受益于童话之善之美,并将其留给自己享用。她早期的作品就充满了对童话的喜爱,如 《北极光》的童话视角,以及 《隐形伴侣》和 《赤彤丹朱》里用童话的幻境来实现对现实场域的置换等。其次,以童话来显示女性自身的成长甚至是救赎,可以看作是作家的思维定势和叙事策略,是对女性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活的一种指涉。对童话故事的运用,使张抗抗的作品产生了独特的韵味。
其一,童话在张抗抗那里是一种对比和隐喻,童话世界的干净明朗与现实社会的杂乱迷蒙形成比照。比如 《北极光》里,陆芩芩 “凝望着人行道对面蓝色的小栅栏”从夏天的想象回到眼前的干净,自然联想小时候读过的童话壁炉,雪女王,漂亮的公主……还有古老的壁炉、雪橇、花篮、圣诞树等。看到傅云祥家的二层楼房,也恍然给她一种童话的意境,使她想起许多美好的故事,可她一走进房子里面,那个童话就倏地不见了。这里,童话就是一种参照物,常常给她错觉,折射出生活远比书本上的描摹复杂。同时,童话这一隐喻性的修辞手段,也往往表现出主人公对现实社会的一种逃离和抗拒,揭示的是她内心的隐秘世界和精神性的追求。理想是云彩,生活却如沼泽,既然污浊的现实境域里人们无从逃避,而童话正好成为精神的避难之所。当现实生活将众多的苦难悲情加之于主人公身上,而主人公的精神力量又无法承受的时候,潜在的女性意识便让主人公逃入其精心构筑的童话世界。芩芩在这个由冰凌花、雪橇、壁炉以及美丽的公主所构建的童话王国里,享受着浪漫与美好,这正好真实地传达出她对现实社会价值的否定和拒绝。童话的意义,也就在于成为张抗抗笔下女性主人公在现实世界里实现精神自救的强力支柱。
其二,童话所呈现的隐喻,曲折地传达出作者机智的反讽与幽默的表达。《隐形伴侣》中,肖潇对爱情的心理状态随着对现实的感知而变化,由热情的向往、投入到彷徨而无助,都伴随着童话的出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被张抗抗得心应手地反复运用。童话中,小金鱼对渔夫祈求: “老爹爹,放了我吧……”这一场景的出现,正是其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郭力曾经做过精彩的论述:“潜隐的思想通过联想与角色切换 ‘投射’于现实,自我得以通过旁观式的幻想抵达欲望,如是完成了对现实 ‘置换’的心理要求。”[9]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叙事机智,她省略了过实的描写,展露出空白任读者去联想,诗化了意象,丰富了人物、场景及意韵。托尔金曾认为,真正的童话应该具备幻想、恢复、逃避和慰藉等四种要素。在 《隐形伴侣》中,肖潇的幻想始自雪白的天鹅蛋,而天鹅蛋的破碎又促成肖潇的逃避;而在逃避过程中所遭受到的挫折和无奈,无疑又与童话里丑小鸭受到的歧视相类似。童话的递相使用,隐喻着作为知青的肖潇们的天真烂漫之梦的破灭,以及在逃避过程中的没有身份认同的自卑感和挫折感。肖潇就是现实场景里的丑小鸭,而肖潇也一如童话里的鸭子一样选择了爱情。但命运的改变,还必须靠着现实世界里的挣扎和抗争,所以当雪白的天鹅和天鹅蛋再次出现的时候,当小鸭子要再去向广大世界的时候,肖潇也在挫折和沉沦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和前进的路向。这种转变是为了通向幸福,主人公是如此,读者所得到的心理暗示也是如此。丑小鸭最后变为白天鹅,正是一种隐喻性的象征,是高度凝练后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起伏的代表性符码。
其三,童话的运用既是一种对现实的规避,同时也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隐形伴侣》里的 “谎花”,即可作如是观。这个差点被作者用来作为标题的花,是雌花还是雄花,作者与人物都是存疑的。陈旭和肖潇,一断其真,一定其假。尽管有着科学家身份的权威苏大姐的指认,但是它并不能消解人物对此的性别之惑。肖潇的 “就没有一种既非雌花也非雄花的中性花吗”的疑虑,显示的不仅是对花的性别的认证,实际上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女性性别的象征意味。具言之,花而不果,表征着叙述者对女性身份以及女性生命的恐惧感,并由此延展到对男性性别和权力的一种恐惧。在张抗抗的小说文本所营造的语境里,繁复的生活充满了不可预知性,其中有些提升了认识,但有的不是女主人公当时所能认知的,那么就只有期待于未来。《赤彤丹朱》里人物的是是非非就是这样。爸爸的历史、妈妈的历史、外婆与祖母的历史,在非黑非红非梦非仇中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但是对这种状态,作者并不是以一种对历史和事件线性把握的方式来展开,而是大量地借助童话以隐喻的方式建构。在这个隐喻方式构建的叙事框架中,历史的意义都是些有限的感知与碎片,它们自身也往往成了被解构的 “寓言”,在历史性的灾难使所有人都无可逃离以及在灾难过后人们对此进行反思的时候,人物往往也都会遇到一个精神救赎的问题。命运无可抗拒,焦虑势必存在,而灵魂却可以救赎。《赤彤丹朱》里的朱小玲,即有着精神自我救赎的需要。但是她的精神救赎,却并非是在真实的情节叙述中完成的,作者借助了童话。在其精神遭遇绝境的时候,她不断地重复讲述 “老爹爹,放了我吧……”。她就是老渔夫手里的那条小金鱼。自由已然不由自己掌握,一方面是恐惧,一方面是幻想。这一童话的反复使用,正说明了张抗抗十分看重它所具有的隐喻意义,表达着人物相同的精神欲求。类似的还有 “仙人跳”在文本里的隐喻作用。她在朱小玲生命的不同时期出现,给了她生命轨迹的不同隐喻和暗示。这个所谓的 “仙人跳”,其实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童话而已,它告诉读者,人在历史中实在太微不足道,你既跳不出历史,同样也跳不出现实。作者的一种历史沧桑感,就在这个 “仙人跳”的象征中被隐喻出来。《作女》中执着于翡翠鸟的故事,也是作者对于醇美纯净的童话境地的向往,同样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随着作家创作心智的成熟,那种童话中的小女儿心态也在逐渐淡化,可童话情结却没有消失,而是在 《第四世界》、《谜面:九十九》等作品中不断地呈现,这正说明张抗抗的童话情结有其连续性和融通性。在其作品中宏大叙事逐步让位于边缘叙事、女性意识的由隐而显的改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童话的作用和力量。纵观张抗抗的创作,童话成了她不可或缺的部分。她对童话的娴熟运用,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值得认真关注和研究。
总之,不管是启蒙还是自审,张抗抗都努力地在思考着社会、人生,以及她自己。而童话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她的创作手段和叙事表现力,更是表征着作者的纯净心灵和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意愿。
[1]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8
[2]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序 [M].上海:三联书店,2006.
[3]张抗抗: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笔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
[4]张抗抗.北极光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7.
[5]张抗抗.大江逆行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91.
[6]朱青.中国当代女作家纵论 [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7]张抗抗.沧浪之水 [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8]张抗抗.女性的身体写作及其他 [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81.
[9]郭力.“北极光”的遥想者——张抗抗论 [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50.
Zhang Kangkang:Enlightenment Mentality,Fairy-tale Complex and Self-examination
(by SUN Zu-juan)
Political concern threads through Zhang Kangkang's literary works.They blend a strong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nd fondness for re-encoding of fairy tales,gradually reveal and deepen her sense of self-examination and express her positive attention to and intervention in society and life.These features combine to show the author's unique perspective in perceiving society and in her artistic expression capacity.
Zhang Kangkang;enlightenment mentality;fairy tale complex;sense of self-examination
I206.7
A
1009-1513(2011)04-0066-05
2011-09-07
本文为江门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江门全国著名文学家研究”(批准号:20081001)的阶段性成果。
孙祖娟 (1955—),女,湖北枝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文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