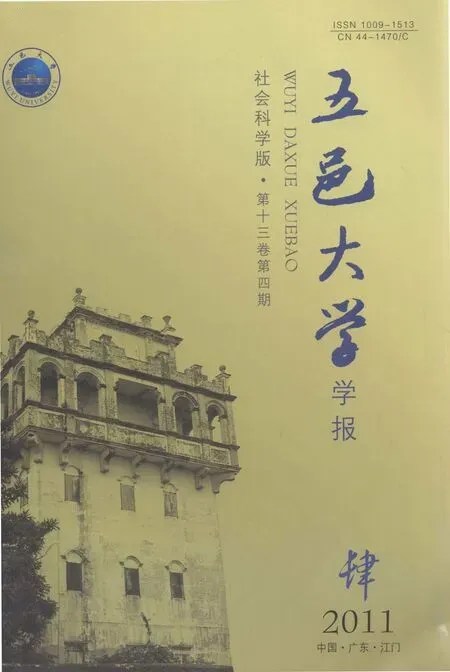孙中山与石长信两篇铁路文本的解读
杨红运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孙中山与石长信两篇铁路文本的解读
杨红运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孙中山与石长信是被贴上对立标签的人物,但他们就铁路建设的论述却有同有异:对铁路的重要性,孙侧重于民生价值,石更强调行政和国防意义;对铁路国有,孙侧重于对社会的整合,石强调对政令统一的影响;对引进外资,孙态度更为明确;就修建规模,孙具有浪漫色彩,石更具务实考虑。
孙中山;石长信;铁路文本
众所周知,由铁路国有引发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而辛亥革命则让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寿终正寝。因此,清政府的 “铁路国有”可谓是一个自掘坟墓的政策。1911年4月,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清廷的 《铁路国有折》,深受清廷的重视,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奏折是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理论来源。次年10月,孙中山发表了 《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这两篇集中阐述中国铁路建设思想的文章,在赵靖、易梦虹所编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下册)(1982年5月第1版)中处于相反位置:孙说被视为革命派观点,石折却被冠以 “反动官僚”之论。然而,客观评析,这两位对立人物在前后一年多时间所著之文章中,相同之处要大于不同之处。
一、铁路价值:石孙观点的汇合
石长信在奏折中指出:在一个时局艰难的时期,人民生计困难,商务衰退,军事、实业、财政、民生都要受到交通的影响。且当务之急是边防需要,“若国家不尽快将东西南北的主干铁路次第兴筑,那么,一旦强邻四逼,就会出现无所措手的情况,人民不足责,其如大局何?”[1]411值得注意的是,石长信对于铁路重要性的看法并非原创,而是当时社会上力主修建铁路者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正如他所说的:“近年内外臣工,疏陈补救之策,咸以大修全国铁路为请。”
孙中山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及了铁路的重要性。与石长信相比,孙显然更关注铁路之于民生的重要。孙中山认为:中国物产并非不丰富,只是有待开发而已。中国亦与各大国发展之情形相同,所急切需要者,乃交通之便利。只要修筑了铁路,物产的价值势必会增涨数倍。“因此种路线,不啻昔日市场与生产者遥远之距离,缩短于咫尺之间也。下蕴藏采掘,金属物产之开发,其利益之丰厚,乃显而易见者,固不待赘言者也。”[1]50-51
不可否认,就铁路的作用而言,石、孙从一个硬币的两面来论述,他们的观点并非对立,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进一步探究,石、孙关于铁路作用的见解也并非独有,只是当时社会关于铁路建设思考浪潮中的两朵浪花。自洋务运动开展以来,时人就从国防到民生来论证铁路之重要性。有人专门写了 《开铁路有十利说》,该文作者认为,建设铁路的重要性有10种,即 “行军速、运转捷、百货通、商旅便、生计开、厘金旺、可以减兵额、荒虽易于赈济、漕米易、可以供京仓”。总的来说,铁路可以使得 “吏治可平”、“国是将定”、“属邦可保”和 “利权可收”。另外一些人还发表了 《修路乃能足食论》、《建仓储米不如铁路轮舟说》、《御水赈饥莫如推广铁路说》、《造铁路可以救灾说》等论著。[2]仅从上述文章的名字就能看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将铁路建设当成了富国强兵的万能灵丹。
进入20世纪后,不少清廷的封疆大吏也不乏对铁路功用的认识。譬如,1903年张振勋曾指出“商战之道,必寓商于农,寓商于公,寓商于路,矿而后可”[3]932。同年,四川总督岑春煊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讲道:物产丰富的四川货物,须经过崎岖的山峡和滩流才能运到汉口进行中转。没有铁路来转运,商务是很难畅旺的。[3]10581904年,江西巡抚夏峕就提到 “建造铁路,实为当今切要要图”[3]963。1906年6月,广西官绅、内阁仕读陆嘉晋、内阁候补仕读梁济等联名68人上书朝廷,他们在请办铁路的奏折中明确指出:“广西地处边陲,运输不便,非建筑铁路,商务断无起色。”[3]11351907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在一份奏折中指出:由于内地山路崎岖和滩流浅急,造成了五金、蚕桑、畜牧、森林等资源丰富的广西,百货运转不便,自然资源未能得到很好开发,若广西能够建筑铁路,不仅湘、粤、滇、黔的货物能够通过铁路进行载运,即广西本省矿产各项的运费收益也是巨大的,铁路对于通商惠工和征兵转饷的好处也是不可枚举的。[3]1140陕西巡抚恩寿在1908年的奏折中也有类似观点。他说延长的油矿质量可与欧美媲美,现今之所以没有开采,是因为运路不通,“故经营的目的当以博采广销,力敌外货为主义,而著手当以开通运路为先”[4]。1910年,商部一份奏折同样指出:中国交通落后不仅造成军政难以统一,而且所有森林矿产也因此被弃利于地。[3]1163当清末预备立宪后,有人论述铁路不仅与国防、教育和商业有关系,而且与宪政的召开也有莫大关系,只有速筑铁路,才能使国会议员的招集得以便捷。[5]1
从上述整个时代对于铁路的诉求可以看到,石、孙关于铁路功用的论述并非是最早的,正因为“铁道之利国利民,吾国今日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无人不知之审矣”[12],就连清朝的上层官员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石、孙的论述是不可能脱离于时代思潮之外的,其论点的不谋而合是顺理成章的。
二、铁路国有:石孙观点的趋同
清朝灭亡的原因很多,而中央对地方控制的虚弱、松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清末乃至民初,不同的政府都试图重振中央权威,加强对地方的有效整合。仅就修建铁路而言,士绅活跃的身影随处可见,其表现形态又各不相同。1904年,潮汕铁路公司开始筹建时,百名士绅和地方官员共同决定了买地的价值;有的士绅想谋占股份、包买器械;有的则想干预公司内部事权;有的士绅则挂虚名、谋职位有兴趣,希望向铁路公司索取高额薪水。当詹天佑带领学生来实地勘测时,又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当地士绅乘机生事,打着省府的牌子企图使公司创建首总理张煜南更改章程;有的暗中联络汕头商人,以洋商先买的借口进行抵制;有的则利用新闻报馆散发长篇大论,进行恶意中伤。[3]937-9381910年,当新宁铁路招股时,由于所认股份以新会县人为最多,该县绅民就提出协助办理筑路事宜,期望通过此举夺得路权。如果得不到士绅的认可,筑路之事就会遇到不小阻力,士绅们会以某处有碍山林、某处有妨坟墓、某处有碍风水为借口来进行抗阻。[3]951诸多的分歧使得该铁路修筑遥遥无期。
士绅们各自修筑铁路、缺乏全局统筹的弊端逐渐被时人所认识,譬如,1906年一位日本领事在其报告书中写道:“粤汉铁路之敷设,已决定由三省各别出资筑造,然各省皆有其特殊困难。例如广东方面,资金筹集虽不成困难,但在铁路管理权上,官商间发生冲突,致使工事的修筑大为缓慢。湖南方面原归绅办,但湖南绅士徒多议论,经费筹集则毫无头绪。此实为粤汉铁路腹心之患也。湖北方面,绅商皆无势力,全赖怨督之措置经营。”[3]1022。同年,商部的一份奏折中也指出:各省所筹划的路线往往未能通盘筹划,再加上省界分明而各存畛域,造成了路线交错,干枝如何维系,轨道如何贯通,地方都未能考虑进去。这份奏折担忧道:“将来通国铁路告成之日,势必有参互复沓骈拇校指之虞,于日后修养之需,亦恐难操胜算。”[3]1152一位美国人同样看到,虚弱的中央只有通过修建铁路来重振权威,如果中央政府向地方势力让步,就将是一个莫大的政治错误。[3]1192-1193张嘉璈更是系统论述了铁路统一的必要性,他认为:“凡百行政赖有交通机关以普及全国。交通不便,决不能的行政之普及。行政既不能普及,更遑论统一哉,是以欲求国家政治之统一,不可不先谋交通行政之统一。”否则,各路的管理章程不一,账目就会混乱。期后果客货往来不便,公司联络困难,营业就会衰落。因此,铁路之统一是当今急务中的急务。[7]
既然这么多人都认识到了士绅自办铁路的弊端,那么石长信和孙中山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石长信认为:这些已办未办的铁路,要么由于资金欠缺造成工程停顿,要么因为亏本造成众多股民观望,要么由于生计困难导致民间集股不能踊跃,要么因为各省绅民狭隘的乡土观念致使铁路支线未能全盘考虑,因此,铁路国有势在必行。孙中山在其文章里也不反对由中央铁路公司筹建铁路。可见,石、孙二人在通盘考虑铁路修建方面是有共同点的。二人的观点也在实际中得到了印证。铁路国有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但是,进入民国以后,这种国有趋势并未改变。截止到1916年,除广东以外的其他各省,先后与交通部订立了赎回合同,铁路国有化算是基本完成。[8]800
只有铁路国有,才能推动其他事业的发展。如石长信所说,在一个幅员辽阔、风气各殊的国家,只有通过铁路联络,才能实现行政统一。孙中山则看到了民国成立后地方仍旧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他期望各地能消除省见,推动铁路事业的统一,对此孙中山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讲道:“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言语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盖省区之异既除,各省间不复时常发生隔阂与冲突,则国人之交际日增密切,各处方言将归消灭,而中国形成民族共同自觉之统一的国语必将出现矣。”[1]54可见,孙中山期望铁路能加强中国各地的联系,进而消除言语隔阂,好让全国人民能够视同亲兄弟。孙中山对于铁路整合社会的思想带有大同思想和浪漫主义色彩。
三、铁路集资:石孙看法的差异
铁路的修筑需要巨资,这使得关于铁路修筑是利用外资还是自筹的争论一直不断。1904年,就在锡良和张之洞主张自办川汉铁路时,亦在担忧铁路的集资:修筑4000多里的川汉铁路,需要费用在5000万元以上。在锡良看来,要是借外资筹办,外国都会争着借款给中国,筹款将并不困难;要在国内招集民股将会十分困难。锡良特别指出在四川筹集民股的一个不利因素:处于偏远闭塞地区的四川民众,根本未看到邻省办矿等股份的成效,他们必然会怀疑数百万民股的可信度。[3]1160而且,民股筹集是按照 “田亩加赋”、抽取租股为主要方式的,这种集资方式在现实中是扰民不断的。四川留日学生就曾看到这种集股给民间带来的痛苦,他们说:“四川自咸同以段,地丁而外,津捐各款,名目繁多;近年来,兴学、练兵、办警察、筹赔款,竭泽而渔,势已不支。而外洋货物,充塞内地,工徒失业,农商亦因此受亏。生计艰难,迥异昔日。疮痍满道,乞丐成群。节衣缩食,卖儿鬻女,而不足以图生活供丁赋者,比比皆然也。凡我川人,环顾故乡族友,岂非一落千丈,十室九空,富者渐贫,贫者且死乎!今又益以川汉铁路之租股,我川人如其何能胜?然勉强以应者,岂非急公好义,有迫之使然者也。是故州县之所敲扑,胥吏之所鱼肉,乡里蜩螳,骚然不靖。”[3]1073租股的弊端更是不少。具体执行筹款事务的局绅保正,只会逢迎上级,欺压百姓。他们还借此来收受贿赂、报复仇怨。如果地主是他们的戚族,保正收租时就可以少报;反之,如果地主与他们有嫌怨或未行贿赂,保正收租时就会多报;处于两个保正管辖区内的土地,他们会重复收租;保正也向那些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重复收租。当百姓控告保正时,官府不仅不予理睬,还会用刑讯来逼迫百姓迅速交租。[3]1086
到1907年,一位名叫杜德兴的人上书都察院,公开批评川汉铁路租股扰民。他从三方面揭露铁路租股的弊端:第一,这种租股利于上户而不利于下户。四川频遭水旱后,疮痍还未恢复,上户遭受的损失很小,下户却多流于乞丐。中下户人家秋收后一般没有余粮,但他们必须缴纳租股,于是,有的要靠卖新谷才能救急,有的要从富家那里借款才能生存。第二,租股在征收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硬性的摊派税捐。由于铁路租股要随正粮同征,纳粮的人必须先交铁路捐才能纳粮。如果百姓不能缴纳这种摊派性的铁路捐,官府就要对他们进行鞭笞棰楚和监禁锁押。这样,造成有些纳粮人鬻妻卖子、倾家破产;有的人捐了巨款却得不到股票;有得虽有股票却3年见不到一丝利息;有的视股票为废物,将其贱卖给别人。第三,这种租股为官府提供了营利机会。由于征收程序混乱,有的按户勒索租股,有的按粮派谷,有的任意苛罚,有的通过多报以求政绩,有的将谷、银进行折合,再将一年之高价定为常态,并不关心百姓收成的丰歉和市场价格的波动。在官绅的勾结和差役的追逼中,乡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因此,百姓认为铁路不是利己的商业,而是害人的苛政。[3]1088-1089
征收铁路租股不仅在操作过程中成为扰民政策,而且集资成效也不尽人意。据有人对1911前全国16个省铁路公司的集股统计,能够按照预期完成的只有1个,完成率不到7%;有2个公司能够完成预期集股的75%;其他的13个公司都未能完成预期的一半,还有6个省甚至根本没有推行过集股。[3]1149就筑路进程而言,靠商股修路的效果微乎其微。截止铁路收归国有时,湖北路段仅筑路基数里;湖南路段才修成100多里;四川路段则因用人不当,致使铁路银行倒闭而亏损了300多万元,筑路完成土方70-80里。[8]801-802因此,即便是在民间自办铁路的高潮时期,时人也未停止呼吁通过外资筹办铁路的方案。如1908年,张之洞致陈夔龙的电报中就说:湖南的士绅是素来不主张借外款的,近来议论也变了,他们知道仅靠本省的租股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他们请求官府借款与本省的租股合力兴办。[3]1194
在这样的困境下,便不难理解当时知识界纷纷呼吁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议论了。知识界认为利用外债修铁路的好处有三点:一是财力匮乏的中国是无法骤然筹到巨额款项来修建铁路的,即使能筹集到款项,也会造成市面恐慌,更会让其他实业因资金的分流而衰落,举借外债则可以避开这些困境。[9]二是时下外国向我国的投资是经济性的,是外国商民为了赢利而放贷的,而非为了扩充势力的政治投资。只要能妥善运用,主权是不会丧失的。[10]三是外债的利息很低,年仅三四厘,而国内普通利息就需要一二分。“只畏外债若蛇蝎而与争回商办,其热心固可敬,而其愚亦可甚矣。”[5]3时人还进一步讲到借债修路的紧迫性,他们认为在当时乃外国资本家苦于无处投资和世界金融低落之机,引 “外债以筑路,实为今日铁路政策中最重要之价值也”[11]。郑孝胥更是大声呼吁:“故为今日之中国计,十年之内,惟以吸收外资为救亡之要著,十年以后,惟以铁道尽通为图存之要著。约而言之,则借债造路而已。”郑还进一步讲道:中国大举借外债,可以让各国都借款给中国,这将利于抑制富有侵略性的德、俄、日三国。而且,只要包工与借债能够并举,外国包工公司基于赢利的考虑,自然会就地从中国招募人员和购买原料,在劳工和原料由中国提供的情况下,中国将能从铁路修筑中得利7成。[3]1165日本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批评中国方面的顽固不化,指出中国在不过分损害利益的条件下可以引进外资。他们认为靠清朝的力量修江西的铁路是不可能的。若当局仍旧顽固排斥外资,即使再过数十年,这些铁路也不能修成。日本人甚至洞察到中国方面的排斥外资,实质上是反对者为争权夺利而攻击对手的手段,而并非内心憎恶外资。[3]979
显然,在石、孙之前,国内关于引进外资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石、孙的观点也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思潮而行的。石长信在奏折里虽没有明确提出借债修路,但他至少是支持此举的。他觉得张之洞与美国公司的毁约之举是够固执的: “计日废约以来,已越七载,倘若无此翻复,粤汉亦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至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1000余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1]412相比而言,孙中山则明确提出利用外资来修建铁路。他认为建筑铁路有三种运作方式,一是利用外资,如京汉津浦线等是也;二是集中外人之资本,创设铁路公司;三是任外国资本家建筑铁路,但以今后40年归还该项路线于中国政府为条件。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三种了。为此,他说:“吾人须屏除一种错误之见解,勿以为外人一旦属办入此种事业,则必破坏国家之主权,妨害吾人之自由。”他说这种办法曾在世界各地施行,但并未妨碍相关国家的主权,如美国早期敷设的铁路就是靠外资,但美国并未因此受害,反而获取很大的好处。[1]53与石长信的含蓄表述相比,孙中山关于引进外资修建铁路的论述更为坚定、明确。
四、时代反思:石孙铁路观评价
从宏观角度分析石长信、孙中山这两篇前后相隔时间不长的文章,可以看到所谓革命派、顽固派在铁路建设问题上的差异并不明显。某种程度上说,石、孙关于铁路建设的论述有着不少相同之处,他们的思考和论证带有继承和发展。与石长信更关注行政和国防相比,孙中山关于铁路功用的论述更多关注到民生方面,他企图通过铁路整合社会的观点带有浪漫色彩;二人都承认仅靠本国力量是无法尽快修筑铁路的,也都不排斥引进外资。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石长信关于铁路干路、支路的区分和规划带有一定务实性,如他所说 “今粤汉铁路直贯桂滇,川汉远控西藏,实为国家应有之两大干路,万一有事,缓急可恃,故无论袤延数千里之干路,断非民间零星凑集之款所能图成”,因此,这两条干路应该由国家经营,支路则可由民间修筑,这样,劳工和资金相对容易征集,收效也快。[1]413相比之下,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的规划更带有浪漫色彩,譬如他认为,10年修筑20万里的铁路是完全可能的,甘肃兰州将有13条铁路穿过,各省省会均将成为铁路中心,重要城市会向各方分射出八九条不等的铁路等等。他的这些设想让世人为之惊叹。实际上,从1865年到1948年的83年间,我国建设铁路总长近2.34万千米,实际通车仅1.2万千米。[12]这与孙中山设想的20万里 (10万千米)相差甚远。难怪有的学者评价道:孙中山在1912年设想的5~10年内通过借款在中国建成可绕地球40圈的铁路计划,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想象。[13]
[1]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下册[G].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宜今室人.皇朝经济文新编:五 [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8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71-79.
[3]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 [G].北京:中华书局,1963.
[4]本部会奏议覆陕西巡抚奏办延长油矿修筑运路暂行缓办折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三日)[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5.
[5]佚名.论外资之得失 [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1.
[6]薛大可.筹铁路刍言 [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2.
[7]张嘉璈.论铁路之统一 [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1.
[8]曾鲲化.中国铁路史 (1924年版)[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9]张嘉璈.论中国难行公债之原因 [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3-4.
[10]薛大可.铁路借款平议 [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3.
[11]张元通.铁路借债政策刍议 [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编·第2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4.
[12]翁有为.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初探 [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7):16-22.
[13]萧功秦.清末 “保路运动”的再反思 [J].战略与管理,1996 (6):1-13.
An Analysis of Two Essays on Railways by Sun Yat-sen and Shi Chang-xin
(by YANG Hong-yun)
Sun Yat-sen and Shi Chang-xin have been labeled as antithesis of each other.They differ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s but also shared some similarities.In terms of the functions of railways,Sun focused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hi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administrative and defense value;in terms of state ownership,Sun emphasize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hi highlighted their role in carrying out unified commands;regarding introducing foreign capital,Sun held a more definite attitude;in terms of scale of construction,Sun was more romantic and Shi was more practical.
Sun Yat-sen;Shi Changxin;texts on railways
K25
A
1009-1513(2011)04-0041-05
2011-08-27
杨红运 (1984—)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朱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