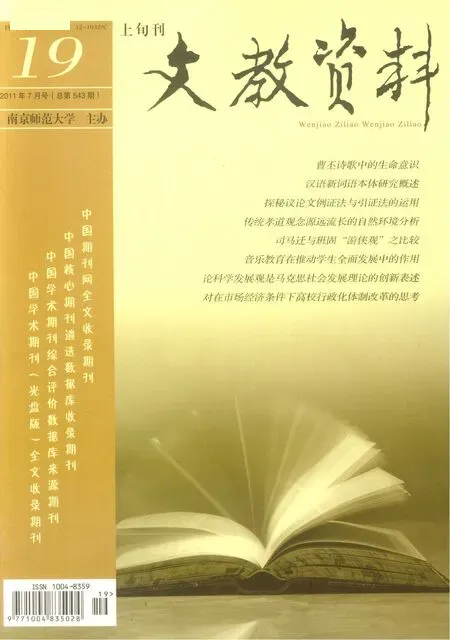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比较
刘秀敏 彭 薇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侠”起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汉,两千年来,悲歌慷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悲剧英雄”。游侠在古代中国一直是遭到排斥的,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伦理纲常的,在法家看来是挑战王权法治的,而在大多数史家看来则是扰乱统治秩序的。然而,司马迁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在《史记》中为游侠单开一篇,勇敢讴歌游侠的侠义精神。东汉史学大家班固也在其《汉书》中为游侠立传,与司马迁的言论针锋相对,认为司马迁是“退处士而进奸雄”①,对游侠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本文仅从游侠传的角度分析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思想主张、评价标准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一、定义不同
《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即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是太史公的经典之作,评论性的文字几乎占据了全篇的三分之一,字里行间慷慨激昂。在他笔下,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不是理想中的顺民或君子,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者所写的,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不为私利、言必行、行必果、扶危济困、舍己为人、坚持正义而不惜个人生命的一种人。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的这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②
而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将信陵、平原、孟尝、春申等战国四公子归为“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继而,又将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借权弄私,败坏社会秩序。
可见,司马迁和班固对“游侠”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强调游侠的侠义慷慨,一个强调游侠的不守法纪。
二、游侠精神内涵和地位认识不同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有名的游侠,其中以朱家、郭解为描述重点,比如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到年长之后“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司马迁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侠义之人。《史记》一书,我觉得太史公对侠义精神的赞扬和追求是贯穿全书始末的。除了《游侠列传》中所提到的几位人物外,司马迁同样也把笔墨和目光投向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而不论这些人是否被“成王败寇”的社会主流所认同。为报知己之恩、出走刺秦王的荆轲,垓下被围、乌江自刎的霸王项羽,等等,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股高于世俗的侠义精神,有独立的人格、坚定的信仰且将这一切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司马迁笔下绝大部分的“游侠”都是失败者,仿佛他们的“失败”见证着更悲怆的执著和坚持——宁为玉碎,他们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完成。因此,司马迁心中的“侠”必定包含着对世俗荣华的不耻与不屑。这是司马迁对游侠的一种膜拜和期盼。
班固则不然。班固在他的《汉书·游侠传》中,开篇就言:“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完完整整地道出了一个正统儒家史官的思想主张——重秩序、重礼法。班固认为自战国游侠之风盛起,“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将游侠视之为封建伦理等级制度的大敌。而班固为《游侠传》所著的楼户的传记,在我看来则全无游侠的豪迈之风,反而风度谦和,“论议常依名节”,一派名士风流。而后所叙陈遵、原涉等人,也不再全然是乡野之士,唯一与前文中人物相仿的,也不过是一句“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这类游侠与司马迁笔下游侠相比较而言,实在是缺乏侠的气概,而更像是市井流氓。
司马迁心目中的游侠精神,到班固笔下全变成残忍好杀、越级犯上的代名词,实在是相去甚远。
三、立传目的不同
《史记·游侠列传》是司马迁表现自己的理想道德、激烈批判统治者的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现实社会太黑暗,忠奸不分、是非莫辨、坏人当道、好人受欺。司马迁在文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在这个告状无门的世道上,除了游侠,还有谁能给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民伸张正义呢?他选取朱家等人作为游侠的代表,正是想以他们“急人所难、舍己为人”这些特点来讽刺和揭露当时汉朝上流社会世态炎凉、卑鄙自私的现象,以及发泄对伪善儒者的不满。司马迁在朱家传中着重写了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称赞他“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在郭解传中称道他的“借交报仇”和“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司马迁歌颂游侠,正是和批判汉代上流社会的道德面貌相表里的。
而与司马迁相反,班固所看重的却是游侠触犯封建法网的一面,他为游侠立传完全是为了维护礼法,向统治者建言警示。他认为游侠的产生,源自社会礼法制度的缺失:周朝礼法完备,所以游侠还未出现;战国时期礼法大乱,游侠阶层便在礼法失序的状况下出现并壮大起来,班固对此非常不满,将四公子全列为“鸡鸣狗盗”之辈;至汉朝,游侠之风大盛,班固依然将此与礼法的破坏联系起来,并疾呼:“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主张必须由明智的君主统治,充分认识到游侠的危害,用礼法制度来加以匡正,从而根除游侠之风。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立游侠传,是为了宣扬游侠的精神,从而达到涤清社会污浊的目的;而班固为游侠立传,则全然是为了禁游侠,让世上不再有游侠。
四、分歧原因
产生以上分歧的原因,和各自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倾向息息相关。司马迁身处汉武帝统治的西汉王朝,连年征伐、苛捐杂税使社会一片凋敝,严刑峻法、酷吏政治更使得民众战战兢兢、苦不堪言。在这样一个人人自保的社会环境里,独立自由、傲然物外、除暴安良的侠客就显得特别可贵和有吸引力。此外,汉初黄老之风盛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③,他的思想是倾向于黄老之道的,也正因为家学渊源,司马迁的思想中仍保留了阴阳、墨、名、法、道等各家的内涵,因此对于“侠”这种非儒非法亦非道的“无党派人士”,他可以做到相对客观地评价。再者,司马迁曾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少年傲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④二十岁的这场漫游影响了司马迁不拘泥于世故的人格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说出这样雄奇之言的人,才有可能会摒弃世俗眼光,为游侠高歌立说。最后,司马迁本身也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受害的一分子,为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和理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游侠对于他而言,是拯救苦难的英雄,也是敢于反抗专制压迫的人格楷模。
再看班固。班固生活在兴盛的明章二帝时期,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西汉末年动乱的时代,应该承认,秩序和等级在当时远远重于自由豪迈的浪漫主义,因此班固不可能在 《游侠传》中鼓励一班不受理法的狂徒到处逍遥任侠,他在《汉书》中流露出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心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至东汉儒学的正统地位已不可撼动,且班固出身儒学世家,班固的父亲班彪撰著《史记后传》时,就表现出了对《史记》游侠和货殖等部分的批判,班固受其父的影响极深,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父亲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和班固,作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在“游侠”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评价,而从“崇侠”到“抑侠”的转变,这其中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站在整体的角度去把握问题,从而对司马迁和班固游侠观的差异有较全面的理解。
注 释:
①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
②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③韩兆琦.史记讲座.广西大学出版社,2008:323.
④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司马迁著.顾长安整理.史记全本(下).北方联合出版传媒,2009.
[2]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五至卷九五).中华书局.
[3]郑权中选讲.史记选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4]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5]张光全.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史学月刊,2003,6.
[6]曹晋.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王立,刘卫英编.中国古代侠义复仇史料萃编.齐鲁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