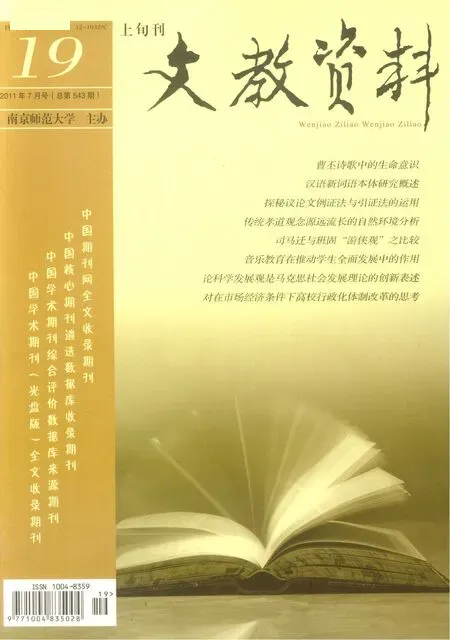曹丕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杨晋亚
(南京师范大学 强化培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生命意识是人对生命本体、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体验,对不同的生命个体而言,这四个字承载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完全一致。生活在三国乱世的曹丕,一生经历丰富,对于生与死的沉思也格外敏感和自觉。对生命意识的书写成为曹丕诗歌中贯穿始终的一大主题。
一、生命价值意识与悲悯情怀
汉魏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年代,东汉王朝经历一百六十多年,已经岌岌可危,天下群雄并起,争夺天下,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相继发生,征战连连,天灾人祸频发,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民不聊生。曹丕生于汉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是曹操次子。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伐,余尝从。”可以说,曹丕对战争的残酷是有亲身体验的。
曹操有许多诗作直接描写战争造成的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惨状,曹丕虽然没有这样直接描写的诗作,但也对战争的艰苦残酷作了揭示。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在随曹操出征黎阳征讨袁谭、袁尚的战役中,曹丕写了《黎阳作》组诗。其中第二首(殷殷其雷)写行军过程中雷雨交加,战车在泥水中颠簸,车夫嗷嗷叫喊,“载仆载僵”,虽然没有曹操诗中的那种阔大深沉之感,但因为是曹丕亲身经历,写得也十分真切可感。另有《黎阳作》第四首(奉辞讨罪遐征)云:“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从侧面反映了战争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令诗》:“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则是直接表现了曹丕对战争的思考,表达了对在战乱中失去生命的下层民众的同情悲悯,反映了他对整个社会的群体生命的珍视。
曾与曹丕并肩作战的将士的死亡也给曹丕造成了心灵冲击。在《陌上桑》中有这样的句子:“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曹丕在此诗中用深沉的笔调展示了战争的艰难,更倾注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将士们“弃故乡,离室宅”,战争持久残酷,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少,死的死,逃的逃,曹丕在行军的过程中无疑与将士们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因此同伴的死去比普通百姓的死亡给他造成的心灵震颤更要深重。曹丕将自己当作了将士中的一分子,一方面为伙伴的死去痛惜,另一方面也不由地想到自己可能会遭受相同的命运而惆怅自怜。
此外,张绣一役长兄曹昂丧命,曹丕死里逃生。在《典论·自叙》中曹丕特别提及了这次战役:“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曹丕年仅十岁便经历如此惊险,更体会到至亲之人的离去,少年时期的这次经历无疑给曹丕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对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有更直接的感受,从而更加认识到生命的可贵与价值。
战争使曹丕对生命的价值有着直接的体认,在对生命本体的肯定中发出了忧生之嗟。生命的脆弱易逝让曹丕在珍视生命的同时认识到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性,所以其诗中也有抒发建功立业的决心的作品。如在《令诗》中承接“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三句发出“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的呼声,表达了匡扶社稷的决心。《艳歌何尝行》云:“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直接抒发了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生命价值的心声。
二、时间意识与感伤主义
强大的汉王朝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历史的盛衰无常、人生的短暂易逝让曹丕深切体会到永恒之不可能。曹丕的游仙诗、游宴诗、抒怀诗都体现了强烈的时间意识。
乱世的氛围和悲剧性的社会现实让文人对生命无常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个人的渺小与阔大的时空、生命的短暂与时间的永恒之间的矛盾唤起了他们内心的悲叹,整个建安诗坛笼上了一层感伤的色彩,曹丕的时间意识也体现在这种对人生易逝的无奈感伤的情绪上。游宴诗《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前三解极力铺叙游宴之欢娱,大宴宾客、狩猎弹琴,可谓快意当前,但第四解由乐转哀,直接抒写“乐极哀情来,廖亮催肝心”。此诗并非以乐景写哀情,而是着眼于前后情感的变化,表现了曹丕作为一个文人的细腻情感,在尽情欢乐的时候也不由地发出沉重的迁逝之悲叹。
曹丕也有几首游仙诗传世。与笃信道教的诗人所写的游仙诗不同的是,曹丕的游仙诗抒写的是对道教所宣扬的人可以长生不死的怀疑。在《折杨柳行》中,前两解写诗人服用仙童所给的药丸,四五天后可以腾云驾雾,倏忽万里。后两解则转为对道教神仙的怀疑,彭祖、老聃、王子乔和赤松子是广为流传的长生不老的仙人,曹丕却认为这些传说是愚夫的妄传,坚定地否认了生命永恒的可能性。魏晋时期道教盛行,有不少人借助宗教的力量缓解迁逝之悲,曹丕否认了神仙,失去了一种宗教情感寄托,他对人生易逝的悲叹也就愈发深沉悲重,诗歌中的感伤情怀也更明显。
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意谓诗人有感于四时变迁万物盛衰而引起文思,文以情生,情因物感。除了游宴诗和游仙诗,曹丕也有一类情因物感的抒怀诗,同样反映了他的迁逝感伤之情。四言乐府诗《丹霞蔽日行》在极短的篇幅内展现了自然界的盛衰与无奈,丹霞彩虹虽灿烂却短暂,谷水木落的行止荣枯不能自主,孤鸟离群的悲剧时有发生不能避免,月有阴晴圆缺,花有开谢枯荣,自然界的物候变迁让曹丕联想到人生苦短,命运难以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荣华富贵也不可能永恒,不由悲从中来,发出“古来有之,嗟我何言”的无奈感叹。
虽然在《大墙上蒿行》和《善哉性》(上山采薇)中,曹丕表露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但是,曹丕并没有单纯地堕入感伤主义和享乐主义之中。《月重轮行》一首云:“三辰垂光,照临四海。焕哉何煌煌!悠悠与天地久长。”反映了曹丕的宇宙哲学沉思和理性的思考:人生短暂、天地和日月星辰永恒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曹丕进一步写道:“愚见目前,圣睹万年。”指出了真正有智慧的哲人圣贤可以眼观古今,其智慧之光可以与天地久长。曹丕不相信道教的成仙之说,但是他相信有一种力量是可以让人达到永恒的。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云:“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可见,文章在曹丕看来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让人获得永恒,这种非宗教的信仰为曹丕的感伤主义找到了一个出口,避免时间易逝的沉重感最终指向虚无,所以,曹丕在肯定人生短暂的同时也肯定了千古流芳的可能性,从而努力实行人生价值,这便与曹丕的生命价值意识联系起来了。
三、个体意识与人的觉醒
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中这样论述汉魏之际士人们的思想变化:“社会的大动乱,数百年来以儒家名教和仁政为旗帜的汉代奴隶主大帝国的悲惨溃灭,引起了社会心理意识的重大变化。这变化集中表现在对儒家的名教和仁政的理想失去了信心,它再也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处处深切地感受和备尝了和儒家许诺的‘仁政’刚好成为鲜明对比的种种痛苦,发出了对人生苦难的慨叹,并且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了一切仁义道德的空谈都是虚假的,只有生离死别,如何求取自身的生存才是真实的。”[1]在动荡的时势面前,人们对自己的生命重新思考和追求,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人们开始发现自我,发现情感、个性和欲望。
人的觉醒也推动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的主体价值意义,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渐渐增多,性格敏感而富有文士气的曹丕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出众的。他的诗作体现了人对爱情、友情、亲情的重新发现与直率表达。
曹丕历来被认为写得最好的诗歌类型是代言体的游子思妇诗,尤以两首七言《燕歌行》为代表。建安时期社会动乱,士人们背井离乡,游子思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思妇诗表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感伤。《燕歌行》两首:“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展诗清歌聊自宽。”直接抒发了妇女的情感欲望,率真自然,体现了从汉代经学中解脱出来的妇女重性情的自然表现。除了写妇女思君外,曹丕也写游子征人思乡思妇,如《杂诗》:“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曹丕也在诗作中表达了夫妇相亲相爱的期待:“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愿为晨风鸟,双飞翔北林。”(《清河作》)“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这一系列诗作表达了游子思妇在孤独中对生命苦乐的抒怀、对爱情的执著、对故乡的思念,展示了丰富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曹丕对人的觉醒的肯定,在这些人性的抒发中蕴含的是人的个体意识的发现。
社会动荡使儒学失去了统治地位,宗教、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宗白华这样评价魏晋时期:“只有这几百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2]生长在这种多元思想相互碰撞时代的曹丕,没有被某一种思想束缚,他的人格是自由的。虽然因为争储事件曹丕留给后人阴险狡诈的印象,但他也有旷达和不拘礼法的一面,通过《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的一件事可窥见一斑:“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建安风骨历来被评为放达通脱,曹丕也不例外,获得了“魏文慕通达”的评价。曹丕除了在诗作中肯定了人的觉醒,体现个体意识外,他自由通脱的个性也是对个体意识的最好诠释。
四、结语
曹丕在诗作中体现着他对社会生命群体的悲悯、对生命主体价值的认可、对人生苦短的感伤、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渴望、对人之觉醒的肯定、对自我人格自我情感的呼唤,他自身经历所体现的那种任情放达的人生态度、浓烈执著的生命热情、自由通脱的精神境界也为其诗作作了最好的注脚。总之,曹丕诗作中浓浓的生命意识展示了他昂然的生命情调和可贵的生命热情,以及对生命和人生的永恒执著。
[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兼与赵沛霖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