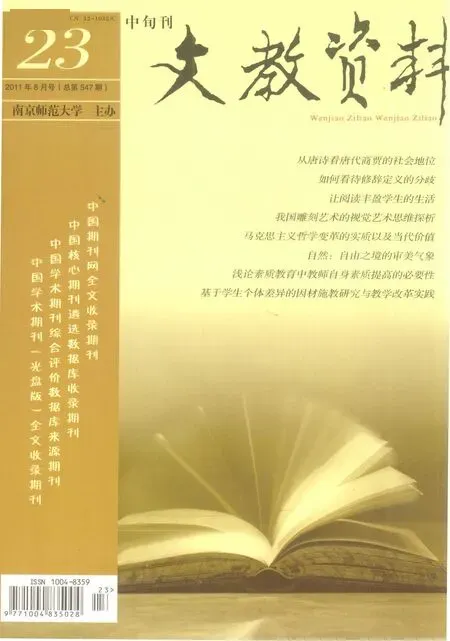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角下歌剧《伤逝》中子君的人物形象分析
雷秀莲
(平顶山学院 师范教育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由王泉、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歌剧《伤逝》,是1981年为纪念鲁迅先生100周年诞辰而作。剧中的两个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受过“五四”新思想洗礼的新青年,他们敢于冲破森严的封建礼教罗网,自由地恋爱,勇敢地同居。但新家庭建立后,子君陶醉于安定、宁静的家庭生活中,渐渐地成为平庸的家庭主妇,而涓生也慢慢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涓生失业后生活出现危机,自私怯懦的涓生失去了与子君携手同行的勇气。从旧家庭冲出来的子君,又被顽固守旧的家庭接回去,最后忧郁而死。他们的爱情悲剧折射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坎坷的人生道路,给人们留下无尽的反思。
一、女性主义与音乐研究
“女性主义在英文中是‘feminisim’一词,起源于法国;法国社会主义者曾用它来表达一种有关妇女运动的新观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女性主义’开始在英美等国家流行,初是用来描述当时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而这一词真正的发扬光大是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年代,自第二次妇女运动的高潮以来,这一词汇被赋予了越来越丰富的含义”。[1]
女性主义渗透到了政治、哲学、历史学、法律、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性主义在音乐界的影响则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算起。“在将近20年后的今日,女性主义已经走入比较平和的阶段。不少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研究对音乐学而言,是添加了一种方法,而不是代替原有的方法”。[2]美国威斯理大学音乐学及女性研究助教,音乐系研究生部主任,美国民族音乐学协理事郑苏在她的 《近十年EML在西方的新发展与女性主义研究》一文中清楚指出:“女性主义:A.要求修正或重写被男性意识歪曲、抹杀的历史;B.重新审视过去文艺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D.女性自性的确定和女性的声音的表达。……”[3]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音乐史教授珍妮·鲍尔斯提到女性主义音乐的价值时说:“在音乐学研究当中,假如把对音乐表演的研究提升到与对音乐作品的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那么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及对女性和女性所关切的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就会立刻变得与这门学科休戚相关。如果除了把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来理解之外,还能用比较多的精力去研究音乐史与社会史的相互关系,那么女性成为研究对象的问题也就变得更为重要了。”[4]
在音乐领域内,女性研究体现在许多方面,如:以女性研究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关于女性的参考书籍,音乐历史研究关于女性的文章,女性音乐家的作品研究,以及男性作品里用以展现女性形象的音乐语言的研究,等等,而且在音乐领域内,女性研究还在持续发展,而且研究方向也在不断扩展。
二、男性主义视角下子君的人物形象
小说《伤逝》自发表以来,学术界就从未中断过对它的研究,其中对子君人物形象的分析,大多都是停留在男性主义视角或是一般社会性的层面上。解读小说《伤逝》,面对“涓生的手记”,我们很容易顺着涓生的角度去审视子君,很自然地首先去赞叹子君的勇敢与坚定,然后随之非议子君的“庸俗”与“怯懦”。然而,涓生对子君的欣赏很大程度上出自男性的本能欲望,以及其人性中对美的本能追求,是从子君为其服务的角度来评价女性的价值,而不是将子君作为和自己等同的完整的人,从精神和灵魂的层面上来追求和欣赏。在涓生面前,子君只不过是一个美丽而弱小的外在的审美客体,爱的本能使他变得迷狂。涓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可是现实中涓生真的读遍了子君的灵魂吗?没有。这只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从本能出发而非出于对人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欣赏产生的爱情结果。E.弗洛姆说:“人们感到对自己的爱人已经一览无余,实际上却毫无所知!如果能够对对方人格有更深的体验,如果能够体会到对方人格的无限性,就不会有这种一览无余的现象,新的奇迹就会天天涌现。”[5]涓生无法走出男权意识的怪圈,对子君的美的评价和欣赏,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本能的欲望及其人性中对美的一种本能的追求。他没有把子君看作和他一样的个体出发,从精神和灵魂的层面来追求和欣赏,而是从被泛化的男性意识出发的,是不真实的。他无法真正了解和他一样作为个体的子君,所以也就不能够真正的爱护子君,以至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能够不离不弃地守在她的身边。当涓生失去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遇到困境时,自私怯懦的涓生的审美视角发生转变,看到忙于家务为家付出一切的子君在他面前是“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严酷的现实使他的审美方式发生了转变。两性间的这种不平等限定了他真正认识和发现子君“美”的可能性,也限制了这平等意义上的交流,“隔膜”成了必然。
由此可以看出,(一)女性成为“他者”,成为男性观看的对象,女性的哀乐悲欢痛苦,被男性定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涓生实际上从来没有了解子君。他后来对子君的抛弃即是对男性定义的所谓“相知的爱情”的反讽。(二)涓生带有浓郁的忧伤、忏悔语调的回忆,塑造了一个忧伤乃至痛不欲生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的痛苦与叹喟,成为抵消他先前对子君所犯罪恶的有效工具。从这一句看,涓生现在“理解”子君,揭去与子君的“隔膜”,就成为男性成熟的表现和标志。这样一来,涓生以前对子君所做的一切“罪恶”,就成为“过错”,成为男性成熟必不可少的代价,是男性人生道路的必然。按照这个解说思路,涓生的罪恶就不成其罪恶,反而涓生以前对子君/女性所犯的“罪恶”,因其是“成长的代价”,男性的“罪恶”和罪恶感被大大地抵消。(三)涓生“诚恳”的“忏悔”,悲伤欲绝的情感,会“迫使”读者同其达成认同,把其与子君一同看成社会/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有效逃脱“罪恶”责任和指责。(四)涓生“诚恳”地揭露自己对子君的伤害,敢于暴露自己的“过错”,并对之进行忏悔,反而造就了一个英雄形象。
三、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歌剧《伤逝》中子君人物形象的意义
“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已经证明,当将性别因素注入分析当中,并以此来分析某一部作品时,我们对该作品的理解就会增加一个新的方面”。[6]人们在分析评价女主人公子君的人物形象时,都会很自然地接受涓生对子君的价值和形象的判断,受到涓生极强的男性霸权主义的影响,这样有碍于读者和观众对子君人物的形象判断,所得到的是失真的子君形象。既然原著是涓生的“手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子君只是涓生,即男性主义视角下的子君,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子君就是不真实的,对她的价值的判断也是站在男性主义的角度判断,所以只有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歌剧《伤逝》中子君的人物形象,才能够拨开涓生男性霸权的迷雾,让失去话语权一直保持沉默的子君站在台前,开口说话,让观众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倾听她的声音,扭转人们对她的人物形象和价值判断,还原一个真实的子君人物形象。
[1]刘霓.西方女性学——起源、内涵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8.
[2][3]郑苏.近十年EML在西方的新发展与女性主义研究.中国音乐,1999,4.
[4][6][美]珍妮·鲍尔斯著.金平译.女性主义的学术成就及其在音乐学中的情况(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季刊),1997,(2).
[5]E.弗洛姆.爱的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2:61.
——《古对今》教学活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