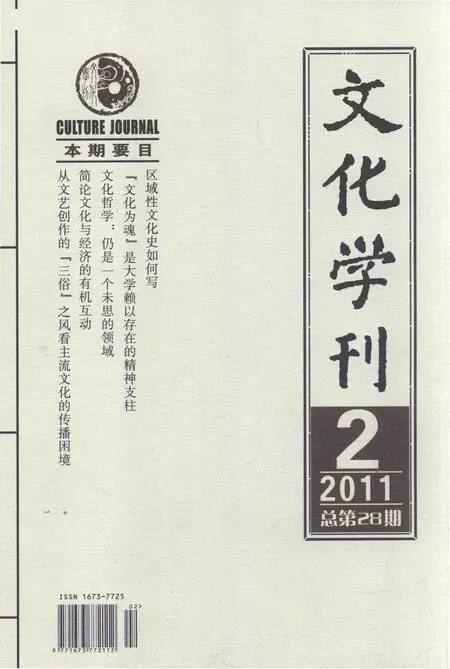白流苏的"破俗"与"随俗"
——从白流苏的心路历程看中国女性的民俗心理
陈超颖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白流苏的"破俗"与"随俗"
——从白流苏的心路历程看中国女性的民俗心理
陈超颖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婚又抢了妹妹的相亲对象,还跑到香港和范柳原“厮混”了一个多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白流苏算是一个勇于“破俗”的大家闺秀。其实,在她的种种“破俗”之举的背后,她有着一颗和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女性一样渴望“随俗”的心——寻求婚姻作为人生的保障。本文试通过解析白流苏为了随俗而破俗的系列举动和心路动机,来分析中国女性的民俗心理及其深层社会根源。
破俗;随俗;民俗心理
在张爱玲塑造的诸多女性人物中,白流苏算幸运的一个。在张爱玲笔下,有多少女人为了得到一张长期饭票,狗苟蝇营,却以悲剧收场。霓喜几次与男人同居,却始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葛薇龙在欲望中挣扎,却沦为男人赚钱的工具,只有她,白流苏,最终修成了正果,将范柳原这个太太小姐们虎视眈眈的猎物收入了婚姻这张网中。在结婚这个事业上,白流苏是成功的,尽管她的成功有着太大的偶然因素。一座城的倾覆就是为了成全她,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天也在帮她了。
白流苏和范柳原交往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这是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她那样身份的女人想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所以,就算范柳原拿“你认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①参见:张爱玲.倾城之恋[A].张爱玲文集[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下文所引该作品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出。这样的话来激她,白流苏也只是当下生气地挂断了电话,第二天仍对范笑脸相迎。这委实无奈。对白流苏来说,婚姻是必需品,是她的人生保障,情感上的保障是次要的,经济上的保障才是根本。这个道理或许白流苏一开始并不懂,否则当初她不会要死要活地离婚,但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却使白流苏更加地需要婚姻,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迫使她明白,结婚才是她的生存之道。
其实,和白公馆里的那两位嫂子相比,白流苏算是那个年代的“前卫”女性。面对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她敢于借助法律的武器离婚;前夫去世,她坚决不当贞洁寡妇前去奔丧……从这些“破俗”的举动可以看出白流苏身上还是流淌着一些新思想的血液的,面对社会对女人的种种野蛮要求,她有自己的倔强脾气。但是,白流苏的“前卫”终究只是表象,她的“破俗”之举充其量也只是在她社会角色允许的行为范围内无伤大雅的小打小闹而已。在她骨子里,她还是那个没落贵族的小姐,寻求婚姻作为自己的终身依靠。在离婚得来的钱被娘家人盘光后,陷入被娘家人百般排挤的境地时,“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丢去了淑女的身份”。盘算再三,她还是觉得“找个人嫁了”才是好的出路。在这个问题上,徐太太一语中的:“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所以,在遇到范柳原之后,白流苏两赴香港甚至最后与范同居的种种“破俗”举动,说到底还是为着一个再俗不过的目的——结婚。
世俗的力量如此强大,白流苏的“破俗”只是她为了随俗而下的一场赌注。破俗是挣扎着的,是内心承受巨大压力,饱受非议的无奈之举,随俗了才能心安理得,扬眉吐气,这就是民俗的控制力。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解析白流苏为了随俗而破俗的系列举动和心理动机,来分析中国女性的民俗心理及其深层社会根源。
一、破俗: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
要分析白流苏的破俗之举,首先要确定白流苏的角色定位。“角色”是指对某一个社会位置或特定身份的人有关的期待行为,民俗角色更具有民俗的规定性。所有的民俗角色在习俗体系中都有既定的行为准则和民俗活动的范围,任何人只要担当了某一种民俗角色,人们就会用习俗为该角色既定的规范对他提出种种要求和期望。一旦他达不到既定规范的要求,他便会遭受到来自习俗的各种程度不等的压力。[1]对白流苏来说,她在民俗世界里扮演两类角色:一是别人的正房太太,二是贵族家庭的小姐。在白流苏内心深处,她渴望安分地扮演好这两个角色,但事实却不允许。前夫娶了她,却打她;没落的家庭给了她贵族小姐的名分,却给不了她与之相应的经济保障,为了生存,她不得不选择破俗。
白流苏的破俗首先体现在她对自己的第一种身份——正房太太头衔的丢弃,她采用了一种在当时看来十分激进的手段——离婚。在《倾城之恋》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后,富家公子娶姨太太还是正常现象,离婚应该还是一件稀罕事,更别提是女方“闹着要离婚”了,所以当初白流苏决绝地提出离婚,就算称不上是惊世骇俗之举,也一定让周遭人跌了一下眼镜。但从“奔丧事件”来看,当时的习俗眼光并不认同法律程序,就像三爷说的,“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就算是白流苏的娘家人,也认为白流苏即使离了婚七八年了,也仍然“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在这样的民俗思维中,白流苏在前夫死后坚决不回去奔丧,可以说是离婚之后的又一次破俗。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流苏曾经的婚姻生活是多么的不幸。流苏三哥的话也透露出流苏曾经的婚姻状况是非常糟糕的:前夫不仅娶了两个姨太太,还把流苏打得不成样子,而这种家庭暴力很可能已经严重到会危害她的人生安全,否则,她不会有勇气顶着巨大压力、如此决绝地想要从前夫太太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如果说白流苏对她第一种民俗角色的丢弃还带有些许主动性,那她对自己第二种身份的挣脱则实属无奈了。白流苏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家里穷虽穷了点,但遗老的架子还是要端着的。这个遗老的架子首先就表现在对家中女子的教育还是采用传统的那一套所谓淑女式教育。三奶奶自诩白家是“诗礼人家”,流苏也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哪儿肯放我们出去交际”,白家的姑娘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守闺阁,等媒人上门说亲。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一开始她按着贵族小姐的规矩,老老实实呆在家中,心中期望她的老母亲能为她作主,再帮她找一户人家。但眼见着家中还有一个未出阁的七妹,三嫂的两个女儿又大了,要说亲也实在轮不上她。再加上身处困窘的经济条件之下,家里的哥哥嫂嫂全部视她为吃闲饭的累赘,毫不客气地侮辱她,骂她晦气,是“天生的扫帚星”。流苏在白家的地位委实尴尬。“奔丧事件”之后,兄嫂当面对她撕破了脸皮,连母亲居然也劝她“倒是回去是正经”。可怜的白流苏成了“一个被宋明理学追杀、被家庭抛弃的孤儿。因为她不是一个思想家,会利用这种孤独去反思人生。她是一个世俗化的人,她要生存,要挣扎”。[2]迫于生存的压力,白流苏这才来了豁出去的勇气,决心放下淑女的矜持,要自己为自己谋划人生了。在她下了这个决心之后,那些“忠孝节义的故事”都变得辽远起来,不与她相关了。
抛开了“忠孝节义”,改变境遇的机会似乎多了一些。这个机会首先就来自范柳原。范柳原本是七妹宝络的相亲对象,但第一次陪宝络去和范柳原相亲,白流苏就抢尽宝络的风头,穿着“白蝉翼纱旗袍”和范柳原没完没了地跳舞,这绝不是“诗礼人家”的小姐该做的事,但谁又能说这不是白流苏的刻意之举呢?在有限的交际圈中,白流苏深知范柳原的宝贵之处,所以就算在白家人眼里,她争取范柳原的每一步举动都是“猪油蒙了心”地“胡闹”,但也顾不得了。跳舞是猎取范柳原的第一步,到后来,白流苏甚至跑到香港和范柳原共处了一个多月,最后却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这在白家人看来简直是“双料的淫恶”,是“耸人听闻的大逆不道”,“杀了她还嫌污了刀”。身处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中,白流苏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她还是顶住压力,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白流苏早已在心里掂量了这场豪赌的后果,“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这场赌局输的代价比较惨重,但赢的结果更是诱人。对当时境遇中的白流苏来说,就算风险再大,她也不得不放手一搏,因为除此之外,事实上她已经无路可走。
二、随俗:为了生存得心安理得
白流苏的举动在表面看起来是破俗的,但她却有着一颗和那个年代的任何女人一样世俗的心。她先后冲破了两种身份的桎梏,却又一心想回到这两种身份中去。对她而言,只有活在这两种身份的外衣下,才能过上既保证经济安全又有尊严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她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即习俗化的过程中所养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标准。
习俗化是指任何个体从他所出生的环境中开始对习俗惯制的适应过程,也是群体对他们的成员个体施以习俗惯制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在习俗体系中学习并增长习俗知识、培养习俗意识和能力的过程。而个体只能和他所处的社会类别、社会分层的阶层、阶级的特定日常生活环节相互关联。[3]白流苏是一个遗老的女儿,这规定了她的身份是社会中上阶层的贵族小姐。她从小在白公馆长大,而白公馆是“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成长在这样一个因循守旧、时时处处照老规矩办事的环境,可想而知白流苏所受的必定是老一派的淑女式教育。
在外人看来,她跑到香港和范“厮混”,不是一个贵族小姐应有的举动,只有范知道,白流苏是怎么端着自己的小姐架子的。在未达目的之前,白流苏在范柳原面前永远故作矜持,她和他调情也永远只在某种范围之内,甚至连范柳原帮她拍蚊子都会突然把她得罪了,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女模样。因为白流苏深谙一个道理: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结婚的希望很少。她的目的是结婚,在这之前,她必须保留好自己的资本,而她唯一的资本就是她的身体。白流苏对自己的身体是有自信的,正是基于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和自信,白流苏才敢于和宝络作这场争夺,也正是基于对这场赌博风险的意识和对于自己资本的珍视,白流苏在和范柳原的交往过程中难免表现得生硬。范柳原一直想让白流苏回归自然,因为他觉得她总是不大自然。从英国回来、又在女人堆里游戏惯了范柳原不会明白,白流苏这么没名没分地和他“厮混”,怎么可能自然呢?
白流苏可以不理会白家人对她的百般讥讽,因为对家人她有一股怨气,想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但她对于周遭的陌生人,却潇洒不起来。在和范柳原的交往过程中,白流苏始终非常在意周围人的眼光。无论如何,她总算出身望族,再不济,在场面上她还想要顾着家族的声誉和她自己的名声。在香港路遇被英国老头包养的萨黑荑尼,白流苏看到范柳原当面对她百般奉承,称她公主,背后却把她贬得一文不值,就担心范也会这样贬损她;旅馆的仆欧与和她搭讪的老太太们喊她“范太太”,窘得流苏脸都僵了。可见,在白流苏的内心深处,她仍以一个淑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举止言行,对于自己的“破俗”,连她自己都深感尴尬。
出于经济上的压力,在和范柳原的这场博弈中,流苏首先妥协了,因为“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可是在经济上安全之后,白流苏的内心仍是不安全的,甚至是痛苦的。她始终相信“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算范柳原给了她一座洋房,她仍是“满心的不得意”。在成为范柳原的情妇后,白流苏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觉得要“躲着人”,想到自己可能会走上自己所不齿的姨太太们抽大烟、姘戏子的腐烂生活,她更是气得发抖。因为这绝对是她的教养所不允许的。只有在成为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子后,她才会“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表现出真正女主人的神态。
三、白流苏们的民俗心理及其社会根源
在白流苏心里,婚姻的名分无疑比爱情的实质来得重要,婚姻能不能带来情感的满足是次要的,能带来经济上的保障才是主要的。她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女性普遍的婚姻观。女人最终的归属就是婚姻,而结婚就是寻找一张长期饭票。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像白流苏这样把结婚当作事业的“女结婚员”有很多。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赋予女性的必然选择。
白流苏们总是把婚姻当做生命的全部,因为她们确实没有其他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技能。就像白流苏说的,“她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传统社会对女子的教养,全是把她们往贤妻良母的路上领,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所以,婚姻对她们来说就像一份工作,喜不喜欢是另一层面的问题,首要问题是解决生计。更重要的是,只有走进婚姻的大门,成为“某太太”,她们才能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才能被周围的人认可。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所担的最大风险就是和范柳原同居了,但范却不娶她,那她就只能往姨太太的路上走,也就意味着和主流社会告别了,这是白流苏万万不愿意的,也是她的身份不能逾越的底线。所以说,她的破俗终究只是无奈的一种手段,归根结底,她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俗”人。
白流苏们的这种民俗心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透过白流苏的两个民俗角色(贵族家庭的小姐和别人的正房太太)的表象看实质,可以发现,在这两个角色中,女性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贵族小姐是父权的附属,而正房太太是夫权的附属,女性在出阁前后的两个人生阶段,都不得依附于男性。“在中国宗法体制下,女性丧失主体/自我的现象在文化承传上有其传统性别规范的背景。《易经》的阴阳观,经过《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等经书典籍的传播转化,已把阳尊阴卑和男阳女阴的观念发展得更为成熟圆满。”《礼记》中有一段论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这段话表明了传统父权社会对女人的定位:女人生来就是依附于人的。这种思想在传统社会根深蒂固,不仅深深扎根于男人们的头脑中,在女人从小到大的民俗化过程中,也一直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至于久而久之,女人们自身也形成了一种依赖型人格,把男人当成自己生活的重心。如果没有走进婚姻的大门,没有得到父权的替代品——夫权的依靠,女人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了。
除了思想上的教化,“张爱玲笔下的大部分女性人物,就如现实的写照一般,都受到宗法父权的经济封锁,从而阻止女性人格的独立。《礼记·内则》有明文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清楚规范了女性在钱财经济方面的权利。男性家长在此统摄家政财产的权利,禁止女性越权”。[4]女性在经济方面的权利被彻底剥削,无疑给女性的身体和心理都带上了无形的枷锁,使女性除了依附于男性以外别无选择。这也就不难理解流苏离婚后为何在娘家处处受气却离不开娘家,因为她离婚得来的钱都被她在娘家的男性家长——她的哥哥控制了;也就不难理解范柳原一纸电报,流苏就千里迢迢从上海跑到香港的无奈和辛酸了。经济上的窘境造成了女性人格上的窘境,而夫权父权社会的现实使得女性无法挣脱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困境,这正是造成传统女性民俗心理的深层社会根源。
[1]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3]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482.
[4]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王 妍】
I247
A
1673-7725(2011)02-0107-05
2011-01-12
陈超颖(1982-),女,浙江瑞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