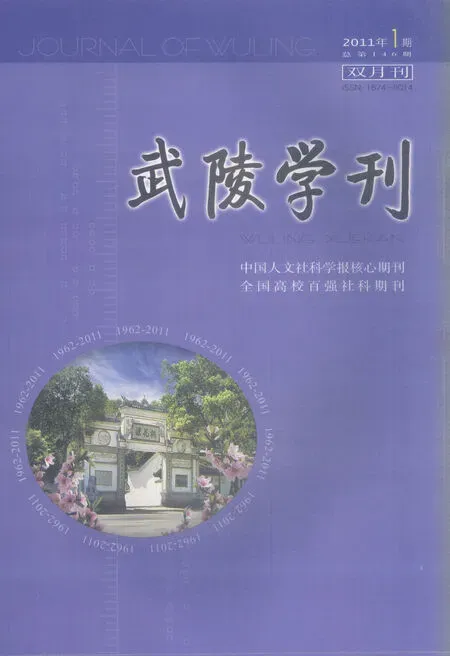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在跌宕中发展
徐超富,詹淑兰,张曙光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在跌宕中发展
徐超富,詹淑兰,张曙光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中国,大学学术自由之风由来已久,上至春秋战国,下至当代,但其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是在曲折中前进,跌宕中发展。不同时期学术自由繁盛与寂寞的原因是由多个因素产生的合力促成的,尤其与政治的开明与否和文化的发达状况密切相关。
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发展
在中国,大学是一个舶来品,只有百余年历史,但中国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却古已有之。高等教育机构是指某一历史时期传播高深知识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由于古代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如稷下学宫、太学、太子学、总明观和国子监等的功能相当于今天之大学,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将这些机构纳入到大学的范畴,这样,讨论大学的学术自由问题,也就不仅局限于近现代大学,而把视线推向了历史的远处。从大学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尽管存在着诸多专制统治的灰色阴暗期,但也有大学学术自由的亮点闪现。
一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百家论争和学术自由高度繁荣与发达时期,出现了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诸子“百家”。后来的许多学说、学术、学问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渊源。而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术自由中心——稷下学宫,也是由战国时的齐国创立的。那时各诸侯国为了称雄争霸,都十分注意人才的任用与培养,齐国当时属强国,对人才的渴求更甚。“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才而争宠之”(徐干《中论·亡国》)。而为了网络人才和发展学术,统治者还令学者“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因此在齐宣王时,稷下学宫已经发展为有着数千人的高等教育机构,学宫之中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氛围洋溢于学宫。稷下学宫的学术自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多种学派名家、大家荟萃。聚集了如孟子、荀子、邹衍、田骈和鲁仲连等学者。这种“百家”之聚会,必然导致不同学说之间的论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的直接交锋。就当时情况来看,各学派之间的论证是完全处于一种平等对话和自由争辩之中的。二是各家自由招收弟子授徒,还可进行串讲串学,如打破师门听课。三是诸子百家学者来去自由。孟子曾2次往返于稷下学宫,荀子达3次之多。四是各个学派著述成果丰硕。如《管子》一书便是在原管仲言论的基础上由稷下先生们集体写成的。在稷下学宫中,各种学说相互斗争与融合,学术自由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地同域,废私学,“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学术界万马齐喑。在秦朝,官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没有,只有一些私学在专制的统治下飘摇。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思想严重地受到禁锢,大学的学术自由无从谈起。因此,可以说大学的学术自由在秦代遭受了灭顶之灾。
及至汉代,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实行文化专制,无百家学术之言,不过,儒家内部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争论,时常发生在太学、太学博士及其弟子之间的古今文之争即是大学学术自由的最佳体现。自从西汉末年发现古文经后,儒家内部便出现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激烈争论,即汉代的所谓“古今文之争”[1]。在太学中,皇帝还亲自领导朝廷官员、太常、太学博士以及诸儒与诸生参与石渠阁论定《五经》和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学术会议。东汉光武帝曾别出心裁地召开过一种学术会议,即通过自由问难答辩排名,结果有一位名叫戴凭的经学全能选手共夺了50多人的座位,即排名向前移了50多位。这些具有一定学术自由性质的论辩活动,既大大地丰富了教师与学生的学术视野,又不断推出了新的学术成果,还开创了太学的学术自由新局面。可见,汉代太学里的学术争鸣并没有因为“独尊”而中断,因为“专制”而消失,而且东汉末年因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相继执政造成的太学的时兴时废也并未让学术自由戛然而止。两次党锢之祸虽然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迫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知识分子有了议论政治的愿望与举动,才让当权者感到恐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及其威慑力。另外,太学学术自由的繁荣,也导致学者著述的丰收,如曾任太学博士的贾谊、董仲舒等就留下了《新书》和《春秋繁露》等著作。因此,学术自由在太学是有所表现的。
魏晋南北朝处于乱世之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都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正因为乱世,它又为文化多元创设了条件,提供了土壤。在不同的时期,统治者对于教育的重视度也不同。在这个时期,最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太学和国子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南朝宋时开设的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馆(具有高等专科性质),公元470年分设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学科的总明观(一般认为这是我国较早的专门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学和国子学大都是统治者用以调和贵族和寒门的矛盾的一种手段,然而尽管恰逢乱世,该时期的大学学术自由也有表现。第一,这一时期太学中出现了儒学与玄学、道教与佛教即二学二教相互碰撞、相互斗争和相互融会的局面,证明这是一个有争鸣、有自由、有成果、有发展的时期。第二,有的统治者重视大学学术发展,如文帝后的明帝、齐王芳奉行尊儒的政策,时有临幸太学、祭祀孔丘。而魏文帝曹丕曾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八百余万字,号曰“皇览”。第三,到了北朝时,除了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皇宗学、太学等等学校外,还有与南朝一样的专门学校,如律学、算学和书学。这说明北朝高等教育既有人文学科也有自然学科,学科的多样化自然也是大学学术自由的一大体现。第四,魏晋南北朝大学中,经学的学习博采众家之长,学习风气良好。“《北史·儒林传序》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然而,不论南朝还是北朝,都盛行博涉的学风。”[2]“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魏晋人注的占了一半。他们注释经书的特点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其成就超过了汉朝经师,其中尤以何晏注的《论语》和王弼注的《周易》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最大。”[3]在这一时期,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学术领域及机构也得到了拓宽和扩展,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大学学术自由之状况:自由化、多元化和组织化。
从隋唐到清朝以来,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施行,大学学术自由受到了科举之限,广大士层人士难以自由地施展拳脚。但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在不同的朝代仍旧各有其表现。
作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与“一治”之唐朝相比较,“一乱”之隋朝的高等教育几乎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更别提大学的学术自由了。但实际上,隋朝的统治者也很重视教育,科举制的兴盛和国子监设国子祭酒“统知学事”便是其体现。而隋文帝在广建佛寺的同时“诏天下劝学行礼”,隋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省,相次讲论”也是其体现。随着统治者的重视,各种教育机构也迅速从废墟中崛起,大学的学术自由之苗依然在悄悄生长着。然而,由于隋朝统治的时间不长,高等教育时兴时废,隋朝的大学学术自由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一度实行“开明专制”,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儒、释、道)并行政策,致使文化多元发展,学术自由可谓相当繁荣,太学之学术也表现出相当的自由空间,如选修制即是明证。唐朝大学的学术自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它的中央官学中,除了经学、玄学、史学以及文学艺术外,自然科学也更多地纳入到学术视野之中,如算学、天文学、医学等。即学术内容拓展了,学术范围拓宽了,学术的视野扩大了。此时的大学学术内容与魏晋南北朝相比更加完善,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国际化。盛唐时期,大学以海纳百川之势融会外域文化,接受外国留学生,如日本、朝鲜等多次派学生来大唐留学,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和进行学术探讨。此外,从唐诗的繁盛及其风格的多样来看,我们也似乎感受到了唐朝大学学术的无羁无绊,唐朝大学学风的酣畅淋漓,唐朝大学学术的博大胸怀。
在宋朝,当时形成的程朱理学,既有别于汉朝的神学目的论及考据训诂派儒学,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化儒学以及隋唐的章句注疏派儒学;既不同于先秦儒家注重现实人事之说,也有别于汉唐儒家以能祸福人的天意为伦理渊源之说[3],它是以宇宙论和人性论视角探求本源,面向人事和社会实际,启迪人们形成做人、为事、治学之约规。这种“义理”之儒学,既是儒学的发展,又是儒学的创新。而作为学问、学术的最佳传播地,当时的国子学、太学或书院中,程朱理学的诞生,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学术集群。如对立面王安石的“新学”和陆王的心学,内部亦先后出现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派、以二程为代表的洛派、以张载为代表的关派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派四大派系。面对如此众多的学派,既有对立面的学术批判和论争,又有内部学术的分支发芽和互相争鸣。生活在这样一个学术环境里,每一个学术流派想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它必定要融入到这种火热的学术争辩、争鸣和批判的学术自由中去。像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论争就曾在学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宋代,起源于唐末五代的书院的兴盛以及自由讲学的盛行,给当时大学学术自由带来了一丝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之所以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其教育教学的自由自主性。”[4]宋朝书院不迷恋和追求功名利禄,而以研究经学、专事自由讲学和自由研究学问为己任,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尽管书院曾四度被废,但它开创的“讲会”形式以及学生自由选课的教学计划,为这一时期的大学学术自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这既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大学学术自由,更在内涵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大学学术自由的精神。
元朝时,统治者采取“汉法”的统治,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因此,这个朝代继承了宋朝的许多政策,自然包括教育方面的制度。元朝在中央建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在国子学中还采用了宋朝胡瑗创立的分斋教学。而兴盛于宋朝的书院在元朝也有了新的发展,元世祖时提倡建立书院,“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史·选举志》)。“南宋灭亡后,一些南宋遗留下来的程朱理学派的理学家,也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开办私学从事于讲学活动”[5],代表人物有许衡、金履祥、许谦、吴澄等。他们在传播程朱理学的同时还专心著述,如许衡在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领导太史院时奉诏修定《授时历》,许衡在参与教学的同时还著有《鲁斋遗书》。虽然处于文化较为落后的蒙古民族的统治下,但是大学学术自由依然隐约可见。
明清之时,“八股文”、文字狱等举措严重地钳制和伤害了学术自由。朱元璋在读《孟子》时,发现了诸如“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对君不恭的地方,便下令国子监撤去孟子牌位,把孟子赶出孔庙,制造了所谓“孟子冤案”;康雍时期出现了庄廷龙《明史稿》、戴名世《南山集》和吕留良《文选》等案;乾隆时期出现了长达19年之久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多块)[1];宋以来理学的强势地位也严重损害了大学学术自由。外界的强力高压政策如文字狱、镇压太学生运动、摧毁书院等使得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习惯性地内化为了一种过于拘谨的自律,这种自律严重地制约了学术自由的主动性和学术发展空间。
从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来看,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在朝代的更替中时而如夏花般繁盛时而如秋叶般寂寞。而这繁盛、这寂寞不可能是某个单一的原因能够解释的,它们是由很多因素产生的合力促使而成的。比如说春秋战国、汉代和唐朝,大学学术自由非常地繁盛,这与当时的政治开明统治和文化发达程度分不开。从政治上来看,当社会处于动荡时期或者转型期,大学学术自由就有发展的可能。如春秋战国时,长期的混战和争霸使得社会动荡不安,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开始向封建制社会转型,处于乱世之中的稷下学宫,就让大学学术自由的思想在封建统治的缝隙中恣意生长。秦亡后的汉朝,吸取了秦亡的经验教训,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令汉朝的学术自由有着发展的机会。毋庸置疑的是,统治者开明的统治以及一系列重视学术的政策的颁布也是大学学术自由思想得以发展的有力保证。如汉朝时,武帝在太学中设五经博士,皇帝领导的经学会议、学术活动以及在当时逐渐形成的一套从封建王朝中央政府到高等学校的比较完备的政策和制度,都对学术自由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一度实行“开明专制”,经学、玄学、文化艺术、医学、算学和天文学均高度发达,各种思想既斗争又融合,大学学术自由极度繁盛。从文化上来说,学问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不管是哪一种学问,蕴含于其中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这必然会导致思想的多元化、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和学科的丰富化,学术自由的繁盛自然也是这些争辩的自然结果。如春秋战国时大学中充斥着儒、道、法、墨等多种思想,教学内容也非常丰富,到了秦汉的儒学独尊,继而魏晋的儒玄、道佛二学二教的碰撞交织,再到唐代的经、玄、史、文、算、医等学科的多样,学术自由也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学科的变化中发展,大学学术自由日益彰显。
相比而言,秦朝、隋朝和明清时期的大学学术自由则显得非常之寂寞。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虽每个朝代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来说,主要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所致。政治上,封建王朝政治一统,刑罚极重。自秦始皇以来,封建专制统治横行,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统治者所制定的政策和国家的管理机构也总是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发展不利,政治上的一统也波及到了学术范畴,学术争鸣自是被限制。如秦朝,在政治上崇尚法家思想,因此,才会有教育上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而极度的刑罚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党锢之祸和明清的文字狱等,也让大学学术自由难以生存,更无从谈及发展。在高压政策下,知识分子谨言慎行,瞻前顾后,学术自由的小苗才露尖尖角便惨遭折断,纵是学者大家如云,学术自由也举步维艰。文化上,由于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的政策,致使大学学术自由没有发展的机会。汉代以来文化主流是独尊儒术,既是独尊儒术,那么别的思想流派定是难以在儒学大流中立足。“清初统治者在振兴文教的同时,在文化上采取了严厉的专制政策,特别是康、雍、乾二朝,文纲迭兴,迫使一些文人学者逃避现实,在旧典籍中重寻故路,走向朴实的考据之学。”[6]如此,又何谈学术自由?大学学术自由的寂寞也就在所难免。
二
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始于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这种始于不是简单的始于,不是模糊的始于,不是渐进的始于,而且是清晰可见的始于,单刀直入式的始于,具有完整性和整体性的始于,总之,它是闪亮登场的始于。蔡元培曾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大学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学术自由思想的办学理念。他说:“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借鉴德国大学模式,组建评议会,建立学科教授会,开我国现代大学“教授治校”之先河。在这种完全清新和充满自由的空气里,汇聚着怪异奇才和思想迥异的学者,开展着学术研究,进行着学术争鸣。不过,在中国现代史上,除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和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可以大书特书一笔外,学术自由的亮点并不多。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争鸣,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展开了自由的、针锋相对的论争和大讨论。可以说,当时许多顶尖学人都参与其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使这一场论争高潮迭起。这也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良好的学术自由氛围。当人们谈到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教授时,冯友兰曾感慨道:“……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7]
大学的使命就是既要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又要扩展学生心智、完善学生人格和修养学生人性。按照卢梭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以及康德纯粹理性是自由的源泉的观点,那么,凡是探求真理和有利于人性完善的一切手段也应该是自由的,因为目的的自由性决定了手段的自由性。而操持在人手中的学术就是通向真理和达至人性之完满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学术它必定是自由的,即学术自由。所以,北大、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上获得如此成就,正是在学术自由精神之光普照下发生光合作用的结果。
但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真正春天,还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持续到今天。可以说,当今中国学术自由是日新月异,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法律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学术自由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我国最早提议将学术自由保护条款纳入宪法的是张君劢。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上,由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案》第九十一条规定:“学术上之研究为人民之自由权,国家宜加以保护,不给限制之。”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此条款始终未能正式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的《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1975年的《宪法》在这一点上又倒退了。1978年的《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科学研究自由保护的条款。1982年的《宪法》对一般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作了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规定,教师有“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学成才,当遵守法律。”第36条又规定:“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
除了法律上的建设与保障外,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探索中,大学自身的地位及内部管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学术自由的生长和发展亦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主要有如下几方面作了调整和改进:第一,我国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学从政府系统中独立出来,不再是政府的一个管理机构,不再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已经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刚开始的这种法人实体,即大学自治的象征意义要多于实际的意义,但时至今日,人们再也不否认其实际意义了。第二,大学领导机制的调整。过去,大学是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现在,大学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变化,实际上就把大学的若干权力作了调整,权力结构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在变化中,学术自由的权利显现了出来,受到了重视,并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第三,大学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大学为此成立了各种委员会,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如学术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和福利委员会。第四,以大学牵头成立了各种专业学会。目前,这种学会形成了省级和国家级两级模式,当然也有区域性的大学协会,大学教师都可以参加相应的学会。学会一般一年举行一次年会,同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本专业的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第五,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放的广度、深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和深化,许多大学都与国外大学建立了联系,开展合作研究,进行学术交流。现在大学里,既有国际性的学术论坛,也有区域性的论坛;既有协作大学联合论坛,又有一对一的学术交流。面对地球村的时代,在全面深化开放的时期,大学国际性的学术活动既频繁又多样,既活跃又丰富,而且这种势头正处在强劲之时。目前建立的各种合作模式和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学术交流机制也为此在高速运转。这些都为学术自由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4]张传燧.古代书院传统及其现代大学借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1):79-83.
[5]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江凌.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78-83.
[7]韩延明.大学理念论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AcademicFreedomofChineseUniversity:DevelopmentintheUpsandDowns
XUChao-fu,ZHANshu-lan,ZHZANGShu-gua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In China,universities have been enjoying academic freedom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nowadays.However,academic freedom in universitie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circuitous instead of smooth development.The ups and downs of academic freedom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related to many different factors,especially liberty of politics and level of civilization.
China;university;academic freedom;development
2010-12-08
湖南省科技厅科学研究项目“大学教育的知识选择、传授与教育质量生成研究”(06FJ4130);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湘文化中教育资源开发研究”(10C0950)。
徐超富(1963-),男,湖南澧县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G529
A
1674-9014(2011)01-0127-05
田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