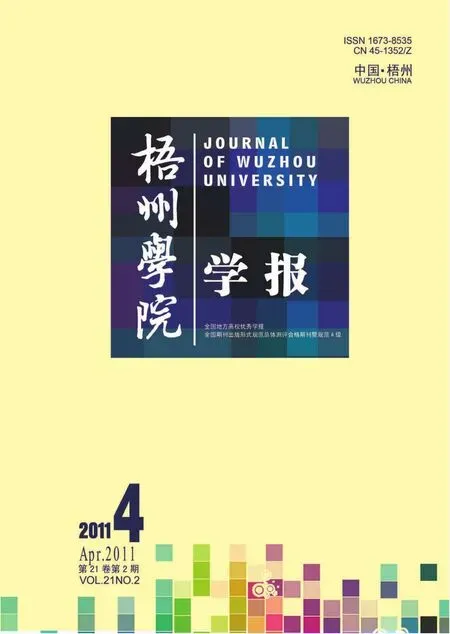审视,然后突围——“我们”散文诗群的引领者之一林美茂访谈录
林美茂,钟世华
(1.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10000;
2.梧州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西 梧州 543002)
审视,然后突围
——“我们”散文诗群的引领者之一林美茂访谈录
林美茂1,钟世华2
(1.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10000;
2.梧州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西 梧州 543002)
近年来,一个由散文诗作者组成的散文诗群体 “我们”在北京诞生,立刻引起了文坛,特别是诗坛的普遍关注。那么,关于这个群体的诞生背景,他们的散文诗的美学理念,他们所提倡 “大诗歌”创作的意义,散文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的当下性与未来性,以及实现美学突围和作为一场文学运动的理由,等等,本次访谈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展开的。通过访谈,得到了许多具有说服力且富有前瞻性的回答。现在的散文诗探索实践,将意味着可能酝酿成一场历史性的文体探索性与独立性的美学运动。
我们;散文诗;大诗歌;意义化写作;突围
访谈背景:2009年3月14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由散文诗作者组成的散文诗探索群体 “我们”在北京的元大都古城墙遗址 “北土城”附近成立,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包括 《诗刊》在内的全国多家诗歌杂志接连刊出了由 “我们”编选的散文诗作品,从而在当下诗坛,引起了不小的积极反响。为此,近年来关注当代散文诗发展的本学报的钟世华编辑,专门针对与 “我们”的诞生以及当代散文诗坛存在的一些问题,对 “我们”进行了一次访谈,参加访谈的作者有周庆荣、林美茂 (灵焚)、亚楠、章文哲、李仕淦共5个人。由于本访谈所设计的访谈内容,涉及到散文诗的历史与现在,以及文体特征等诸多重要问题,属于一次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访谈,在此我们把“我们”的引领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当代代表性散文诗人林美茂的观点,整理成一篇相对完整的访谈文章,多角度地了解与把握灵焚对于新时期散文诗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应该具备的美学理念、艺术追求、文体自觉等问题的思考。我们相信这些观点,对于促进我国新时期的散文诗的创作与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意义和创作指导意义。
问:“我们”散文诗群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它的意义与价值有哪些?
答: 散文诗最初在中国的诞生,只是一种属于朦胧的自觉写作,并不是一种很明确的文体追求。而到了鲁迅的 《野草》,更是他把自己所谓的“小感触”,权且称之为 “散文诗”,其中的创作散文诗自觉就显得更为模糊。然而,在这种状态写成的 《野草》,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诗作品的一座里程碑。九十多年来,凡是谈到散文诗除了 《野草》之外,似乎就再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了。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段颂歌年代,虽然有像柯蓝、郭风这样颇具影响的作家从事散文诗创作实践和散文诗创作倡导,然而,他们的作品对于散文诗的文本建树甚微。当然,不可否认,正由于这些前辈们的文体坚持,催生了三位极其重要的作者:耿林莽、李耕、许淇,以及两位散文诗发表阵地的拓荒者:邹岳汉、海梦,从而带来了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散文诗创作的 “繁荣”,散文诗作者与读者群也日益壮大,由邹岳汉创办的 《散文诗》和海梦创办的 《散文诗世界》两种专门刊登散文诗的杂志,其发行量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类诗歌杂志。
按理说,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这是值得散文诗作者们欣慰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些成果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其中的绝大多数散文诗作品,仍然停留在横的相互复制与纵的表现手法的移植模仿之上,称得上探索性的作品很少。所以,散文诗在中国除了那些写散文诗的作者之外,主流文学中散文诗的话语权基本缺失,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散文诗长期以来不被有美学高度的作者、以及高明的读者所接受。在分行新诗中早也没有人再提到胡适的 《尝试集》、郭沫若的 《女神》了,而散文诗却仍然停留在 《野草》的辉煌与阴影里说话,以此确认自身的存在。从分行新诗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各地诗群辈出,各种探索层出不穷,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创作成就。正是因为那些大胆而前卫的探索者对于传统的破坏与重建,使中国的分行新诗创作引领着时代的审美走向,甚至一次又一次引领着社会思潮,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散文诗呢?90多年来就连一个由散文诗作者组成的探索群体都没有出现过,更谈不上什么群体纷呈的美学探索实践了。
“我们”散文诗群的诞生,首先是要打破这样一种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局面,希望以此为契机能够引爆一场当代散文诗艺术的探索、发展的美学实践运动。所以, “我们”大胆地让散文诗走出散文诗的小圈子,向当代文学的左邻右舍虚心学习,并吸纳一些新生的散文诗创作的探索性力量,推动散文诗艺术走向真正的繁荣,而不是满足于表面上人数增加的所谓 “繁荣”。我们更希望通过 “我们”群体的出现,让那些至今为止还安于现状的散文诗作者们也能根据自己的各自美学倾向、审美理想,结成一些与 “我们”一样的探索群体,各自都以群体的力量,探索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促进散文诗坛的多元美学倾向共存时代的到来。
以上是从散文诗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简单勾勒来谈 “我们”诞生的背景,而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诞生不可或缺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对于散文诗这种体裁自身的认识,促成了我们组织群体探索的决心。从散文诗自身的审美可能性来看,它是一个可以兼容所有文学体裁的表现手法于一身的最自由的诗歌表现形式,它如一面检验诗人才华的镜子,让诗人们通过散文诗创作反照自身,认识自身作为诗人发展的可能性。通过 “我们”,可以吸纳一些具有挑战精神的诗歌作者参与散文诗创作实践,克服他们至今为止对于散文诗认识的偏颇,走出长期以来狭隘的诗歌观念,从更为广泛意义上认识现代汉诗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让散文诗这只山中的百兽之王回归到文学自然界,不再只是一种圈养在家中的小宠物。
至于 “我们”散文诗诞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不是 “我们”自己可以评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它是一个历史问题,应该是未来文学史谈论的话题。
问: “我们”诞生至今将近两年,它对现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有哪些推动作用?
答: “我们”最初是由五个人讨论、组织、酝酿的,最终在北京的其他十几位诗人热烈响应之下,于2009年3月14日的一次在京诗人们的“北土城”聚会中诞生的。
这两年多来, “我们”进行过几次重要的散文诗作品的展示。2009年4月17日,在周庆荣的搜狐博客“北京老风”上公布了“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态度”一文,算是 “我们”散文诗群的正式挂牌。同年6月在 《诗潮》上第一次推出 “我们”散文诗群的作品,7月在 《诗选刊》、9月在 《中国诗人》、12月在 《新世纪文学选刊》等杂志上,连续推出了 “我们”成员的作品大展。而从2010年开始,分别在 《青年文学》 (上半月)、 《诗刊》 (下半月)上开辟了 “我们散文诗档案”和 “散文诗”专栏, 《诗林》也在2010年6月号上专门推出了 “我们六人行”, 《黄河诗报》在12月份推出的 《中国当代诗群回顾与年度大展》中,也把 “我们”与其他诗群一起收入大展的作品之列,推出了18位 “我们”散文诗群作者的作品,等等。由 “我们”编选的散文诗作品两年多来陆续与作者和广大诗歌读者见面,不仅仅在散文诗界,在当代诗坛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两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包括海外的作者160多名作者纷纷来信来稿,希望加入 “我们”。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底, “我们”与吉狄马加、王久辛、高兴、树才、楚天舒、潇潇等引领的 “中国诗人俱乐部”合作,编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分行新诗和散文诗合集 《大诗歌》一书,该书在2010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当代诗歌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因此也促成了一些原来只写分行新诗的作者开始尝试散文诗创作。
“我们”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我们”的崛起,让长期以来安于现状的当代散文诗坛,不再固步自封,开始产生危机感。比如,有些原来一直觉得自己还写得不错的散文诗作者,当他们看到 “我们”推出的一些作品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寻求突破的路径,出现了一些自觉探索性的追求。而一些原来看不起散文诗的新诗作者,通过 “我们”推出的作品,也看到了散文诗的艺术可能性,开始尝试散文诗写作,从而发现其实散文诗并不是自己原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很好写的体裁。相反地,感到散文诗比分行新诗更难以驾驭,并认识到要写好散文诗,必须要有坚实的思想、艺术的积累,也因此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探索的路径。甚至有一些作者因此发现,其实散文诗才更为适合自己的诗歌表现形式,只有在散文诗中,自己才能找到展现自己创作潜力的巨大可能性。就这样,由原来认为散文诗只是亚文学,转变为意识到散文诗是一种更为立体的诗歌文学,一时间, “我也写散文诗”成为许多诗歌作者在聚会时谈论最多的共同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 “我们”的出现,让当代诗歌界逐渐认识到,长期以来现代汉诗的发展是有缺陷的,忽视散文诗这种诗歌体裁,对于现代汉诗的建设是不完整的,现代汉诗应该包括分行新诗和不分行散文诗,按照邹岳汉的观点,它们是新诗的左右两翼。可是,长期以来,现代汉诗只是拖着一边翅膀在飞翔,这样失衡的飞翔,其所能抵达的路途距离是有限的。那么, “我们”的出现,并通过 “我们”推介的散文诗作品,已经初步让一部分人认识到这种 “两翼说”的合理性。而如果最终能够完全唤醒当代诗坛的这种认识,这不仅仅对于当代散文诗的发展,而且对于当代新诗的整体发展,其推动性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问:如果看待 “大诗歌”的 “大”和散文诗文体自身的 “小”?散文诗该如何体现其 “大”?如何揭示其所具备的 “大”的特质?
答:自从 《大诗歌》一书问世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解,那就是有一些人把 “大诗歌”等同于 “散文诗”别称,所以有一些散文诗作者担心“我们”正在企图把 “大诗歌”替代 “散文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所说的 “大诗歌”,首先是从诗歌文学出发而言的,那就是说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狭义的诗歌理解,认为现代诗歌文学就是那些分行的新诗,即分行新诗=现代汉诗,而忽略了散文诗也是现代汉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克服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诗歌文学的狭义认识, “我们”采用了 “大诗歌”这个概念让散文诗与分行新诗等一起,在诗歌文学中平等共在。我想,无论是谁,无论其如何强调分行新诗的优越性,或者另一些人强调散文诗的体裁独立性,都不可能的,更没有权利否定散文诗属于一种诗歌文学。
这是从体裁意义上关于 “大”的问题,而从作品本身来说, “大诗歌”之 “大”,主要应表现在诗歌作品中所揭示的、体现的思想、情怀、审美、境界之 “大”的问题,而绝不是从作品的长短、题材、词藻等大小问题而言的。至于散文诗的 “小”之说,这个问题最初就是错误的认识,人们认为散文诗的 “小”,可能受到了诸如鲁迅的“小感触”、柯蓝的 “以小见大”之类话语的影响,从而把散文诗作为 “小文学”体裁来看待。鲁迅的 “小感触”只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他的 《野草》哪一篇是 “小”的? 《墓碣文》、 《影的告别》、《过客》等,这些作品虽然短小,但其思想、审美含量决不亚于他的那些小说。散文诗除了其篇幅的表象上相对地小于散文、小说等之外,其思想、艺术的感染力、作品的审美、情怀的承载能力等不 “小”于这些体裁。
当然,散文诗因为篇幅较 “小”,要在作品中体现其 “大”,需要通过作者的思想、情怀、境界、审美表现能力来把握。要达到其所具备的“大”的特质,必须能够把小说的叙事和故事情节、散文的细节和抒情、剧本的对话和独白等,通过诗歌语言的凝练、寓意、抽象、意象性表现等技巧进行审美架构,让有限的语言,通过最大限度的语言意味性挖掘,从而突破语言意义的限定性,突破语言的确指,让语言的意义衍生,使散文诗作品所揭示的思想、情感、审美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立体审美的内涵繁殖,其 “大”就会自然生成。
问: “大诗歌”究竟追求一种怎样的诗歌写作?它的美学定位有哪些?
答:前面讲到了 “大诗歌”与写作者的思想、情怀、境界的关系,那么 “大诗歌”所追求的诗歌写作,基本理念还是需要的。 “大诗歌”的追求一定不会属于那些 “小我”的情感、低俗的情绪垃圾宣泄、甚至无病呻吟的所谓抒情。 “大诗歌”要达到作品 “大”的审美,其作品中的抒情、叙事等就不会仅仅始于 “我”而终于 “我”。始于“我”写作容易把读者带进作品,这是写作者比较普遍的经验。然而,在作品中的 “我”一定要上升到 “我们”,进而扩展到 “你们”,抵达 “他们”的世界,最终是作为人的情怀审视世界。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停留在自己的世界中写作,必须与他者一起,共同完成一个通过 “你”这个个体来审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人类存在、思考、境遇等生命境界与状态的把握与呈现。
诗歌文学最初始于吟诵文化,其诞生于人类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为了统一集体的呼吸与节奏而编造的劳动号子。由于贴近生命的自然状态,顺应呼吸的韵律节奏而善于吟唱,所以,它在人类的文字出现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人类保存、传承族群的历史、文化、精神等最重要的记忆工具,而不仅仅只是审美需要。所以,“大诗歌”理念对于诗歌的要求一定要拒绝诗歌的文字游戏,无生命词藻装饰,要尽最大可能让诗歌回归生命本身的自然律动,寻求向人类生命原初的鲜活律动自由回归而写作。
问:请你谈谈 “意义化写作”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答: “意义化写作”是周庆荣最初提出来的,那是关于 “大诗歌”写作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我的理解,所谓的 “意义化”,就是指写作者的 “担当意识”、 “责任意识”、 “审美意识”的结合,让作品抵达某种生存意义的志向、指向。比如,一束鲜花,其必须作为某种观赏物,或者作为礼物赠送给自己祝福、倾羡的人的时候,这束鲜花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一块砖头,它要作为某种建筑物的一部分的时候,或者发挥其某种存在功能的时候才能成为其存在的意义,等等,这是所谓的 “意义”一个层面。而更深的层面则是,我们能够从鲜花、砖头的某种状态中获得自身的某种状态、命运、审美等对应性觉醒、定立性启迪,从而让自己的生命获得更为丰富的把握。诗歌作品也一样,每一首 (章)作品,都必然是由于某种 “意义”的需要而诞生。诗歌作品一旦作为作品公诸于世,它的话语功能总是携带某种责任的,对于社会的一般大众来说,仍然具有某种导向的作用。这种作品就是其 “意义”之所在。而这种 “意义”的产生,正是诗歌文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存在的理由。那么,作为诗歌写作者不能只是追求自己的感官快感,或者自我表现欲的满足,诗歌仍然必须具备生命的审美意识,必须对自己的话语具备担当的、责任的意识,不能忘记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怀、审美。所以,我认为 “意义化写作”的提倡,不仅仅只是一种担当、责任意识的坚持,还应是对于近年来诗坛出现的诗歌写作的庸俗化、低俗化的一种自我提醒与审美理想的自卫。
问:与分行新诗、散文等文体相比,你认为散文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长处究竟在哪里?
答: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认为散文诗是分行新诗与散文的结合,既可以吸收诗歌的优点,也可以吸收散文的优点,如 “混血儿”一般优生地存在,由于这种1+1=2,所以,无论与两者哪一种相比,都显得大,显得丰富。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线性思考,散文诗这一文体的诞生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那么其必然如余光中所言,只能属于 “非驴非马”[1]的文学杂种。散文诗应该是一种可以综合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学、艺术的一切可以吸收的表现、表象手法,成为一种具备立体审美的诗歌体裁。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诗歌是戴着镣铐跳舞,散文是一种散步,如果按照这种划分法,那么散文诗既属于诗歌文学,又比分行新诗来得自由,那么自然属于没有镣铐的跳舞了。但我觉得把诗歌比作戴着镣铐的跳舞只适合于古典诗词,现代的分行新诗应该属于没有镣铐的跳舞,也就是说比古典诗词来得自由。而把散文比作散步,过于诗意了,因为在文体分类中,包括一张借条、几句留言都可以归入散文。所以,用走路来比喻散文更为贴切,而散步恰恰适合于用来比喻散文诗。也就是说,散步诗比跳舞来得自由,比走路来得富有诗意。为此,散文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最大的长处应该在于其 “自由”的灵魂,如散步,可以放松身心,在从容的状态中展开思考、体现审美。正是因为 “自由”,散文诗才可以吸收其他所有文学、艺术体裁的长处,为我所用,这是 “散步者”才能做到的。但是,正如 “自由”是建立在 “自律”的基础之上一样,散文诗的这种自由,需要极其丰富的情感、敏锐的悟性、深邃的思想、高度的审美能力才能真正懂得其中的难度,才能真正拥有 “散步”之从容。
问:散文诗发展到今天走过了九十多年,你觉得散文诗的局限性有哪些?散文诗的难题是什么?
答:九十多年来散文诗的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散文诗过于缺少应有的探索精神,以及人们对于这种诗歌体裁缺少应有的美学价值的认识。另一个方面,已经存在的散文诗作品,长期以来把散文诗矮小化,也就是我说过的 “把老虎当作猫来养”。一些关于散文诗的言论也总在误导人们的正确认识。这些误导削弱了许多散文诗作者的自信,从而使散文诗作者群的素质普遍偏低,思想高度、审美境界、写作情怀都远远落后于文学的左邻右舍。
当代散文诗最主要的难题有两个,其一是如何提高散文诗作者群的整体文学素质,提高他们的审美辨别能力,至少要能够看得懂哪些作品是好作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探索自己突破的途径。之所以说这是难题,那是因为许多人对于自己已经形成的审美定式,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所谓的名气还充满肤浅的自信,不愿面对现实,甚至抵制一些探索者的探索性作品;其二是如何让当代诗坛的新诗作者认识到散文诗所具备的巨大美学可能性,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散文诗创作的美学实践,让他们成为改变当代散文诗现状的新生而有力的审美力量。这看起来容易其实相当困难,因为几十年来所形成的 “偏见”,绝非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加上散文诗的 “合法公民权”尚未获得,在急功近利成为社会大趋势的今天,这就更加困难了。
为此,如何让散文诗写出站得住脚具有说服力,创作具有审美高度的 “好作品”成为 “我们”的当务之急。散文诗只能靠文本来说话,任何空洞的鼓吹、自我标榜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两年多来致力于推介、编选可以向分行新诗学习,切磋、交流的散文诗作品,在各种刊物上亮相的理由之所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得到了一些新诗作者的认同,吸收了一些新诗作者转向散文诗写作,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还远远不够,一块坚硬的岩磐只是出现了一道裂缝,终于可以往岩磐里面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仅此而已。
问:你对当下散文诗的批评怎么看?你认为当前最需要的批评是什么?
答:在当代,可以说散文诗批评基本上是空白的。除了王光明的 《散文诗的世界》一书,对于散文诗的历史和文体研究达到了文体研究的学术高度之外,其他关于散文诗的评论、理论基本上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比如,长期以来散文诗作者,甚至一些以散文诗理论见长的学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散文诗的文体独立性的吁请之上,缺少扎实的文本研究作为这种吁请的理论支撑。
造成其说服力欠缺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大多数研究只停留在历史文本的研究之上,而这些历史文本本来只是散文诗萌芽期的作品,作为散文诗的标准文本本身就缺少说服力,所以,他们总在抱怨没有好的文本。其实,他们如果把目光的一部分放到当下不断出现的、富有探索性的新文本 (而不是那些本来就不成熟的传统散文诗手法复制而来的新文本),从这些新文本中分析、阐述散文诗的美学可能性,那么,当代的散文诗批评应该会取得一定的成就的。遗憾的是,这种研究很少。还有,散文诗的批评,不能只停留在散文诗一种文体之上,必须与文学的左邻右舍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散文诗作为文体差异性的美学之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散文诗的批评具备散文诗作为独立文体的建构性意义。也就是说,应该把散文诗与分行新诗、与散文、甚至其他文学体裁的美学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凸现出散文诗作为独立文体的美学特质、指出其应有的文体美学建构。然而,当代的散文诗批评中,这种研究几乎可以说是空白的。
所以,我认为当前散文诗批评最需要克服的问题有三点:第一,要抛弃偏见,不能把散文诗当作亚文学对待,充分相信散文诗所具备的巨大美学可能性。第二,不要盲目相信权威,学会自觉地挖掘、发现当代优秀的文本,而不是总是停留在从传统的所谓经典文本上来看待散文诗。第三,要确立散文诗的独立文体信心,相信 “现代正是散文诗的时代”,必须从数千年的文体发展的历史来认识当代社会之所以诞生散文诗的必然趋势。
问: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在散文诗的文体定位和地位上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和不确定性,对散文诗带来更多的是什么?是发展还是阻碍?
答:在20世纪初,当时散文诗刚刚引入中国,大家对于这种诗歌体裁还不知道,那么,这时候关于其文体定位以及文学中的存在地位的讨论是有必要的。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争论持续了90多年,到了现在仍然如此,这就显得极其可悲了,这一方面说明散文诗一直还没有在文学国度中获得合法的公民权;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争论让文学界难以承认散文诗的独立存在地位。所以,我认为这种争论不仅不利于散文诗的发展,而且大大阻碍了散文诗的健康发展,使散文诗作者因此回避大文学而自我圈地,拒绝在与其他文体的交流和学习中提高与发展散文诗,从而使散文诗成为一些人孤芳自赏的温床。
到了今天,这种文体已经存在于中外文学之中,没有必要总在进行身份的确认,只要从那些以散文诗的身份出现的文本中,研究其作为一种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美学特征就可以了。而散文诗作者更没有必要总在呼吁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可,只要努力写出自己的文本,只要自觉地进行散文诗的创作,这就足够了。散文诗作者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 “写什么”与 “怎么写”的问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 “是什么”的吁请之上。
问: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 “散文诗,作为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被历史传承的可能性”,你认为这种可能性主要表现在哪里?
答:我所说的 “可能性”是从中国诗歌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立论的。
回顾中国的诗歌发展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主流诗歌文学,如诗经、离骚、九歌、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小令等,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诗歌文学究竟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流,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在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中,古典诗歌文学中的诗赋词令无一幸免,人们转向新的审美需求,选择白话诗。白话诗中人们本来应该包含分行新诗与不分行散文诗,然而,几十年来人们更为青睐分行新诗,把这种诗歌表现形式作为古典汉诗向现代汉诗演变的正统继承者,散文诗虽然与此同时诞生,但除了最初的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地淡出了主流文学的视线。这有一点像唐代的诗与词的关系,唐代也有词的存在,可是唐代的主流在于诗而不是词。然而到了宋代,这种主流却让位给了词,为什么?这是非常值得研究与探讨的问题。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心灵的审美需求根据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寻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时期,在一个被颂歌笼罩的时代,当然应该是节奏明快、易吟易颂易歌的分行新诗首先被人们接受;而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虚拟世界被打开、快餐文化流行,可读性、可思性、叙事性、抒情性、场景性、细节性、情节性等,可以集多种文体要素于一身的散文诗是否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需求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预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一切关于散文诗美学探索实践,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都具备一种拓荒性与建设性的意义。
问:散文诗的难度写作应不应该提倡?
答:周庆荣对此回答很精彩,他认为: “写作者写出的作品,别人能读懂,但别人可能想不到 或者不愿意费神去想,这本身便是写作者的难度”。 “难度”确实不应该是语言或者是结构上的追求,如何让更多的人读懂作品,不是在语言意义上,而是在语言背后的那些思想与情感等意义上的读懂,这应该是最大的难度。
其实,文学艺术无论是哪一种,只要属于文学艺术其写作或者创作都是有难度的,既不可能简单到可以用说话、呼叫、随手涂抹来实现,又不能只是自言自语,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什么,表现什么。所以,创作始终是与难度如影随形的。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立论首先是有问题的。 “难度”问题是不需要提倡的,而是作者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自觉问题。
当然,这种提倡或者说提出可能是针对 “散文诗好写”的肤浅广告言论而来的。然而,一个有高度有追求的作者,难道值得在意那些不攻自破的肤浅言论吗?
问:如何看待散文诗的抒情性?散文诗中的情感与生活中我们体验到的情感有何不同?
答:所有诗歌文学都必须具备抒情性特征,不仅仅只是散文诗。当然散文诗应该是更加适合于表现在叙事中展现、完成其诗的抒情性的文体,这个与分行新诗在意象的差转与审美跳跃的节奏中完成的抒情性的特征是有区别的。散文诗中的情感与生活中的情感当然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散文诗,文学作品中的情感都一样,那是经过提炼过的,从个体上升为集体、群体的情感。生活中的情感往往只是局限于某一个体的生命经验,而作品中的情感必须是某个时代、某一种人群的共同生命经验。为此,这些情感一般必须上升到情怀的高度来展开。即使是一种情绪,也必须在情怀里展开,属于一种既个性又共性的表现。
问:你认为散文诗的使命是什么?
答:散文诗的使命与其他文体一样,让人类曾经的在场生命得以传承。既要喊出时代的疼痛,又要唤醒社会的良知。在建筑一个时代的审美经验的同时,为历史提供一种沉沦与救赎的灵魂宗教。
问:当下的散文诗应该如何 “突围”?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答:这个问题我在1987年6月的一篇题为《审视,然后突围》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其实,在前面几个问题中也都涉及到了与 “如何突围”有关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我当年提出 “突围”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散文诗坛在柯蓝的引领下出现了空前的 “繁荣”,散文诗学会创办的 《中国散文诗报》,在全国兴起了一股散文诗创作热。可是,综观那些发表的作品,没有几篇是可以卒读的,而散文诗作者的整体素质也比较偏低,这样的 “繁荣”只能让人更感到 “荒凉”;另一方面是从自己散文诗的创作经验出发,我深感到散文诗这种诗歌表现形式大有可为,它比分行新诗更为自由和丰富,内在的思想和艺术含量更大。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将来的分行新诗会逐渐被散文诗所替代,从而把中国诗歌文学推向新的高峰。然而,像这样的具有无限的将来可能性的体裁,却总让写新诗的作者们看不起。
可是,凡事不能怪别人,要先反省自己。大家看不起散文诗,是因为散文诗自身确实没有让人看得起的作品。尽管这样,当时的许多人还在沾沾自喜,认为散文诗繁荣的时代到来了,在全国还搞得很热闹。面对此景,我选择了退守自身,不投稿,基本不与那些所谓的散文诗大家交往。同时,我深感中国散文诗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美学突围,那是没有希望的。至于如何突围,我当时还年轻,只能根据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经验出发,提出了以下三点:第一,散文诗创作必须有文化背景的关注与呈现,让作品超越作品本身,达到人类普遍意义的暗示力量。第二,提高作者的整体素质是关键,因为作者的素质决定作品的质量。第三,至于如何提高素质问题,我提出了拓展思维空间,树立哲学意义上的平等观念、用整个生命与世界相遇的创作要求。并进一步指出要做到这一点,改变观照世界的方式,树立文化的自觉意识成为关键所在[2]。现在看来,20多年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虽然有些情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其实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我自己的这种无法克服的 “散文诗情结”,造成了时过20多年,人到中年,在每天忙得找不到北的日子里,还要跟一群散文诗的朝圣者们一起,发起、组织了 “我们”散文诗群,进行着这样一场散文诗美学 “突围”的大实践。
[1]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M]//余光中.寂寞的人坐着看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5.
[2]灵焚.灵焚的散文诗[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70-172.
Survey and then break throagh——An Interview of Prof.Lin Meimao,One of the Leading Writers of“WE” Prose Poetry Group
Lin Meimao1,Zhong Shihua2
(1.The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10000,China;
2.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Wuzhou University,Wuzhou 543002,China)
In the past fewyears,a prose poetrygroup called“ WE”,consisting ofsome prose poetry writers,was founded in Beijing,which attracts much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circle,especiallyin the circle ofpoetry.In viewofthis,the author ofthis paper has made an interviewconcerning the following topics:the background for the birth of this group,the aesthetic ideas of their prose poems,the significance oftheir advocatingthe creation of“ Great Poems” ,the contemporariness and prospects ofsuch a poetic style,the reasons for realizingan aesthetic breakthrough and conducting a literary movement,and so on.So,what are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mentioned topics?In a word,it is time for the prose poetry to depart from its period ofstaying lonely and keeping watch because prose poetry is a literary style which can extensivelycombine intoone all the finest expressingtechniques ofother literarystyles.Representingan inevitable developing trend ofthe modern Chinese poetry,prose poetry is very likely to be widely used as a leading poetic style development ofliterature in the future.Therefore,“ WE” is carryingout an aesthetic breakthrough in group.And,the current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prose poetrywill develop intoan independent,style-exploringaesthetic movement ofhistorical significance.
“ WE”;prose poetry;Great Poems;meaningful writing;breakthrough
I226.6
A
1673-8735(2011)02-0062-09
2011-02-18
林美茂(1961-),笔名灵焚,男,福建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哲学、日本思想、散文诗。
钟世华(1983-),男,广西合浦人,梧州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钟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