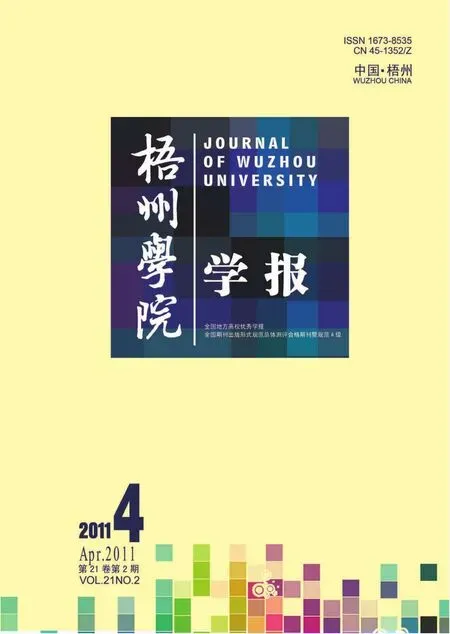古苍梧部落的文化密码——西江龙母神话与图腾文化
陈侃言
(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广西 梧州 543002)
古苍梧部落的文化密码
——西江龙母神话与图腾文化
陈侃言
(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广西 梧州 543002)
西江龙母神话,反映了西江流域古苍梧氏族先民的文化图腾由蛇图腾升华为龙图腾,与华夏民族的龙图腾同步演进,系华夏文化版图的重要组成部份。龙母崇拜是比龙崇拜更升华、更具崇高美的母仪崇拜,是水文化、孝文化、真善美的产物和结晶;宣示了和谐社会的原始真义:民意不可违,权威不滥施,以人为本,利泽天下,社会和谐。
龙母;图腾;苍梧;密码
一、故事
闽粤海边两岸渔民沿习祭祀妈祖,已是众所周知,风靡天下,而以蛇为图腾的仓吾部落的蛮夷们之水上女神为龙母,却不大为北方学者所知,或知而蔑之。
据传战国时期,龙母姓温(一说姓蒲),藤县人,出生时天降祥瑞,鸟雀和鸣。长成后有辟谷之术,异力超人,能望空而语,与神灵对答,预测祸福;白鹿随从,能蹈浪行江,行医济世,遂为统领世间百兽之西江女神。
某日,温氏在西江边浣纱,发见一大石卵,拾回孵化出五条小龙,悉心饲养。五龙长大,龙母教其为人间造福,守护江河,体恤舟渔,行云播雨,利泽天下,不得翻江倒海,遗患人间。五龙孝顺驯服,温母被百越民众视为首领,率众开荒拓园,治涝抗旱,使百姓安居,从此苍梧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渔樵颐乐。
正遣童男童女往东海求方士觅长生不死药的秦始皇闻知,喜不自胜,即遗使迎龙母进京,五龙随行护送。龙母四次起程,均行至桂林而折返,终不舍苍梧百姓。始皇乃允其永留西江以慰民心。以上就是西江两岸民众世代口耳相传两千多年的龙母神话故事梗概。
龙母仙逝后,西江各埠均建有龙母庙,两岸民众时常祷拜,历朝皇帝和南来官员均有祭祀。
汉高祖十二年,封程溪夫人(龙母之生母为悦城程溪梁氏)加赐御葬;
唐天佑二年,封永安夫人,又封永宁夫人;北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宣抚使狄青征交趾,水师凯旋,认为是龙母庇佑之功,乃重修梧州龙母庙,皓封龙母温氏为永济夫人和灵济崇海妃,五龙子及龙母姐妹亦一一赐封;
南宋绍定四年封为显德夫人。
明洪武八年,封程溪龙母圣妃,后又封为护国通天惠济显德龙母娘娘,原封侯爵之五龙子皆封王爵;
清康熙加封为水府元君;
咸丰加封昭显;
同治加封溥佑;
光绪加封广荫。
龙母故事在西江中游各埠广为流传,版本众多,然主要故事梗概大致不离此说(1)。不同的是,温氏的籍地,各埠争说是当地人;龙母庙之立,又争谁先谁后的问题,这都无伤于龙母是西江流域民众心中的女神的大局,倒是各埠民间和文人由此衍生出林林总总的以龙母为中心的故事、传闻、传奇及演义,使西江文化宝库更添充实和色彩。
二、神话传说的演变
龙母的故事,当然是神话传说。在神话分类中,属英雄神话、文化神话,已不是创世神话了,己从“宇宙初开”演进到“秩序规则”了。苍梧人的龙母神话同华夏民族古老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一样具有显著的人类审美特征:崇高美。
中国古代的神话往往都以人的生存与自然力斗争为主题,强调人的力量,化人为神,具有超自然的神力,把人格理想化,带有鲜明的社会性,以致使神话历史化,使神话人物成为历史人物。中华民族受儒家思想影响,不语“怪力乱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贬斥神话,并且着意加以改造,把“神”人化,把神奇怪诞的传说作出一番看似合理的诠释,使之化为历史,载入简册。
龙母的姓氏出身(甚至其生卒年都被“考证”出来:生于楚怀王辛未年公元前290年农历五月初八,卒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1]、秦始皇迎龙母、历代皇帝煞有介事地皓封龙母等情节,均系将神话历史化的作为。而温氏其人,究竟先是神话人物而被传说衍化成历史人物,抑或是历史人物而后被神化,则无从考究。人被神化,古来有之,如三国的关羽,唐代的吕洞宾,宋初的陈抟等。这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
同时,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都激情洋溢、能力神异、人性良善,是人格的化身和榜样,这就使神话寓言化了,传输了人生的哲理。后世的某些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从神话的宝库中选取自己需要的部分,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便把它改造为寄托思想的寓言,在形象的故事中包寓某种哲理,于是神话就被寓言化了。龙母教导龙子行善,利泽天下,化暴力为和谐秩序;龙子孝顺龙母;秦始皇不以天子之尊而怠慢龙母,以祖龙自居而降格认迎龙母等情节,就是神话寓言化所蕴藏的人生和社会哲理。
神话与原始宗教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中的“神”,本来就是先民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而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也与原始宗教借助巫术控制自然同出一源。神话中含有宗教的因素,是很自然的事,故易为宗教所利用。神话流为仙话,是神话宗教化的主要表现。两千多年来西江流域民众(乃至近代延及港澳和海外华人)对龙母的祈拜,代代相传,香火不断,仪式隆重;龙母诞期更是万人空巷,笙鼓喧嚣,龙帜飞扬,万民跪拜,虔信忠忱,热烈非凡。可见其宗教化程度之深。
从总体上看,西江龙母神话与中国北方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牛郎织女、穆天子西王母等古代神话一样,其显著的演变结果便是它的历史化、寓言化和宗教化。
三、图腾文化
原始社会的先民缺乏科学知识,更不认识其规律,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既敬畏恐惧又好奇窥测,便形成了对自然的崇拜。
自然崇拜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山川、风雨、干旱、雷暴、太阳、月亮等的崇拜。人们的生活生产都很大程度地受到风、雨、干旱、雷暴、寒暑、洪水等的影响,初民认为是神在支配着这些自然现象,便通过祭祈活动以求得神的保佑,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祖先崇拜,是先民对祖先的尊敬和爱戴,尤其是那些曾带领他们与自然斗争,克服困难和有发明创造的英雄人物(如神农氏、燧人氏、螺祖、鲁班等等),期望得到祖先的帮助和指引。于是自然就产生了祖先崇拜。
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须有个载体、有物寄托,这个寄托的载体就是图腾。
所谓图腾,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当作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它们会保护自己,并能从中获得它们的超人的力量、勇气和技能。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龙、凤、蛇、鹿、鸟类、虎、麒麟等动物都曾作为图腾崇拜物。例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中玄鸟(演而为凤凰)便成为商族的图腾。初民没有文字记载他们经历的历史,就在石壁上刻上一些印记,如崇拜物,这就是图腾。氏族、家族等社会组织就以图腾命名,并以图腾作为标志。
据专家学者研究考证,图腾文化是由图腾观念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也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为了表示自己对图腾的崇敬而创造的各种文化现象。图腾崇拜的出现,反映人类综合能力的提高,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综合为图腾文化。图腾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奇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图腾文化的核心是图腾观念,图腾观念激发了原始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逐步滋生了图腾名称、图腾标志、图腾禁忌、图腾外婚、图腾仪式、图腾生育信仰、图腾化身信仰、图腾圣物、图腾圣地、图腾神话、图腾艺术等等,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绚丽多彩的图腾文化。图腾崇拜又非是一成不变的,会演变升华为另一图腾崇拜。
图腾标志或称图腾徽号,即以图腾形象作为群体的标志和象征。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具有识别和区分的作用。图腾标志与中国文字的起源很有关系。
图腾与氏族的亲缘关系,往往通过氏族起源的神话体现出来的。如桂东一带的瑶族,奉狗为祖先,其瑶族神话中说,在一次大地震、大洪水的大灾难到来之前,一对男女正在梳洗,一只狗突然叼走梳子向高坡奔跑,两男女便穷追不舍。此时地震洪水突至,家园尽毁,族群尽丧,两人因此逃出生天,从此繁衍了瑶民族,视狗为恩人,奉为图腾。
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同时通过图腾标志,得到图腾的认同,受到图腾的保护。图腾的标志常见如:旗帜、族徽、服饰、纹身、图腾舞蹈等。图腾崇拜须由巫祝主持祭祀仪式,形成了民俗积习,便成为人类原始社会最早的一种宗教信仰了。
苍梧百越部落最早的原始崇拜的图腾是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训“蛮”说:“南蛮,职方氏八蛮。尔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王制云:南方曰蛮。 《诗·角弓》:如蛮如髦。传曰:蛮,南蛮也。采芑蠢乐荆蛮。传曰:荆蛮,荆州之蛮也。它种,从虫。说从虫之所由,以其蛇种也。蛇者,虫也。” 这就是说,所谓蛮人,即是自称为蛇种,以蛇为图腾的人。岭南苍梧氏族自古被称为南蛮、蛮越、蛮夷。正是崇拜蛇的民族。
五岭以南,森林密布,气候炎热,草盛莽青,盛产蛇类。百越先民与蛇共生共荣。侗族传说其始祖母与一条大花蛇交配,生下一男一女,滋生繁衍成为侗族祖先。壮族也有《蛇郎》的神话,西江的疍户自称龙种,断发纹身,以像蛟龙之子,入水可免遭蛟龙之害。但苍梧人吃蛇,是世界闻名的。梧州曾有世界最大的出口蛇仓,蛇医蛇药世界闻名。既然崇拜蛇为图腾,为何又杀食图腾?这并不奇怪。这是其他族群也有的现象。祟拜而至亲近、亲近而至将其作为牺牲品供祭祀,于是吃图腾便是自然之事,从图腾中获取图腾的奇力,从而再升华到更神异更理想的图腾崇拜。由蛇而龙,便是这种崇拜的升华。
由对蛇的崇拜而升腾为龙的崇拜,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主要因素必然是华夏族人的部落不断南移迁徙所影响。如屈原的祖先在“殷之末世……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见《史记》)。屈原的祖先流落到了蛮夷的中心地区苍梧,与苍梧蛮夷融合了。屈原在《离骚》中自悼身世、呼唤远祖就说“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又如武王伐纣时,季连部落积极参与,得到奖赏,其中熊、罗两个氏族的首领均被周天子封为子爵。熊的封地在湖北荆州,称楚国;罗的封地在湖北房县,称罗国。春秋后期,楚国渐强,不断兼并邻国。公元前690年,楚灭罗[2]。罗人集体南迁,今日两广凡有罗、那的地名均系周时罗人南迁的地方(罗人带来的稻作文化,在岭南如鱼得水)。在漫长的上古岁月,由于生存发展和战争,华夏大地的各氏族、部落从未停止过迁徒和移民,苍梧是北方落难者的避风港,有迁移就有交流、融合。苍梧自古就是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驿站。文化融合,苍梧原土著的蛇图腾崇拜必被北方南迁的华夏龙图腾崇拜所替代。
我国文化人类学者、民俗学者都达成共识,认为华夏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是由蛇图腾崇拜升华而来的,简说如下: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载,华胥氏(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的母亲,伏羲与女娲婚合而生黄帝),在 “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大迹就是大的脚印,即雷的脚印。雷泽,就是雷藏身的地方。那雷是何方神圣?那雷是“人头而龙身” 的半人半兽的神物,打雷时飞升上天,平时隐藏于地,这就是半龙半蛇的神圣图腾。伏羲姓风,风字繁体框内是个“虫”字,即说伏羲是由虫生的。虫即指蛇。夏人的祖先先是蛇,后而升华为龙。后来屈原在他的《离骚》又加以文学改造,说是雷神向华胥氏求婚而生伏羲,把神话加以历史化了。古甲骨文的龙字是虫上加个王,即龙是蛇中之王,龙本身不存在,而蛇则是龙的原形[3]。
四、密码中的古苍梧
岭南西江流域百越先民由蛇图腾而升华为龙图腾,这一图腾文化的演变,与北方华夏图腾文化的演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使最迟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成。这便可证明,战国时代的苍梧已在华夏文化版图之内,战国时代的苍梧地域,就在西江流域中游及桂江流域,不是以前权威学者所指称的在洞庭湖南边。
龙母神话传说、苍梧先民龙图腾崇拜,这些远古的历史事实,对古苍梧、古广信、古交州、今梧州的历史文化意义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社会习俗、民间风尚那种文化流风之份量可比,它是苍梧历史文化的根本源头。
假如没有了西江龙母神话传说,梧州在先秦及以前的历史就是一片空白,战国时代的苍梧地域就可以任人指称而北移,上古舜帝巡葬之苍梧说不定被人考证到了山东的鸣条去了。
在记载先秦史料的史籍中,“岭南”一词尚未出现。说到华夏大陆南端一带的地域和氏族、部落,常见的说词就是:交趾、南越、苍梧、越裳、南海、百越、题雕等等。及至汉武帝时,在苍梧设苍梧郡和广信县,并将交趾刺史部移至广信县(交趾剌史部后又改称交州),这时的苍梧地望就很分明了,前、后《汉书》都记载得很具体,即西江上漓水与浔水交界处。但,汉武帝之前的“苍梧”又在何处?屈原《离骚》中提到的“苍梧”又在何处?是否也是漓浔交汇的那片地域? 《史记》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礼记》:“舜葬于苍梧之野”;司马相如《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在他的赋提及的“入洞穴,出苍梧”、“必耸身于苍梧之渊”,这些“苍梧”、“苍梧之野”又在何处?
说到汉武帝之前的“苍梧”许多古藉均习惯把“洞庭、苍梧”连在一起说。于是许多专家、甚至一流的权威国学大师都说,此苍梧在洞庭湖南边,属湘南,与广西无涉。理由似乎很充分:舜葬九疑,九疑就在湘南。有的打圆场说古苍梧原在北方,后来逐渐南移的,云云。
那么笔者就得发问了:上古史学家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参与考证、编绘的都是国家级的单位,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国测绘局、中国地图出版社及众多大学历史系等文史单位上两百多名专家、学者。在这本地图集里,春秋战国时的中国地图清楚端正、明百无误地在漓江与西江交接处标明:“苍梧(仓吾)”字样!难道他们都搞错了?不知“洞庭、苍梧”之连说?
说到底,原来是中国的行政地图作怪。打开现代中国地图,在两广交界的北部,湖南大大地插了一块进来。零陵、郴州已向南越过广西的北界,九疑山更向南直伸入广西贺州地区北部,而贺州是十多年前才从梧州划出另立,即是说,九疑山直插今苍梧的北部。
把那几条人为的省界拿开,九疑山就与古苍梧抱成一团,在古苍梧郡的北部。1999年出版的《辞海》解释曰: “(苍梧)其地当在今湖南九疑山以南之广西贺江、桂江、郁江区域。”此辞条即是说:九疑山在古苍梧郡之北部也。
可是有的学者和国学大师就只会“看图说话”,对着湖南南端现代的省界就断定古苍梧就在湘南,与广西无涉。
其实古籍中“洞庭、苍梧”之连用,只说明两个事实:1.苍梧在洞庭湖、或古洞庭郡的南边;2.洞庭南边最著名、最耀眼、最不可忽视、最必须提及的就是苍梧。舜之所藏,不著名、不耀眼、可忽视、不屑提及吗?这苍梧,就是以漓浔交汇处为中心的古苍梧;就是其北部有条九疑山脉的苍梧;就是苏东坡所说“独在天一方”之野“舜所藏”的苍梧(2)!就是宋人陶商翁咏梧州诗所云:“川流八桂末,地势九疑余”、“苍梧之邦舜游处,九疑七泽皆相连。”(3)的苍梧!
古苍梧的九疑山在上古时代很出名,又在古苍梧的最北部,自然就成了北方文人关注的目标,这九疑山就另得个别名雅号曰:苍梧山,并在地图标示。但苍梧山不等于苍梧之野,九疑山也不等于苍梧之域,苍梧山、九疑山不等于整个苍梧之邦,苍梧部落、苍梧方国自有其族类的聚居中心,苍梧古郡自有其郡治所在呀。
领袖曾有诗云:“班竹一枝千滴泪”说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泪洒九疑班竹。注释家们很省心,注曰:九疑山即苍梧山。多一个字也不落,多半句话都不提。读者也很省心,不必再求甚解,于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由当年人手一册的领袖诗词选而深入全国人心、家弦户诵:“九疑即苍梧”。
现代专家如是说,那就听听古代的知识分子怎样说的吧。
战国时的屈原在《离骚》中说:“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 (重华即舜帝)此屈子扬言要渡沅水、湘水,再南征,向舜帝面陈、表白、倾诉,甚至告状。舜居何处?屈原在该诗曾自述其祖:“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淮南子》说屈子“朝发帝居之所”。 (居,即藏也。)苏东坡南谪时在梧州写的诗说: “我行忽至舜所藏。”(3)(藏,葬地。古人对帝王忌讳,不言葬,而说居或藏。)战国时这位屈诗人都知道舜藏之所并不在洞庭湖边,而要远渡沅、湘二水而南征,才能到及苍梧;苏东坡也知道“帝居之所”、“舜所藏”处在梧州。无独有偶,西汉末的扬雄在他的奇赋《反离骚》(4)中,嘲讽屈原“横江湘以南往兮,云走乎彼苍梧,驰江潭之泛溢兮,将折衷呼重华。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他说屈原嚷著要渡江、湘南下,管他江河正泛滥,说什么要去那个苍梧面见舜帝,抒心中之烦情,恐怕舜帝不耐烦你的纠缠未必肯听你的。这扬雄距战国时的屈原几近300年,一样知道去苍梧要远涉江湘而南下。因为这是常识。
古苍梧在哪里?是相信2000多年前楚国的屈原、西汉的扬雄、1000多年前的苏东坡呢,还是信现代的大师?
屈原也没有指明这古苍梧的地标,这个问题很是棘手。
请看看西江龙母的神话,西江龙母神话虽然从未以文字形式载入过国史,但在民间代代口耳相传。文字史册尚有销毁湮灭之虞,民间口耳相传却无人能毁,有人在,传说就在,神话故事就永远流传,这是历史保存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历史,不仅仅存在文字中。这神话最精彩的一个密码就是:温氏龙母与屈原同时是战国人,苍梧这位女子藉地西江。 “战国”、“苍梧”,“西江”连起来的密码逻辑,或者说是证据链,就是:战国时的苍梧在西江。
民间传说当然不会在2000多年前为“舜之葬所”、“古苍梧在西江”而捏造一个 “战国龙母”的神话为笔者今日所用。倒是可证,战国时的苍梧在西江,秦与蛮夷的西江苍梧在当时早已有文化上的联系了,而且还很亲密,真龙天子要认龙母娘娘作妈妈。
西江龙母神话传说是梧州文化的渊源和命脉,决不可等闲视之。
五、文化渊源
以古苍梧为中心的西江流域的古越民族,在上古时代与江汉间的楚荆民族已有文化交往。春秋战国时代苍梧地属荆楚,是泛楚文化的属地,形成特色鲜明的楚越文化。徐杰舜在《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中说,楚越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表现如下八个方面:
1.宗教信仰——信鬼盛巫,崇拜龙凤;
2.民族性格——强悍刚劲,崇尚武力;
3.饮食——好食水产异兽,喜酸甜苦冷;
4.服饰——高冠佩玉,蛮腰长袖;
5.居住——层台累谢,园林风味;
6.器用——广泛使用竹编制品;
7.艺术——能歌善舞,巫歌盛行;
8.葬俗——像君设室的棺椁制度。[4]
楚国在秦王扫六合的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灭亡了,被融入华夏民族大融合潮流中,楚国虽灭,楚越文化和楚越民族的心理特征却成为华夏民族及至后来的汉族特征的血肉部分。
西江流域的古苍梧民族自古以来“信巫鬼、重淫祀”,所谓“巫”就是以舞降神的女祝,女巫祝是执行神的意志的化身,“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对龙的图腾崇拜十分突出。屈原在《楚辞》中对龙的描写十分丰富生动“驷玉虬以乘鸢兮”,“为余驾飞龙兮”、 “驾八龙之蜿蜿兮”。以龙为御,把龙作为腾云驾雾、漫游天际、潜藏深渊、上腾九天的神物。显示楚越民族十分丰富的想象能力和人文理想。龙是水文化的产物,没有丰富多样的江河文化生活,就不能产生龙的图腾。龙母传说的产生是在战国末期。龙母崇拜,是岭南西江各越族的母仪崇拜。
母仪崇拜是比龙崇拜更为高级、更人性化的崇拜,更具美学的崇高美!
古代神话传奇,华夏水域均有龙王传说,洞庭龙君、钱塘龙君、泾川龙君、濯锦江龙君、东海龙王、北海龙王等等,这些龙王龙君大多都是雄性暴君,唯独西江是慈祥的龙母、孝顺的龙子。这正是岭南文化特有的母仪崇拜、人性化的崇高美,可见岭南西江文化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这是龙母神话的又一密码。
秦始皇一统天下,自视甚高。龙是长生不老,横行天下、驾驭众生的神灵,秦始皇自称“祖龙”,这在司马迁《史记》中是有文字记载的。他是中国以龙自居的第一人。当他派童男童女渡海去寻长生不老药之时,听得苍梧有龙母龙子的故事,即派人请龙母进京,要认苍梧龙母为妈咪,显示作为君王的他尚具人性的一面。龙子护送龙母沿漓江北上,几次折返,终不舍西江民众。始皇人性未泯,乃允其永留西江以慰民心。这是龙母神话的再一个密码。
六、文化密码,精神内核
龙母神话传说,蕴含着古苍梧氏族的文化密码,破解不难,它从历处深处透露出的信息,今人尽可作如下解读。
1.战国时的苍梧在西江,秦始皇时苍梧已属秦地,苍梧地在西江流域,千古不易,而非湖南的永州,更不在洞庭湖边,这点很重要。汉武帝以前的苍梧郡被不少权威的专家学者硬说成在湖南洞庭湖南边,苍梧的历史只能从汉武帝时算起,只有2000多年,以前的3000年的存在,被人一笔勾销,这既有违史实,也非梧州人所能接受。
2.苍梧文化是水文化、江河文化,不然就没有龙母的传说。龙图腾是西江水域的“保护神”。龙图腾,既是苍梧人民的一份文化遗产,又是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
3.苍梧古越族的原始图腾是蛇,蛇的升华神化就是龙,与华夏龙图腾二者是如此契合,是有文化的融合、承传关系的,是一脉相传的,与华夏龙图腾的升华同步演进。岭南百越土著,从来就是龙的传人,有着先进的远古文明,被蔑称南蛮、蛮夷是历史的错误。
4.母仪崇拜是比龙崇拜更为高级更为人性化的崇拜,更具美学的崇高美。
5.龙母对五龙子的教诲和约束,不仅仅是劝人行善,更核心的是体现民意对权威的约束和诉求,体现民意至上的诉求:利泽天下。
6.龙子护母,显然是孝文化的样版;秦始皇隐称祖龙,知南方有龙母,贵为天子也格降迎母,这也是孝文化的真实写照。
7.龙母终未奉旨晋京,敢逆天子权威,始皇帝并不责怪,可见民意不可违,亦可见孝文化之不可违,不能赢者通吃,要有政治伦理,和谐社会的秩序规则也由此缔造。和谐社会的原始真义:民意不可违,权威不滥施,以人为本,天下太平,于此可见。
8.是先秦的儒家文化与南越苍梧的巫道文化的一次尝试融合中的冲突。
龙母文化2000多年盛传不衰,历受文化大革命之浩劫也不能使其毁灭,红卫兵们无人敢动龙母一毫一发,可证神圣之威严及其文化精神之生机不朽。
这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核昭示:民意不可违,权威不滥施,以人为本,利泽天下。
注释:
(1)见清同治版《苍梧县志》;清嘉庆版、同治版《藤县志》 ;民国《藤县志稿》 ; 《肇庆府志》 、 《悦城考通祖庙志》及 《龙母庙》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2)见《苏东坡全集》诗《吾滴海南,子由雷州……》:“九疑连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我行忽至舜所藏……”。
(3) 见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
(4) 见前《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
[1]龙母庙·附录[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2] 何浩.春秋时楚灭国新探[J]江汉学刊,1982(4).
[3]参见百度“图腾”词条。
[4]徐杰舜.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从《楚辞》看楚族的民族特征[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The Cultural Symbol of the Ancient Tribe of Cangwu——The Myth on Dragon Mother and Totem Culture in the Xijiang River Valley
Chen Kanyan
(Wuzhou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Wuzhou 543002,China)
The myth on Dragon Mother in the XijiangRiver valleysuggests that the cultural totemofthe ancient ethnic tribe ofCangwu in the XijiangRiver valleywas converted fromtotemofsnake intothe totemofdragon,the evolution ofwhich kept pace with that ofthe totem ofsnake ofthe whole Chinese nation.Therefore,it is an important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It is obvious that the warship ofDragon Mother in the cultural symbol ofthe ancient tribe ofCangwu is greater and loftier than the warship ofdragon.It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culture ofwater,culture offilial duty,trueness,kindness and beauty.It conveys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harmonious society:no violation ofpublic opinions,no abuse ofauthority,taking human beings as the essential,distributing benefits all over the world,structuringa harmonious society.
Dragon Mother;totem;Cangwu;symbol
G127
A
1673-8535(2011)02-0019-07
2010-12-25
陈侃言,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梧州市历史文化研究协会名誉会长。
高 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