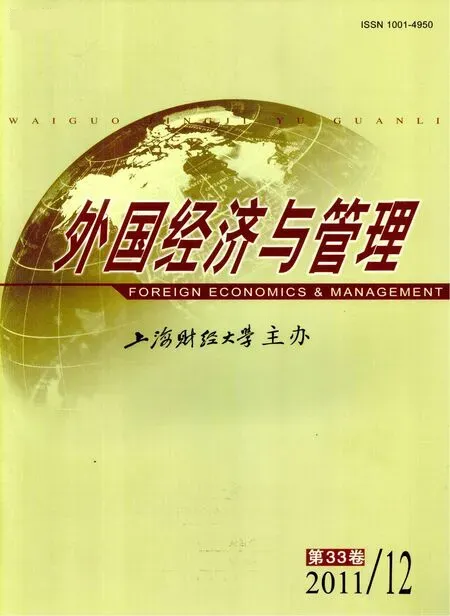泰罗制百年流变探析——兼纪念泰罗制诞生100周年
郭 英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虽然从1911年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原理》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但管理学界对泰罗制的研究兴趣却丝毫没有消减,对不同时期出现的管理理论与泰罗制之间关系的探讨也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在泰罗制诞生100周年之际,有必要深入研究泰罗制的理论流变问题,即探讨泰罗制在时间、地域、技术、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变迁等不同条件下的变形和演进规律;同时还应该探讨不同时期出现的管理理论与泰罗制之间的关系,以判定相关理论是对泰罗制的超越还是继承,这将直接关系到泰罗制研究乃至管理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本文欲对泰罗制的百年流变轨迹进行粗略的梳理,并着重讨论泰罗制研究的三个主要范式以及不同时期出现的管理理论尤其是全面质量管理(TQM)等与泰罗制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问题。
一、泰罗制研究的三大范式
泰罗制一般泛指泰罗在20世纪初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也被称为“泰罗主义”。泰罗制使人们认识到管理学是一门建立在明确的法规、条文和原则之上的科学,它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经过充分组织安排的大公司的业务活动。
在会计史研究领域,先后出现过三种研究泰罗制的基本范式,它们分别是经济理性范式、马克思主义范式和福柯范式(或后现代范式)(Fleischman,2000)。本文认为,这三种范式也完全适用于管理学领域的泰罗制研究,而且在探讨新的管理理论与泰罗制关系的研究中,它们也是比较常用的范式。
长期以来,经济理性范式一直都是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即便其他两种范式对它发起过严峻的挑战,但也未能撼动它的霸主地位。经济理性范式(economic rationalist)有时候也被称为新古典范式(neo-classicalparadigm),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密不可分。该范式认为,泰罗制代表一系列旨在提高效率、创造利润的方法,其主要思想可概括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制定工作定额、挑选最好的工人、实施标准化管理和激励制度。该范式的最基本主张就是“管理就是效率”。在秉持这一研究范式的学者看来,泰罗制有两点对经理人员特别有吸引力:一是泰罗制坚信存在“唯一的最佳管理方法”(the one best way),通过科学实验就能找到这样的方法,这也是泰罗制的思想核心;二是它可以减少工人“磨洋工”(soldiering)的现象,尤其是有计划的磨洋工。在秉持这一研究范式的学者看来,工人“天性就会磨洋工”,这是理性人的一种正常表现。
根据经济理性范式,理性人就是泰罗制的人性假设。因此,这个范式热衷于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来研究泰罗制。英国莱切斯特大学管理学家Wagner-Tsukamoto(2008)认为,虽然泰罗怀有开展心理革命这样美好的愿望,但科学管理在实践中,尤其是早期的实践中遭到了工人的普遍抵制,因为泰罗没能对理性人假设一以贯之,而只是把工人看作是理性人,但却忽视了管理者也是理性人,必须防止他们采取自利行为这一点。因此,Wagner-Tsukamoto指出,如果真想实现心理革命,就必须借助于新制度经济学把劳资双方都看成是理性人,对泰罗制进行重构,引入利润分享等机制。不过,Weisbord(2011)在对泰罗的人性假设与麦格雷戈的X、Y理论进行比较以后指出,在管理实践中,X假设和Y假设同时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主要是指依据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以及Harry Braverman(1974)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来开展泰罗制研究的范式。这个范式认为,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泰罗制的发展,构想(conception)逐渐与执行(execution)分离(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构想活动逐渐集中到少数管理人员那里,工人逐渐被去技能化(deskilling),进而导致技能退化(Braverman,1974)。推行泰罗制的结果便是:工匠的技艺遭到破坏,工人被剥夺了工艺知识和自主权,最终在劳动过程中只能充当齿轮和杠杆的角色。在这一研究范式看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只能雇用工人的劳动时间,但无法保证工人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因此,资本家要面临工人劳动能力不确定的问题,并会想方设法迫使工人在工作中发挥最大的能力。而泰罗制被认为就是这样一种迫使工人在工作中发挥最大劳动能力的管理模式。概括地说,这一研究范式的核心思想就是,资本借助于泰罗制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最终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最大产出。根据这一范式,泰罗制的核心特点就是计划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来实现计划与执行的分离:一是采用科学方法来了解工人所掌握的知识,并把它们转化为规则、程序等;二是把所有的脑力劳动从一线岗位中分离出来并集中在计划部门;三是不让工人决定如何工作,而是精确地规定工人该如何做(Pruijt,2000)。
Braverman(1974)认为,计划与执行的分离或者说去技能化,对于资本家或管理者来说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由于相关知识被管理者或技术专家所垄断,因此,决策权集中在了他们手中。第二,过细的分工使得雇主不再需要雇用人力资本较高的工匠,而只需雇用半熟练甚至非熟练工人即可。后两种工人为数众多,因此,根据供需关系,工人的工资必然会下降,这对资本家来说就意味着成本的下降。此外,后两种工人的可替代性较大,替换工人给资本家造成的损失基本可忽略不计。第三,管理者或者技术专家负责动脑,工人只负责动手,因此,与传统工匠对整个生产过程了然于心不同,泰罗制条件下的工人无法了解整个生产过程,无法了解生产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当然也无法反对管理者的管理(Jaros,2005)。也就是说,泰罗制类似于一种愚民政策,借助于它,资本家就能规避工人的反抗。因此,在Braverman(1974)看来,泰罗制是一种具有多面性的管理模式,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而且也是系统控制工厂的有效手段,是管理层可在阶级斗争中运用自如的有力武器(Jaros,2005)。
马克思主义范式旨在阐明,泰罗制通过精确地规定工人该做什么来减少工人磨洋工的可能性,并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通过决策权上移来实现工人劳动的体力化;通过过细的分工对工人实施去技能化,降低工人的思维能力,提高工人的可替代性,最终弱化工人的抵抗能力;通过采用所谓的“不偏不倚、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来实现对工人控制的正常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其实,由管理控制需要衍生而来的技术不可分割性,使技术不再是一种中性或独立的存在,而是一种与管理方法交织在一起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帮助资本加强劳动控制的有效手段。
所谓的福柯范式,主要是指运用福柯(Foucault)在其1979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来进行管理学研究的范式。正如该书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福柯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社会如何通过规训与惩罚来塑造社会想要的“驯服个体”的过程。福柯认为,封建社会主要通过作用于肉体的暴力惩罚来对人实施控制,而现代社会则采用以收养院、医院、监狱等机构为代表的更加文明、隐蔽的手段来对其成员实施规训。该书运用知识谱系学(genealogy of knowledge)的方法来进行论述,即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对人的惩罚从以暴力为主转向以规训为主,而权力则从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转变为微观、细致的生物权力。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对人的管理出现了不连续性,君主权力为人们所拒斥,而生物权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采用知识谱系学的方法,也就意味着考察社会对人的管理模式的转变,并不存在一种思想比另一种思想更先进的前提假设,而是要关注不同思想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
关于科学管理,福柯范式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科学管理为什么被称为革命性管理,或者科学管理为什么与它之前的管理发生了决裂,也就是说科学管理有哪些鲜明的特点?会计史学者往往倾向于认为,成本会计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成本会计,科学管理第一次采用精确的量化计算方法对人进行规训。美国会计学家、现代会计学的奠基人利特尔顿(Littleton,1957)曾经对泰罗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正是劳动定额和物资消耗定额的产生才催生了标准成本,并且为现代会计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从更大范围的组织和管理研究来看,用精确的量化计算方法对工人进行规训,导致量化的精确知识成为管理者的权力来源,这正是科学管理的独到之处。
关于量化的精确计算知识,我们可以比较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科学管理出现之前的例子。McKinlay(2006)运用福柯的规训思想对工业革命早期的管理实践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New Lanark工厂的管理实践进行了分析。McKinlay认为,欧文最出名的规训发明也许是“沉默的监视(silent monitor)”。这种管理方法的操作思路是把一方小木块的四个侧面涂上四种不同的颜色以表示工人不同的工作绩效。当时,不光New Lanark工厂记录工人的工作绩效,英国的其他棉纺厂也用“耻辱账户”(disgrace account)来记录工人的行为和绩效。不过,McKinlay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工厂主会把这些数字符号集中起来,更不用说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分析,并据此对工人的行为做出干预。没有数据的积累,没有系统的干涉以测量和修正行为,没有工厂管理制度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下结论说这就是粗浅形式的权力或知识。第二个是科学管理出现之后的例子。在Sewell和Wilkinson(1992)关于Kay工厂的研究中,他们也提到了类似的规训策略,每个工人的上方都有一个类似于交通信号灯的电子牌,根据工人前一天的表现显示相应的黄色、红色、绿色。而这种电子牌显示的颜色被作为团队内部同事监督与上级监督的依据,无论是团队内部的同事还是上级督导都据此来对不合格的成员进行规劝、培训甚至辞退。
Clegg等(2006)指出,英国《济贫法》的立法初衷是解决如何让失地流浪农民进工厂工作的问题,但是,该法案仅仅解答了农民为什么应该(进厂)工作的问题,并没有回答如何工作的问题,而科学管理解决的正是如何让进厂的失地农民以更高的效率工作的问题。但在提高工人的效率时,资本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自己并不了解工人的劳动能力,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的劳动能力处在黑暗之中,而黑暗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因此,资本家面临着工人“磨洋工”的问题。怎样让工人的劳动能力变得可见,或者说,如何使工人的劳动行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预期的问题在福柯那里就表现为:如何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期望。福柯通过重新阐释18世纪英国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举的“全景敞视塔”(panopticon)监狱例子,详细解释了这种能够驯化个体的规训技术。福柯认为,全景敞视监狱代表了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规训方式。按照福柯(1979)的说法,现代管理跟古代全景敞视塔发挥了相同的监控功能。“全景敞视塔是一种监控百姓的一般化模式,在日常生活中执行监控任务,确定各种权力关系。”泰罗通过动作研究把工人的劳动能力充分暴露在资本家面前。资本家可以清楚地了解工人的劳动能力,导致工人必须按照科学管理所设定的标准来从事劳动。
由上可见,以上三大研究范式侧重点各有不同,经济理性范式强调的是效率、人性假设,马克思主义范式强调把泰罗制放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来分析,而福柯范式则认为泰罗制是现代社会文明进程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把其成员驯化成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一思路在工厂管理中的体现。
二、新泰罗制与后泰罗制之争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新理论与泰罗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直关注日本管理的Clegg(1990)认为,关于柔性制造系统的观点大致有三种,可以分别被称为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新管理主义(neo-managerialism)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观(neo-Marxian critique)。
持新浪漫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一个关键的断裂点上,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丢失了的前现代社会的社区以及像19世纪家庭手工业工匠传统这样的一些乌托邦梦想有可能会失而复得。在新管理主义看来,所谓的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柔性是指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过程的再造,而专业化则是指对专业市场或者利基市场的占领。新管理主义强调,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组织需要柔性,但组织柔性离不开依照日本管理模式对柔性雇员进行开发。新管理主义的信条就是“让管理者来管理”,这也是科学管理的基本准则。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新管理主义者所关注的并非是一种时代的断裂。他们更愿意用新福特制(neo-fordism),而不是后福特制这个词来概括泰罗制,并且认为新福特制这种资本对雇佣劳动的进攻(offensive)实践和残酷压榨——通过降低劳动报酬和抨击劳动力保护法来建立高弹性的劳动市场以提高边际利润的战略,仍然保留了建立在科学管理原理基础上的泰罗制大规模生产模式。集体合作、技能丰富化被认为是新福特制的新的控制手段。在他们看来,新福特制关注如何重新获得、利用和控制那些工人曾经拥有但被剥夺了的关于生产过程的默会知识。对于资本家如何把工人的劳动力转化为实际有效的劳动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资本家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如Burawoy,1979)则认为,一旦进入生产车间,工人的所作所为便不再光能用“强制”来解释,还应该考虑另一个因素,即工人的应允(consent)。
Lomba(2005)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关于新出现的管理理论是对泰罗制的继承还是抛弃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可通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模式(JIT、团队工作制、职工参与制)和美国模式(模块化生产、员工个性化发展)代表了一些不同于泰罗制的控制工人的新手段,应该把它们称为后泰罗制(post-Taylorism);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认为,新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如自动化生产、电子监控、柔性生产团队等,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粗浅的改进,而泰罗制的精髓——劳动分工——并没有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的管理技术加剧了分工的碎片化,强化了对工人的控制,实际上是弱化了工人自治。因此,后一种观点是一种新泰罗制(neo-Taylorism)观点。
本文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新泰罗制与后泰罗制之争,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在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范式。从时间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Braverman(1974)的观点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Jaros,2005):首先是Michael Burawoy(1979)以及后现代管理学者从理论上对其进行了批评;其次,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现实中不仅存在去技能化的问题,而且还存在技能升级的现象,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技能升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Adler,2004)。
Piore和Sabel(1984)的柔性专业化理论,戴明等人的TQM理论以及 Womack、Jones和Roos(1991)的精益生产理论,都对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去技能化观点发起了挑战。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就是都认为:由于团队取代个人成为最基本的工作单位,作为个体的团队成员都必须掌握多项技能,并且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因此,泰罗制所主张的那一套已经过时,它们才是一种代表与泰罗制决裂的力量,可被称为后泰罗制。
后泰罗制认为,由于团队取代个人成为基本工作单位,新的管理理论在以下几方面实现了对泰罗制的超越:(1)团队制工作减少了管理层次,因而意味着决策权下放,工人享有一定的自主权。(2)由于决策权下放,工人需要参与决策,因此,工人的劳动不再仅仅“被体力化”,或者说工人不再仅仅要“更辛苦地工作”(work harder),而且还要“更聪明地工作”(work smarter),也就是说既要动手又要动脑。(3)每个团队成员都必须不断通过接受培训或者开展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技能,从而导致团队成员的技能多样化和升级化,而不是去技能化。(4)资本家通过科学管理对工人实施的直接控制为团队共识、团队价值观等取而代之,资方不再通过控制工人来提高效率。因此,Sewell(1998)在总结这些后泰罗制理论的基本观点时指出,这些新的管理理论实现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双赢(Sewell,1998),即资本家达到了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而工人收获了扩大自主权的好处。
这种后泰罗制乐观情绪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批评。David Boje(1993)就批评指出,通过对TQM的解构,可以发现TQM不过是日本在现代主义背景下对泰罗制的基本原则进行修饰的产物,TQM中的持续改进依旧离不开动作和时间研究。团队工作制似乎是改变了层级制下上级控制下级的模式,相对于传统的泰罗制工作方式好像是提高了团队成员的工作参与度,而且还丰富了他们的工作技能。但实际上,在团队内部,每个成员都可以观察到其他成员的活动,而且任何一个成员都能感受到别人的这种“凝视”眼光,因此,传统的一个管理者“凝视”多个工人的控制模式为多个团队成员“凝视”一个同事的控制模式所取代,而且这种由团队成员的“凝视”目光构成的监督网络相对于传统的层级制监督模式而言,少了明确的权威中心,因此,这种全景敞视式的控制较之层级制控制模式更加难以抵制。而TQM所倡导的对工人任务的再技能化(re-skilling),或者说工作丰富化(job enrichment),看起来加大了对工人的授权,但事实上只提高了工人的可替代性。而且,工作丰富化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不会回到传统工匠、艺人时代的丰富化程度。Hackman和Wageman(1995)就曾经指出,TQM有一种两难困境:对组织成员进行充分的授权以实现集体目标与企业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模式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不过,在Boje(1993)看来,这种潜在的冲突很少会实际发生,因为集体目标往往也是由管理层设定的,而且对组织成员的授权也是相当有限的。泰罗曾经认为头等工人就应该像沉默的公牛一样劳作,而TQM要求一线员工不断提出高质量的意见或建议。实际上,虽然一线员工能够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但从技术层面讲,技术专家也能提出类似的建议。显然,管理层之所以重视一线员工的建议,是因为一个人很难反对自己提出的建议:如果改进工作的建议是由一线员工提出的,那么,即便相关建议会增加他们的工作负荷,也很少会受到他们的反对。
Steingard和Fitzgibbons(1993)也曾指出,TQM依然建基于Morgan(1986)的机械隐喻之上,每个员工被要求围绕机械系统运转。他们也认为,传统的上级对下级的规训式“凝视”为员工的自我监视、自我控制所取代。持续改进意味着对成本、收益的不断优化,意味着一线员工“磨洋工”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与泰罗为了减少工人磨洋工而提倡的动作与时间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泰罗制的典型研究工具秒表在TQM中依然得到了沿用,只不过现在持秒表的不再是工程师、管理顾问,而是一线员工自己。Hackman和Wageman(1995)研究发现,在实施TQM的企业里,一线员工还被希望找到持续改进和简化工作过程的方法。这种方法一旦被找到,就会被记录下来,然后被标准化并在企业内部推广。结果,一线员工就基本丧失了决定如何工作的自主权。
Sewell和Wilkinson(1992)在仔细考察上述Kay公司以后指出,在这家实行TQM的公司里,没有设置福特制模式下的缓冲槽,目的就是要减少一线员工磨洋工的可能性;大量使用电子监视设备,原因就在于电子监视设备较之上级监督下级的传统模式更加接近完美的全景敞视监狱;团队工作制的有效实施是电子监视与同事监视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Sakolsky(1992)使用福柯的规训权力(discilinary power)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来解释工作场所的计算机监督支配(如计算机辅助生产)与质量小组活动。Sakolsky认为,在支配劳动过程方面,除了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严密控制劳动过程节奏的做法之外,还有福柯所谓的以更隐晦的方式支配劳动过程的微观规训技术(micro discilinary)。
以上这些学者基本上是借用福柯的规训概念来揭露新的管理理论在新的技术背景下保留泰罗制理性化的实质。本文认为,福柯的观点还可用来讨论TQM管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比如,Zbaracki(1998)就曾经指出,好像存在两个版本的TQM,第一个版本的TQM偏技术化,有一系列定义明确的组织干预措施,对如何使用和分析信息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二个版本的TQM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它远远超过了戴明、朱兰等人当初的统计概念。Zbaracki认为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要用制度理论来解释,但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也可用福柯的理论来解释。作为一种规训模式,科学管理的边际贡献率正在不断下降,员工对它的抵制也在不断加强,因此,任何有可能在员工与科学管理之间建立起直接关系的管理方法都有可能招致员工的抵制。从员工的角度来讲,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而对管理层来说,哪里有抵制,哪里就要调整行使权力的策略以驯化抵制者。因此,TQM技术色彩的弱化恰恰说明管理层已经意识到了以往种种在科学管理模式下行使权力的策略的局限性,因此有意突出TQM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授权、参与决策等等,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有效控制,从而对工人的驯化从身体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虽然马克思主义范式在团队工作制这种新的工作方式面前暴露出一些不足。例如,Braverman关于技能的定义主要偏重于体力劳动,没有论及工人的社会技能等其他一些技能,也很少关注工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默会知识。而且,他也没有考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以及工人为何愿意参与看起来对自己不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问题(Meiksins,1994)。但是,Braverman的劳动过程理论在面对新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时依然有其不可比拟的理论洞察力,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的一些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虽然员工持股计划等导致劳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没有变,只不过基本的工作单位由个人变为团队而已,目的在于更好地降低一线员工对控制的抵制,更有效地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流趋势并未改变(Meiksins,1994)。因此,我们应该在保留劳动过程学派批判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就是一个方向。
由于马克思主义范式强调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因此,它与福柯范式的一个可能的连接点就是对后科层控制模式的批判。后科层控制模式是由Richard Edwards(1979)在《充满斗争的领域》一书中研究现代工作场所控制模式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利用美国一些大公司(如IBM、AT&T、GE、Polaroid、Ford Motors等)的数据来说明,自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工作场所控制方式也从直接控制(又分为资本家亲自控制和层级控制)转变为结构控制(又分为技术控制和科层控制)。这些变化的主要触发因素就是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即资本家、工人和其他阶级为了保护和增进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Edwards认为,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种控制模式:一是直接控制(direct control),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这种控制模式通过直接的监控来实现对工人的控制。二是技术控制(technological control),典型代表是流水线生产,始于20世纪初,这种控制模式随着泰罗制的流行而得到强化。三是科层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盛行于“二次大战”以后,通过非人性化的正式规则和程序来实现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可以看出,Edwards所阐述的这三种控制模式都偏重于对工人或员工身体的控制,而没有涉及情感和心灵控制。在Edwards(1979)看来,工作场所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怎样组织工作,采用多快的工作节奏,工人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工作、可以享受哪些权利,以及不同雇员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等问题,都是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问题。当雇主企图最大限度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工作“努力”(effort),而工人必然会抗议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时,工作场所就会变成战场(Ed-wards,1979)。面对工人的抗争,雇主必然会通过重新组织劳动过程来缓解矛盾,通常就是重构控制结构以减少工人的抗争(Edwards,1979)。
Edwards(1979)注意到上述三种劳动控制模式不完全适用于高科技产业的知识员工,并且预测未来会出现后科层控制模式(post-bureaucratic control)。我们认为,后科层控制模式是由知识员工工作方式的两个特点所决定的:一是责任自主制,二是团队合作。责任自主制要求知识员工参与工作内容设计,但执行可完全由他们自己掌控,前提条件就是在规定的时间里按质按量完成工作或者递交合格的产品,因此无需现场监督或者打卡坐班。此外,高科技工作讲究团队合作,许多研发活动与计划不是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而团队工作方式能够提供同侪学习(peer learning)的机会,创造团结合作的工作氛围。因此,这种既自主又不乏参与性的工作组织方式被认为比较人性化且又能维护劳动者的尊严,是一种通过组织安排来造就积极主动的员工(active worker)的管理模式(Hodson,1996)。
马克思主义范式与福柯范式的结合,能够很好地解释心灵控制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柔性专业化、TQM和精益生产等都强调减少对工人的控制,并提高他们的自治性。但有研究表明,在实践中,控制和效率依然密切相关(Barley和Kunda,1992)。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再是Peter Senge(1990)所谓的“如何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实现控制”,而是“如何在看起来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实现控制”(Graham,1998)。Tompkins和Cheney(1985)曾提出过“协同控制”的概念,并且认为这就是一种后科层制控制模式。Barker(1993)通过研究ISE Communications公司自我管理团队发现,在这家公司的自我管理团队里,成员个人会因为感受到来自同事的巨大压力而被迫遵守团队规范,这就是“协同控制”的一种体现。Barker认为,与传统的科层制控制相比,协同控制在概念上和实践中都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但它遵循的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依然是不断提高理性化程度。Sewell(1998)认为,现实中企业不仅采用团队工作制,而且还采用电子监视设备,正是电子监视设备的采用使得推行团队工作制成为可能。如果只有团队内部的压力和实行协同控制,那么,在每个团队成员并不能清楚了解别人的工作绩效,尤其是那些表现较差的成员的工作绩效的情况下,就会因为出现搭便车问题而导致团队解体。相对于传统的控制模式(在传统的控制模式下,管理者也许会打瞌睡,而电子眼显然不会有这种问题),电子监视设备的采用大大提高了管理者监督团队成员表现的能力。在现代企业里,传统的垂直监督模式依然存在,但监督针对的不再是个人,而是团体,另外还出现了水平监督,即团队内部的协同控制。所以,Sewell(1998)认为,在团队工作制条件下,自治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自治不仅意味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拥有一定的决断权,而且还可以“通过建议、示范和规劝来对团队其他成员的工作施加影响”,自治不再是个体意义上的自治,而是团队意义上的自治。因此,水平监督与垂直监督的结合,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新的规训方式,即“借助于理性化的监视和团队内部的规训力量的复杂互动来实现名义上的自治和实质上更加严厉的控制”(Sewell,1998)。从结合马克思主义范式和福柯范式考察团队控制问题的研究中不难看出,这些学者大多认为,传统的泰罗制技术控制模式已经让位于强调协同控制的后科层控制模式,但后科层控制模式遵循的是与泰罗制控制模式相同的逻辑,即不断提高工人、员工或团队工作的理性化程度。
三、对泰罗制的反动——反泰罗制
泰罗制除了监督成本高,面对多变的市场缺乏柔性,不利于培养员工的创造性、高层管理者信息负载过重,对一线员工缺乏吸引力等缺点之外,还往往会因为自身所带有的独裁专断色彩而与民主原则发生冲突(Pruijt,2000),因此,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进行了一些所谓的反泰罗制管理尝试,试图找到一种与泰罗制彻底决裂的管理模式。
从形式上看,反泰罗制在某些方面与新泰罗制十分相似。例如,反泰罗制主张以团队为基本工作单元,也试图消除泰罗制所造成的计划与执行的分离,也会导致劳动强度的加大。
不过,仔细分析也不难发现反泰罗制与新泰罗制存在明显的区别。首先,反泰罗制跟源自于对泰罗制的修正的TQM等新泰罗制管理模式不同,思想渊源更加多元化。事实上,反泰罗制的团队理论、劳动过程理论与两个最前沿的问题有关:一是马克思、韦伯(Marx Weber)、福柯等关心的工作场所监督和规训方法。反泰罗制发展的一个特殊方面就是新的劳动组织方式,如JIT和团队工作制。二是Mike Savage、James Barlow、Peter Dickens和Tony Fielding(1992)等关注的经理阶层的崛起、工人技能退化和地位下降问题,特别是组织扁平化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正经历了从泰罗制劳动过程向后泰罗制劳动过程的转变,解释这一现象的代表性理论有Aglietta(1976和2000)的调节理论、Piore和Sabel(1984)的弹性专业化理论、Atkinson和Meagher(1986)的弹性企业模型和精益生产与日本化管理,而企业实践的典型案例就是沃尔沃的半自治团队。反泰罗制包括社会技术系统设计、工业民主和工作生活人性化等思想(Pruijt,2003),但社会技术系统设计等管理思想在人性假设等方面明显不同于TQM,坚信一般人也有能力学会操作复杂的生产系统,并且希望获得管理复杂生产系统的机会(Niepce和 Molleman,1998)。
其次,反泰罗制所主张的团队工作制没有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改善工作生活质量的前提条件,在反泰罗制的工作团队中没有专门的团队领导人,而是团队成员轮流坐庄充当领导人的角色。而在日本的TQM中,团队领导人往往是固定的,既负责决策又从事生产活动(Pruijt,2003)。也就是说,在反泰罗制工作团队中,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决策,而在新泰罗制工作团队里,参与决策的成员是非常有限的。英国管理学家Jay在著名的团队问题专家Belbin(1984)所著的《管理团队:成败的原因》(Management Teams:Why They Succeed or Fail)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企业太执迷于员工个人的素质、经验和成就;它们专注于有关员工挑选、发展、培训、激励和晋升的问题,并且对于员工个人的优、缺点进行喋喋不休的评论。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对于某一特定工作而言,是不可能找到最理想的人选的,因为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反泰罗制的核心思想就是:能否赢得和保持管理成功这主要取决于团队(而非某个个人)、团队的整体表现以及团队内部的异质性成员对团队产生的不同影响。
再次,与新泰罗制无限追求理性化不同,反泰罗制虽然也追求技术进步,这自然也要用到科学管理中的动作研究之类的技术,但对理性化的追求不是无限制的(Pruijt,2003)。在TQM等的新泰罗制实践中,持续改进的思想要求工人不断努力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其表现形式就是不断减少操作中不必要的动作,从而使工作任务变得更加简单。同时,工人寻找更好方法的活动独立于其日常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段。一个是按照规定进行标准化操作的时段,这可以看作是受泰罗制束缚的时段;另一个是参加质量小组活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段,这一时段可以看作是摆脱了泰罗制的束缚。不过,后一时段相对于前一时段而言要短得多,有可能一个月里就那么几个小时而已(Benders和van Hootegem,1999)。此外,工人找到的新方法也必须经得起检验,然后才有可能被标准化并得到推广。因此,“持续改进意味着生产的持续理性化”(Niepce和Molleman,1998)。而在社会技术系统设计等反泰罗制的管理实践中,对工作过程的持续再设计意味着不断的试验和学习,在这一点上与新泰罗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这种再设计是团队成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因而能够丰富他们的日常工作。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反泰罗制条件下,既然要赋予团队自主权,那么就应该相信团队的创造力,而不应该过多地干预团队决策,更不应该强调对“唯一最佳方法”的追求。
最后,相对于泰罗制、新泰罗制在全世界的流行而言,反泰罗制暴露出稳定性差、普适性不强的问题。从地域看,反泰罗制主要出现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等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家,而且也都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如经济高涨、失业率较低,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获得成功(Pruijt,2000)。如果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管理尝试就有可能失败,如沃尔沃公司的半自治团队试验就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法国学者de Montmollin(1975)指出,虽然反泰罗制这种思潮非常流行,也很容易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但它背后隐藏的过分乐观主义的思想值得警惕。虽然新泰罗制与反泰罗制都提倡团队工作制,但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团队工作制(Pruijt,2003)。
我们认为,反泰罗制实质上强调的是管理应该尽可能释放员工的潜能。管理学多年的研究证明,大多数员工并没有把自己的创造力和智慧全部用在工作上。如果管理者能够释放这部分员工个人自由控制的能量,并把它集中用于改进企业组织现行的运作模式,那么,组织将受益无穷。为此,管理者应该为员工设计两份工作,并建立两种团队:一是“日常工作”,即协助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并组建“现在团队”(present team)来对现在的组织进行变革,以便组织能够更快地回应顾客,“现在团队”的工作重点就在于围绕不断完善的组织模式来不断改进组织现在的工作。在组织模式的完善过程中,管理层次趋于减少,工作程序变得越来越便捷,团队工作制日趋普遍,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日益密切。简言之,就是创建一种反应更快、更具柔性的企业组织。二是“变革工作”,这种工作由所谓的“未来团队”(future team)来完成。“未来团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未来,或者说创造未来顾客和未来市场,其重点在于组织及其管理创新(Blanchard和Waghorn,2005)。只有组建这样两种不同的工作团队来完成两种不同的工作,企业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组织。换句话说,企业必须同时组建两种不同的团队来实施两套不同的战略。
我们认为,反泰罗制对劳动过程的监控就是后科层控制模式,这是一种值得玩味的控制模式。实质上,它意味着管理阶层用信任、授权和自主等修饰词来掩盖其追求效率与实施控制的真正目的(Sewell,1998;Barker,1999)。首先,责任自主制意味着员工必须要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种对工作的控制不是来自于上级的直接监督,而是来自于任务本身。其次,计算机已经成为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每个员工的工作状况完全可追踪记录,因此,责任自主并不意味着免于被监控,反而受到了“电子全景监控”(electronic panopticon)(Callaghan和Thompson,2001)。最后,团队工作制也意味着源自于团队成员协同控制的同侪压力,团队成员不仅要分工合作,而且都知道彼此的工作状况,这种团队成员之间的工作状况透明化迫使每个团队成员必须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地工作,不能成为团队的害群之马(Sewell和Wilkinson,1992)。因此,后科层控制是一种根据福柯(1979)的“全景敞视论”(panopticism)对知识员工实施有效控制的手段,与Edward所提到的直接、技术和科层控制不同,是一种直接源自于工作任务与团队伙伴的社会控制,也是一种知识员工工作自律的规训机制,从知识劳动者的身体出发,把规训内容“铭刻”在每个劳动者的身体上,并且让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驯化。这种权力关系不再是一套外显的控制体制,而是隐藏在身体监控背后,迫使被驯化的行为主体“自动、自发”地努力工作。
四、结 语
福特公司的装配流水线、丰田公司的TQM和沃尔沃公司的半自治团队被认为是工作设计的三大范式(Pruijt,2000)。或者说,它们分别代表了泰罗制、新泰罗制和反泰罗制的工作设计模式。在我们看来,泰罗制强调的是“让管理更有效率”,新泰罗制强调的是“让管理更有人性”,而反泰罗制强调的则是“让管理尽可能释放员工的潜能”,它们分别代表三种完全不同的管理价值取向。
在《科学管理原理》问世百年之际,重新回顾泰罗制的发展轨迹及其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对一种理论的关注,而是要重新梳理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通过对泰罗制百年流变轨迹的粗略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泰罗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认为泰罗制早已过时、管理理论已经实现了一轮又一轮的突破的观点都有误导之嫌。百年管理学依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们距离现代管理的起点并不遥远。
从研究范式来看,经济理性范式、马克思主义范式和福柯范式这三大泰罗制研究范式,也在相互融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范式与福柯范式的结合,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结合,即所谓的批判性后现代管理(critical postmodern management)问题,已经成为后现代管理研究的一个新趋势。管理和组织研究的“范式之战”看起来出现了缓和的迹象,而且似乎越来越偏向于Pfeffer(1993)的论点——范式的统一可能代表着管理学发展的主要方向,而库恩所强调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也许并不适用于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
从新泰罗制与后泰罗制之争以及对新泰罗制与反泰罗制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管理学研究既强调建构又重视批判性反思,Mats Alvesson、Cynthia Hardy和Bill Harley(2008)等学者认为对管理和组织研究的反思可以分为两种,即R型反思与D型反思,这里的“R”是指“重构”(reconstruction)、“再造”(reframing)、“再生”(reclaiming)、“再现”(re-presentation),而“D”则是指“解构”(deconstruction)、“辩护”(defence)、“抨击”(declaiming)、“去固定化”(destabilizing)。研究者应该在研究中辩证地运用这两种反思模式,要指出现有知识的不足,然后构建不同的新知识。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充斥了太多的时尚理论,因此,保持批判性反思对于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TQM为典型代表的新泰罗制带有鲜明的日本文化特点,而以社会技术系统为典型代表的反泰罗制则带有鲜明的欧洲发达国家讲究所谓的民主的特点。我国从20世纪初经穆藕初等人引入泰罗制开始,50年代末对“马钢宪法”的批判衍生出“鞍钢宪法”(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是后福特制的萌芽)这样一种带有鲜明我国本土特色的管理模式。我国本土化的管理模式在泰罗制的流变过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可能是我国管理学者应该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
*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罗珉教授提供的悉心指导和对论文的修改,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1]Blanchard K and Waghorn T.The system:A story of intrigue and market domination[M].London:Perseus Books,2005.
[2]Boje D.The resurrection of Tayloris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s hidden agenda[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1993,6(4):57-70.
[3]Clegg S R.Modern 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s studie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0.
[4]Clegg S R,et al.Power and organization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
[5]Fleischman R K.Completing the triangle:Taylorism and the paradigms[J].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2000,13(5):597-623.
[6]Hackman J R and Wageman R.Total quality management:Empirical,conceptual,and practical issu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5,40(2):309-342.
[7]Jaros S.Skill dynamics,global capitalism,and labour process theories of work[J].Tamara Journal,2005,15(5):5-16.
[8]Lomba C.Beyond the debate over post-vs neo-Taylorism:The contrasting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work practices[J].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05,20(1):71-91.
[9]Morgan G.Images of organizations[M].Beverly Hill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86.
[10]McKinlay A.Managing Foucault:Genealogies of management[J].Management & Organizational History,2006,1(1):87-100.
[11]Niepce W and Molleman E.Work design issues in lean production from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Neo-Taylorism or the next step in sociotechnical design?[J].Human Relations,1998,51(3):259-286.
[12]Pruijt H.Repainting,modifying,smashing Taylorism[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2000,13(5):439-451.
[13]Pruijt H.Teams between neo-Taylorism and anti-Taylorism[J].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2003,24(1):77-101.
[14]Sewell G and Wilkinson B.“Someone to watch over me”:Surveillance,discipline and the just-in-time labour process[J].Sociology,1992,26(2):271-289.
[15]Sewell G.The discipline of teams:The control of team-based industrial work through electronic and peer surveilan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8,43(2):397-428.
[16]Sewell G and Barker J R.Coercion versus care:Using irony to make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surveill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4):934-961.
[17]Steingard D S and Fitzgibbons D S.A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1993,6(5):27-42.
[18]Wagner-Tsukamoto S.Scientific management revisited:Did Taylorism fail because of a too positive image of human nature[J].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2008,14(4):348-372.
[19]Weisbord M.Taylor,McGregor and me[J].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2011,17(2):165-177.
[20]Zbaracki M J.The rhetoric and reality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8,43(3):602-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