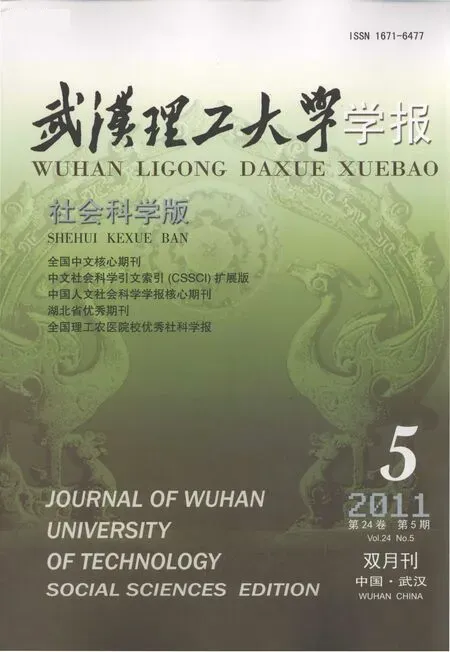科技哲学视阈中的幸福
彭列汉,曹夏鹏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3)
幸福是人生的追求与目的。格雷曾说:“幸福——人类一切追求的最终目的。”[1]科技作为为人类谋取福祉的事业,一直为人类所重视,所推崇。特别是在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主体价值体系更加多元化、立体化,科技发展与人类幸福的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下,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犹为重要。
一、幸福的伦理本性
幸福问题是伦理学领域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众多思想家的关注。“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2]。以至于有学者声称:“把幸福作为研究课题是一件冒险的事。”[3]
有学者认为,幸福是人性得到肯定时的主观感受。幸福有几种形式:正面对人性的肯定,即我们常说的快乐;反面对人性的肯定,虽在该过程中产生的是沮丧、愤怒等情感,但仍是幸福的一种形式,是道德良心的表现;因人性的复杂形式而产生交织着正反两面的体验,如爱与恨的幸福感。由此可见幸福的本质是“心理体验和伦理规定的统一”[4]1。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说:“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5]费尔巴哈所讲的幸福同样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之上的,他把快感和情欲的满足作为幸福的标志,提出“没有感觉就没有幸福”,认为心灵的感应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6]。而莱布尼茨强调理性的幸福,他认为“理性与意志将我们引导走向幸福,而感觉与欲望只能把我们引向快乐”[7]。德谟克利特也曾明确指出,“使人幸福的并不是体力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8]52-53。德国哲学家包尔生将这种理性的幸福观发展到自我实现主义的幸福观[9]。在他看来,人类的幸福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快乐主义幸福(即感性的幸福),一种是自我实现主义幸福(即理性的幸福)。幸福指向主体本身,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梭伦认为“谁拥有最多的东西,谁才能戴上幸福的头衔”[10]。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幸福观。然而在古希腊先哲们看来,财富匮乏固然会使人受到物质的羁绊,自由受到束缚,但对财富的欲求过多,往往也容易使人在对财富的追逐过程中心灵受到束缚,同样也不自由。于是“梭伦对人的幸福作过一番很好的描述:这就是具有中等的外部供应,而做着高尚的事情,过着节俭的生活”[11]。一个中等水平的财富才应该是人们向往的目标,因为这样可以使人去做“合于德性的事情”,去享受自由。其实这与马塞尔的不等式“有≠是”有异曲同工之处[12]。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不等于就拥有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幸福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幸福是心理体验与伦理规定、感性与理性、精神圆满与物质满足的角度统一。
二、科技发展与幸福相互联系之可能
作家毕淑敏认为:“科学与幸福一个是情感的范畴,属于精神的领域。一个是物质的范畴,属于无生命的领域。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虽然有的时候,轨道会发生小小的交叉。”[13]这与休谟的观点一致,认为科技强调理性,而幸福应该是感性的范畴,两者关联度不大甚至无关。培根则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相信科技会给人们带来福祉[8]345。即使是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科技将是未来人类具有最大幸福和祟高道德的保证。科技发展与人类幸福是否有联系?两者发生联系何以可能?
近代,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征服与控制的关系。虽然科技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但人类社会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及社会危机,而罪魁祸首却是科学技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科学技术的异化。于是,人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盲目发展,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负荷着“正价值”,而且也负荷着“负价值”。于是科学技术由于价值负荷概念而进入了伦理学领域,并与“心理体验和伦理规定的统一”而幸福联姻。
我们亦可通过对“价值”这个概念的界定来对其作进一步分析。从广义上来看,价值是指当主体与客体发生作用时,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即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样,因为从价值论上来讲,“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科学技术由于负荷价值即要满足人类主体的“需要”,而与人类幸福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14]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不仅具有形而下的工具意义的物理关怀,而且具有形而上的价值目的的终极关怀。这就应和了人类幸福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观念。由此可见,科学与幸福并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也不是偶然“有小小的交叉”,而是一直相伴相生。
人类幸福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的统一,科技在谋取人类幸福的事业上,首先是作为工具价值存在的,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同时,也间接地满足精神需要,这样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幸福就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盲目的,是为发展而发展的,它应该在一个框架内或者规范下发展才能避免盲目性和恶魔化,这样人类幸福就规范科技发展方向的角色,科技发展的起点是与人类幸福有关的。所以说科技发展是人类幸福的基础,人类幸福要成为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并规范科技的发展。
三、科技哲学视域中幸福认识的误区
从古至今,由于人们生活的环境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不同,在对待科技发展与公众幸福度的关系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区。我们可以将这些误区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误区一:幸福=田园之乐
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幸福就是与科技无关的田园之乐。如庄子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而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成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5],向往回归到结绳记事的纯真年代。“孔颜之乐”是儒家幸福观的典范,是一种所谓安贫乐道的幸福。在孔子心目中,精神的历练,灵魂的圆满,德性的不懈追寻,能使人忽略物质而真正达到幸福的彼岸。总的来说,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主流的孔孟老庄尊崇精神世界的圆满,淡化物质世界的享受,淡化“技艺”对生活的改造。近代奕缳、倭仁等保守派人士更是敌视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西方的科技都是奇技淫巧,立国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西方文化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如赫拉克利特认为,科学研究是为了按自然办事,听自然的话,即认识与服从“逻各斯”,以便过上理性的、道德的生活,达到认识幸福的目的。这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待科技的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不重视科技与人类造福的密切关系。
诚然,古代人通过拼体力,拼物力,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是古代人民会感到幸福吗?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们用生命换来了征服自然的壮举。
反映了人类在缺少对自然力有效掌控的情况下幸福感是缺失的。如果说远古时代科技的不发达是人类的必然阶段,那么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就是人为的灾难了。中国近代由于不重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发展极其缓慢,中国人处处被动挨打,成为“东亚病夫”。社会总体不幸福,个人就更不幸福。科技发展是人类幸福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幸福只是纸上谈兵。
(二)误区二:科技是天使——科学乌托邦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逐渐成为承载人类幸福的主宰。早在17世纪,培根就提出“科学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科学”的口号,一下子把科学摆在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随后科技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了生产力,在邓小平那里成了第一生产力。伦理学家们认为幸福就是满足需要,可以说科技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似乎幸福指数就会相应地提高。所以自19世纪至今的200多年里,很多人预测科技乌托邦即将到来,相信科学技术将会把人类从劳动、疾病、痛苦,甚至死亡中解脱出来。科学乌托邦主义传统认为:“一旦科学到来,科学就为获得真正的知识而努力,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更广和更加总体化,因此我们解开任何事物的秘密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科学的觉醒,自然地就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安逸的工作、个人的实现甚至是永生。”[16]人类陷入了科学万能的盲目热情之中不能自拔。
诚然科技发展为幸福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科技并不必然导致幸福的出现。科技进步是幸福的基础,但单单有基础是远远不够的。早在科技革命兴起,工业革命呈席卷之势的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就认为科学作为资本与人对立。“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17]。如前文所说,幸福是个体体验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体力劳动强度的相对减少,个体的生活在相比以前的社会是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在社会制度影响下,大工业生产对于工人的各种要求却相应地提高,工人失去了自由,就毫无幸福可言。
当代人会认为马克思时代出现如此情形是因为科技不够发达所致,那么在科技已极大发展的今天又如何?即使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今天,有些问题如海啸、地震、死亡、疾病等等,依然是目前科学还不能解决的。尽管当今世界各种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呈现蓬勃之势,但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科学充满盲目乐观的科学乌托邦思想,特别是在那些相对落后的现代化正在进行中的国家与地区,科技俨然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是福是祸殊属难料。
(三)误区三:科技是魔鬼——科学霸权
18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史无前例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惠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人们生活在这个被科学技术所雕凿的社会就一定幸福吗?答案是否定的,20世纪开始,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对社会而言,普遍的富足与相对的贫困同在,无限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并存。在现代性的境域中,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对未来都呈现一种迷茫状态。在风险社会中,出现了反科学的人文思潮,其把战争的残酷,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都归罪于科学以反对所谓的“科学霸权”,作为天使的科学一下子被贬为魔鬼的化身。这从而致使社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普通大众,也跟着摇起“反科学”的大旗。
不可否认后现代性的科技观将人们从盲目迷信科技的泥潭中唤醒,将之引向对现代性的反思状态,使人类开始审慎地运用技术。然而其中极端者却将“科技异化”等同于“科技”,对科技本身进行批判。科技并非是魔鬼,如果真有魔鬼的话,那也是滥用科学的人类,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工具。”[18]科学的妖魔化其实是人类自身的妖魔化,那种忽视科技发展是为全人类造福这一终极目标,为各种各样膨胀的欲望和利益所驱使,铤而走险,毫无节制地滥用科学技术最后达到危害人类自身的地步,却将其恶果嫁祸于科学的行为,就是对科学的妖魔化行为。
四、科技发展切入人类福祉的途径
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属人的,作为人类发展强有力的工具在总体上必然是趋善的,科技“善”“恶”之分的决定权在于人类自身,“幸”与“不幸”也只有人类自身才能体验。科技研究无限而使用却有度,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应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关注。
(一)真正意义上“求真”是科技发展趋“善”的基础
科学的目的是求真,通过对自然真实的理解让人们能够正确地解释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为人类造福。从价值论上来说,自从“科学负荷价值”理论被人们广为接受以后,科学在价值语境中分为趋“善”还是趋“恶”的,幸福处于价值论核心位置(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从价值论的维度来分析,幸福感的多少就与科学的“善”相联系起来。然而科学之“善”(the Goodness of Science),常常被归结为是与科学之“真”(the Truth of Science)相关联的某种属性。当人们承认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形式之时,对科学之“善”的理解往往转换成与科学之“真”有关。尽管,科学终究是人的科学,它离不开人的活动,现实的科学也并非真理的不偏不倚的裁决,发挥作用的时候并不总是基于一种来自真理的力量。但是“真”是善的基础,要做到科学之“善”首先要做到科学之“真”。科学探索活动本身也是人生幸福的重要源泉之一。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所以人们说,万物都是向善的。”[4]10-11在他看来:“在科学的理智活动中,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思辨力强,享有的幸福也就大,因为思辨本身就是荣耀。”[4]228这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技研究中会体验到来自于活动本身的幸福。而作为大众来说,一方面科技发展带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从而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解放了人的身体;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整个精神层面焕然一新,使人的精神世界更丰满。可见科学本质上是趋善的,但“科学之恶”究竟从何而来呢?事实表明,很多科学之“恶”是由于各种各样形式的“伪科学”造成的。当今社会有许多披着科学的外衣来推销其私货的各种伪科学玷污了科学的名誉[19]。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杜绝伪科学是一项涉及到科学家、社会、公众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
(二)让公众真正了解科学技术发展是科技趋善的关键
在如今这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信息的不对称是造成公平性缺失的根源,在很多情况下,公众的不幸是由于不了解科学技术造成的。
现代社会有必要让公众知道科学是什么。单单是让公众了解具体科学常识的科普教育在新的时期是远远不够的。基于这种理念,美国率先全面贯彻HPS教育。HPS教育是让公众通过学习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来推行科学教育(histo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cience teaching)的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旨在让公众理解科学的前提下推动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教育可以联结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联结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但最终目的是促进科学与文化的联结”[20]。美国Michael R.Matthews教授在出版、编辑多部科学教育学著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推行科学教育最好的办法是将科学教育与科学的史学维度和哲学维度相结合。当公众掌握了科学基本知识,了解了科学进步多元性与科学本质之后,科学教育所面临的大部分理论与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21]。HPS使科学教育有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指导。一方面理解科技本身对于促进科技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公众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有了更准确和更具体的了解就能促使他们更理智客观地看待科技发展。
(三)人类幸福之两翼: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现代人因为价值意义的失落而彷徨迷惘,忽视了解决人生意义与价值判断的问题,把科学的进步与人生、社会等问题隔离开来,导致科技文化张扬而人文文化陨落。早在1937年9月,爱因斯坦就为在普林斯顿召开的一次神学讨论会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的时代是以在科学领域以及继之而来的技术应用取得辉煌成就为标志的时代,大家都为此而欢欣鼓舞。但我们不能忘记,仅靠知识和技能还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和受人尊敬的生活。人们有理由把道德标准和价值的宣传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像如来、摩西和耶稣这样的圣人所做出的贡献要比那些有创见的人们所做的贡献还要大。”[19]显然,在这里爱因斯坦不是一味鼓吹宗教主义或者是人文主义,而只是想告诉我们,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至少应该是平衡的,并驾齐驱的,在某种意义上,人文文化甚至比科学文化更重要。
幸福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科学文化与人文人化在本质上都是属人的,科学文化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趋向于理性,人文文化塑造人类自身,趋向于感性。如果塑造人性的人文文化得不到发展和丰富,那么发展科学文化就容易偏离正道。
总之,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同发展,既要大力弘扬科学文化,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又要在人文文化的指引下,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限制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确保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科学文化是基础,人文文化是保证,只有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幸福。
[1] 格雷.人类幸福论[M].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3.
[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66.
[3] 周国平.情感和体验[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3.
[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0.
[5]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9.
[6]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35-569.
[7]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2-53.
[9] 邢占军,黄立清.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种主要幸福观与当代主观幸福感研究[J].理论探讨,2004(1):34.
[10] 高延春.“以人为本”的幸福维度[J].江汉论坛,2009(12):54-57.
[11]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7.
[12] 傅佩荣.哲学与人生[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
[13] 毕淑敏.科学与幸福不成比例[J].科学与社会,2002(1):42-43.
[14] 希尔贝克,伊耶.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81:567.
[15] 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 DonIhde.Consequences of Phenomenology[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6.
[18]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19] 董光璧.真与善的协调:爱因斯坦的榜样[J].科学与社会,2002(1):45-48.
[20] 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M].陈恒六,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社,1987:17.
[21] Michael R.Matthews.Science Teaching——the Rol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M].New York:Rout ledge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