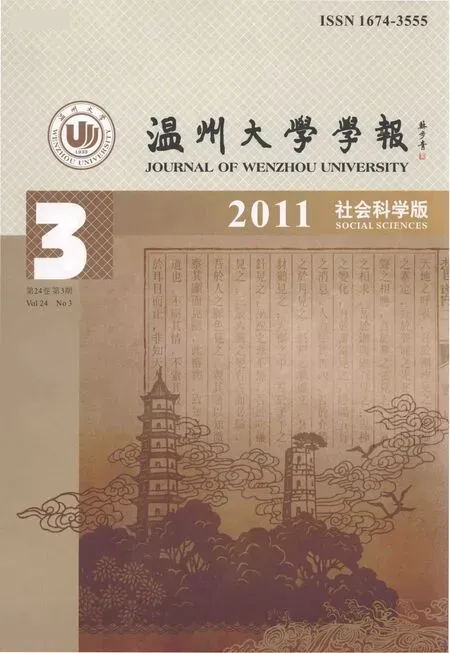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
张邦卫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
张邦卫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传播视域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媒介文学化”与“文学媒介化”两个维度。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发现,“文学媒介化”借助于新媒介(网络与手机)得到了大力彰显。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既是“文学媒介化”的结果,也是“文学媒介化”的“新宠”。“文学媒介化”不仅使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也使短信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更,从而在整体上促使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变迁。
文学媒介化;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网络文学;短信文学
法国学者祈雅理指出:“观念是一些力量在思想上的投射,这些力量奠定着人们从思想上了解宇宙的基础,并决定着历史现实的进程。观念的模式像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的模式一样,总是经常地变化着。”[1]从古至今,文学观念的模式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在当下的媒介社会,文学观念的模式将一如既往地依循生气勃勃的媒介力量再一次进行创造性的重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早已成为我们共同恪守的文学法则。在媒介时代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景象”都是由媒介所呈现的,换言之,“世界”不再仅仅是媒介反映与呈现的对象,而更多是媒介反映与呈现的结果。那么,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与媒介”必然会成为无法迂绕的对象化存在。陶东风认为:“其实,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以及文艺学的学科边界。”[2]所以,在新世纪文学的“被建构”的序列与进程中,“文学与媒介”以及“文学与媒介”的两个具体表征——“媒介文学化”、“文学媒介化”就显得尤其惹眼了。
一、文学媒介化:文学与媒介关系的现代表征
假如我们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性存在的话,那么文学必然会无可避免地与林林总总的对象化他者构成各种互动关系。文学与世界(社会)关系域也必然会为许多具体化的关系项所填充,诸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经济、文学与语言、文学与作者、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媒介、文学与传播、文学与文化等都是这个关系域的应有之义。从文学的传播视域来看,文学与媒介关系的现代表征随着媒介从载附工具向功能主体、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功能媒介向权力媒介的变迁而呈现为一种“文学的媒介化”。
所谓“文学的媒介化”,主要是与“媒介的文学化”相对而言的,二者都是对“文学与媒介关系”的异质性表述。拙著《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曾经指出:“考察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事实,‘媒介性’与‘媒介化’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媒介性本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因为文学总是凭附于一定的物质媒介,但媒介并非工具,也不只是信息,还更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媒介不仅建构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还几乎影响和参与了现代与后现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迫使文学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媒介化有两种构成:一是‘媒介的文学化’,这是媒介盗用文学的‘象征资本’以包装自己的‘商业资本’的策略;二是‘文学的媒介化’,这是文学在媒介场、媒介文化的强权下拓展生存空间的策略。媒介时代的文学具有文字、声音、图像的同构性,而且具有在技术支撑下的多媒介性。在媒介时代,文学并非文学的专利,而成为所有媒介制品的公器。文学在被解魅与边缘化的同时,媒介/媒介文化则不断中心化与强权化。”[3]2从“媒介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媒介化”这一转向,深刻地折射出文学与媒介互动关系场域中权力话语的迁移。“文学的媒介化”表征的是文学对媒介的依附与献宠,透露的是文学文本不过是穿着审美外衣的媒介文本,彰显的是媒介的文化霸权及媒介的文学生产力。
关于“文学的媒介化”,赵勇在《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一文中认为:“在印刷媒介独领风骚的时代,并无所谓的‘文学媒介化’一说。在这里特意强调的文学媒介化,主要是指由于新媒介(主要是网络与手机)的使用,文学的写作方式、发表方式、阅读方式等等均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文学很大程度上已经媒介化了。”[4]诚然,从新世纪文学十年的实践来看,“新世纪文学很大程度上已经媒介化”不失为精辟之论。但是,如果认为“文学的媒介化”仅仅是在新媒介(即网络媒介与手机通讯媒介)流行之后才出现的文学新态的话,则似有不妥。事实上,在第四媒介(互联网)和第五媒介(手机)出现之前,文学的表现媒介不仅有着文字与图像的杂糅,也有影视文化背景下图像增殖与语言式微的格局的存在,文学的传播媒介依次呈现着口语媒介、手工传送的文字媒介或具有简单复制功能的手工印刷媒介、机械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的递嬗与共存。特别是由机械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所构成的大众媒介,体现了以往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比拟的强大威力和优势,对工业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文学也不例外。
本雅明在 1935年论述了以平版印刷、摄影和电影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技术”对现代艺术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机械复制不仅能够复制所有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从而导致它们对公众的冲击力的最深刻的变化,并且还在艺术的制作过程中为自己占据了一个位置。而这种新的复制技术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通过成批的机械复制而把传统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的审美特质——“灵韵”(aura,或译为“光环”、“光晕”、“韵味”等)“排挤”掉了。“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韵。这是一个具有征候意义的进程,它的深远影响超出了艺术的范围。我们可以总结道: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它以一种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复制品能在持有者或听众的特殊环境中供人欣赏,在此,它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这两种进程导致了一场传统的分崩离析,而正与当代的危机和人类的更新相对应。这两种进程都与当前的种种大众运动密切相关。”[5]这样,机械印刷媒介的文学意义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文学传播的数量、距离、范围、速度和力度等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文学得以迅速地走向工业化生产的规模;还有,机械印刷媒介为文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大众传播方式,从而使文学传播从手工传播演变成为大众传播,也使文学从精英主义走向平民主义、从数量有限的手工业生产变成了数量巨大的工业生产,文学也就成了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陈平原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6]事实上,大众媒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制造文学的生产意识、广告意识、消费意识,也制造文学的现代、后现代与后现代之后。尼克•布朗认为:“电影和电视作为再现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创造和确立各种社会成规与性别成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7]正是如此,作为社会成规与文化惯例之一的文学同影视等电子媒介有着密切的依存与寄居关系。以中国文学为例,电视的巨大影响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从电视连续剧《渴望》(1989–1990年间)、《编辑部的故事》(1990–1991年间)、《围城》(1991年)等开始,电视上升为“第一媒介”,并对文学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代社会中,现代传播媒介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正如南帆在《启蒙与操纵》一文中所说的,现代传播媒介的横空崛起,“一系列电子产品的意义突破了技术范畴而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运作”,从而使“现代传播媒介除了具有强大的启蒙意义外,又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文化权力中心”[8]。作为一个整体,现代传播媒介所拥有的决非普通的文化权力,而在电子传播阶段甚至呈现为一种文化霸权。电影、电视作为再现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创造和确立各种社会成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学而言,正是这种施控性极强的文化霸权,现代传播媒介在挤压与之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同时,又大力改造异质文化并使之在同质化、类型化的轨道上滑行,一种趋同的媒介文化(主要是影视文化)便得以生成。
由是观之,“文学的媒介化”本是文学与媒介关系的应有之义,在口语媒介与手工印刷媒介语境下早已潜滋暗长,在机械印刷媒介与大众媒介语境下早已初步呈现,只是在网络媒介与手机通讯媒介的语境下大力彰显而已。那么,文学媒介化之后,文学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有人认为,文学媒介化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已消解了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经典内涵:现实“世界”的真实被网络虚拟化,“作者”从专业人士的唯一走向普通大众的群体性,“作品”从自足封闭走向多元开放,“读者”从被动接受走向了主动参与[9]。还有人认为,文学媒介化之后,整个媒介时代的文学场是以媒介为中心的辐射影响场,文学场域内的各参与主体也出现了身份的锐变,文本就是文化商品、读者就是文化消费者、作者就是文化生产者、社会就是市场[3]344-345。这些变化都是显在的,新世纪文学尤其值得正视。
二、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变革
截止 2010年,新世纪网络文学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如果对新世纪网络文学进行盘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以“扩大化”的态势诞生了许多让文坛颇不宁静的“大事”。在 2000年,网络文学掀起了一个出版高潮,在《悟空传》(今何在)的带动下,《这个杀手不太冷》(王小山)、《我不是沙子》(沙子)等网络作品相继出版。与此同时,《告别薇安》(安妮宝贝)与《旧同居年代》(多人合集)也火爆上市。而陈村主编的“网络之星丛书”(为首届网络原创文学获奖作品,包括小说卷《性感时代的小饭馆》、小说卷《我爱上那个坐怀不乱中的女子》、散文卷《蚊子的遗书》)也适时出版。在2001年,宁肯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投稿多家期刊而未果,最终不得不把它放在网上,因其影响较大,后被《当代》相中而予以发表。在 2002年,慕容雪村即写即贴的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火爆“天涯”网站。宁肯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在2003年,木子美因在博客上发表其性爱日记《遗情书》而迅速蹿红,并成为当年点击率最高的私人网页之一。正是因为“木子美现象”,网民开始关注博客,甚至有了所谓的“博客文学”之说。在2004年,“起点中文网”崛起。在2005年,《诛仙》等网络小说出版,该年被称之为“奇幻小说年”。一批传统作家与批评家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在2006年,博客上爆发了“韩白之争”,引发了一个月左右的混战。以《鬼吹灯》为首,“恐怖灵异”类网络小说开始走俏。在2007年,“穿越小说”在各大网站纷纷推出,形成继玄幻、历史、盗墓等三波网上写作热点后的新热点,该年所选出的四大穿越奇书是《鸾: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木槿花西月锦绣》、《迷途》和《末世朱颜》。此外,像《许你来生》、《勿忘》、《望天三部曲》、《女儿国记事》、《清空万里》、《弄儿的后宫》、《小楼传奇》等以“主流产品”推向市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发网络诗歌风潮。盛大文学公司成立。由“起点中文网”主办的“全国 30省作协主席小说联展”正式启动。“纵横中文网”开站。《瓦砾上的诗》、历史玄幻小说《巫颂》与《尘缘》、历史架空小说《家园》与《窃明》被称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网络作品”。在2009年,《明朝那些事儿》推出“大结局”。至此,当年明月于2006年在网上连载,即写即贴达三年左右的七部作品全部出版。而《明朝那些事儿》系列也成为近年来少有的行销500万册的畅销书。此外,玄幻类小说《盘龙》(我吃西红柿)、玄幻类小说《斗罗大陆》(唐家三少)、科幻励志类小说《狞魔手记》(烟雨江南)、职场小说《争锋——世界顶级企业沉浮录》(凌语嫣)、黑道小说《东北往事:黑道风云 20年》(孔二狗)、幻想小说《卡徒》(方想)被称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网络作品”。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6月25日,由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与中文在线17K文学网主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在中国作协会议室举行了闭幕式和揭榜仪式。《此间的少年》(江南)、《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慕容雪村)、《新宋》(阿越)、《窃明》(灰熊猫)、《韦帅望的江湖》(晴川)、《尘缘》(烟雨江南)、《家园》(酒徒)、《紫川》(老猪)、《无家》(雪夜冰河)、《脸谱》(叶听雨)荣获“优秀作品十佳”;《尘缘》(烟雨江南)、《紫川》(老猪)、《韦帅望的江湖》(晴川)、《亵渎》(烟雨江南)、《都市妖奇谈》(可蕊)、《回到明朝当王爷》(月关)、《家园》(酒徒)、《巫颂》(血红)、《悟空传》(今何在)、《高手寂寞》(兰帝魅晨)荣获“人气作品十佳”。
新世纪网络文学十年,成绩斐然,这充分说明了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扩大化的合理性,究其根底,这主要是缘于新世纪网络文学完全改变了以往的文学生产模式。一般来说,网络写手往往会选择文学网站或某个门户网站人气较旺的栏目“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而这种“发表”通常并非一次成型,而是即写即贴,及时更新。一旦写手的帖子引起网民关注,点击率就会在短时间内飙升,跟帖也会急剧增多。与此同时,点击率高的热帖也会吸引书商和出版商的目光。他们像娱乐圈、体育界的“星探”一样,游走于各个网站之间,反复权衡某个写手是否具有市场价值,某部作品变成印刷读物后能否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而一旦写手被他们相中,那就意味着一颗写作新星的升起。近年来,像《诛仙》、《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形成“网上开花网下香”的局面,可以说是按照同一生产模式打造的结果。而在这种文学生产中,编辑、文学评论家和专业读者大多处于“失语”状态,起作用的恰恰是原来被遮蔽的普通读者的声音。他们以网民身份,以跟帖形式开口说话,又以制造出来的点击率取得了某种轰动效果。正是网民、跟帖、点击率与书商这几个因素共同促进并加速了网络文学的生产。所以,我们认为新世纪网络文学生产的参与元素有写手、网民、跟帖、点击率与书商,从而形成了写手缀文、网民读文、跟贴与点击率推文、书商出文的文学产业链,并且链链相扣,缺一不可。
事实上,传统的文学生产的参与元素主要是作家、编辑、评论家与书商,他们之间虽然有内在的关联,但并非缺一不可,有时甚至只有作家即可完成生产,比如许多作家的“手稿本”与“遗著”、那些宣称“束之于高阁,留之于后世”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所谓的编辑、评论家与书商都是缺席的。在传统的文学生产中,作家的诞生、作品的出现主要是通过专业人士来推动的。而每一次作品的发表、出版、研讨与评论,其实就是他们动用专业眼光,在自己的评价体系中进行比较的结果。所以,这种文学生产其实就是“在符号纵聚合轴上的批评性操作”。相对于传统文学生产的专业比较方式而言,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则主要是通过群选方式来进行的。网民的点击、看帖、传帖、跟帖越多,即意味着某作品的人气指数越高。这种由点击率所呈现的人气指数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书商的出版决心。因此,广大网民就有这样一句网语——“点击率说明一切!”此语虽有偏至,但却深刻地道出了新世纪网络文学生产的助推器便是网民的点击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其实就是“在符号横组合轴上的粘连操作”。当然,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决定了新世纪网络文学更少具有纯文学的气质而更多具有泛文学的性质、更少具有精英文化的气质而更多具有大众文化的性质。正如赵勇所说:“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与生产效益对主流文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它的价值观念、操作方案、产业化模式等等也开始向整个文学界蔓延。”[4]
三、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短信文学的生产变更
截止 2010年,新世纪短信文学也走过了它的第一个十年。如果对新世纪短信文学进行盘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新世纪短信文学的生产以“规模化”的态势风生水起,令人咋舌。它因手机的兴起而兴起,因手机的流行而流行,因手机的普及而普及。与网络文学一样,短信文学同样也是文学媒介化的“新果”与“新宠”。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的,“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以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10]作为通讯革命的产物,手机短信以新媒介的姿态对文化进行了再创造,从而直接促进了短信文学的生成。网络作家千夫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①详见: 文献[14].:“凭借人们对短信已经形成的习惯和依赖,手机已经成了和人体不可分割的一个电子器官,这个器官每天在创作、述说我们内心的情愫。”
2000年1月,日本一位业余作家通过手机连载方式发表小说《深爱》,一年内预订该短信小说的读者人数就突破2 000万,这部石破天惊的小说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本世纪最为争议的作品”。同年,英国Lassalle娱乐公司也专门成立过一个以短信形式发送诗歌的网站,很受欢迎。2003年3月,老牌文学刊物《诗刊》在全国30多个城市发起“春天送你一首诗”的活动,发出了“反对短信息污染,提倡e时代文明”的宣言,号召群众用诗一样的语言为传统节假日和目前流行的节日撰写文明、高尚和具有优秀文学修养的短信息。同一时间,江苏电视台也在全国发起“中国原创短信文学大赛第一季短信诗歌征集活动”。2003年,中国第一部短信小说《短信情缘》赢得了众多年轻读者的喜爱,该书敏锐地捕捉了空气中那不易为人察觉的躁动,衍生出具有时代气息与趣味的爱情故事。2004年6月,由千夫长创作完成的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外》,它的文本独具创意,每一篇只有 70个字(包括标点符号),是专为手机短信定制而成的,但其内容却是按照长篇小说的情节向下发展的,所以被称为国内“首部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它的出现不仅拓宽了拇指文化的领地,也强化了短信文学的影响力。2004年6月底,国内著名人文杂志《天涯》、著名网站海南在线“天涯社区”与海南移动公司联合举办全国性的首届“短信文学”征文大赛,邀请铁凝、韩少功、苏童、格非等文学权威担当评委,大赛主办方宣称本次“短信文学”大赛“期望发掘具有广泛流传价值的短信文学经典作品,同时欲开拓继网络文学之后的文学新品种——短信文学,掀起‘拇指文学’新高潮”。大赛征文的首要条件是从作品形式来讲的。征文分小说、散文、诗歌3类,小说、散文字数不超过210字(以三条短信字数计),但以70字为佳;诗歌不超过16行,但以8行为佳。这种在文字上的简洁凝炼的要求,恰恰道出了短信文学复古式的文学个性,即在有限的字数中容纳尽可能多的内涵,这正是使短信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点,也是信息时代的特殊产物,就像古代的“五言七律”一样。这种形式上的严格有时反而能够极大地激发创作者的创造力,同时也非常具有挑战性。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短信文学”大赛,使一直只是在民间流传的短信文学得以浮出水面,它第一次在全国正式承认短信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品种。2004年8月2日,千夫长的短信小说《城外》(仅有4 200字)的版权,被某通讯公司以人民币18万元的价格独家买断,稿酬之高,令人咋舌,这从另一角度透出了短信文学的影响力。因此,“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完备,短信已成为文学新阵地。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们对文学的认知,甚至短信文法还可能影响文学创作,比如短句方式,数字文学等。短信文学也必将带来一个新的文学研究领域。”[11]
以日本文学为例,据《参考消息》报道:2007年,日本的手机小说正在成为带动电影、音乐、出版等多媒体联动的一大产业①参见: 《参考消息》2007年11月28日刊登的《日本手机小说已成“大产业”》一文.。在网络投票中排名第一的小说《片翼之瞳》全 3卷的首次印刷数量就达到罕见的 45万册。另一部名为《屋顶上的天使》的原创作品,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网友们最想改编为电影的小说。文章认为,手机小说正在改变出版发行业界的旧有模式。发表手机小说的门槛很低,许多年轻作者唤起了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女性读者们的共鸣,因此在年青人远离文字的时代,却不断涌现源自手机小说的畅销书;此外,由于影视和音乐等衍生产品的开发,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正在形成。文章还指出,在2007年上半年的10部最畅销手机小说中,已经有5部发行了单行本。2006年的图书市场规模为9 325亿日元,比处于高蜂的1996年下降了15%。而从 2006年开始渐成气候的手机小说市场,仅仅依靠出版单行本就达到了几十亿日元的规模。另外,手机小说对其它产业也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如改编成电影的手机小说《恋空》,其单行本的发行量达到了195万本,电影《恋空》的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了20亿日元,主题歌也成为流行单曲。
由是观之,新世纪短信文学的规模化与初步产业化,不可避免地与短信文学的生产方式的变更有关。正如王富仁所说,“在当代社会,媒体的主动性加强了,媒体的选择在有形与无形中影响着文学的生产。”[12]与传统的文学生产相比,短信文学的生产元素主要有写手、用户、转发率与书商,其中写手的平民化与“随身写作”和网络文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转发率不仅成为衡量短信文学作品的标准,也成为书商出版印刷本与单行本的尺子。转发率与流行度,是短信文学生产的核心要素。与新世纪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类似,短信文学的生产也是一种“在符号横组合轴上的粘连操作”,包括写手缀文、通讯公司发文、手机用户读文与转文、书商出文等流程。虽然短信文学的生产缺乏像网络文学的生产那样的评点式的跟帖,但是手机用户对某部作品的转发与群发恰恰又是一种没有言语表达的评价与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短信文学的生产是一种全流程的生产,诚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13]马克思在这里讲的虽然是一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也同样适用于短信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特别是短信文学的生产还是由通讯公司的经济资本所决定的资本生产,从而使短信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变得更加全程化与对方化。此外,短信文学的生产还具有诸如生产短小精悍、转发“短平快”、回复迅速简洁等特点。所以,我们认为新世纪短信文学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文学生产方式建构起新的文学惯例与文学机制,诚如一位作家在评手机小说《城外》时所说[14]:“《城外》之后,我们有可能将面临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城外》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重新建构了一种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多数文学读者而言,消费与审美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这样一来,文学的边界扩展了,但文学的精神也可能变异了,这究竟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
总而言之,文学之为文学与文学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察新世纪十年文学,文学媒介化不能不说是新世纪文学最鲜明的现代表征与文化症候,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均是文学媒介化的当下硕果,而它们也确确实实地修改着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形成必然会影响阅读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消费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转型,甚至是整个文学审美的重构。
[1] 约瑟夫•祈雅理. 二十世纪法国思潮: 从柏格森到莱维•施特劳施[M]. 武永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3.
[2] 陶东风. 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J]. 文学评论, 2004, (6): 60-63.
[3] 张邦卫. 媒介诗学: 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 赵勇. 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 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 (1): 64-73.
[5]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张旭东, 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0: 60-63.
[6] 陈平原. 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 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C] // 陈平原, 山口守.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562.
[7] 尼克•布朗. 电影理论史评[M]. 徐建生, 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 149.
[8] 南帆. 启蒙与操纵[J]. 文学评论, 2001, (1): 61-70.
[9] 白烨. 中国文情报告(2007-200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09.
[10]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吴燕莛,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11] 李存. 试论“短信文学” [J]. 文艺评论, 2005, (1): 26-31.
[12] 王富仁. 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J]. 读书, 2004, (5): 86-89.
[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8-9.
[14] 桂杰. 短信小说《城外》“一鱼八吃” [EB/OL]. [2005-02-06].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758/3171595.html.
Med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Change of Mode of Production of New Century Literature
ZHANG Bang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jiang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Hangzhou, China 310018)
Under horizon of commun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edia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dimensions: “literaturization of media” and “med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Through study of the first decade of new century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med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has been strongly displayed with the help of new media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 Internet literature and 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literature are not only the result, but also the “new favorite” of “med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Med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not only make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internet literature change, but also makes that of SMS literature change. Thus, it promotes the change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new century literature as a whole.
Med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New Century Literature; Mode of Production; Internet Literature;SMS Literature
(编辑:付昌玲)
G206
A
1674-3555(2011)03-0035-08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3.00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1-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W1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07JC751019);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项目(2009N31);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08B002)
张邦卫(1968- ),男,侗族,湖南芷江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媒介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