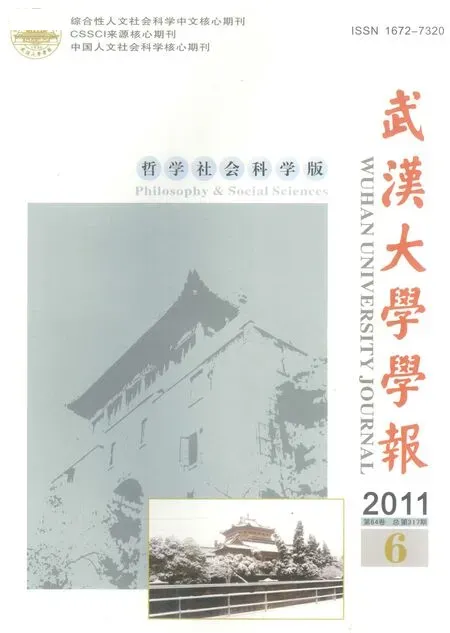私法上自然人法律人格之解析
叶 欣
一、法律人格的主体及技术的考证
“人格”被广泛运用到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就法学范畴来说,法律人格在法律主体体系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法律人格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构成要素,从身份化、伦理化到普遍化,所采用的抽象性技术为民事主体的地位奠定了平等的基础。
(一)法律人格的主体扩张
在罗马法时期具备法律人格的人可归类为身份人。要作为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需要具有自由(Status libertatis)、市民(Status civitatis)和家族(Status familiae)的身份。当时,还不曾用现代的“权利能力”一词来概括这种资格,而用人格(Caput)来总称这三权①周 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8页。。Caput则成为法律上认可的主体的判断标准,也就是区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面具”,没有特定身份的人是被排除在法律主体之外的。于是,在罗马法就出现了“(自然意义上的)人为非(法律意义上的)人”情形,当时法律确立的是一种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在家庭内部家父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家子(包括家庭内的妇女、卑亲属、奴隶等)根本没有法律人格,而是通过监护等方式受到家父权的支配。
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民法将伦理性作为法律人格的本质属性,伦理性乃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所具备的自然属性包括生命机能、理想情感、意识思维等方面。近代民法上具备法律人格的人可归类为伦理人,至此,有生命机能的自然人被接纳为法律上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再是基于身份地位,而是在年龄、精神状况、身体功能、自理能力及品性修养上存在差异,从而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现代民法则将法人等非生命实体逐步纳入到法律人格的范畴,实现了“非人可人”的质的转变,法律人格的主体出现了扩张的情形。“‘法律人格’并非指人的整体,而是指脱离了人的整体的人在法律舞台上所扮演的地位或角色,因此该语源是象征性的”②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法律人格不仅限于伦理性的要求,而是可以延伸至自然人之外的实体。“从逻辑上讲,并非不可以将法律人格赋予动物、群体、公共机构、基金会、协会等其他实体”①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688页。。关于环境保护、善待动物等一系列的生态化法律问题已被提出以法律人格扩张化的方式来寻求解决途径。
法律人格是权利义务归属于民事主体的标志,在私法中体现为人的法律地位或私法上作为“人”的资格,并不仅限于有生命意义、伦理意义的人才能成为民法上的“人”,还包括自然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也有权利义务的内容。法律人格由最初罗马法上的身份等级所决定逐渐演变到凡是伦理意义上的人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乃至于包括并不具有人性的法人也可以成为民法上承认的民事主体,整个民事主体的发展经历了由“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过程,确立了体现尊重人的尊严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法律技术机制。
(二)法律人格的技术:理性人预设的演绎
通过抽象人格的技术性手段确立理性人的形象,方能实现法律人在价值上的形式平等。依据康德伦理人格主义哲学,“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②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6页。。作为人格人应当是能够自我约束和控制、拥有成熟的心智、作出理性判断的人。“为了能够被视为完整的人格人和法律主体,人应如何具有此种性质?”“当人约束住他的情感,他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黑格尔语),即具有人格人的内质,这就是‘成熟年龄的、思想健全的睁开眼的传统民法的人’”③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74~79页。。近代民法上理性人格的预设是对人的本质的抽象,将人统一规划为意志自由、享有自治能力的人,成为满足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的法律人;是能够排除个性与低能的差别,准确把握自我利益、遵循规范的法律主体。德国学者阿尔巴克确信:“意思能力对于作为伦理意义上的人格具有决定性”④村上淳一:《德国市民社会的构建》,载《法学协会杂志》1986年第8期,第826页。。申言之,必须是具备意思能力、理性认识能力的人才成为民事主体。将冷静、睿智的理性预设作为享有法律人格的前提,确认人与人之间彼此并无差别,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应当说,法律人格被赋予了理性的预设,乃是在自然法学说的影响之下,基于维护整个人类利益的理念上的认识。
那么,在现代民法中如何对待无理性者无人格的问题呢?受到康德影响的《奥地利民法典》起草人之一的蔡勒(Zeiler)认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才能称为人格”⑤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第163页。。为了解决非理性人的法律人格问题,德国民法在法律技术上运用了行为能力概念,并且将人格转化为权利能力(Rechtsfaehigkeit),于是这部分人虽然不是行为者但仍能成为利益的享有者,从行为类型化的角度对其权益进行保护;在理性的弥补方面通过监护制度来延伸其行为能力,从而获得与他人平等的实际权利。近年来,随着人权保护思想的兴起,大陆法系国家陆续对传统民法进行了立法修改,将对成年人行为能力的限制模式转变为以尊重自我决定权为中心的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则通过对普通法上代理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对特定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这一系列的修法运动使得尊重法律人格的精神以立法技术的形式得到了实践和发展。法律人格演变至今不但没有排除非理性的未成年人、痴呆者和精神障碍者,而且还包括了不具备伦理性的法人等其他法律主体,最终导致生物人与法律人在伦理性特征上的分离。这种分离区别于罗马法身份等级的人格划分,而是人格的理性化至普遍化的一种升华。
二、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关系解读
(一)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的等值论之争
对于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关系,历来争论不休,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究竟是否等同呢?有以下不同看法:
1.肯定说。有学者认为“正是基于人格内涵的丰富性,形成对人格属性的普遍认识:即人格和权利能力等值”①付翠英:《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辩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载《法学》2006年第8期,第71~72页。。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最早提出了私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法国民法典》未提出人格或权利能力概念,但在其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德国民法中不存在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概念,而是用法律技术化的权利能力术语取代了法律人格。看来似乎近现代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对人格和权利能力一般都不加区分地使用。事实上,两者并不具有等值性,虽然都是为了体现民事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存在,但法律人格解决的是抽象上的法律地位平等,权利能力强调的是民事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资格的享有平等;并不能因为一些国家立法上的欠缺而否定任何一方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可以被对方所取代。应当说,人格象征着法律主体的地位,是具备更高位阶、更深层次的法律评价;而权利能力是民法上的人享有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一种资格,是一种人格的具体表现;不同的人可能因年龄等原因不能享有特定意义上的权利能力,但其人格确应是平等的,此说不能成立。
2.否定说。代表性观点认为,权利能力概念是运用法律技术吸纳非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结果,其不能体现“法律人格所记载的‘人之成其为人’所包含的人类尊严和社会进步等等宏大而深刻的人权思想”②尹 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6页。。笔者赞成否定说,并且认为两者主要区别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存在基础不同。自然法思想是私法上法律人格确立的思想基础,它本身就是“伦理性的必然,自然法原理所要求的”③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第191页。。自然法学者在界定人格概念时最初是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的。在他们看来,人格是具有理性思想的人所具备的,即具有伦理性。可以说法律人格蕴涵了自然法中人的理性基础,伦理性乃最初判断人格的法律标准。而权利能力是由于实证法(Positives Recht)的规定出现的,自然人须基于法律的授予和认可方得具有权利能力,非人类的实体则可由法律的拟制规定获得权利能力。
第二,法律地位不同。近代法中宪法确认的自然人基本法律地位的法律人格,有着高度的抽象性和丰富的内涵,体现人的尊严、独立、平等和自由,是宏观层面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而权利能力受到法律人格的约束并依附于人格而存在,是抽象法律人格的具体功能、实际地位的私法体现,是人们赖以实现人权内容的具体手段和方式。
第三,产生的逻辑顺序不同。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认为:“人格存在不是别的东西,它仅仅在于:它是出发点,是源自一个合法则的理性意愿或一个作为实践活动的理性活动的出发点的X”④马克斯·舍勒:《伦理学中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52页。。由人格派生出的能力、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才具有法律意义和实现的可能,因为法律人格先于权利能力产生,成为法律主体享有相关能力的先决条件,是自然人获得相关能力的逻辑起点;权利能力则是法律技术化的结果,是法律人格衍生出权利(义务)的成文法律规定内容。
第四,蕴涵理念不同。“人格所昭示的平等成为推导人所拥有的价值的一个必要的起点”⑤胡玉鸿:《“人格”在当代法律上的意义》,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7页。。人格关注的是每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同等的对待和法律上的存在,彼此并无年龄、性别、血缘、宗教、职业、民族上的差异,呈现伦理性的人本价值理念,具有更为深层次的抽象特征;而权利能力强调的是作为法律主体的人是否能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是权利和义务具体化的基础,并规范着人们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成为连接民事主体与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制度化桥梁。
(二)法律人格的性质定位
在认识到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并不等同后,不得不追问一下,法律人格是私法上的抑或是公法上的概念?法律人格从其历史范畴来看,体现了人的一般法律资格和法律地位,属于宪法规定的范围。但权利能力的出现从宪法意义上的人格分化出私法意义上的人格,使得公法上的人格概念发生私法化的分离,从而实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人格并存:宪法意义上的人格成为私法意义上的人格的上位概念,并且前者成为后者实现的强有力保障。应当说现代民法的法律人格已经逐步扩大其伦理性内涵,成为技术层面规范主体资格的一种手段,而宪法上的人格概念侧重关注自由、平等的价值,其投射的范围更加广泛。
在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峙的社会结构下,人能够以民事领域自然人和宪法领域公民的双重身份、按照不同的逻辑与规则,参与不同性质的法律领域的活动与交往。法律上的人格包括公法上的公民人格和私法上的自然人人格,只是两者的价值诉求有所不同:前者侧重公民与政治国家关系的层面,抗衡国家公权力的肆意侵害;而后者注重自然人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方面,预防私人之间的人格侵犯。
三、自然人法律人格发展趋势的现代转变
(一)从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的理性回归
在罗马法上同时具有自由、市民和家族的身份者才有人格,即完全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身份成为人格认定的基础,具有极不平等的色彩。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人格变更就是改变先前的身份”(Est autem capitis deminutio prioris status commutatio)①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73页。,身份是人格的构成基础。在罗马法出现以身份为认定法律人格的技术后,古代自然法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为身份人格向伦理人格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早期斯多葛学派以伦理学为起点,认为“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性动物。在服从理性命令的过程中,人乃是根据符合其自身本性的法则安排其生活的”②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任何人的本性均是平等的,人的理性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反映出的人们在法律上无差别的本质。有学者指出事实上的人格与法律上的人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基于伦理而非逻辑上的必然③Jan Klabbers,“Legal Personality:The Concept of Legal Personality”,US Law Reviews and Journals,2005,Spring,p.6.,即法律承认的人格享有者只需具备伦理的要求,无需作出逻辑上的推导。近代民法为了使人人平等这一伦理性基础在法律上进一步巩固,将作为人类普遍的伦理价值转化为自然人法律人格的依据,人的自然伦理性理所当然的成为法律上人的本质。《法国民法典》的抽象人格,《德国民法典》的权利能力,仍是建立在人的伦理属性基础之上,在这种无差别的伦理价值中,实现了真正的法律上的平等。近代法律人格的基本特点在于个人的伦理属性成为了自然人法律人格的适格标准,由此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完成了由最初的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的理性回归,奠定了现代民法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基础。
(二)从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的必然分化
近代民法基于平等性的社会基本判断,赋予一切民事主体的平等地位。《德国民法典》上的标准人是“植根于启蒙时代,尽可能自由且平等的、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Abstrakte Einzelmensch),是兼容市民的感觉和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Homo Deconomicus)”④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第155页。。伦理为基础的法律人格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根本价值,抽象人格则是伦理人格的逻辑产物。但现实社会的人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具体的人,存在强弱之分,市场经济中强势主体利用隶属关系、信息不对称、经济力量的差距等有利因素,在与弱势主体的交往活动中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抽象的法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于是,现实社会中民事主体的复杂化、多元化,事实上存在的贫富差距、经济实力的强弱,使得抽象人格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必然发生人格的分化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和理论认知的转向。具体而言,现代社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企业主和劳动者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消费者处于单个个体的弱势地位,无法单凭自身的薄弱力量与相对方博弈;而劳动者是从属于拥有强大资金后盾的企业主,处于一种受支配的地位。种种现象表明现代的社会生产和民事生活并不能真正实现法律主体的平等。事实上,弱而愚的自然人才是真实的人,为了实现弱者与强者的平等对话、协商,应当突出身份的现代法律意义。当弱者与强者的实力越来越悬殊时,法律应当赋予强者更为严格的义务和责任。由此,消费者和劳动者这两类人的具体人格在法律上的确立,意味着他们的特殊身份被法律所认可,进而发挥保护弱者的自由和合法权利的功能。
现代民法重视对弱者的保护和特殊权利群体的出现,将民法发展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但此“身份”非彼“身份”,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扮演多样角色的人频繁的变换着不同的法律地位,现代民法中的这种受到保护的“身份”已经异化于传统“特权”的永久享有和恒定不变,会因合同的缔结而不断发生适时的变化。由此可知,新“身份”的涵义与身份的原初意义——特权和等级的象征是不同的,前者的出现标志着弱势群体身份的崛起,体现了国家保护具体人格的立法精神。现代民法上的身份关系不仅限于血缘、婚姻等家庭亲属关系,不论是生理、心理或精神上有障碍或有缺陷的人还是具体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都应当在法律地位上彰显出平等价值的光环。
四、余 论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民法中人格的理性标准的淡化与注重保护弱者的具体人格之间有无差异?前者通过行为能力制度、监护制度来维持民事主体所必备的理性,并不是强调绝对的无理性者无人格;后者则将处于经济上劣势地位的人在法律关系中的“身份”具体化,尊重与保护其合法权益。从罗马法上戴“面具”的人到里佩尔《职业民法素描》中穿上“工作服”的人,人格所蕴含的理念发生着变化,体现了现代民法越来越关注职业、能力、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人的利益。但是,法律精神虽然注重保护弱者,却并不意味着近代民法平等价值要求的“褪色”。其实,平等性要求与保护具体人格之间不存在冲突,具体人格的出现是为了实现法律上的实质平等,必须以区别对待的方式关心弱者、抑制强者,使得不平等的具体的人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这些权利易受到侵害的人,靠个人力量不能与强者对抗而达到自己的愿望,需要法律的倾斜性保护,才能获得人格尊严的尊重。那一部分形式上增加的权利并不等同于弱者的特权,而是为了追求实质的社会公平这一价值,所作出弥补性的权利衡平保护。
从法律人格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其内涵的丰富,身份人格走向伦理人格、抽象人格转向具体人格,逐步实现由形式上的平等到实质上的平等,打破了古代罗马法身份人格的枷锁,巩固了平等这一价值在现代民法中的重要地位。人格平等是民事主体自愿缔结契约的前提;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受到限制时,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赋予了身份新的涵义。现代法剥离隐藏于抽象人格之后的自然人各自具体的特征——经济力量、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对具体人格的人提供法律上的公正对待,使其享有如同其他自然人一般同等的待遇。通过具体人格的确立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将有利于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也有助于完善整个私法制度与体系构造。
——兼论平等理念下现代法的权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