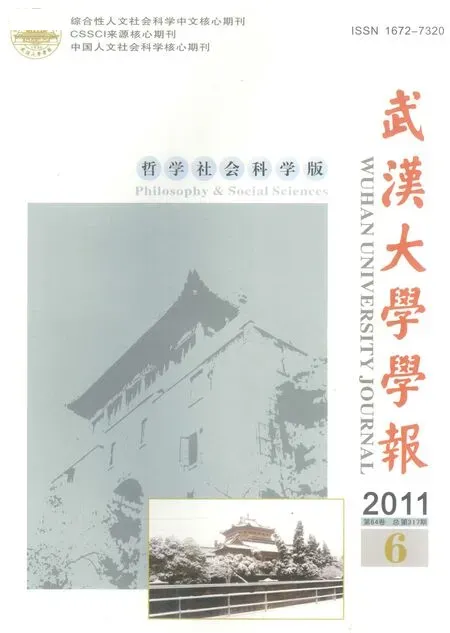“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杨志民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部分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小国之所以强大,不在于有坚船利炮,而是有议会、宪法等古老的中国所不曾拥有的东西。他们认为,中国要变得富足强大实现救亡图存,就必须仿袭西方的宪政体制。自此,近代中国的宪政之道得以开启。
然而,纵观整个近代中国立宪,自1908年满清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始,虽相继制定过名目繁多的宪法和宪法性质的约法,但始终是有宪法而无宪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探讨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上的“宏大叙事”。在“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下,近代中国的立宪被政治化,宪法与政治融为一体;而政治又始终无法打破“权力一元化”的传统模式。因此,在近代中国的立宪活动中,宪法始终缺乏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缺乏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行切实保障。因此,中国若要实施宪政,就必须注重“微观论证”的理性分析,将对宪法和宪政研究的重点积聚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具体制度设计上。
一、“宏大叙事”与“微观论证”的中西文化差异
所谓“宏大叙事”,是“法理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视野以及实际选题往往偏重于对社会或国家具有全局性问题的论述。诸如法与正义、法与政治、法与经济、法与科技、法治问题、人权问题、法律价值、法律文化以及立法问题等等。”①谢晖:《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载《文史哲》2003年第4期,第92页。也就是说,在法律和法学领域,“宏大叙事”着眼于研究法律现象在整个社会、国家中的地位、作用、意义。注重的是对法律问题进行整体性和全局性研究,缺乏对法律所应该涉及的具体制度、规则细节问题的微观剖析。
与“宏大叙事”相对立的是“微观论证”。所谓“微观论证”,是指法学研究的问题视域只及于法律本身,而不及于和法律相关的外部世界。它是通过对法律之内部问题的观察和梳理,以解决实在法可能存在的冲突、漏洞、不足、超前、滞后等问题,以完善实在法从纸面的法到实践行动中的法之过程①谢 晖:《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载《文史哲》2003年第4期,第92页。。与“宏大叙事”迥异的是,“微观论证”强调的是借助形式逻辑的分析和推理手段,通过对法律体系具体问题和具体细节的深层剖析,以探求法律问题的内在实质规律。“宏大叙事”与“微观论证”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分析和观察问题的方式。
对事物从宏观和整体层面进行“宏大叙事”式的分析,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文化范式和思维模式。与之相反,西方宪政文明的发展,十分重视微观论证和理性的逻辑推理。梁簌溟先生曾对此有过较深论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为“直观”,即“总是不变更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相反,西方人则不一样,“西方的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看”。为了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具体区别,梁先生还举了一个医学方面的例子:“同一个病,在中医说是中风,西医说是脑出血。中医说是伤寒,西医说是肠窒扶斯。为什么这样相左?因为他们两家的话来历不同,或者说他们同去观察一桩事而所操作的方法不同。西医是解剖开脑袋肠子得到病灶所在而后说的,他的方法他的来历,就在检查实验。中医中风伤寒的话,窥其意,大约就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之谓。但他操何方法由何来历而知其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呢?因为从外表望着象是如此。”②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37页。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是整体而直观笼统,表现为宏大叙事;西方人则讲求科学,分析问题讲究抽丝剥茧式的严密的逻辑推理,表现为微观的理性论证。
梁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尚人治,西方政治的尚法治,虽尚有别的来路,也就可以说是从这里流演出来的。”③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37页。即传统中国崇尚人治,而西方遵从法治,从文化上来分析都与中西方分析问题方式的差异有关。具体而言,由于“整个着看”的“宏大叙事”的传统文化范式,表现在哲学层面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即达到以人为中心的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主张主体与客体不分,强调主客体的统一,反对将主客体二元界分。由于没有将认识对象从所属整体事物中独立出来,由认知主体对之进行解剖式的逻辑化认识过程,因而很难达到对事物进行本质性认识的程度④陈晓枫、易顶强:《略论传统直观思维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78页。。由于“宏大叙事”的影响,传统中国从老路子里根本无法衍生出法治与宪政。整体化的“宏大叙事”和“天人合一”表现在国家治理层面就是追求“家国一体”。在“家国一体”的结构模式下,不但不能将国家与社会进行二元界分,而且社会被国家的强权阴影所遮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被国家强权所吞噬。法律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法律的核心价值目标是维护一元皇权的稳固,而非限制国家权力从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律与政治在价值追求上完全实现了合一。由此可知,在传统中国,法律根本就没有肯定过公民应当享有权利和自由,而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一元化皇权。在法律上该一元权力不容分割,并且以之为原点自上而下地进行权力分配。它既不存在受到横向的其它权力制衡,也不像西方国家权力要受到公民权利自下而上的逆向制约。在古代中国,公民只能被称为“臣民”而不是国家的主人。
西方人崇尚科学和对事物进行微观论证的思维模式是以理性为特质。其主要特征被叶秀山总结为“对象性思维方式”⑤魏敦友:《回返理性之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9页。。所谓对象性,就是从主体出发,将客体视为外在的客观实在,并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从而预设了主——客体二元分立的认识结构。对象性思维通过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从而强调主体的独立性。主体可以运用逻辑方法以探求客体的内在本质⑥朱海波:《理性主义——西方立宪主义的文化基础》,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67页。。这与传统中国追求主体与客体合一的一元化、整体化和直观化的“宏大叙事”思维模式迥异。对此,哲学家张岱年教授也曾指出: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同民族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西方民族的思维是以逻辑性为其基本特征。远在西方古代,理性的“形式逻辑比较发达。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⑦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通过不断地对事物进行二元界分,并依据形式逻辑来探求事物的内部结构和本质,西方人逐渐形成了对事物注重于从微观层面进行理性分析的文化特质。而这种对事物进行二元划分和强调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传统中国却并不具有。
正是这种中华文明中所不曾具有的理性精神,促进了西方宪政文明的衍生。强调二元界分和微观论证的理性思维使得西方人在思考国家的建构时,首先把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对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进行二元划分。其次,为了防止因滥用公权力造成对私权利的侵犯,二元划分的理性思维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公权力进行必要的界分,从而廓清权力的行使边界。在对权力和权利通过微观论证进行分离的同时,仍然通过微观论证,设置权力制衡机制,如违宪审查机制等等。通过这些机制严格限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以防止其被掌权者滥用。正是由于对权力的界分和对权力行使边界的廓清,西方宪政文明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权力应当受到有效的制约并且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使,而不能逾越被设定的界限。否则,“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再次,在社会权利层面,法律也同样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不断进行微观化和具体化,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权利保障体系,而且在法律上不同位阶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形成了符合形式逻辑的有机体系。最后,在公民的私权利和国家的公权力之间也同样存在逻辑关系。从宪法上说,国家的公权力来自于公民的私权利,因此公权力始终要接受公民的民主监督。在国家权力的有序运行和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之间形成了符合形式逻辑的有机体系。综上所述可知,由于强调对法律问题进行微观论证的理性思维,西方催生出了宪政和法治文明。
二、“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重构了近代中国立宪
近代中国虽然大量地移植和仿袭了西方的宪法,但由于“宏大叙事”的文化传统所发生的重构作用,使西方宪法上的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设计被破坏,国家的权力结构始终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近现代中国宪政运动最后失败。具体而言,在近代中国由于“宏大叙事”的传统文化范式对立宪的影响,法律与政治仍然融为一体而缺乏应有的界分,法律始终是为实现国家权力的集权服务。“有宪法无宪政”因此也就成为“宏大叙事”的文化传统重构舶入宪法的精确评定。
立宪各派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功利性地解读了宪法,将宪法视为推进政治集权和维护权力一元化的重要工具,反对将宪法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并将宪法的核心功能定位为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甚至被当成是导致国人“自由散漫”和“一盘散沙”的有害的东西来对待①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例如,梁启超就曾认为:“自由云者,团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也。”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44~45页。所谓“团结之自由”,其实就是主张强化国家权力形成国家集权。这与宪法、宪政追求个体自由的价值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法的根本动力不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体自由,而在于寻求富国强兵和自强图存的良方。实现国家的富强需要的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宪政。因此在近代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但不能制约国家强权,反而被国家强权所压制。对此,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上,亦或是在宪法的文本上,“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下追求权力一元化的现象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在理念上,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满清皇室,他们无不希望借助宪法来专控国家的最高权力。革命党人立宪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追求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是希望借助立宪来聚集革命力量进行排满,从而控制国家最高权力。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曾认为,为了争取国家富强,实现“扑满而兴汉”的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做成像堡垒似的革命团体③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页。。立宪党人则希望通过仿效英国的宪法实现“议会主权”、“君主虚位”和“责任内阁”,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由立宪派控制的国会中,从而架空皇室、排斥革命党。满清皇室则更是希望通过立宪实现“皇位永固”④陈晓枫、易顶强:《宪法秩序的文化内涵》,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4期,第34~35页。。
其次,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上追求权力的一元化,反对对最高权力进行分割。在近代中国立宪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影响宪法实施的障碍:比如,在选举法中对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设定苛刻的条件,使得只有极少数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如,“五权宪法”中的“万能政府”和“权能分治”;立宪以后还须经过“行宪”才能建国;再如以党训政等。通过这种障碍设计使得人民主权被虚化,国民大会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国家权力仍然体现的是集权而不是权力制衡①陈晓枫、易顶强:《宪法秩序的文化内涵》,第34~35页。。我们试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为例来说明。
孙中山认为,西方的“三权宪法”存在众多弊端,比如容易造成立法专制等。为了消除此类弊端,创造“中西合璧”式的宪法,孙中山发明了“五权宪法”。“五权宪法”的权力结构设计不是采取分权制衡的结构设计,而是追求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五权宪法思想始终强调,治理社会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万能政府”来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从而迅速推进中华民族走向富强②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6页。。“万能政府”的集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民的“政权”与政府的“治权”之间,集权于政府的“治权”;二是在政府的“五权”之间推行行政集权。
在“五权宪法”中,人民享有四项“政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又被称为“权”;而政府则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项“治权”,又被称为“能”。在“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上,“五权宪法”并不追求宪政国家的“政权”对“治权”的制约,而是希望人民不是事事牵制政府,应该对政府表示充分的信任,即实行“权能分治”。所以在机构设置上国民大会并不设立常设机构,只是一个临时议事的机构。这种“权能分治”的制度设计就使得代表国民行使四大民权的国民大会往往会被架空,处于有权难行的状态,而政府则实现了集权。同时,组成政府的五个“治权”之间也不是采取诸权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而是分工配合的关系。孙中山认为分权只会导致各权之间相互牵制而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各权之间的关系应当像一窝之中的蜜蜂“分职任事”,各自担任觅食、采花、看门等不同的任务。这样政府五权之间就能够相互帮助,以形成群力,那么政府就可以发生无限的威力③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30页。,也只有这样,“政府才可望发展成为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也就可以像“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④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30页。。由此可知,从五权宪法各权之间“分工配合”的权力设计来看,“万能政府”就是趋向于强化政府权力的政府。五权之中最为重要的权力就是行政权。五权之间的分工配合关系在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其余四权都要配合行政权力来整合资源,所以,“万能政府”也是追求行政集权的政府。
最后,在宪法文本上,权力的一元化设计也体现的尤为明显。从1908年满清政府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到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期间虽然有数目繁多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但无一例外都是追求权力的一元化。以1928年国民党颁布的《训政纲领》为例,《训政纲领》第一条开门见山地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二条规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仅此二条规定,便实现了训政时期的“以党治国”、集权于党的政治原则。虽然《训政纲领》第四条规定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分别行使五项治权,但第五条同时又规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国民党中执委不仅可以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同时甚至还可以修正及解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因此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中执委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毫无疑问是一元化的。
三、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中国宪政之路的必然选择
虽然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宏大叙事”的文化传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内在地导致了近代宪政的失败。我们已经认识到,宪政可以强国,宪政还可以富民,但如何实现宪政,如何建设一个可以强国富民的宪政,则需要使法律与政治保持必要的价值分野,通过务实和理性的“微观论证”来进行。从法律的制定及实施层面,来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保障;合理界分国家机关的权力,实现各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之间形成有机体系。
首先,应该明确,宪政之目的在于保障民权,而不是其他。2004年3月14日,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运用法律治理国家,通过法律实现民权保障,是宪政的核心和归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加强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研究和保障,科学地、符合逻辑地设计立法、司法。
比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保障?这个命题实际包含有非常广泛且具体的内容,必须进行理性的设计。应该包括:逻辑地解析基本权利的具体内涵和外在表现形态,并以完整准确的法律术语进行表述;在包含各个不同阶位、不同门类的具体法律中进行具体的、符合逻辑的、不相矛盾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保护这些权利的实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享有辩护权,辩护权可以自行,也可以委托律师实现。但是,在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如何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新的律师法赋予律师的会见权,由于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规定不相衔接,甚至矛盾,导致该权利的实现成为一个问题。近几年发现的一系列有影响的案件,无不与辩护权被轻视、漠视有关。对该项权利的漠视必然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言论自由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监督权等等,但是,却没有对这些权利进行全面、准确表述的法律。现实存在的对公民居住权、房产权等等的大量侵害案件问题,就是因为法律的缺省、含糊所导致。
其次,应该明确,政府的权力应该具有边界。现代宪政国家采取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就是有限政府。只有明确了政府的权力边界,才能考察政府是否恪尽职守,是否超越职责,是否滥用权力,是否懈怠、推诿,损害人民利益。现实中出现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收费公路的政策,就没有中国交通的现状和成就”等等,应该属于政府或者政府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对行政权力滥用的情况所致。相反,过多的上访事件等等,则存在民众过度依赖政府,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性设计政府各个系统、部门、机构及个人的权力职责范围,并予以清晰地界定。
再次,应该明确,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包括合理界分国家机关的权限,实现权力相互制约,以及人民对于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
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国家机关体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余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并应当向其负责或报告工作。但是,由于我国的国家机关之间缺乏合理的权力界分,不仅使得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甚至被冠之以“橡皮图章”的称谓。相反,现实中部门立法、行业立法却屡见不鲜。这些冠以法律之名的所谓“法律”不过是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有时甚至是少数人个人利益的体现,既不是国家意志,更不是人民意志。在司法及行政行为中,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名义出现,实为私利的更是见怪不怪。我国刑法的原则之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禁止适用类推。但是,许霆案却为了银行利益,类推定罪处刑。由于对国家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现象不断见诸于各类新闻媒体。
综上所述,由于传统“宏大叙事”文化范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宪政始终是法律与政治融为一体,宪法没有发挥其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应有价值。西方宪法在舶入中国后成为了帮助推行行政集权和维护国家权力一元化的重要工具。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放弃这种“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而将改革的中心集中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从微观的视角来制定符合逻辑的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制度,以更加务实的理性态度来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宪政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