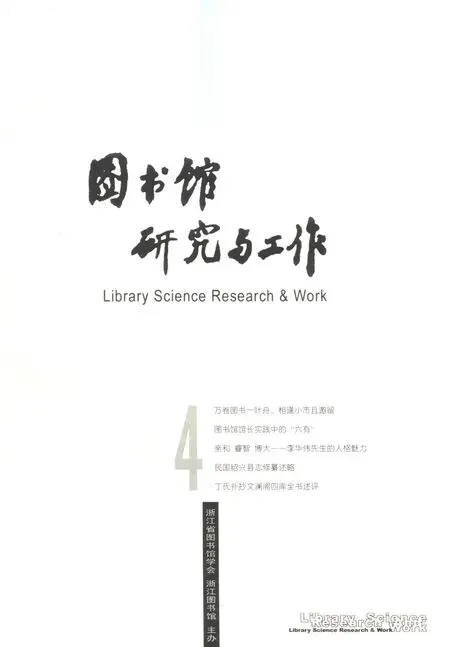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活动于江南古书旧籍市场上的“书船”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作者信息〕徐雁,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与江、浙经济发达地区所存在的私刻、坊刻业相适应,自明嘉靖、万历以来,曾经活动着一种沿内河水系和运河专营书籍买卖的“书船”。
因与书香为伍,经营者颇识书文化之道,所以湖州书贾足迹所至之处,多能获得主顾家的礼遇,一般都敬之末座,称为“书客”或“书友”,甚至在明末清初还出现了子承父业的书估世家。
吴敬梓(1701—1754年)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写道:“(王冕)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栓了,坐在柳阴下看。”那“书客”,当指以“书船”为交通工具,在乡村城镇间兜卖书籍、纸墨文具的流动商贩。自此百余年后,尚有鲜明的“书客”影像,印存在缪荃孙(1844—1916年)的童年记忆中:
余幼时在申港(今属江苏江阴——引者注),时有书客负一大包,闯入书塾。包内湖笔、徽墨、纸本、《四书》、经书,村塾所需无不备。议价后,问家有旧书、残破书否?见村童临帖稍旧者,均欲以新者相易,盖志在收书也。
十岁时,在澄怀堂读书。书室有阁,阁上尽破碎之书。一日,书估尽搜括之,雇数夫担而去。但见有钞本、有刻者,有绢面者,有小如掌者,有大盈尺者,不知何名也。易得者道光《字典》、角山楼《类腋》、雅雨(堂)《韩集》、《三国演义》、《左传》等书,皆新装订者。一村有十余塾,无处不到。(太平军)乱后则无。村中亦止有一二学塾,藏书亦尽毁于庚申(1860年)之乱矣。〔1〕
由此可见,由“书船”这一江南特有的书籍流动贸易方式所造就的“书客”群体对书文化的影响。
1 “织里书船”的来龙与去脉
据浙江湖州学者说,“书船”又称“织里书船”,“是明、清乃至民国湖州独有的一种船,一种专门卖书的船。据史志记载,书船始于明初,嘉靖至万历年间,因雕版印刷业发达,书船步入鼎盛阶段。明代、清朝、民国特别盛行,直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日本人汽艇入侵江河,方才慢慢绝迹”,“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去织里郑港、谈港一带访求遗迹,上了年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书船业的兴旺景象。”据介绍:
织里书船都为当地农船改装而成,仅三、五吨。置船棚,棚下两侧置书架,陈设各种书籍,中间设书桌和木椅,供选书者翻阅时享用。书商们向刻书家趸购书籍,装货出运,由两名船夫轮流摇橹,一路沿埠相售。书船是方便文人求知购书之所在,船一到船埠系好缆绳后,就任人上船选择书籍。同时将预备好的书目传单放在衣袖筒内,随时出入官宦、生员、举子之家……于是商人从袖筒内取出书目单,任由主家浏览选择。书商们则被人们誉称为“书客”。
“书客”们不仅卖书,还想方设法收购秘卷佚本。沿埠购书的主家若有看过的、多余的孤本奇书,取来交换新书;或者,“书客”们有意识地向沿埠贫穷人家收购闲置着的上辈手里传下来的好书。所以,“书客”们的手中常常会拥有秘本好书,又转售与雕刻家刊印。这不仅是双方得利的好事,而且推动了晟舍刻书业和贩书业的发展。书商们往往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各地书籍的刻刊与销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晟舍和其它地方编纂和刻书业的繁荣……织里书船在运贩新书的同时,也为藏书家藏书的聚、散,起到中介、流通作用,所以更促进明、清至民国时期江、浙私家藏书的兴盛。〔2〕
大抵在晚明时,湖州的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诸家,都曾广储古书旧籍,镂刻所藏秘册。如凌、闵二家所刊,多择善本,刻板工艺精良,并从创意朱、墨两色套印本,发展到三、五色套印本,其选题涉及小说、戏曲、史籍、唐人诗集和儒家经典等。陈继儒(1558—1639年)说:“吴兴硃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垂涎购之”,有“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之评。据陶湘(1871—1940年)《明吴兴闵板书目》统计,明亡前二十余年,闵、凌二氏所刊套印本多达117部145种。
另一方面,数百年来,积累于江南民间的古书旧籍资源已颇丰厚。归有光(1506—1571年)在《世美堂后记》中曾说:“吾妻……以余好书,故家有零落篇牍,辄令里媪访求,遂置书无虑数千卷。”这是明嘉靖初年(1522年)的事。
品种多样的新书与存量颇为丰富的古旧书货源,以及耕读之家和藏书家日益增长的对读书、藏书的需求,使得地傍太湖的织里镇及其附近的郑港、谈港等地村民从中发现了商机,而得以借助“书船”来从事书籍零售或批发。
“书船”主人往往浮家泛宅地沿着发达的江南水网活动,其范围大抵北达京口(今江苏镇江),南抵钱塘(今浙江杭州),东至松江(今属上海)。他们出入各地文人儒士和藏书人家,既兜售新印图书,顺便也兼顾着买卖古书旧籍。浙江归安人张鉴(字秋水,1768—1850年)说,“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出则偏舟孤棹,举凡平江远近数百里之间,简籍不胫而走。”
“苕贾(估)”之名享誉江南,无论是客居者还是本地人,都对苕贾的“卖书船”留有深刻的印象。“吴江四子”之一、曾寓吴兴南浔镇的藏书家张隽(字非仲、文通,约1590—1663年)有《寓浔口号》云:“自于香火有深缘,旧管新收几缺编。旅食数年无可似,最难忘是卖书船。”〔3〕而乌程人汪尚仁(字敦夫、静圃,生卒年不详)《四勿斋吟集》中有《吴兴竹枝词》云:“制笔闻名出善琏,伊哑织里卖书船。莫嫌人物非风雅,也近斯文一脉传。”〔4〕
2 出生于龙游书贾之家的知名“书客”——童珮
在晚明的书林文坛,最为人乐道的,当数浙江龙游书贾之家出身的童珮。
按:浙江龙游,春秋时期建有“姑篾”古国,迄今已有2200多年建县史,古来就有“四省通衢汇龙游”之称。文化资源积淀丰厚,有“儒风甲于一郡”之誉。市场意识形成较早。“龙游商帮”是明清时期全国十大商帮之一,是唯一以县域命名的商帮。
据当地县志记载:“(龙游)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故俗有‘遍地龙游’之语。”明人王士性(1547—1598年)在《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浙江》中,有“龙游善贾”的称说,说其所经营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眼之类的细软宝物,但“千金之货,只一人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蓝缕,假痈巨疽膏药,内皆宝珠所藏,人无知者。异哉贾也。”后为顾炎武(1613—1682年)《肇域志》所引用。童彦清、童珮父子在江南从事买卖古书正当这一历史时段。
童珮字子鸣,又字少瑜,性喜读书作诗,曾就学于归有光。他继承其父童彦清的贩书业务,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侨寓无锡,主要在苏南水网地带做古旧书的生意,并以所撰诗文与文人士大夫往还。归氏在《送童子鸣序》中说:“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以鬻书为业。异时,童子鸣从其先人游昆山,尚少也。”但当童子鸣再次与归有光相见时,他已长大成人,不仅能写出清俊可诵的诗,而且还诵读了许多书。
那么,既爱读书又爱做诗的童珮,又是怎样经营其贩书生意的呢?当时的书法名家、诗人王百榖(1535—1612年)在《金阊集》卷四中有一篇传记,略云:
童君名珮,太末人。家山坂中,山田饶者为直黄金半镒,太末人非厚富不能田,童君乃从其父为书贾人。父娶吴女,生童君,童君遂作吴音,行迹亦多在吴中。买一舫不能直项,读书其中,穷日夜不休。为诗皆性灵,读之萧萧有云气。特不善修行骸,人知者知其人,不知者知其诗,甚即白眼视之,蔑如也。其书帆樯上下皆罗列,手一编,读罢即投置他所,不复归旧箧,故其书漫无甲乙次第。人来售,又不耐检校,悉弃去。每慨世人不能读古书,见一奇士即授之。玄篇奥帙,往往零落不存。〔5〕
如此一副名士作派,难怪归有光要为之忧心不已:“子鸣鬻古之书,然且几于不自振,今欲求古书之义,吾惧其愈穷也。”〔6〕
童氏不仅买卖书籍,自己也选择收藏一部分,藏本皆手自校雠,且善配补古书。他校辑有唐诗人杨炯《杨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焦竑说:“《杨炯集》二十卷,今不传。第诗数十篇耳。近童珮搜访遗文,合为十卷,有《王子安集序》”,认为其学术价值在于“可为《文中子》非伪书一证。”〔7〕在天一阁旧藏中,还曾见有童氏辑刻的唐文人徐安贞《徐侍郎集》二卷。
王世贞(1526—1590年)对生平有嗜书异行的童珮,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送陆秋生吊童子鸣》诗中写道:“絮酒轻千里,生刍托寸心。一贫无挂剑,百感为分金。泪向吴江尽,恩偏越峤深。山阳夜中笛,肠断不堪寻。”
胡应麟(1551—1602年)曾觅得童珮家书目,多至二万五千卷。他发现:“颇多秘帙,而猥杂亦十三、四,至诸大类书则尽缺焉。盖当时未有雕本,而钞帙故非韦布所办,且亦不易遇也。”〔8〕可见其藏书结构,具有“掠贩家”的典型特征。
王士祯(1634—1711年)见到《童子鸣集》后感叹说:“余观南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叹书贾中乃有嗜古雅尚如斯人者。龙游童子鸣亦以贾书而有诗名。其集吴郡黄河水所定,凡六卷。”是即《童子鸣集》(一说凡八卷)。
3 苕上书估与“湖州书舶”的书籍经营活动
胡应麟(1551—1602年),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别署“石羊生”,浙江兰溪人。学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也是在文献上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古旧书业史的第一人。王嘉川认为,胡氏的《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不仅总结了历代的图书收藏,考察了历代图书典籍的兴废情况,而且探讨了藏书功用、藏书家类型以及明朝当代图书事业发展情况等,是“中国第一部图书事业史著作”。〔9〕
在《经籍会通》中,胡氏自述从童年起,就养成了爱书之癖。少年时,他随同其做官的父亲,“遍历燕、吴、齐、赵、鲁、卫之墟,补缀拮据垂三十载”,“穷蒐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这才收集到了古书旧籍二万余卷。他总结其四方奔走、穷蒐委巷的淘书经验,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书业资料:
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两都、吴、越,皆余足隶所历,其贾人世业者往往识其姓名……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不售矣。〔10〕
“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之说,表明当年我国四大书业中心分别是北京、苏州、金陵和杭州,而金陵与江、浙一带已有“贾人世业者”,说明其时类似于童家之家传书籍买卖业务者,已非个别。
据《汲古阁主人小传》说,江苏常熟人毛晋(1599—1659年)曾悬榜于门,高价征购宋椠旧钞和新刊善本,结果“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常熟城里流传出“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语。浙江归安人郑元庆(字子余、芷畦,1660—约1730年)则在所辑《湖录》中说,历史上收藏之家往往托付“书船”主人代为觅求奇僻之书,“今则旧本日稀,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但事实上,直至清代、民国前期的三百年间,这一带依然是华夏古书旧籍资源的集散地,足以说明此一区域民间书籍积聚之富,而“书船友”则是其资源集散的重要中介之一。
湖州“书船友”曾为清廷编纂《四库全书》征书效力,在华夏古旧书业史上历来为人津津乐道。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谕旨云:“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人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物色”,翌日又有一谕专寄两江总督高晋云:“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买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因此后来俞樾(1821—1907年)为《武林藏书录》题诗,咏其事云:“山堂书贾推金氏,古籍源流能缕指。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不知何路达宸聪,都在朝廷清问中。星火文书下疆吏,江湖物色到书佣。”
浙江海宁藏书家陈鳣(1753—1817年)博学好古,尤擅版本校勘与训诂之学。生平好藏书,勤于访购,遇宋元古书、旧抄,不惜高价购置,其向山阁藏书十余万卷。他有《赠苕上书估》诗两首云:
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
几回展读空搔首,废我行囊典敝裘。
人生不用觅封侯,但问奇书且校雠。
却羡溪南吴季子,百城高拥拜经楼。
另有《新坂土风》诗云:“阿侬家近状元台,小阁疏窗面面开。昨夜河头新水长,书船多是霅溪来。”自注云:“邑中无书肆,惟有苕估书籍。”
黄丕烈(1763—1825年)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从来不吝其与书船主人交往买卖古旧书的笔墨。如《普济方》跋云:“初,书坊某云书船有残宋本《普济本事方》……昨,书船之友携来各书,倶无惬意者。因询前书,云尚在某坊”;又《曹子建集》跋云:“此系活字板,当属明本。余向亦有之,不知何时散逸,后为书船友收得……”;“此家豫章《外集》六卷,得诸书船友邵姓,云自江阴杨文定公家收来,卷端有杨敦厚图章,即文定孙也。装潢精雅,亦以其为宋刻,故珍之”等等。〔11〕可见活动于江南一带城乡的“书船”、固定经营于都市的书肆与藏书家和读书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王稼句在《书船》一文中指出:
“书船友”在书贾中是别一群体,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里,将书坊、书友、书船友、估人、骨董人都分别注明,绝不混淆,(他)提到的“书船友”,就有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他从曹处得抄本《铁崖赋稿》,从吴处得金本《中州集》,从郑处得宋本《新序》、宋本《冲虚至德真经》,从邵处得残宋本《普济方》、残宋本《豫章黄先生外集》,这几位就是乾隆至道光年间活跃在苏州的书船中人。
太平军乱后,书业萧条,叶德辉就在《书林清话》卷九里感叹道:“吴门玄妙观前,无一旧书摊,无一书船友,俯仰古今,不胜沧桑之叹矣。”就是追忆“书船友”在坊间走动的情形。〔12〕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浙江湖州藏书家陆心源(1834—1894年)在《(同治)湖州府志》中说:“太湖有书船,夙善聚书。(太平军)兵后得于书船者,尚不下数万卷。”
郑士德在《中国图书发行史》中指出,清代前期的杭州书肆和书坊,“除收售本地的古旧书外,还代为销售本地刻书家刊行的新书,并从苏州等地书坊补充新书货源。杭州、湖州、苏州、无锡之间有水路相通,这一带以贩书为业的书船,常常装满新刻的书籍,沿苕溪、运河在各处销售,同时也贩运给杭州的书店……对活跃图书贸易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3〕
〔1〕 孙安邦点校;缪荃孙著.云自在龛随笔.卷四〔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9:213-214
〔2〕 叶银梅、嵇发根主编.人文织里.第四章〔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4:98-101
〔3〕 周庆云.南浔志〔M〕∥史念海,谭其骧等.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卷上.上海:上海书店,1992:603,231
〔4〕 许学东主编.古诗吟湖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8:201,274
〔5〕 转引自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738
〔6〕 归有光.送童子鸣序〔M〕∥归有光撰.震川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267-268
〔8〕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49
〔9〕 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第三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153
〔1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40-44
〔11〕 屠友祥校注,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10:272,498-499,613
〔12〕 王稼句.书船〔M〕∥王稼句.听橹小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9:65
〔13〕 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第九章〔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0: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