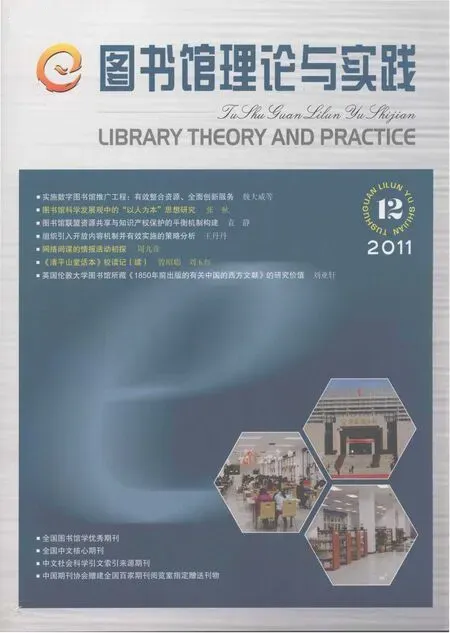《清平山堂话本》校读记(续)
●曾昭聪,刘玉红
(1.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632;2.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广州 510610)
《清平山堂话本》是明代洪楩所刻的《六十家小说》的辑佚本,多宋元话本。此书最早有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刊印会影印本《清平山堂话本》15篇和马廉平妖堂影印本《雨窗集》《欹枕集》12篇。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合此二种影印出版,仍以“清平山堂话本”为名(1987年重印)。1957年,谭正壁据前二种影印本加以校点,仍以《清平山堂话本》为名,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这是现存最早的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据此重印。[1]此后,其他较重要的校注本或标点本主要有:石昌渝校点本、[2]王一工标点本、[3]程毅中辑注本[4](其中收《清平山堂话本》17篇)、韩秋白校点本。[5]以上诸本,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谭校本最早,可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然亦有不少失误,这主要表现在对宋元时代的语言现象尤其是俗字、俗语词理解不够,以不误为误的误校情况在此书中甚多。其他校点本亦或多或少有其不足。对于以上几种校点本中的误校、误点、失校等情况,已有一些论文及刘坚《近代汉语读本》[6]对其作出若干补正,但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之处仍然很多。笔者近来据前述两种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对漫漶、墨丁、空白等处有大量修补,不据)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例如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先生翻译成日语的《雨窗欹枕集》和《清平山堂话本》[7])对《清平山堂话本》进行校注。今选其可读者二十馀条胪列于下,请方家教正。因笔者曾撰文《〈清平山堂话本〉校读记》,[8]故此文以“续”名之。
1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
扣,谭校:“通作‘彀’字。”程校:“当作‘彀’字。”高云海、刘志军《校议》以为“机扣自有机关义,无烦借用通假”,[9]盖本《汉语大词典》此条释义。按,“彀”由张满弓弩义引申为范围、圈套义的用例及“机彀”的用例很多,而《汉语大词典》“机扣”条仅举此一例,不具说服力。故当从谭校。
2 《西湖三塔记》:妈妈听得出来,见宣赞面黄肌瘦,妈妈道:“缘何许久不回?”
“听得出来”四字,入矢义高以为是衍文,他在校语中说:“この前に‘聽得出来’という四字があるが、衍文と認める。”因而在其译文中删此四字。按上文:“慢慢依路进涌金门,行到自家门前。娘子方纔开门,道:‘宣赞,你送女孩儿去,如何半月才回?交(教)妈妈终日忧念!’”入矢义高致误的原因是把上文“娘子方才开门”的“娘子”误译为“母上”(妈妈),因而误以为此四字为衍文。
3 《西湖三塔记》:只见树上一件东西叫,看时,那件物是(事)人见了比嫌。
比,谭本、石本等校为“皆”字的残缺,程本以为:“比嫌”即“鄙嫌”,今吴语有“嫌鄙”,乃鄙薄之意。按,明代小说中“嫌鄙”用例较多,为厌恶之义,本书编者洪楩为钱塘人,用吴语的相近形式是有可能的。“鄙嫌”用例如《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四:“《遗史》曰:张邦昌僭位王时,雍谄事之,凡事有‘臣启陛下’之语,虽邦昌之僭,亦鄙嫌之。”底本“比”字清晰,未有残缺,故程说为优。
4 《西湖三塔记》:娘娘听了,柳眉剔竖,星眼圆睁道:“你尤(犹)自思归!”叫:“鬼使那里?与我取心肝!”可令把宣赞缚在将军柱上。
谭本、石本校“令”为“怜”。按,“令”未必误。“可”有“再”义,近代汉语中多有用例,例如元高文秀《襄阳会》第一折:“咱且屯军居止。若聚集的些人马呵,那其间可与曹操雠杀,未为晚矣。”又无名氏《看钱奴》第二折:“儿也,我写了可与你说。”“可令”即再命令(上文已有令缚宣赞取心肝之事)。
5 《西湖三塔记》:手持七宝镶装剑,腰系蓝天碧玉带。
“天”,当作“田”。“蓝田”,县名,以产美玉闻名。“蓝田碧玉带”,用蓝田所产之碧玉做的腰带,极言其珍稀,并与上文“七宝银装”相配。
6 《风月瑞仙亭》:卓员外道:“先生去县中安下不便,敢邀车马于舍,何如?”
诸本径录为“弊”,又均校为“敝”之误。不妥。弊尖,乃“弊”之正字。《广韵·祭韵》:“弊尖,困也,恶也。《说文》曰:‘顿仆也。’俗作弊。”“弊”有“残破”之义。《国语·晋语六》:“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战国策·秦策一》:獘“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淮南子·说山》:“獘箄甑瓾在袇茵之上,虽贪者不博。”獘,一本作“弊”。《风月瑞仙亭》中之“弊舍”,乃卓王孙自谦之词。
7 《快嘴李翠莲记》:这们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儿滴滴地。
们,底本作“们”,谭本、石本误录为“门”。按“们”“门”二者词形不同而义通,作词的后缀,用在指示代词后面,相当于“这么”“那么”的“么”。元无名氏《刘弘嫁婢》第一折:“着我出去,便出去了罢,受他这们闲气做甚么!”《西游记》第八十六回:“猪八戒见了就哭道:‘可怜啊,那们个师父进去,弄做这们个师父出来也!’”
8 《快嘴李翠莲记》:张太公道:“小娘子放心,令尊与我是老兄弟,当得早晚照管;令堂亦当着老妻过去倍伴,不须挂意!”
倍,谭本、石本、程本均校为“陪”的误字。不妥。“倍”是“陪”的古字。《穆天子传》卷六:“丧主即位,周室父兄子孙倍之。”郭璞注:“倍,倍列位也。”洪颐煊校:“倍,古陪字。”唐韩愈《大行皇太后挽歌词》之三:“追攀万国来,警卫百神倍。”9 《快嘴李翠莲记》:哥哥、嫂嫂相傍我,前后收拾自理会。
傍,程本校为“帮”。按,“傍”可音bànɡ。“傍”有靠近义,引申有帮助义。《新书·胎教》:“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
10 《快嘴李翠莲记》:先生道:“新娘子息怒。她是个媒人,出言不可大甚。自古新人无有此等道理!”
大,诸本均校为“太”字之误。按,“大”作副词可表程度深。《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这西湖不深不浅,不阔不远:大深来难下竹竿,大浅来难摇画浆;大阔处游玩不交,大远处往来不得。”
11 《快嘴李翠莲记》:关了门,下幔子,添些油在晏灯里。
晏灯,程注则疑有误。按“晏”即“晚”义,不误。唐韩愈《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有时来朝餐,得米日已晏。”故“晏灯”即夜灯。刘坚《读本》:“即夜灯,终夜不熄灭的灯。”释义甚是。
12 《快嘴李翠莲记》:两亲相见毕,婆婆耐不过,从头将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一一告诉一遍。
两亲,诸本均校为“两亲家”,按“亲”有“亲戚”义。本篇即“诸亲”“诸亲九眷”等词,其中“亲”即“亲戚”。“亲”下未必有脱字。
13 《快嘴李翠莲记》:亲操井臼与炮厨,纺织桑麻拈针线。
炮,诸家校为“庖”字之误。按,当为通假字而非误字。《韩非子·内储说下》:“晋平公觞客,少庶子进炙而发绕之。平公趣杀炮人,毋有反令。”又,《韩非子·难二》:“凡为人臣者,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炮”均通“庖”。
14 《快嘴李翠莲记》:擗柴挑水与炮厨,就有蚕儿也会养。
擗,诸家校为“劈”字之误。按“擗”有“分、析”义,不烦改动。三国魏曹植《送应氏》诗之一:“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包节级措手不及,被解宝一枷梢打重,把脑盖擗得粉碎。”“擗柴”不误,即劈柴义。
15 《洛阳三怪记》:这条路游人希少,正行之间,听得后面有人叫“小员外”。
希少,石本、程本均校改为“稀少”。按“希”非误字。“希少”义同“稀少”。《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宋苏轼《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不涉浮山之崄,时有覆舟,然尚希少。”
16 《洛阳三怪记》:风亭弊陋,惟存荒草绿凄凄。
弊,谭本、石本校为“敝”字之误。按“弊”字不误,“弊陋”义为破旧粗劣。《北史·列女传·姚氏妇杨氏》:“以姚氏妇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宋苏洵《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帏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又,凄凄,谭本、石本、程本均校为“萋萋”之误。按,“凄凄”不误,义同“萋萋”,茂盛貌。唐无名氏《甘棠灵会录》:“春草凄凄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
17 《洛阳三怪记》:只见庙中黄罗帐内,泥金塑就,五彩庄成,中间里坐着赤土大王,上首玉蕊娘娘,下首坐[地]着白圣母,都是夜来见的三个人。
庄,诸本以为当作“妆”,或以为“装”之误字,不妥。“庄”,乃“莊”之俗字。“莊”有装饰义。《古今韵会举要·阳韵》:“莊,《说文》:‘盛饰也。从艸、壮。’壮亦盛也。”晋法显《佛国记》:“然后彩画作诸天形像,以金银琉璃莊校其上。”《南史·后妃传上·潘淑妃》:“帝好乘羊车经诸房,淑妃美莊饰褰帷以候。”
18 《洛阳三怪记》:忽一日,行到鱼池边钩鱼。放下钩子,只见水面开处,一个婆子咬着钩鱼钓。
前一个“钩鱼”之“钩”,诸本校为“钓”。按“钩”有动词义,“钩鱼”亦通,似不烦改动。“钩鱼钓”,诸本校为“钓鱼钩”。按,“钓”可作名词,指鱼钩。《淮南子·说林》:“无饵之钓,不可以得鱼。”南朝宋谢惠连《咏螺蚌》:“纤鳞惑芳饵,故为钓所加。”唐韩愈《题秀禅师房》诗:“暂拳一手支头卧,还把渔竿下钓沙。”故“钩鱼钓”未必有误。不过从上文来看,校作“钩鱼钩”似更好。
19 《洛阳三怪记》:黄罗抹额,污骖皂罗袍光;袖绣团花,黄金甲束身微窄地。
“黄罗”句,据程本,《警世通言》卷十四《一窟鬼赖道人除怪》有类似文字:“黄罗抹额,锦带缠腰。皂罗袍袖绣团花,金甲束身微窄地。……”“窄地”即匝地,“微窄地”言金甲几乎长及地面。“光”后似可补“耀天”二字。
20 《张子房慕道记》:手冷如钳,脚冷如砖。
钳,刘瑞明《〈张子房慕道记〉的校勘及时代讨论》以为当作“铁”字。[10]按,钳为古刑具,为束颈铁圈。《旧唐书·刑法志》:“又系囚之具,有枷、杻、钳、锁,皆有长短广狭之制。”故“钳”字不烦改。
21 《张子房慕道记》:高祖听罢,心中大喜,龙颜甚悦,即排鸾驾,前往白云山前,寻访一遭。行至一日,只见茅庵一所,不见张良,令人来到名山,有诗为证:……
“令人来到名山”一句,入矢义高疑衍,其译文略去此句,并注:“原文はこのあとに‘令人來到名山’といぅ一句があるが、前後の文脈が通じないから、省くことにする。”(原文是“令人来到名山”,前后文气不通,故略去。)按,从尊重原典的角度考虑,将此处视作倒文而非衍文似更好。可以改为:“行至一日,只见茅庵一所。令人来到名山,不见张良,有诗为证”。其中“令人”之“人”,指高祖。这样理解,即文从字顺。
22 《张子房慕道记》:红颜(花)爱色抽心死,紫草连枝带叶亡。
连枝,刘瑞明《讨论》校为“恋姿”。按“连枝”指树枝条连生一起,喻同胞兄弟姐妹或恩爱夫妻。不误。此句和上句“红颜(花)爱色抽心死”谓世上人情牵挂,最终只会致人于死。
23 《阴骘积善》:且说张客到于市中,取珠欲货,不知去失。
去失,程本疑为“丢失”之误。按“去失”不误,义同“丢失”。《元典章·吏部八·案牍》:“人等俱系专管案牍人员,年来不为用心关防,多有去失文凭籍历。”
24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那风过处,只见两个红忔兜巾天将出现,甚是勇猛。
忔兜,此二字《古今小说》无。疑“忔”字衍。红兜巾,即红围巾。
25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标题。
花灯轿,入矢义高以为是“花籐轿”之误:“原文は‘花灯轎’。‘灯’は‘籐’の誤。南宋の都の杭州の繁昌記‘夢粱錄’によれば、婚礼の時の嫁迎ぇには花籐轎を用いる習わしだつたといろ。”可从。因典籍未见“花灯轿”之用法,而“花籐轿”用法则数见。入矢义高所引《梦梁录》(据学津讨原本《梦粱录》卷二十《嫁娶》)原文是:“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缾、花烛、香球、纱罗、洗潄、妆盒、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雇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担子,或棕担花籐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又如,宋卢炳《洪堂词·前调》:“名园精舍,总被游人到。年少与佳人,共携手嬉游歌笑。夕阳西下,沈醉尽归来,鞭宝马,闹竿随,簇着花藤轿。”“藤”同“籐”。
26 《曹伯明错勘赃记》:这曹伯明每日五更出去接客,只是不在家多。你去五更头,等他来时,打死了他,咱两个永远做夫妻,却不是好?
五更头,当作“五里头”,涉上文“五更”而误。入矢义高注:“町の門に通ずる城外の地名であろぅ。今でも城外に、この名で呼ばれろ土地が、中国のところどころに見られる。”(与城门相通的城外某地名。现在中国各地城外还有这一称呼的。)有注而无校。确切地说,当作“五里头”,指距城市五里远的一个地方。下文“五里头”“五里地”“五里路”交替出现,均是指距城市五里远的一个地方。这多种不同的地名写法,可能是因为该地距城市的距离五里远,但又没有固定的地名,故“说话人”临时为之取名,以表现故事情节发生地是在城市近郊五里远的地方。类似用法典籍习见。如《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一《神仙门·卖酒遇仙》:“道人喜,又曰:‘闻宅上有丧未葬,贫道善风水,宅上自有地在五里头某处,宜急葬,则立致富贵。’”《警世通言》卷三十七:“陶铁僧拽开脚出这门去,相次到五里头,独自行。”如果是在离城更远的地方,同样可以距离远近的数字命名。《新编五代史平话·晋史平话卷上》:“汉王乃筑坛一所,在褒州四十里头。”今地名中犹沿用有此类用法,如西北师范大学所在地即为兰州市十里店桥。
27 《夔关姚卞吊诸葛》:三顾频繁,两朝开济,何处寻遗迹?
程本据《花草粹编》校“繁”为“烦”,不必。二字可通用。如《清平山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烦阴已转,日影将斜。”烦,通“繁”。烦阴,即繁荫,浓密的树荫。
[1]谭正璧校点.清平山堂话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石昌渝校点.清平山堂话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3]王一工标校.清平山堂话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0.
[5]韩秋白点校.清平山堂话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修订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7](日)入矢义高.雨窗欹枕集[M]//清平山堂话本.东京:平凡社,1958.
[8]曾昭聪,刘慧.《清平山堂话本》校读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5):51-54,109.
[9]高云海,刘志军.《清平山堂话本》校议[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5):95-97,11.
[10]刘瑞明.《张子房慕道记》的校勘及时代讨论[J].文教资料,1999(4):9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