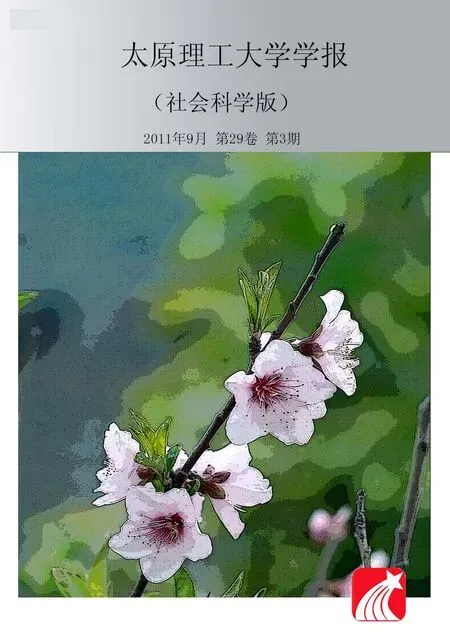医疗侵权过错的证明困境及其对策*
王德新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医疗侵权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进行诊疗活动中,因故意或过失造成患者遭受损害的案件,诸如医生误诊、手术失误、护理不当等。对于医疗机构的侵权责任,各国普遍奉行“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对于由谁来证明存在医疗过错,却一直存有争议。2010年7月1日我国《侵权责任法》生效,该法原则上要求:由原告患者证明被告医疗机构有过错,仅在第58条规定的三种例外情形下实行“过错推定”。证明责任分配往往决定了当事人胜诉的几率,在诉讼法上有“证明责任之所在、败诉之所在”的法谚。[1]44在当前医患关系颇为紧张的情势下,《侵权责任法》要求患者承担证明责任的规定是否合理,颇值得探讨。
一、医疗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及其证明的困难性
医疗过错,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实施诊疗活动时,对于患者遭受的损害存有的主观心理状态。医疗过错是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在医疗侵权案件中,患者在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方面存在显著的困难,原因如下。
第一,医疗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医师从事的是一种专家活动,要判断其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注意义务、程序、步骤等,对不具有医学知识的患者来说十分困难。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根本不知道医务人员在诊断、治疗活动中负有哪些注意义务,也很难判断他们是否尽到了这些注意义务。
第二,医疗诉讼中的证据多在医方控制之下。由于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病历资料等均由医方书写并保存,因而,无法避免书写不实或者篡改病历的可能性。在诉讼中,要求患者举证无疑增加了其举证和胜诉的难度,而要求医方举证则相对容易。
第三,患者一方在接受治疗时可能处于无意识状态,无从了解医疗活动的情况。例如患者因为病重处于昏迷状态,或者由于治疗手段之需要(如进行手术)而将患者麻醉。此种情形下,患者自然无法证明医方存在过失。
第四,患者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除了在专业知识、接触证据的机会、掌握医疗活动信息等方面处于弱势一方之外,患者作为一个自然人,在经济实力方面往往也无法与医疗机构相提并论。没有经济实力,患者在支付律师费、搜集证据的开支、鉴定费用等方面都会存在困难,这对于司法正义的实现来说显然是一个现实的障碍。
总之,医疗活动的特点决定了患者在证明医方存在医疗过错方面存在特殊的困难。正因如此,西方各国对于医疗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纷纷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以减轻或免除患者的证明责任,保障患者的权利。
二、各国缓解患者的证明负担的法律对策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的法律实践和学说
在英美法系国家,医疗侵权案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援用“通过事实推定过失规则”(Res Ipsa Loquitur)来减轻患者对医疗过错的证明负担。该规则的含义是:当某种事实和现象发生时,法院可直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无需举证证明。
在美国,目前已有37个州的法院在判决中援用了“通过事实推定过失规则”。其适用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在一般情形下,若非出于某人之过失事故不致发生;第二,引起事故之方法、工具或其代理人系在被告的排他性控制下;第三,事故的发生非基于原告之自愿行为或过失所致。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第328条D项对“事实推定过失原则”的规定就体现了上述三要件说。[2]89为什么要“通过事实推定过失”呢?一个原因是,当事人双方的资讯不对等。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患者可能处于无意识状态,无从知道医师是否有过失,加上有关医疗之证据,医师较患者容易取得,造成当事人双方因资讯不对等而有程序上的不公平。第二,避免出现医疗同业者之间的“沉默共谋”(Conspiracy of silence),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医医相护”。在美国,许多医师都不愿作为原告的专家证人作不利于被告同行的证言,“沉默共谋”无疑使原告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3]112
“通过事实推定过失”的具体效果如何?有三种学说。第一,过失推论说。认为其效力只不过是使原告避免了遭受败诉之“指示判决”,被告并不因此负担较重之证明责任。第二,过失推定说。认为其效力不仅使原告避免败诉之“指示判决”,且迫使被告负担证据提出责任。换言之,说服责任虽不转换,但须就无过失亦可能发生损害之事实加以合理说明。第三,证明责任转换说。认为其效力是发生证明责任“倒置”,即被告应就其无过失负证明责任,否则难免遭到败诉之命运。[4]76其中,过失推论说系传统观点,过失推定说为目前的通说,但也有判例显示,有逐渐向证明责任“倒置”说演变的趋势。这表明,进一步减轻患者对医疗过错的证明责任,是英美医疗侵权法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大陆法系的法律实践和学说
在法、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医疗侵权也采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但是,它们往往采取“表见证明”、“举证责任转移”等技术性处理来减轻原告患者的证明负担。
首先,表见证明制度。为了缓解“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德国法院创造了“表见证明”制度。通说认为,“表见证明不是独立的证明手段,而仅仅是在证明过程中对经验规则的应用。这种应用的前提是存在所谓典型的发生过程,也就是指有生活经验验证的类似的过程,由于这种过程具有典型性,它可以对某个过去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验证(类似性证明)。如果法官采纳了某个表见证明,当事人只需要提出反证就可以推翻,而无需进行反面证明。”[5]141也就是说,“表见证明”并不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只是减轻了原告的证明负担。自1951年12月13日判决的遗留止血钳事件、1957年2月12日判决的梅毒输血案等案件以后,联邦德国司法法院开始应用“表见证明”的方法减轻患者对医疗过错的证明负担。[6]513在1965年前后,日本医疗过失诉讼、公害诉讼大量出现,由于此等案件在过失及因果关系的举证上都相当困难,遂在德国“表见证明”理论的基础上酝酿出了“过失之大概推定”理论。[7]132“过失之大概推定”理论与“表见证明”非常相似,都是为了减轻原告的证明负担。
其次,证明责任倒置。20世纪60年代以后,德国法院关于医疗侵权的许多判例均认为,如果医生的行为有重大失误,造成病人身体遭受重大损害,应由加害人就其失误行为为不存在故意、过失,以及该行为与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进行证明。[8]92与“表见证明”相比,证明责任倒置不仅使被告对其行为不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因不能证明而导致的败诉结果。不过,证明责任倒置的适用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第一,必须有“重大医疗过失”存在,即明显地违反医学界公认的技术规范。对于是否存在重大的医疗过失,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第二,必须存在充分因果关系,即医疗过错足以引起患者所受到的伤害。因果关系只能根据医学知识及经验来判断,因此诉讼中往往借助于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来作出判断。
(三)新西兰、瑞典、加拿大的法律实践和学说
有些国家在探索解决医疗过错的证明难题方面走得更远,开始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意味着,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不再是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诉讼中双方都不需要证明侵权行为人是否有过错。
1972年,新西兰颁布了《事故赔偿法》,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建立了无过错责任赔偿体系。根据该法,适用无过错赔偿的范围覆盖了几乎所有因突发事件造成的人身损害,当然也包括医疗侵权在内。事故赔偿的费用,主要取自于用人单位、劳动者本人、车辆所有人和政府税收。[注]See the 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1972,N.Z.Stat.No.43.1975年,瑞典创设了医疗保险制度,保险费取自地方医疗单位和执业医师。凡是因不当医疗行为产生医疗损害,致患者住院10天以上或误工30天以上的,均可得到无过错赔偿。1988年,挪威实施了与瑞典相似的制度,丹麦和芬兰也建立了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在加拿大,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建议采用“有限的”无过错责任制度,同时推行多项制度改革来减轻患者对医方过错的举证困难,如降低律师风险代理费、加快诉讼程序、缩短诉讼时间、探索医疗纠纷的替代解决方法、严格控制医疗质量,以及有效管理医疗风险等。
三、我国缓解医疗过错的证明困难的法律对策及其评价
(一)我国缓解患者证明医疗过错的困难的三种方案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法院对医疗侵权案件实行过错责任,要求原告患者证明被告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后来,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备受质疑,于是出现了如下新的法律对策。
1.方案一:适用“消法”的规定,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1994年1月1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实施。该法第4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消法》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有一种观点认为,医患关系本质上也是消费关系,医疗侵权应该适用《消法》规定的无过错责任。2000年10月,浙江省人大制定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第一次明确宣告医疗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但是,地方法规的这种做法没有得到中央立法的认可,随着后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现,地方法规已无继续适用的空间。
2.方案二: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但以“过错推定”的方式使证明责任倒置
2002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第49条还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可知,《条例》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则无责任。但由哪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呢?2002年4月生效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可见,最高法院采用“过错推定”的方式,要求被告医疗机构对自己没有过错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否则,推定被告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显然,这是对“医疗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进行了倒置。
3.方案三: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并要求原告对医疗过错承担证明责任
2010年7月1日,我国《侵权责任法》开始生效。该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58条又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综合这两个法条可知,我国新的《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侵权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并原则上要求原告患者对被告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负证明责任;仅在第58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下,保留了最高法院原司法解释中对医疗过错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做法。
(二)对几种医疗过错证明责任分配方案的初步评价
1.《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不符合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
在现阶段,各国对医疗侵权实行“过错责任”仍是主流。但是,基于患者证明医疗过错的困难性,无论是英国、美国的“通过事实推定过失”原则,还是德国、日本的“表见证明”、“过失的初步推定”理论,抑或“证明责任倒置”制度,都试图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原告患者的证明负担,以克服原告举证困难而带来的司法不公问题。
就我国对医疗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三种方案而言,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的“过错推定”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最为接近,其优点如下。第一,符合举证便利的原则。医疗侵权案件中,病案资料、住院病历、病程纪录、诊断文书等等重要的书证,记载了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分析、治疗方法、治疗护理过程及治疗效果等医疗活动的全过程,而这些材料一般保存在医院,由被告举证显然更方便。第二,通过证明责任倒置,有利于督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勤勉尽责,减少庸医误人的现象。第三,有利于推动医疗制度改革,转变医务人员的服务理念,保障人民人身权益。
相反,《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有所倒退:第54条规定医疗侵权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第58条表面上设置了三种例外实行“过错推定”,但其实不然:(1)第一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和第三项“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本来就属于过错的认定方法问题;(2)第二项规定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属于证据法上的“证明妨碍”问题,我国司法解释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注]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毫无新意;(3)《侵权责任法》采取有限列举的方法,很难应对实践中举证困难的各种情形,由此导致司法不公的现象将难以避免。
2.《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医疗侵权实行过错推定被多数学者所认可。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586条规定:“因专家的执业活动引起的侵权诉讼,由专家就其执业活动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9]63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第1985条规定:“在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证明不存在医疗过错或者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10]267令人遗憾的是,最终最高立法机关没有采纳学者们的建议。究其原因,与社会各界力量的博弈不无关系。
在2002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认为,医疗纠纷证明责任倒置于医患双方都有利,不仅切实维护了患者的权益,对医疗机构也是一个不断完善、规范的良好契机。但在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议案,从医院的种种难处出发,建议暂停医疗纠纷证明责任倒置,[11]75其理由如下。其一,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为防范潜在的诉讼,避免在诉讼程序中举证不利,可能会采取“保护性”措施。如,为将来免除责任而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全面检查,增加患者的诊疗费用等。其二,认为这将会影响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探索精神,最终制约和阻碍医学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完善诊疗规范、提高医生职业道德等方法化解。
总之,《侵权责任法》第54、58条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也不利于缓解我国日趋尖锐的医患紧张关系。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医疗侵权实行过错责任是合理的,但为了追求司法的公平正义,最高法院应采用“过错推定”等司法技术手段减轻患者的证明负担。
三、关于医疗侵权案件归责原则的一个远景展望
只要医疗侵权案件还坚持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论实行“谁主张、谁举证”,让患者证明医方有过错;抑或实行证明责任倒置,让医方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都势必使医患双方将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医疗过错”上。进而,医患双方的利益会对立起来,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
这一矛盾之所以不可调和,原因如下。(1)一方面,患者期望一旦遭受医疗侵权能够及时得到赔偿;另一方面,医务人员为避免出现“过错”,诊疗活动可能日趋保守,缺乏创新意识,这会妨碍医学的进步和发展,最终损害广大患者的利益。(2)医疗侵权诉讼发生后,由于法院认定“过错”需要医疗鉴定,所以围绕“过错”的消耗战艰苦反复,诉讼成本很高,无论结果如何,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是“双输”。(3)医方为竭力抗辩其医疗“过错”,人为掩盖医疗“过错”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4)经验表明,在过错责任原则下的医疗诉讼中,医方疲于诉讼、荒于医疗,患者也很难得到司法救济。(5)当大多数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济的时候,医患矛盾就可能演变成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如何克服这种两难的困境呢?我们认为,如果医疗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就能避免要么患者证明困难、要么医疗机构疲于应付的困境。而且,新西兰、瑞典等国的实践表明,医疗侵权案件实行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也是完全可行的。在这种制度之下,只要患者受到的医疗损害属于法定的“赔偿范围”,无需证明医方有“过错”,也无需法律诉讼,就可以获得经济赔偿。从而彻底解决医务人员疲于诉讼,以及受害人常常无法得到及时赔偿的问题,从根本上化解了医患双方的利益对抗,使医患关系更加和谐。不过,实行无过错责任也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发达的医疗保险制度、严格的医疗质量及医疗风险管控制度、高度透明公正的医疗鉴定制度等。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相关配套制度会越来越成熟,将来通过医疗保险等途径推行医疗侵权无过错责任,从根本上化解医疗过错的证明困难是完全有可能的。
参考文献:
[1] 肖建华,王德新.证明责任判决的裁判方法论意义[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2):44-51.
[2] 黄天昭.医疗纠纷之民事归责原则[D].台北: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5.
[3] 张新宝,明 俊.医疗过失举证责任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112-124.
[4] 丁中原.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研究——以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为中心[D].台北: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1.
[5] [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 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 黄丁全.医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7] 于 敏.日本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 叶自强.举证证明责任的确定性[J].法学研究,2001(3):89-100.
[9]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0]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1] 王国征.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价值取向[J].政法论丛,2009(5):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