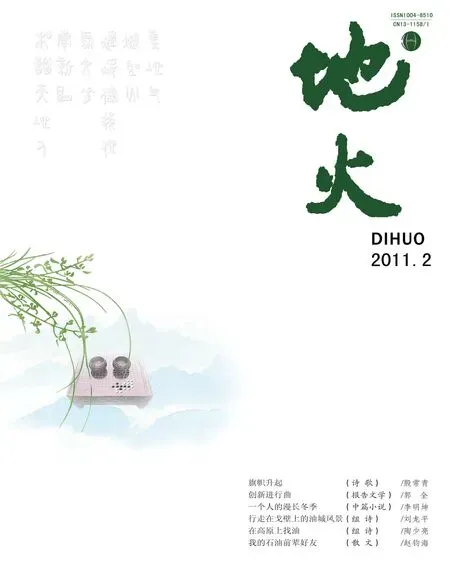回眸
——可贵的人生姿态——刘莉《大庆往事》读后
■杨铁钢
回眸
——可贵的人生姿态——刘莉《大庆往事》读后
■杨铁钢
刘莉,在步入中年的2008年,结集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散文集《大庆往事》,展示出了一种可贵的回眸历史、人生的姿态。之所以说她的回眸是可贵的,就在于她以自我深切的体认、敏锐独到的感悟、形象典型的故事、自然素朴的语言回顾和呈现了一个地域五十年的发展、一个家族近百年的演化、一个女人四十五年的成长。而其中最能给人以新意和启迪的是她对地域文化的品鉴、文学创作心理的探究。
对地域文化的品鉴
大庆,是新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与存在。在短短五十年的开发、建设、发展的历程中,在物质层面生产了二十多亿吨石油,上缴利税1.7万亿元;在精神层面形成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大庆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都是举世无双的,从文化角度说也是如此。大庆文化是大庆人创造的,但当我们真正地站在文化的角度反思时就会发现:已有的认知与成果更多地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如此的认知遮蔽了丰富的内容,这样所形成的认知成果与现实的人与生活缺乏更紧密的链接,因此更多地显出抽象、空洞甚至说教的色彩。刘莉及她的《大庆往事》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以现代人的思维、从世俗生活的视角回眸反思大庆文化,使大庆文化成果的创造者们产生回味的欣慰;使大庆文化成果的享受者们触摸到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的真实律动;使想了解认识并持续发展、完善大庆文化的人们有切实的路径可寻。刘莉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与收获,前提条件在于她是一个有强烈而明确的文化意识的人。
大庆油田星火一次变电所——“星火一次变”,是体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标杆单位,也是刘莉走出校门、走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因此,她深情地称“星火一次变”是《我的“星火”》。“50多岁,矮矮胖胖”的林子成——“林工”,为了把“我”这样的新上岗青工尽快培养成技术能手,不厌其烦地讲理论、提要求,有时“气得他拿着图纸追着我们讲,非要把我们‘整直溜’不可。”他“一般是上午到岗上讲课,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要求我们自学。他怕我们不按照他的要求做,就常常悄悄地来查岗。”正因为有如此的环境和如此的严师,“星火一次变”才成了出人才的地方,
一共送出去了19位所长,50多名值班长”。尽管“我”离开了那里,但“星火在我心中依然如故。那里特有的氛围和风气,形成了‘星火’的文化或‘星火’的精神”。可见,是“星火一次变”这一具体的工作环境、氛围,和“林工”这一具体的人物通过他的具体的言传身教——文化,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星火”深深地植入
我”、“我们”的心里,使“我”、“我们”成为承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星火”。由此可知:文化,是具体的;精神,是抽象的。抽象的精神要通过具体的物化载体和行为模式来体现、传承。刘莉以切身的体验认识到了文化的这一本质,做出了朴素而又精辟的表述:“文化或精神就像衣物被泡在水里,慢慢地浸泡。浸泡了这种文化或精神的人,就像贴了标签一样。因此,在‘星火’工作过的人,不管离开‘星火’多少年,我总能一眼就把他(她)认出”。显然,这样的表述已超出了个体的认知,具有了一般普遍的意义。这就是文化的本质显现,这也是刘莉文化自觉的有力证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是一句大白话,但从哲学、文化学角度去思考和理解,就会发现其中所蕴涵着的客观与主观的关系、文化环境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等深刻的内涵。在《大庆牌女人》中,刘莉以自觉的文化眼光回眸,夹叙夹议地挖掘和表现了大庆的发展历程和大庆人的文化品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和认知。刘莉生于大庆、长于大庆,并投身于油田的生产建设工作二十余年。她熟知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建设的特殊时代背景,以及参与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建设的人们、尤其是“老会战”的独特经历,由此,她得出大庆是男性化的城市,宏大的气势和十足的雄性是它的底色的结论。这是一个文化学的结论,这一结论揭示出了大庆地域文化的品质特征。正是受这独特的文化环境和品质的塑造,才孕育产生了“大庆牌女人”。“大庆牌女人”由两代人组成:第一代是“大庆的老家属们”,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们一起战天斗地、拼命苦干,一起构筑起了大庆文化宏大的气势和十足的雄性的底色。为此,她们消泯了性别的意识,少见了行为的差别,而大庆也正因此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今天的我们在享受和赞美这一文明成果时,所应记取的是:文明的些许进步都离不开必要的付出与牺牲,而铭记文明创造者们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是尊重文化、创造文明的伦理法则。第二代“大庆牌女人”是指“出生于大庆油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人们”,即刘莉这一代。她们生长在“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环境中,由此决定她们“农民的生活、工业的眼光,农民的日子、工人的劳作”的行为模式和生存状态。如此的环境条件、行为模式、生存状态,自然而必然地造就出了她们独特的性格:农民一样坚忍不拔的意志,军人一样严明的纪律性;为人实在、坦荡直爽、敢爱敢恨、敢拍胸脯、敢叫号;“她们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自卑,同时又因不用努力学习就能参加油田生产而优越;她们瞧不起外地来的人,却又因不屑于心计而在很多地方输给了人家”。这是历史的剖析,也是文化的认知,更是真诚的坦露。有此等的回眸及所得,也就不愧于既往,定稳健于当下,必无畏于将来。这,就是文化底蕴的魅力和力量。
龙岗村,三十年前叫“样板村”,1963年5月,刘莉就出生在这里,因此,她写《样板村》,她称《龙岗,我的梦开始的地方》。两篇作品表现了大庆人居住文化的演变与内涵的形成。刘莉详细形象地向我们描绘了样板村的“样”:“建筑格局极富规划性,整个村落方方正正……成排的干打垒,整齐划一……托儿所、水房、厕所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村子到了尽头“就是大田了,是奋斗管理站的家属们种的各种农作物”。为什么建成这个“样”?刘莉告诉读者:一是按照周恩来总理为大庆制定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而建;二是利用了“当地的黄泥和着羊草”夯筑而成;三“结构是照着东北农村民宅的样式搞的”。为什么成了“样板”?是因为“当时任油田总指挥的宋振明亲自抓油田矿区建设”,在龙岗建了这个“规划、布局堪称样板的新型干打垒村子,并指示今后建居住区一律按此样板建设,‘样板村’就这样叫了”。刘莉如上的这段史实的回顾与还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最为完整、最具说服力的文化个案解剖:会战时期大庆人的居住条件外受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影响,内受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支配、直接主事者制度化的限定,所以在器物层面上才形成了如此独特的样态表达——组团式,统一化。这种居住建筑文化一直沿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但至今在局部地区仍有遗存。刘莉只是在还原,其剖析也不含价值判断的内容。但仅此也足以给读者从文化的视角开辟一条认识事物、反思人生的通路。而正是这条通路更能有效地导引世人绕开许多人为的遮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去关注、体验人生,创造先进的文化与文明。
交流与重构是不同文化样态共生、影响、变异的主要形式与表现。刘莉以一篇《上海娃子》为我们形象地呈现了这一文化景观。“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庆忽然来了许多上海知青”。怪异的穿着打扮,奇特的言行举止,立刻使他们在老一代大庆人的眼里、心中成了“另类”,但同时,他们却成了小大庆人——“正在发育中的青少年”们的偶像。于是,他们成了上海娃子的追星族,从各个方面、尤其是穿着打扮上极力效仿,结果是“我们的装束好像是在一夜之间改变的,和上海娃子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接下来,他们遭到了以学校老师为代表的老一代大庆人的抵制。这种效仿与抵制在当时无疑是被局限或框定在政治的意识形态范畴来认知与对待的,所以,它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事件,而被高估和夸大,因而那抵制也就必然粗暴而激烈。今天,人到中年的刘莉回眸此事,认为:“上海娃子们的到来应该算做推进大庆都市化进程的第一次浪潮,他们的生活方式、服装服饰带有明显的城市印迹,这对于大庆这样一个工农结合而生活方式更趋向于农村的矿区来说,真可以说是吹进了一股与石油文化迥然不同的但却是清新淡雅的文明之风”。显然,这个结论是公允的,它既揭示了文化交流与重构的规律,也符合人性图新求美的法则。而这样的结论,也只有超越狭窄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进入广阔的文化领域关照才能够得出。
有了文化自觉,才必然地扩大关照世界、洞察人生的视角和视野,但同时也会因此而多了一些烦恼甚至痛苦。刘莉就为《老展览馆院里的沙果树林》在一夜之间被砍伐而“疼”,“疼得有点发闷”。因为在她的眼里、心中,老展览馆院里的那一片沙果树林,是大庆“这座生硬的刻板的粗糙的不近人情的男性化的城市”的“情人”……“有了她的存在,这座城市才有了灵气、有了人气,使这座阳刚有余而阴柔不足的城市稍稍找到了一点平衡”。为什么非要砍伐她?公开的说法是她的脚下“埋着石油”;而事实上“花果林被砍伐不是因为要打井,而是为装饰材料批发市场建货场”!可见,是物质战胜了精神,野蛮击败了文明!因此,刘莉,不,所有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们都不能不为此而深深地心痛!
人类一切成果的总和就是文化。人创作了文化,文化也滋养了人。因此,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与文化的关系恰如人与空气的关系,须臾不能离开。但现实生活中又确有许许多多的人意识不到文化的存在及其对自身生存的作用与意义。这样的人与人生便不免盲目与被动。自觉而积极的人与人生应有清醒的文化意识,这意识的内涵起码应包括如下的内容:确认自身文化动物的身份,进而遵从文化、崇尚文明,学习文化、创造文明;对自身赖以生存的文化体系的品质有明确的认知——知其源流,明其优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应然。以如上的认知指导自我的人生实践,使自我成为享有、维护、创造良性文化的一分子。刘莉在《大庆往事》中的所为所愿正在于此,因此便获得了超越一般的新意和价值。
对文学创作心理机制的探究
统观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发展实绩,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相对说来,对作家内在世界的关注与把握始终是弱项。具体的表现有二:一是疏于对作家创作心理机制的探求;疏于对作家自身及其所表现对象心灵的揭示与表达。前者导致我们对文学创作规律认知的盲目;后者导致我们创作成果的肤浅。刘莉在其《大庆往事》中,多有对文学创作心理机制的探究与揭示,并以自身的创作实绩予以表现、验证,给我们带来了难得少见的理性认知与作品审美的个案例证。
从刘莉做出的理论描述与创作实绩表现可知:写作心理的独特性表现在顺序的三个层面或阶段上:
第一,由个体的生活经历所积淀而成的独特心理体验与模式。它们构成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表现对象和创作冲动。《大庆往事》中,我们常见刘莉采用“情结”概念来概括表达她的经历或感受。由于生在大庆、长在大庆、工作在大庆,所以“石油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故事、一种景象、一种情绪、一个情结”——石油情结;由于《李老师》的启蒙和培养,刘莉从小热爱歌舞,但因受家庭经济条件制约而没买上小提琴,形成的“音乐的情结一直被我深藏着”;“西油库小孩在树林里与样板村的小孩打起来……把我方小孩活活烧死后扔到油库东南角的岗楼上”,对此,“至今尚未解开”的《西油库情结》;受父亲远离故土、思念家乡而形成的“故乡情结”;经历了十月怀胎和“12小时死去活来的折磨终于换回了那一瞬间的痛快”《分娩》,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伴儿”,才真正理解了“‘恋母情结’是双向的,做母亲的同样有‘恋子情结’”。何为情结?词典的解释是“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底的感情”;刘莉的描述是忘不了、解不开、成为“记忆核心”的“情绪或情调”。正是这些情结才构造成了刘莉个体的心理内涵与趋向模式,并成为《大庆往事》创作的原料与动力。正是受此类情结的驱使和对此类情结的表现,才使《大庆往事》中的多数篇章感情真挚,情节动人,表现新颖。
第二,写作的人有着与常人不太一样的心理结构。在题为《乘着梦的翅膀》的《自序》中,刘莉说“总觉得喜欢写作的人,他们的心理结构可能是与常人不大一样……对于创作来说,一个人生活经历的丰富固然重要,心路历程的坎坷也不容忽视”。首先肯定刘莉的感觉——认识是准确、正确的——写作的人有着与常人不太一样的心理结构。其次明确:这里的心理结构是狭义的,即仅指作家在有了生活经历和成果后,坐在书桌前开始提笔写作后的心理状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刘莉以切身的体验向我们描述到:“许多事情其实都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是无中生有的……我会通宵达旦地想事儿。我会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想得复杂了,我会捕风捉影般地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事情连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或不完整的故事,我会把本来就不存在的事情想得有鼻子有眼,跟真事儿似的……我时常分不清是梦还是醒……爱做白日梦……想把自己的理想放到这个想象的或者虚拟的世界中去实现”。可见:想象、捕风捉影、连缀、梦幻、虚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独特的心理结构的具体运行机制和机理。这也是所有作家、作品创作产生的共性表现。而不同作家、作品的差异则源于其各自想象、捕风捉影、连缀、梦幻、虚拟等能力、方式的大、小、强、弱、隐、显的不同。刘莉也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差异的存在,并据此对文学写作进行了专业与业余的区分:“创造生活即虚构的能力或水平仍处于业余状态……总是摆脱不了生活经历的桎梏……只会临摹生活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们因虚构能力的低下而导致无法进入创作的那种自由的、飞翔的境界”。不仅如此,文学写作时的心理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不同作家的不同写作状态的形成。如刘振学总能在处理纷繁的事物间隙“挤时间写”,好像“在他的大脑中有一个可以随时转换的按钮”——“文学的按钮”,而刘莉本人就“必须有大块的时间,慢慢地酝酿,把自己调整到近于半仙儿的状态才能够进入到文学的境界”。刘莉如上内容的思考与阐发极有理论的认识价值和实践的指导意义。如果每个文学爱好者、甚至专业作家都能从心理结构的角度对自我的写作进行一番探究与剖析,就会更自觉地遵循文学的规律开展创作,就会发现自己现存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完善心理结构,调整写作状态,在有效地总结、学习、借鉴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
第三,写作的独特心理结构的物化成果——作品的显现。作家凭借其独特的写作心理进行文学的创作,其成果当然是作品的产生。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如能注重从心理的角度进行体认,一方面会窥探出作家的创作心理,加深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知与把握;另一方面更能加深对作品所表达的深度和作家深层次用心的认识和了解。仅以《大庆往事》中所表现的部分“梦”为例以证。
梦,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常见的心理现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想成真的成语老话都说明:梦,虽属虚幻,却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大凡爱好写作的人都多梦和爱做梦,并把他们的梦境或梦境与生活紧密融合,写入作品,由此既构成表现的内容,又反映着作家独特的用意与创作风格。刘莉是爱做梦的人,并“幻想着能发明一种机器,把它接在人脑里,能自动地录制梦里的景象”。她“经常借助于梦”,会见最疼爱她但已去世的姥姥。她将梦境中的姥姥和生活中的姥姥串联起来,就免除了对姥姥的《记忆丢失》,同时,也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示出了一位慈祥、机警,敢做敢为的姥姥平凡而又曲折的一生。而其中,姥姥借梦找到了被潜伏在家中的那个越狱逃犯所藏匿的物品,及“我”因为拍摄姥姥的录像带的丢失而日思夜想终于成梦,但梦境与现实不完全对应的两个例证,既呈现了梦形成的心理机制,又区分了梦境与现实不同对应程度的两种类型:完全对应——梦想成真;部分对应——梦未全真。生活如此,人们可能习以为常。但如此生活的文学表达却具有了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趣味。
高中时,“我”暗恋着同学王小华,并经常在梦里与他缠绵,即使是在走向社会之后,当年的情形依然常常入梦。正是如此的梦积淀成《寻找》的潜意识,而“我”的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与现实生活——“我”到精神病院参观、意外与“他”相遇、了解了他的经历遭遇后,“关于他的梦也不做了,我知道这个梦已经破灭了”。这是对有关“梦”的生活经历的还原,但当读者接触到了这一还原之后,所油然而生的则是人生难料、世事无常的幻灭与感喟。而这也正是刘莉寄寓这还原与表达的真实用意之所在。
《我陪父亲回家乡》是为了圆父、女二人“回家的梦”。但其内涵不同:对父亲而言,是落叶归根;对“我”而言,则是走进生命源头。因此,父亲的“回家乡”更多情感的成分,而“我”的“回家乡”则于情感之外带有理性的意念。也正因为有此内在深层次的差异,所以父亲一回到了家乡,便如水银泻地,立刻融为一体;而“我”,则要靠诸多的记忆、想象,当然还有梦幻的连接、沟通,调整心态、调配情绪,感性与理性交织发力,才一步步地融进“家乡”的氛围中、情绪里。到家后的午间“家庭成员的全体大会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的形式最隆重、内容最丰富的一顿饭,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这种热闹和其乐融融的气氛让我忽略了吃饭本身。我忽然想起我曾经渴望与动物们同在一张桌上吃饭,和它们友好相处,动物们可以通人性,我同样可以通兽性,这也许是离这个理想最近的时候了,这种情景很让我温暖和感动,好像在梦里。我们在堂屋里说话,鸡鸭猫狗就在人的脚下走来走去,我却不曾看见它们在屋里拉屎,所以屋里没有异味”。曾经的渴望、梦境在祖籍故乡变成了现实。因为来得突然和猛烈了些,心理的距离还难以一下子调适到位,所以便产生了虽处真实却“好像在梦里”的心理感受。而也恰因有此心理感受的形成,才产生了爱屋及乌的情感趋向,才使“我”与故乡、亲人融为了一体。
以上三例足以验证和说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经历都会积淀形成独具个性的心理内涵和结构。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就在于他们不但像常人那样,将现实生活经历积淀形成独具个性的心理内涵,而且还具备将如上的内涵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独特心理结构和能力。因此,只有既表现出因现实生活经历积淀形成的独具个性的心理内涵,同时又能充分地发挥和体现作家独特的创作心理结构与功能的作家和作品,才堪称是成熟和优秀的。刘莉及她的《大庆往事》近似之,所以可喜可贺。

涌动版画/王洪峰作
——高大庆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