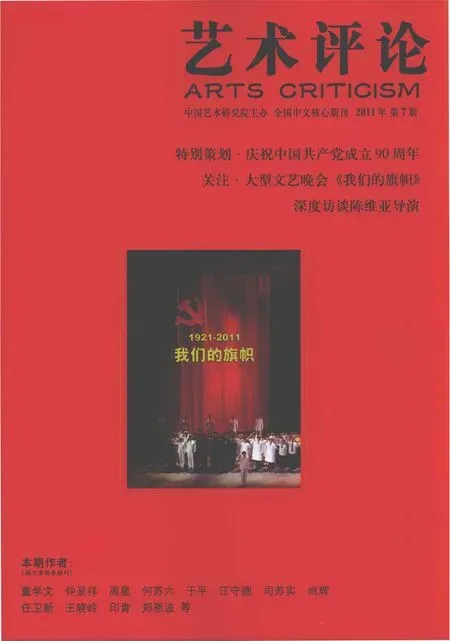我和我的阿尔巴尼亚文友们
郑恩波

斯巴秀和戴代——我的两个阿尔巴尼亚弟弟
毫不夸张地讲,在留阿的学长们中间,能在4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与当年的阿尔巴尼亚同学保持着兄弟般的深厚友谊和同志式的亲密合作的关系的人,恐怕只有鄙人一个。我当年是以进修生身份赴阿学习的,同时在几个年级的文学班里听课,所以结识的朋友很多,其中在63年入学的那个班里认识的泽瓦希尔·斯巴秀和斯皮洛·戴代两名同学是与我最要好的挚友。用北京话来说,我们是40年的“铁哥们儿”。
斯巴秀于1944年出生于斯克拉巴尔农村,矿工之子;戴代于1945年出生于纪诺卡斯特附近的扎高立,农民之子。二人都酷爱文学,自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发表诗歌。我比他们大5、6岁,出生在辽南渤海边的一个山村,也是自中学时代起,就爱文如命并有散文作品发表。我们都尝过吃不饱饭的滋味儿,我们都是苦水泡大的穷孩子,有许多共同语言,所以相识不久,就成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28号房间,我住在30号房间,只隔一个门儿。我几乎每晚都要到他们屋里串门儿,有疑难问题找他们解答,更是家常便饭。即使是考试的时候,他们对我也是照帮不误。有时夜里时间拖得太晚了,我怕回自己房间打扰别人睡觉休息,干脆就在他俩的屋子里摆起椅子搭床边儿。这么一来他们俩的聊侃劲头更大了。我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突然,我被尿憋醒了,睁眼一看,灯还亮着,他们俩各自手拿书本搁在胸口上,睡得香着呢。
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还未走出地拉那大学的校门,就翻译了阿果里的长诗《德沃利,德沃利》,卡达莱的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和《六十年代》,维赫毕·斯堪德利的长诗《一次交谈的续篇》等一系列著名诗篇,为我后来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译介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这些作品大都发表和出版了。可是,有谁知道,在我的那些翻译成果里,也浸透着他们兄弟俩的汗水呢。
不久,我们都毕了业。我被安排到《人民日报》工作;斯巴秀和戴代分配到《人民之声报》工作。我们虽然分别了,但共同的新闻工作却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俩的才气都很出众,《人民之声报》上几乎每周都发他们富有浓厚的文学气氛的长篇通讯;我在北京,也在《人民日报》国际版上,以“红山鹰”、“红英”、“辛文冰”等笔名,热情满腔地为中国的头号朋友——英雄的阿尔巴尼亚大唱赞歌。那是伟大的中阿友谊日益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兼翻译,多次赴阿访问。每次我都不空手而去,总是给我的这两个弟弟带点具有纪念意义的礼品,他们俩也把自己出版的诗集送给我。就这样,我们已把学生时代的友谊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两国新闻战士之间的友谊。
一个人的成长,如同历史的发展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正当我们处于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兴旺时节,突然间,六月里下了一场九月霜。我因各种原因不得不撂下了手中的笔,去“五·七”干校整天与骡马为伴。后来听说,当我身陷逆境的艰难时刻,斯巴秀和戴代对我的命运极为关心,到处找熟人打听我的情况。有一件事即可证明他们对我的一片兄弟之情:1974年,被流放干校2年之久的我,终于被宣布无罪解脱,再次赴阿访问一个月。他们俩得到这个消息,在我抵阿的第二天,就立刻到达依迪宾馆看望我,犹如亲人一般询问我和家人的生活细情。语言的亲切,感情的温暖,是当时我从中国朋友那里感受不到的。
那是一段真假难辨,不正常的历史发展时期。斯巴秀写了那么多洋溢着澎湃的爱国激情的好文章,只因写了一两首在高层领导看来不太健康的歌词,便受到公开在报上点名的批评。不久,他被迫地离开了《人民之声报》,几经周折,调到歌剧芭蕾舞剧院从事歌词创作。当时,我从朋友那里听到这消息之后,伤心极了,为斯巴秀这朵刚刚绽开的鲜花过早地遇到霜打感到痛心、惋惜。心里暗暗地思忖:像斯巴秀这样忠于人民和祖国的人,都要受到如此打击,难道还有可信赖的人吗?痛心之余我又坚信:金子有时会被埋在垃圾堆里,但它迟早还要重新发光,即使被打碎了,还是要卖金子的价钱。于是,我把报社里积存了几年的《人民之声报》,全都摆到办公桌上,将斯巴秀的一篇篇充盈着才华和灵气的通讯及诗作全都剪下来,张贴好,然后找印刷厂装订车间的师傅帮忙,给他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作为对斯巴秀弟弟的一种安慰和支持,尽管此事当时他毫无所知。
以后的10多年,中阿关系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曲折,我与他们俩一时失去了联系。可到了1990年,中阿关系又出现了复兴的转机。这年夏秋之交,我应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的特别邀请,作为阿尔巴尼亚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又踏上了已经久违了16年的阿尔巴尼亚的神圣土地,再次与他们重逢了。这时的戴代已荣升为《人民之声报》总编辑,但对我的学友之情依然丝毫未变,不仅几次到我下榻的“地拉那旅馆”看望我,与我畅叙友情,陪我到历史_语文系路南边绿荫蔽天的树林里悠闲散步,寻找青年时代的足迹和影子,而且还对报社接待室下达命令:“今后一个月里,每天都要把当日出版的《人民之声报》、《劳动报》、《光明报》、《教师报》给郑恩波同志留一份,他是我们报社最好的朋友。”这样,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便免费阅读了上述的各种报纸。在当时,戴代能对我这个老同学做到如此地步,已很不容易,实属难能可贵。
这时的斯巴秀,似乎已从人生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情绪还好,但不愿意提念往昔记者的生涯。我主动向他索取通讯集,他无不感慨地说:“那些东西没有太大意思,等我手上这部诗稿印出来后一定送给你。”我告诉他我已有了一本《斯巴秀通讯集》,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笑呵呵地向道:“谁送给你的?”我告诉他是我自己为他剪报、装订而成的。他先是爽朗、开心地笑了笑,忽然,仿佛恍然大悟了似地,紧紧地把我抱起来拎了一圈儿,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郑,谢谢你的好意,我的中国大哥……”
1999年秋天,中国作协赴马其顿代表团归来后,转交给我一个便条儿,是斯巴秀写给我的,从斯科普里向我问好。我为他能率领作家代表团,参加闻名欧洲的斯特鲁加诗歌节的盛会而感到欣慰,同时也自然地联想:何时斯巴秀也能来中国访问呢?
2003年春夏两季,我因为要帮助BGP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在阔别阿尔巴尼亚13年之后,又到了这个我日夜思念的国家,借此机会也会见了斯巴秀和戴代两个弟弟。转眼之间,他们也是将近花甲之年了,再也不见当年风流潇洒的模样。像我一样,岁月和磨难也在他们不算苍老的脸上,刻下了不少皱纹。斯巴秀浓密的黑黑的卷发,失去了往昔的光泽,但依然精神矍铄,健步如飞,气宇轩昂,十分健谈。那面容整个儿是普希金的翻版。衣着打扮,还是那样普普通通,随随便便,跟学生时代没有太大的差别。戴代的背稍有点驼,但却还是目光炯炯,鹤发童颜,不大不小的将军肚儿也初见规模。穿戴也不像当年在报社工作时那么平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经济状况不太寻常,俨然一个大老板的神态和气度。不同的仪表、装束,给他们目前的职业和身份,作了很好的脚注:斯巴秀——浪漫味十足的诗人,总统府的文艺顾问;戴代——“阿尔滨”出版社的大经理,全国著名的图书出版家。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过了50岁,什么难于启齿的话都说得出口。斯巴秀和戴代兄弟俩也不例外,跟我一见面,就把这些年来的酸甜苦辣、坑坑坎坎,一股脑儿全兜了出来,字字句句都撼动我的心弦。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我是个爱书如命的读书虫,因此,戴代便把我领到他的书库,慷慨而真诚地告诉我:“郑,这回可到了你早已梦想过的地方,这里的书随你挑任你选,你想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爱拿多少,就拿多少。”我知道他的每本书都是有成本的,怎么能凭自己所好乱拿呢!他见我只是浏览,迟迟不行动,于是,架起梯子,到书架的高处,三下五除二,眨眼功夫抽出一大堆,专往文艺评论著作上盯。这堆书对我即将撰写的另外两部专著,将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我惊奇地发现:他的“阿尔滨”出版社以出版人文科学图书蜚声全国乃至巴尔干和欧洲,所有的书,不是经典名著,就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正经八百的书。我实在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职业道德。斯巴秀不从事图书出版发行事业,也就不能在向我赠书这方面与戴代比武打擂。可是,他是个诗人,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坛上三大诗歌巨头之一,他能把自己这几年出版的3本诗作《阿尔巴尼亚诗歌》、《界线》、《危险》全都送给我,已经足矣。
7月14日晚上,我邀请13位阿尔巴尼亚好友,在地拉那“五·一”花园的“中国餐厅”小聚,斯巴秀和戴代是当然的上宾。当朋友们喝得最酣畅的时候,斯巴秀诗兴大发,朗诵了即兴写给我的一首诗,使晚餐的欢乐、喜庆气氛达到了高潮。诗中写道:
最亲爱的郑恩波,
对于我来说,你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
永远留在心窝:
你的纯洁,你的聪慧,他人很少具有的珍宝——
人的真诚的品格。
啊,人,啊,诗人,啊,来自伟大中国的伟大朋友,
我向你致谢,因为你给予我的帮助很多!
你渴望它腾飞,四处传播。
衷心地感谢你,斯巴秀弟弟!你的这首诗,是对我多半生的事业作出的最能让我感到欣慰和快乐的评价。
亲爱的斯巴秀和戴代,我们虽然出身贫寒,却有着坚定的志向,宁折不弯的品格。我们对青春无怨无悔,因为在为共和国复兴、繁荣的伟大事业中,也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硕果!我们都有过夙愿:决心为实现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尽管我们已是雪染霜鬓、皱纹满腮的老人,但心里依然还燃烧着青春的烈火。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很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让我们经常想想自己的年龄,赶紧快马加鞭,全力拼搏。我们虽然是异国兄弟,血管里却跳荡着相同的脉搏。愿我们永远肩靠肩,手拉手,决不能在历史的大搏斗中落伍一个。让后世人拍手喝彩,赞美评说:阿尔巴尼亚的斯巴秀和戴代,中国的郑恩波,他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雅科夫老师一家人
结束了在BGP的工作后,该公司领导给了我在当地休假10天的优厚待遇,要我好好会会阿尔巴尼亚老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我一生的事业是紧紧地与阿尔巴尼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曾经是我们的第一号朋友的国家里,我有数不清的朋友。确实如此,一般的相识者不算,光在新闻界、文艺界的“铁哥们儿”,也有十几个。

在要拜会的诸多朋友中,我自然想到了现任阿尔巴尼亚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经理和总编辑阿尔奔·佐译。他是阿尔巴尼亚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我当年的恩师雅科夫·佐译的长子。雅科夫老师于1979年因患癌症去世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一腔尊师之情倾注在恩师的儿子身上。我也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在我的潜意识里,阿尔奔就跟雅科夫教授一样。
按照朋友的指点,七月初的一个早晨,我汗水津津地来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敲门,未过10秒种,门就打开了,只见一位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笑吟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显然,我的突然来访出乎他的预料,脸上露出一点惊愕的神情。我立刻来了个三言两语的介绍,话还未说完,他立刻紧紧地抱住我,眼睛里含着泪珠,激动地说:“郑叔叔,您这是打哪儿来啊?从天上吗?”我问他:“37年了,我已变成了老头了,你还认得出来吗?”他轻轻地松开胳膊,满脸喜色地说:“人不管怎么变,眼睛是不会变的,您这双善良的眼睛,跟37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再说了,爸爸珍藏的照片中,还有您跟他在一起的合影。他在世时,经常对人提起您,说您是他所教过的外国留学生中最勤奋、最有天份的一个。您想,我们心中能没有您吗?”
听着阿尔奔这句句情深意切的话语。端详着他那大大的跟雅科夫教授几乎完全一样的四方脸,此时雅科夫老师善良慈爱的音容、举止以及他与我既是师生又是挚友的亲密交往中的一些细枝末节,顿时像电影镜头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在专门学习了一年阿语之后,于1965年秋季开学开始,到语言文学专业一年和二年级,听与文学有关的课程的。听“文学引论”课时,班里只有我这么一个留学生。授课教授40岁刚过,但丝毫没有青年教师常有的那种急躁的毛病。他的话讲得很慢,关键的地方要反复重说好几次,写字快的阿尔巴尼亚学生,能把他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然而,只学了一年阿语的我,听老师讲课犹如坐飞机一样,很多句子记不下来。这时,这位教授便把全班同学搁置一边,走到我面前,把重点内容一句句地重复几次,直到我全听懂了,记录下来为止。这样特殊照顾我的事不是一次,几乎每次上课都是如此。这位善良仁慈,关心我到如此地步的教授不是别人,就是雅科夫·佐译先生。同学们告诉我,雅科夫教授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 《死河》,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颇有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气魄。他原来是历史_语文系的专职教授,自1965年开始,便作为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专职作家,集中主要力量从事文学创作,附带在我们系里讲授文学理论。平时主要在从事写作的基地阿波罗尼亚生活,有课时他才来系里。从阿波罗尼亚到地拉那有100公里,可他从来未缺勤过。
我对作家向来怀有崇敬的感情,对学者型作家更是要格外敬上几分。于是,每次下课之后,总要和雅科夫老师攀谈几分钟,有时甚至陪他回家,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时间久了,他便主动找我顺着回家的人行道走上一程。记得有一次,上完课后,我陪着他一直慢行到水流潺潺的拉那河边,谈兴仍然未尽。他特有感触地告诉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一期法文版的《中国文学》,对该杂志特感兴趣,以后如有可能,希望能经常读到它。我知道我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有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所以立刻告诉老师,从今以后保证让他一期不漏地读到这本杂志。我兑现了许下的诺言,从这次谈话开始直到回国,我把每一期杂志都及时地送给了他,有时甚至亲自送到了他家里。
我从地拉那大学回国后,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点名并批准,被安排在《人民日报》工作,主管国际部领导的对阿宣传版面,有机会常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对此雅科夫老师感到非常欣慰、自豪,经常把我的点滴成绩介绍给他的朋友们。1974年11月—12月,我作为由张潮同志率领的《人民日报》记者团的成员兼翻译,又一次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再次到了费里区。车一开进费里城郊,我就想到雅科夫老师,因为他创作的基地阿波罗尼亚就位于离费里只有20公里的海滨。多么想在此见到他老人家啊!要知道,到那时我已有6年未再见到他了。可是主人告诉我,雅科夫近日不在阿波罗尼亚,到外地去了。闻听此言我是何等的怅惘。我把这一消息及时地报告给团长张潮同志,他也感到很遗憾,因为听了我的介绍,他也很想会晤这位阿尔巴尼亚的肖洛霍夫。可是,中午我们在餐桌上酒喝得正酣时,陪同我们的《人民之声报》负责同志却接到了一个由地拉那打来的长途电话。5分钟后,负责同志喜笑颜开地回到餐桌旁,告诉我们:“我们最敬崇的作家雅科夫·佐译从地拉那打来电话,说他得到《人民日报》记者团到费里区访问,特别是团里还有他得意门生的消息,感到分外的高兴,今晚他要在阿波罗尼亚的波扬村的一个农民家里设宴欢迎、款待记者团全体同志。”这一消息使得记者团全体同志酒兴大增,个个都喝成红脸大汉子,不是关公胜似关公。
晚6时,雅科夫·佐译老师主持的具有米寨娇农家特色的盛大宴会正式开始。雅科夫老师的左边是团长张潮同志,我被他拉到左边,紧靠他的身旁。那天晚上,餐桌上一共上了多少道菜,事过30年实在是记不得了,不过,说那餐桌是用最美味的佳肴堆成的小山,那是不过分的。雅科夫老师平时很少喝酒,可那天晚上打破了惯例,不仅酒喝得多,话也说得多,而且全是实话实说,一句外交辞令和官腔都没有。大家正吃着喝着,突然,几位歌手在手风琴的伴奏下,来到这户农家的庭院里,唱起民歌来,好听极了。唱着唱着,他们又走进屋里,当着我们的面唱起中国歌曲《打靶归来》、《在北京的金山上》和《真正的朋友》,两位少女还化妆跳起米寨娇民间舞来,欢乐、友谊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欢迎尊贵朋友的最高礼仪。宴会结束后,雅科夫老师还主动邀请我们一起照了像,并且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份富有地方特色的小礼品作为纪念。对我这个学生还有点特殊待遇:将他的最新作品《幸福之风》(第二卷)签名赠给了我。当时他只有51岁,我35岁。然而,万万没有想到,5年后,万恶的癌症竟夺走了这位风华正茂的天才作家的生命,这次重逢反倒成了他与我的永别……
件件往事正在我的脑海里翻涌,忽然电话铃响了,阿尔奔赶忙去接电话。这时,女秘书按照阿尔巴尼亚家庭欢迎尊贵客人的礼节,用干净漂亮的塑料托盘端来了面包、食盐、白酒等。阿尔奔很快打完电话,端起酒杯对我说:“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尊贵的朋友,我爸爸的中国学生,今日的作家和阿尔巴尼亚文学专家郑恩波先生到我们这儿来做客!”我也端起酒杯回答道:“很高兴见到我尊敬的教授,阿尔巴尼亚当代最杰出、最富有天才的小说家雅科夫·佐泽先生之子,今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阿尔奔·佐泽先生!”这一礼仪让我想起当年到雅科夫老师家里做客时,他夫人杜拉塔教授代表全家欢迎我的情景,也想起她那能给人无限温暖的慈祥的微笑、高雅的风度和谈吐。于是,便关切地向阿尔奔问道:“您母亲怎么样?她好吗?我的问话使阿尔奔的眼睛红润起来,小声地说:“妈妈,她……头几年也离开了我们……”阿尔奔的话仿佛像一个炸雷轰得我头晕脑胀。我的手立刻颤抖起来,连酒杯也端不住了,赶忙放进托盘儿里,酒水洒得满盘子都是。“这……这怎么可能呢?”我问话的声音也发颤了。阿尔奔说不出话来,只是耸了耸肩膀。我这颗容易动感情的心,从一进阿尔奔办公室开始,就一直不平静,此刻更是七上八下了,眼前又浮现出一连串的镜头:
杜拉塔,这位留学保加利亚的高才生,在索菲亚与雅科夫相爱,比雅科夫小5岁,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回国后,先是从事教育工作,后到《教师报》从事新闻工作并间或有文学作品发表。晚年任“纳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辑出版了许多文学名著。她本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我每次到她家里,她都像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那样,为我和雅科夫老师烧茶和咖啡,骄娇二字跟她毫不沾边儿。
1968-1969年,我在地拉那“米哈尔·杜里”印刷厂陪同中国印刷专家工作时,她正好在“纳伊姆·弗拉舍里”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为出版书籍的事情,常跑印刷厂,这样,我们就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每次见面,她都宛如一个老大姐一般,问我工作中有何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有一次,她还笑盈盈地把由她担任责编并写了序言的法特米尔·加塔的新版长篇《沼泽地》送给我,嘱告我最好多读一些加塔的小说,因为他的语言是很规范化的文学语言,多阅读这样的文学作品,对外国学生学习外语非常有利。至于她请我到印刷厂餐饮店喝咖啡和茶,吃小点心,那更是常有的事儿。
坐在我面前,与我促膝交谈的阿尔奔,已不再是当年那个13岁的喜欢蹦蹦跳跳的少年,而是一个稳重健谈的大学者了。他那洪亮的声音,脸上不时露出慈祥的微笑的表情,让我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坐在我面前的不是阿尔奔,而是雅科夫老师。见我心情有些激动、难过,成熟的阿尔奔马上把话题转到他弟弟身上:“您还记得我弟弟阿格隆吗?”我立刻回答:“那还用说!当年他还陪我看过电影,那也是您爸爸的安排,他说小孩子是学外语的人的最佳教员。阿格隆现在怎么样?”阿尔奔说:“他比我强,不仅是个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当过歌剧芭蕾舞剧院院长,而且还是个稍有名气的作家、诗人。现在已不再当剧院领导,而专心致志搞艺术。”我见他言谈中稍有点自惭形秽的意味,便自然地插话:“听说您也写小说,有部中篇叫《当嫁的姑娘》,不要说在阿尔巴尼亚,连在科索沃都很受读者欢迎。”“哪里呦,提不得,那只是一篇青年时代的练笔作。”阿尔奔有点不好意思。
时间已近11时30分,按计划我还要去拜会文学评论家约尔高·布辽和作家协会的同志,所以只好告辞了。可是,阿尔奔坚持非亲自送我去不可,我只好客随主便,跟着他一起下了楼,径直向语言文学研究所走去。
根据阿尔奔与我的约定,第二天我又准时地到了他的办公室,从他 手上接过由他负责修订印行的第12版的《死河》,他嘱咐我:将来翻译这部小说,就要根据这个版本译,我向他做出保证:不把这部作品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我死不瞑目。7月14日,我在“五·一”花园中国餐厅设晚宴款待阿尔巴尼亚文友,阿尔奔自然是被邀请者。晚宴结束临别之前,我对他提出请求:“相信不久我还会来阿尔巴尼亚,届时我要买上一束最鲜艳的香馥馥的玫瑰花,请您陪着我,到文化名人陵园凭吊我的恩师雅科夫和师母杜拉塔。”高大魁梧的阿尔奔的眼睛里立刻涌出几颗泪珠,与我紧紧地拥抱了5分钟,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