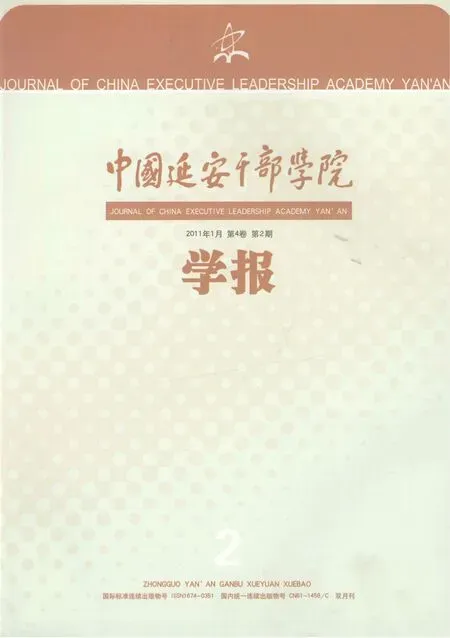邓小平宪政思想解读
殷啸虎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上海 卢湾 200020)
邓小平宪政思想解读
殷啸虎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上海 卢湾 200020)
邓小平的宪政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涉及了强调依宪办事,维护宪法权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制约权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以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方面的内涵。它明确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模式,阐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指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道路和方向。
邓小平;宪政思想;解读
近代意义上的宪政,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宪政(Constitutionalism)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形态,最初的含义是以宪法来控制国家权力行使的一套制度设计,规范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在现代社会,宪政具体表现为一种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民主政治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的思想理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对宪政建设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作过阐述,但他关于尊重和维护宪法权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强化权力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相关论述,实际上涉及了宪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涵盖了邓小平宪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强调依宪办事,维护宪法权威
宪政以立宪(宪法)为起点,在形式上,宪政必须有一部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无宪法即无宪政,宪法是实施宪政的依据。从世界各国宪政运动的实践看,无不以宪法的形式(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将宪政运动所取得的成果确认下来。宪政运动大多是以立宪活动的形式表现的。因此,宪法是宪政成果的记载和集中表现。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和依据。从外在的表现形式看,宪政以宪法规范政治行为,同时又依据宪法的规定设立国家机构,确立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从内在的规定性来看,宪政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通过制定并实施宪法,来体现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因此,宪政的实现,不仅要有一部体现立宪主义价值的宪法,更要求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确认“宪法至上”的原则。
所谓宪法至上,是指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家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不得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宪法存在的权威被人们所忽视,或者说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过程中,不是真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那么,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实现就无从保障,宪政也就无法实现。可见,要实现宪政,就必须要强化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1]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特别强调宪法权威的重要性,尤其是他鉴于“文化大革命”在“革命”的幌子下,践踏宪法,否定宪法权威,从而使得国家秩序遭受破坏、公民权利受到侵犯的惨痛教训,曾经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2](P371)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尊重宪法,维护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据邓小平理论于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的序言部分,在肯定“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同时,明确指出:“本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邓小平在强调维护宪法权威的同时,对我国宪法自身的不断完善也提出了要求。宪法作为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它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它必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同时,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为了保证国家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对宪法进行适时的修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对宪法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针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于1980年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将宪法修改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并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2](P339)正是经过这次修改,产生了我国的现行宪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纲领。当然,现行宪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先后经过了四次修改,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步在全社会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宪政的核心是民主政治。毛泽东曾经指出:“宪政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的政治。”[3](P732)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就是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理论,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根本制度,它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得到了充实和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4](P220)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的三权分立制度,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4](P220)从根本上说,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中国国情相符的,而三权分立制度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1987年,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卡特时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4](P24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本质要求,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来看,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因此,人民代表大会不但享有立法权,而且亦掌握了对执法过程的统一监督权,这就保证了国家权力行使的人民性。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组织形式,人民才能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力。现行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恰如邓小平所说:“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4](P25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确认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也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指明了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同年10月19日,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招待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2](P204)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2](P205)
为了从制度上确立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基本方针。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同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5](P250)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5](P165)这一精神,在现行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宪法的序言中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了宪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宪法保障。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政的基本价值目标。一切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归根到底应体现为对人的关怀、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保障人权体现了宪政的价值追求,它不仅是宪法和宪政的核心内容,也是宪政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目标。在邓小平宪政思想中,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具有重要地位,并特别强调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2](P144)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庄严承诺:“宪法规定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6](P12)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中,将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由原来的12条增加到18条,并且恢复了1954年宪法有关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增加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批评建议权等内容。
当然,人权保障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主要表现为国家整体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社会各方面能协调合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只有社会的稳定才能保证实现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大的人权就是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生存是前提,发展是基础。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最主要的方式是发展国家的经济,而经济要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的稳定性对于人权发展的保障。他说:“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4](P212)
邓小平特别注意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人权保障问题。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权与中国的人权存在着本质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数人权”与“少数人权”的区别:“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所谓的‘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4](P125)
同时,针对西方国家极力鼓吹的“人权至上”、“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观点,从中国的历史出发,邓小平提出了国权高于普遍人权的思想。国权就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解决对内对外各种事务和管理国家的权力,表现为一国对内对外事务有着最高的权力。国权是一个国家个人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根本保障。从人权的发展来看,各国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由国家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首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然后立法机关制定一系列的成文法律法规来细化人权的规定以及通过司法机关具体实施来保障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权实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独立的国权,沦为他国的附庸,就根本无法实现人民的人权。为此,邓小平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4](P331)“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4](P345)“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4](P348)在人权与国权(主权)的关系上、在人格与国格的关系上,把国权(主权)和国格放在首要地位,目的是为人权的实现提供根本的保障,从而真正实现全体人民的人权。
四、依法制约权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
权力制约是宪政的重要内涵。依一定原则,通过宪法将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的本质是对政治权力的有效规范和制约,目的在于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使政治权力的运行合理化、规范化。因此,宪政是一种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通过确定依法行使权力的主体和行使权力的程序,把行使权力的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所要求的范围之内,是宪政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要求。宪政不仅通过宪法的制定,为规范、有效地限制政府权力规定了一套制约与平衡政治权力的制度设计,而且通过这一套制度设计的规范、有效地运作,来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
中国社会长期奉行集权专制体制,革命胜利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建立相应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使得传统的集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下来。而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集权体制的恶性发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文革”的教训,引起了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深刻反思。而作为中国人民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迈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则是比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坚决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并把这作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他在1987年10月13日的一次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这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4](P256,257)
但是,又如何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以解决因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而形成的种种弊端呢?对此,邓小平提出了建立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基本思路。
第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建立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方面,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割的。在加强民主的同时,必须强化法制,实行依法治国。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运用法制手段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各项工作和活动都有法可依;二是要维护法律权威,不允许存在法律以外的特权,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法律监督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四是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使他们在工作中严格依法办事,减少和杜绝各种违反法律规定,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
第二,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认为,因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而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等等弊端,在相当程度上与长期实行的党政不分的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4](P163-164)当然,实行党政分开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4](P257)
第三,明确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为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提高工作效率,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就必须在强调集体领导的同时,明确领导者个人的职责和权限,建立分工负责制度。邓小平指出:“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2](P282)“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2](P150-151)
五、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Rule of Law)又称“依法治国”,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指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法治的核心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法治首先意味着政府和公民都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国家和政府权力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就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而言,就在于通过规范、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而这一目标,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才能真正地、完全地实现。因为宪政作为一种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基本的价值目标,就是个人自由和法律秩序。法治的落实,首先要求有一部合乎宪政精神的宪法。任何合乎宪政精神的宪法都必然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肯定和保护,二是对政府权力行使的规范和限制。只有实行宪政,才能真正推动法治的发展,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邓小平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他还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可见,邓小平把依法治国的外在形式——民主法制建设,摆在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7]
作为邓小平宪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主张摒弃“人治”,实行法治。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总结了长期盛行的“人治”思想的危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P333)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邓小平在1986年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4](P177)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通过立法,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针对当时立法不完备的情况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2](P189)“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要加强立法工作,集中力量制定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P146-147)
其次,要求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P254)在不久后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2](P332)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三,强调民主和法制的统一。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P146)这一段话,后来被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成为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其后邓小平又再次强调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2](P189)“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2](P276)“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P359)
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实质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建设的根本是宪法之治。邓小平的宪政思想,明确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模式,阐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指明了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道路和方向。对于推进中国宪政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1]毛艳.邓小平宪政思想初探[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R].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7]班克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及其意义[J].广西社会科学,2002(3).
[责任编辑 刘 滢]
An Interpretation of Deng Xiaoping’s Constitutionalism Thought
YIN Xiaohu
(Institute of Law,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Luwan Shanghai 200020)
Deng Xiaoping’s constitutionalism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It involves emphasizing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maintaining the constitution’s authority;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improving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 and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respecting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checking power by law,constructing a power checking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implementing rule by law,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It defines the model,clarifies the core issues,and designates the path for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Deng Xiaoping;constitutionalism thought;interpretation
A849
A
1674—0351(2011)02—0030—06
2011-01-31
殷啸虎(1959— )男,上海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9&ZD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