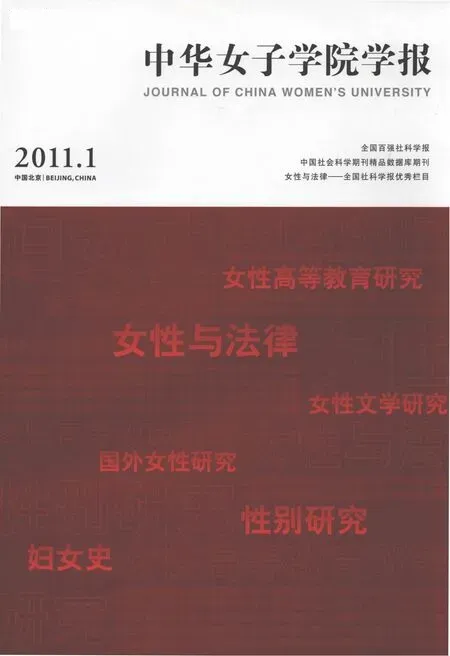新中国前期妇女福利发展的思想与实践
黄桂霞
新中国前期妇女福利发展的思想与实践
黄桂霞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并采取相应措施解除妇女的后顾之忧,如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妇女福利获得长足发展。但在社会变革时期,妇女福利发展遭遇寒流,劳动的去性别化以及针对妇女的劳动保护制度的停滞甚至倒退,给妇女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并导致了男女平等的异化。
新中国前期;妇女福利;思想与实践
从妇女福利发展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的妇女福利有三个层面:一是有业就,就业权是政治动员、行政干预实现经济领域的权利平等的结果;二是同工同酬,就是以制度保障妇女的福利权利和待遇平等;三是共享发展成果,广大妇女在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分享了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各个领域获得长足发展。
一、妇女福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所能借鉴的经验都来自苏联,而且苏联经验是巨大成功之后的总结,更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甚至效仿。因此,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和制定上起了很大的示范效应。在苏联计划经济建设经验基础上,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在妇女福利方面,也主要是参照苏联的发展模式,将妇女发展融入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
1.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是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需要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二是妇女自身发展的需求。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妇女走向社会。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需要有巨大就业潜力的城市妇女广泛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要,也迫切需要农村妇女广泛参与。因为,农村男性一直致力于革命和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主力已经没有多少后备资源可以开发,因此,农村妇女也就相应地成为农业发展的巨大劳动潜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实现经济独立,促进男女平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男女平等成为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产的口号之一。
其次,妇女自身发展需要妇女摆脱家庭束缚。一是妇女想要摆脱传统的性别压迫制度,必须要获得经济独立,从家庭走向社会,“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并且参与社会决策。妇女在参与经济生产和政治运动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在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并且保障男女“同工同酬”的基础上,妇女普遍就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妇女解放的主要路径。
广大妇女参与社会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在农村,农业合作社的成立,使得妇女成为集体人;在城市,广大妇女积极就业,成为单位人。由于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城市的国营经济,主权都在国家,所以集体人和单位人事实上都是国家人。广大妇女从家庭人到国家人的转化,从根本上削弱了男女不平等的制度基础,与男性一样在社会生产中处于平等地位,而且有“同工同酬”的保障。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同时,妇女通过摆脱对男性和家庭的依附,实现了自身的解放。
2.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妇女发展开辟新天地
妇女福利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村的农业合作社,经济集体化,生活高度集中化,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的兴起,不只是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也为广大妇女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解除了后顾之忧。
首先,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工农并举,需要大批人力进入生产行列。而当时,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群众除一部分参加社会生产外,绝大多数还被束缚在家庭圈子里,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消耗在繁琐的家务劳动中。因此,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广泛地、直接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中来。
其次,大规模的集体生产,需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家务和家庭照顾分散了他们很大的精力,影响了其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效率,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生活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家务劳动社会化、生活集体化则为他们解除了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
再次,大规模的集体生产,需要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调配资源,统一组织政治文化活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生活集体化是我国人民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是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出现的,也为解放妇女、促进男女平等提供了客观条件。
最后,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必然要求。因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152
3.受益于社会发展的妇女福利大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妇女福利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旧社会废墟上,想要提高妇女的生产生活水平,就要进行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民生产热情高涨,生产力快速发展,为妇女福利的全面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1956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数占总农户的96%,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是1949年的4.4倍,1958年工业总产值是1949年的9.3倍,农业总产值是1949年的2.3倍,1958年的国民总收入是1949年的3.48倍,1958年职工工资是1952年的1.47倍,1958年农民收入是1952年的1.43倍。[2]
其次,男女平等的制度政策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旧中国,压迫妇女最沉重的是封建的婚姻制度。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制度。
再次,医疗卫生工作保障了妇女的生殖健康。为保护妇女劳动力,新中国自成立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保护制度和政策,对劳动者,尤其是参与重体力生产的女工给予了很好的保障,为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和较全面的保障。在城市,主要是建立了制度化的生育保障制度,覆盖了所有就业的女工人、女职员以及机关女工作人员。在农村,则形成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卫生院、卫生所、卫生室,院所内有助产士或妇幼保健员,负责指导当地接生站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在城乡普遍建立了三级妇幼保健网——妇幼保健站、接生站、接生组。接生员大都是农村劳动妇女,平时主要做农副业生产,由卫生所进行新法接生培训后,兼做接生员。
二、妇女福利发展在社会变革中的偏转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经济集体化和城市普遍就业将妇女从家庭推到公共领域,使妇女与男性一样共同劳动,但由于过度强化男女平等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加上冒进的“左”倾思想的指导,在当时人们革命热情极度高涨的情况下,出现了忽略男女生理差异的去性别化现象,导致在社会变革时期,针对妇女的劳动保护制度非但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甚至出现停滞、倒退现象,这给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一度导致男女平等的异化。
1.忽略生理差异的劳动参与
在大跃进背景下,城市妇女就业规模和水平全面提高,妇女就业领域不断拓宽,与男性共同劳动;但行业、职业间的平均分布,也为日后的妇女就业留下了隐患。同时,国家对妇女过度的保障和保护在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强化了城市妇女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性。
在以重工业引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时期,国家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鼓励甚至动员广大妇女加入到重工业和重体力行业中去,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与此相适应,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融合发展,形成了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期间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则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撰文要求劳动部门“用妇女劳动力顶替部分生产部门现有的年轻力壮的男劳动力”。他举例说:“……旅大市纺工系统妇女劳动力占44%,轻工业系统占33%,重工业系统10%左右,这个比重还可以扩大。”[3]哈尔滨市劳动局副局长更明确说:“……她们不仅适合于商业、服务业和轻工业中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基本建设中,也可以大量吸收妇女劳动力”。[4]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男工女耕”是大庆油田首创的一种劳动分工组合,男性职工全力钻井,女家属则开荒种地,甚至顶替从生产岗位抽下来的职工,从事粮油加工经销,参加公路的维护保养、烧红砖等工业辅助性劳动,直接从事或支援油田建设。“铁姑娘”,最早是人们对大寨青年妇女突击队的赞誉之称,赞扬其铁肩挑重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并无与男子竞争之意,更无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意思。但在后来则演变成为“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去性别化思想,并以此掀起一场女性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甚至挑战生理极限的运动。
在挑战性别分工的运动中,行业性别隔离被一一打破,劳动的去性别化运动广泛开展,这是劳动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全民皆工的产物。此时的“去性别化”旨在鼓舞妇女向男人看齐,争取平等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劳动机会和“社会”贡献率,而不在于争取与男人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全面、真正平等的权利,而且这种劳动机会的平等仍是以男性为标准,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事”为条件的单纯的“劳动形式”的平等,是以女性要努力作出和男人一样的社会贡献为条件的单纯的平等,忽略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别,忽略了女性对家庭生活的更多贡献。忽略男女生理差异,去除家庭贡献,而以单纯的“社会贡献”来衡量妇女的劳动贡献当然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而当时的女性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2.男女平等的异化
男女平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成为共产党衡量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重要指标。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随着社会劳动力需求和革命热情的继续高涨,全面消除男女之间的差别甚至差异以求男女平等,最终导致了男女平等的异化。
在劳动领域,动员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与男性同台竞争,即使在重体力和重工业领域,妇女也与男性担当同样多的重任,包括劳动强度,有些女性为了张扬“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不顾生理极限,在建筑、钢铁等行业,比男性干更多的体力活。
在生活领域,男女平等的异化被推向了高潮,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性别气质,倡导女性应与男性扮演同样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男女应一样的行为方式,出现了妇女“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潮流。
在制度文化上,国家通过制度建设和主流话语干预,力图构建男女平等的新型性别关系,消除旧有文化意识形态,铲除旧有性别文化制度,实现国家权力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成功干预。但在具体路径上,国家采用推动妇女从家庭走向公共领域,通过参与社会生产获得经济独立,赋予他们政治上平等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文化教育上的平等教育和培训机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追求结果的平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男女平等的异化——男女一样。在抹杀性别差异的男性标准下,妇女以挑战生理极限为代价,结果是获得一定认同却未获得自我独立的文化基础。因此,当制度保护和行政干预失去作用时,缺乏自我建构的女性便又开始茫然了。
三、新中国前期妇女福利发展的经验及困境
一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该国福利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框架;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着福利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福利制度也是经济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化作为强大的制约力量,深刻地影响着福利制度的实施范围和效果。
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消除了私有制的剥削压迫,为广大妇女参加生产获得经济独立提供了制度基础。而党和政府针对妇女的生理特点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则很好地保障了妇女的特殊权益。
1.妇女福利发展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控制和管理着全部的经济、政治和生活资源的分配,在城市实行的是单位制,在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由此,国家通过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而且赋予了单位和人民公社垄断就业机会、收入和服务分配的权力。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下,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妇女福利上也遵循了国家统包统配的大锅饭制度。因此,这一时期的妇女福利是通过就业和单位保障来实现的。
首先,为保障城市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所有劳动者都被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到单位内,而女性则采取与男性搭配分配的政策安排到各个单位或部门。“对于失业的和在职职工家属中之劳动妇女及其他家庭劳动力妇女,应尽可能根据原料和销路的条件,组织她们替工厂加工或进行其他手工业生产,并依据需要和可能吸收她们参加其他工作。”[5]289)“对于现在要求出来工作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妇女,还应特别照顾到她们大部分由家庭事务的拖累,逐步有计划地采取适当办法,吸收她们参加工作,譬如要她们半日工作或每天几小时,而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这也是两利的办法。”[5]291
其次,国家通过单位制保障职工的福利。国家通过建立职工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以及职工住房来保障职工基本生活的同时,也提供给职工包括生育、死亡、养老、伤残、医疗等的基本生活保障,为妇女全身心参与社会生产提供方便;同时也设置了职工探亲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冬季取暖补贴和生活困难补助等,来调节计划经济时期低工资高积累的社会分配。
再次,国家通过制度政策等推动男女平等。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制度。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明确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5年颁布的《关于女工人员生产假期的通知》和《关于女工作人员生产假期的通知》等,为妇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2.妇女福利发展的尴尬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边探索边实践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及全民皆工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在促进妇女就业和男女平等的同时,也使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更加尴尬,最终导致妇女福利发展深陷困境。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妇女福利在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社会的突然变革,使得逐步走向正规稳步发展的福利政策也遭遇了革命的寒潮,严重掣肘了妇女福利的发展。
首先,妇女福利发展遭遇社会发展变革。大跃进时期的政治动员和劳动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高涨的热情,特别是“男女都一样”口号的宣传与渲染,使妇女在去性别化的劳动参与中,尤其在参与重工业领域和重体力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超负荷劳动而导致身体伤病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运动导致人们对事物判断的偏离,福利被当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整个社会福利在此期间几无发展,在某些领域某些项目上甚至出现了倒退,妇女福利事业也在劫难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与破坏。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覆盖全体职工的生育保险在工会经费和劳动保险金停止提取后,没有了经费来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全权负责的生育保险转为集体承担。1969年2月,财政部颁发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稿)》,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工会经费和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社会保险统筹制度中断,生育保险制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国家统筹失效,形成企业生育保险,各企业只对本企业女工负责,其多层性及灵活性也随之消失。
其次,在妇女社会福利发展步履维艰的同时,妇女还面临着生产劳动与家务劳动双重角色的尴尬。一方面,虽然新中国通过制度建设和主流话语的干预,唤醒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平等的意识,使得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功绩,但政治动员和行政力量对家庭模式以及男女在家庭劳动中的角色变化的干预作用甚小。比如,在家庭领域,国家力图通过大办集体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解除妇女劳动的后顾之忧,但由于这些公共服务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快因不适应社会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家务劳动社会化条件的不成熟最终阻挡了妇女走向社会的脚步。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不是回到公共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艰难挣扎,这些在社会已获得解放的妇女,却无法摆脱公有制下的“家庭”的压迫。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社会福利视为事关社会稳定与经济恢复发展的要务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福利还起到了巩固新政权的作用。新中国前期,妇女福利之所以取得很大发展,并为新世纪妇女福利打下良好基础,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男女平等,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政策保障妇女福利发展和男女平等,为妇女福利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为妇女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打破了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传统性别制度,“男女有别”的不平等失去了合法性。从现阶段来看,借鉴前期妇女福利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深入探讨社会变革时期妇女福利发展滞后的原因,总结社会变革期的教训,抓住目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的有利时机,对于加快推进新时期妇女福利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妇女福利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男女平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
[2]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文瑞.进一步地解放妇女劳动[J].劳动,1958,(15).
[4]张琢琨.积极挖掘劳动潜力,缓和劳动力紧张情况[J].劳动,1958,(17).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艳玲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Women Welfare Development in the Propha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Guixia
(Women's Institute of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Beijing 100730,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obilized women to widely participate into social production labor and took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free their mind of apprehensions,such as initiating public canteen,nursery,and kindergarten and so 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T o some degree,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has been attained and women welfare has obtained the rapid development.Nevertheless,during the social transition,the women welfare ha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The de-gendering of labor and the stagnation and even regression of working protection system focusing on women have made irretrievable harm for women,leading to the dissimilation of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prophase of PRC;women welfare;thought and practice
10.3969/j.issn.1007-3698.2011.01.020
D442.7
A
1007-3698(2011)01-0108-05
2010-12-18
黄桂霞,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10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