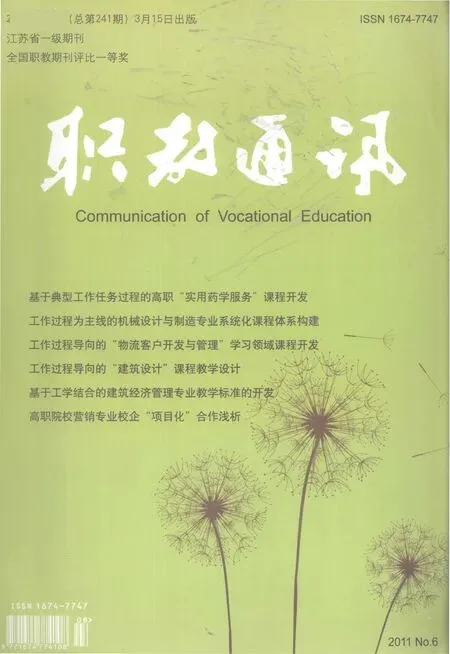校长,一个夹层中的职业
臧志军
校长,一个夹层中的职业
臧志军
在教育普及的今天,任何人在其一生中都会碰到很多位校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读高三时的校长。那是一天下午,吃完饭我提前到学校,在学校的老银杏树下,一位长者突然叫我的名字,并问了许多关于我的家庭和学习的问题,看他那个样子肯定有点来头,我只能如实回答他。后来同学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说我太粗心,每次开校会应该去留意一下主席台上黑压压的人头。我也颇有点不好意思,一校之长能认识我,而我居然不认识他!后来因为求学与工作的关系,又遇到过很多位校长,但算起来,这应该是我一生中与校长最为亲密的一次接触。谢谢这位姓周的校长给一个整日埋头于书本堆的小伙子带来的心灵上的抚慰以及一丝至今都留在心头的小小的虚荣。
最近也接触过不少校长,言谈中总觉得他们与我记忆中的那位校长来自不同的星球。我记忆里的那位中学校长就像老式家庭里的一家之长,坐在堂屋的圈椅里看着门外的子孙玩耍,他是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又保持相当的距离;今天的校长则更像现代企业里的厂长、经理,他们关心的不再是那些孩子,而是案头上由那些孩子幻化成的数字。哪一个孩子上学是否开心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的报到率;哪一个孩子是否通过技能鉴定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的考工通过率;哪一个孩子是否找到工作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的就业率。我甚至感觉在这些校长的世界里数字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其他都成了“浮云”,也许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教育的图景。
我也在不断提醒自己,无论是对高三生活的回忆、还是对当下校长们的印象其实都是片面的,许多年前我还是个学生,周校长只需向我展示他体恤学生的一面;今天,我是职业教育战线的一员,校长们只能用更为宏大的叙事来与我讨论更为宏观的问题。如此说来,校长其实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他(她)可能是一个说教者,一个榜样,一个行政系统里棋子,一个发号施令的上司,一个唯唯诺诺的下属,一个调动数亿资金的经理人,一个争取成为好伙伴的企业合作者,等等,等等。所以,在我等当不了校长的人看来,校长其实是一个处于学生、教师、上级官员、合作企业等各种社会关系挤压中的职业,学生认为他(她)应是学问典范和道德楷模,教师认为他(她)应是出色的教育管理者和公正的仲裁者,上级官员希望他是行政意图的忠实贯彻者,合作企业希望他是在商言商的对手……这种复合的职业期待对校长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校长们普遍喊累是可以理解的。
校长的复合职业身份由这个社会决定,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加以改变,但社会并没有规定校长如何在这些职业身份之间选择侧重,校长仍有展现个人特质的空间。
最近经常与上海某著名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交流,发现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累,相对许多校长要轻松得多。问到诀窍时,他提得最多的是计划与放权两个词。首先是细化计划制订的流程,把计划制订变成凝聚共识的过程,一旦计划通过,就严格执行。他举的例子是校长办公会的议题在每年年初就被确定下来,每个议题的讨论时长也是固定的,都不能更改,职能部门只能把本部门最重要的议题呈现到会议上,因为只有一次讨论机会,过了村就没了店,所以倍加珍惜。其次是严格界定中层管理人员的责权利关系,在放权的同时,用责任来挤压权力扩张的空间。这样一来,中层管理人员必须敢于承担责任,也勇于承担责任,因为他就是所管辖事务的最终决策者。这位校长引以为自豪的是,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校长都无须亲自出面。校长不需要开没完没了的会,不需要应付没完没了的汇报,那他干什么呢?用这位校长的话来说,是思考学校的战略性问题,处理一些战略性事务。
我到过这所学校,相信校长所说大体不虚。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要达到这个境界所需要的是多年的努力,其中的辛苦自不必为外人道。但许多人并不会关心这种状态的形成过程,反而会认为一个太悠闲的校长就不像校长了,而我们从这位校长身上看到,校长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不必去满足所有的职业期待。问题是校长们可以舍弃哪些职业期待,而同时又必须满足哪些?从我这样一个被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多数校长选择偏向自己的官员身份和商人身份,所以他们才会热衷于谈论官位、资金、效益等话题,他们在法律上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身份常常是被淡化的,学生和教师经常成为可有可无的棋子,就像前文所说,早被数字化了。这也许是校长们所处的情势使然,但这不应成为借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尽管身处夹层,但并非没有回旋的空间,校长们不应忘记他们作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身份,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能在离开学校数年后回忆起校长对自己的关心,而不只是说“那个校长啊,我认识他,他又不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