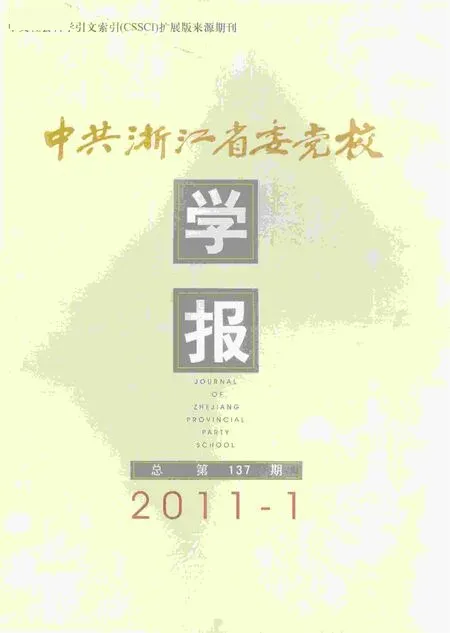全球视野下的宗教传播与中国宗教
——变革、挑战与对策
□ 邹函奇
全球视野下的宗教传播与中国宗教
——变革、挑战与对策
□ 邹函奇*
随着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和全球宗教复兴,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向和新特征,给我国宗教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影响和挑战。如何认识、规范和主导我国的宗教传播活动成为新世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全球;宗教传播;中国宗教
宗教是一种来自于传统又具有文化功能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宗教产生开始的以商业和战争为媒介的早期宗教融合,到国家政治势力支持下的跨国宗教传播,再到殖民地时期的宗教传播及二战后的宗教国际对话,宗教传播伴随着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整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趋势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传播便是这种影响的一种情境互动。然而,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宗教的边缘化,相反却出现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全球范围内宗教传播的新特征给我国宗教局势带来了重大挑战,如何应对全球性宗教传播给我国带来的影响、维护我国宗教稳定局面,成为我国宗教工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全球范围内宗教传播的新特征
随着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和全球宗教复兴,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以及各种部族宗教、新兴宗教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向和新特征,不仅改变了全球宗教格局,也使宗教传播真正超出了时空界限,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有全球视野。
(一)西方宗教南下与东方宗教北上带来全球宗教格局的转变
全球宗教的复兴主要是指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兴和持续发展。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相互交叉,使宗教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流动现象,带来了全球宗教格局的转变。当前全球基督教传教的重点是“北纬10-40度之窗”的“未得之民”,①北纬10-40度之窗,是指由西非延伸至整个亚洲,介于北纬10度至40度之间的长条形地带,这一地区通常被称为福音的顽抗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未得之民”(未皈依基督教者)的集中地区。关于北纬10-40度之窗,可参见Window International Network网站:http://www.win1040.com这场被称之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覆盖了从东亚、东南亚经中东到北非的广大地区,与从北非、中东到南亚的所谓伊斯兰弧形地带多有交叉重叠。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有的宗教获得了比基督教更快的发展和分布:如伊斯兰教分布于全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巴哈伊教分布于218个国家和地区,犹太教分布于126个国家和地区。①David Barrett,George T.Kurian and T odd Johnson,eds.,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2nd ed.,vol.1(New Y 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二)世界范围内基督宗教重心南移
基督宗教从欧美向南半球的大规模文化和地理上的结构性转移,是二战以来全球宗教传播的重要变革。原殖民地国家不断高涨的政治和宗教自觉运动在实质上改变了非西方教会的活动处境,从而使基督宗教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兴盛起来。②[美]达纳·L.罗伯特“: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20世纪初,全世界85%的基督宗教徒还居住在西方,到1950年已有25%居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而到21世纪初,在此三大洲居住的基督宗教徒至少有60%,而且这一比例还在稳步上升。③徐以骅“:美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史述评”,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美国宗教的“路线图”》(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 ,第 348-349 页 。一个典型的20世纪末的基督徒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更多的是生活在社会边缘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而不是来自全球北方富庶国家的中产和富裕阶层。④David B.Barrett and T odd M.Johnson“,Annual Statistical Table on G lobal Mission,”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4,no.1(January 2000):pp.24-25.然而,基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并不代表北方的衰弱,美国的基督徒数量仍然居高不下;世俗化程度极高的西欧各国,其基督宗教徒的数量均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可见,所谓的重心南移,主要是指基于后殖民时代宗教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南部”的基督宗教徒数量的增加,而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
(三)逆向传教改变了全球基督宗教的传统传教路线
与基督宗教重心南移相对应的是全球基督宗教传教路线的改变。目前,世界基督宗教的主要动力来自赤道以南,逆向传教成为20世纪晚期以来传教领域的新转变。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传统上的宣教接收国的传教士,如今却大规模的到欧美等传统上的宣教输出国进行传教活动。“21世纪初,一位典型的基督教传教士已非男性白人,而可能是女性或其他种族。”⑤Ibid.如韩国向海外派遣基督教传教士的规模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韩国约560个教会团体派遣16616名基督教传教士到世界上的173个国家和地区宣教。⑥[韩]苏恩仙“: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对韩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阿富汗人质危机为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9年硕士论文,第10页。然而,对逆向传教是否成功或者其影响力进行评价时,传教士的人数却不是唯一指标。如在英国的来自亚、非、拉的传教士尽管人数众多,传教热情高昂,教会也办得红红火火,但他们的传教对象大都是本国或本民族在英国的移民,受到民族、种族、文化以及传教资金的限制,他们很难传教于本土的英国人之中。⑦孙艳燕“:当代英国宣教状况概览”,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第99-141页。
(四)宗教传播的本土化趋势与本土宗教的竞争意识的觉醒
世界各大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融入了本地文化,使用本地语言诠释教义,各类宗教已自我转化为地方性宗教。21世纪各大宗教的各种形式都代表着某种全球和地方成分的合成,并具有其自身的完整性。这种本土化趋势不仅是宗教对话、宗教融合,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宗教与另一种宗教、或多种宗教之间的竞争。当一种宗教的传入促进了宗教交流的同时,也唤醒了本土宗教的自我意识,使自我意识得以彰显。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宗教复兴是非西方社会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化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⑧[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1页。在我国台湾地区,尽管外国传教士相当努力,但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台湾的合计数量却从未超过人口的7%;虽然一些派别在增长,但实际基督教徒的合计人数一直在下降。自1980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宗教复兴实际上是佛教和道教的复兴,而这种复兴是反抗西方基督宗教的竞争意识的体现。①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宗教复兴与台湾民主政治转变”,沈恺译,范丽珠校,载《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现代性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编,2010年6月,第2页。
(五)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推动下的隐性宗教传播
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各宗教内部和宗教之间的联系,也为宗教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舞台。②关于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学界看法不一,本文采用徐以骅、秦倩“:如何界定宗教非政府组织”一文中的定义,即“:宗教非政府组织是指那些宣称或实际显示其身份和使命是建立在一种或多种宗教或精神传统之上,以期在国内或国际层面推进公共福利或事业,且不直接以传教为目的的非政府、非营利和志愿性组织”。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第五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在1990-2000年的十年间,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从1990年的1407个增至2000年的1869个,增长率为32.8%。③Anheier,G lasius and Kaldor,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到2006年这一数量达到了3000个。④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2006,vol.5,p.10.在这些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中,实力最强的有“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和天主教救援服务会(Catholic Relief Services)等。⑤Julia Berger,Religi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An Exploratory Analysis”,no.14,Voluntas(2003),p.2.现代宗教非政府组织并不以传教为职责,而是更多的致力于慈善救济、灾难援助、教育医
疗和建立经济发展项目;然而宗教非政府组织在进行救援活动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宗教道德和价值观念带入受援地区和人群,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宗教理念的传播。
(六)以网络为媒介的传教活动打破了传教的时空界限
如果说全球化推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带来了以网络宗教(或称“电脑宗教”、“虚拟宗教”)为特征的宗教传播史上的大变革。网络对任何宗教都具有超于以往任何传教媒介的“放大效应”,而网络途径的易于进入也大大拓展了宗教的普世性。事实上,网络的无国界性使得任何地方性宗教至少在虚拟空间上都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宗教。⑥徐以骅“:国际视野、当代关怀——传教运动与国际关系”,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第13页。美国宗教的网络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目前几乎所有教会都建立了网站或网页。穆斯林世界在这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互联网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在2000年前后,绝大多数以伊斯兰为核心内容的网站由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的穆斯林建立起来。21世纪以来,互联网逐渐向东南亚穆斯林国家、中东和北非国家延伸,阿拉伯语、马来语等语种的伊斯兰网站相继建立。宗教传播的网络化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个人化和私人化,宗教信徒可以通过网络完成许多以前必须在公共场合完成的宗教活动,如祈祷、布道、教义咨询、教会交流和个人宗教体验等;另一方面,网络化也带来了对宗教传统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扩张。
二、全球宗教传播对中国宗教的影响和挑战
以科技发展和信息革命为支撑的全球化变革,造成了各民族国家“国界”的“淡化”和“主权”的“弱化”,全球性的宗教传播活动对各国的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入。我国宗教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之中,宗教的全球性传播不仅对我国宗教产生了影响,甚至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
(一)传统宗教格局受到冲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倾向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各大宗教均有明显发展,但各宗教发展并不均衡。随着犹太教、印度教、摩门教、巴哈伊等新兴宗教的不断传入,以及一些本土民间宗教和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发展,传统的“五大”宗教基本格局正受到冲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这种多元化,一方面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文化、价值观念及宗教信仰对我国原有精神信仰体系的渗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代多元社会中一些社会成员对新价值观的探求欲望,是人民生活和精神需求的自我调整。此外,宗教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教派分化导致有些宗教的教派矛盾、教派纷争不断发生,影响了宗教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某些新兴宗教、民间宗教中的一小部分极端分子极易沦为邪教,走上违反法律、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歧途。
(二)宗教的国际化意识进一步增强,国际宗教交流活动增多
全球化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我国宗教再也不可能存在于自我封闭之中,必将持开放的态度和国际化的视野,以适应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环境。我国四大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属于世界性宗教,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和爱国爱教的原则下,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和交流。甚至在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已获得全球意义。世界上也有不少宗教、教派和信教群众视中国宗教为其正宗和本源,来大陆祖庙进香、拜佛。因此,我国宗教这种“走出去”、“请进来”的趋势必将呈上升势头。我国宗教的国际化意识增强,有利于扩大中外宗教界的交流和了解,宣传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宗教国际化意识的增强也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提供了机会,对我国宗教主权和独立办教的原则构成威胁,必须予以警惕和防范。
(三)宗教主权受到挑战,来自境外势力的渗透和干涉压力增大
宗教传播的全球性扩展了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的路径选择,一些境外势力进一步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干涉中国内部宗教事务,挑战我国的宗教主权。美国在人权领域频繁利用宗教问题对我施压的政策从未改变,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自1998年以来,每年都要发表一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情况进行点评,其历年的报告中一直将中国定位为“迫害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美国的宗教团体还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国境内的分裂主义分子。美国、韩国、香港等地的基督教“差会”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直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进行商贸活动和以医疗卫生、学术、文化交流等多种渠道对我国宗教进行渗透。梵蒂冈在我国秘密任命地下主教,扶持地下势力,直接指挥我国天主教教内事务,与我爱国团体争夺教会领导权。境外的伊斯兰教分子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也加紧对我国新疆等地进行渗透。流亡海外打着宗教旗号的藏独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怂恿下,利用宗教对国内的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息。境外势力对我国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干涉导致了我国某些宗教出现了不正常的发展和混乱,严重威胁到我国宗教和社会的稳定局面。
(四)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三股势力有膨胀之势
冷战结束使得原本掩盖在两大集团阴影下的国家出现权力真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潮泛起,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乘机四起,导致了部分地区局势的动荡。三股势力在国际上的膨胀趋势对我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国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长期以来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思想基础,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和恐怖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势力为了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目的,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事件,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恐怖活动。在西藏问题上,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勾结国际敌对势力,披着宗教外衣,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在国内制造骚乱甚至暴乱,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在国外捏造种种虚妄不实之词,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和国际社会,制造所谓“西藏”问题,并企图使之国际化。2008年3月14日,达赖集团策划和煽动了拉萨打砸抢烧事件,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三、正确处理全球背景下宗教传播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宗教传播远远超出了国内问题的范围,对于宗教传播的认识必须要有全球视野。我国宗教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文化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等特点,应本着有理、有利、有序、有效的原则,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宗教的全球性传播给我国宗教带来的影响与挑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稳定发展、国家统一的大局,又与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思想观念与时俱进,科学对待宗教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得到了与时俱进的诠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将长期存在,党和政府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手段去发展宗教,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要发挥宗教对社会有益的一面,抑制它对社会不利的一面,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宗教仍被认为是高度敏感、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不稳定、突发事件频繁的时期,很多人一提宗教传播就紧张、害怕,动辄就把宗教传播等同于境外势力颠覆我国政权的宗教渗透。其原因在于对宗教的基本看法还囿于传统意识形态,在认识观念上没有走出把宗教定位为社会消极因素的误区。在此背景下,宗教传播被严重地泛政治化,在涉及到宗教传播问题时,人们总是倾向于防范、限制的心理。当今中国,要处理好宗教传播问题,引导宗教传播活动发挥构建和谐社会的正向作用,首要的问题就是转变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宗教传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传播。
1、正确认识宗教传播的长期性、变化性和发展性。宗教传播从宗教产生之初便已存在,有宗教就有传播,宗教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在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传播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传播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增强,导致了传播主体、客体、方法、媒介等均发生了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宗教传播必将融入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之中并长期发展下去。在实际工作中,认为宗教传播只是短期存在的现象,或者对宗教传播采取封堵的态度试图阻止其发展,都是不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的错误认识。应该在正确认识宗教传播的长期性、变化性和发展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的传播特点,给予清醒适时的判断并做出理智客观的策略选择。
2、正确区分宗教传播与宗教渗透。所谓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及宣传,企图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的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对于威胁我国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宗教渗透活动,应该立场坚定,综合运用行政、外交甚至司法手段予以坚决制止。同时,应该避免一概地把来自境外的宗教传播活动都等同于渗透,避免草木皆兵的态度,除去附在宗教传播身上太多的政治色彩。
(二)加强宗教法制化建设,有序规范宗教传播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在宗教领域也应该实行依法治理,走宗教法制化道路,以法律为准绳有序地规范宗教传播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一批关于宗教的法律法规,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是目前我国最高级别的宗教立法,改变了长期以来宗教工作无法可依的局面。但我国至今尚无一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宗教问题的权威的基本法。我国宗教的法制化体系还不够完善,这不仅给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压力,也是导致宗教问题政治化的不得已的原因之一。
1、出台宗教基本法,完善宗教法律体系。我国宗教立法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宗教基本法的缺失,这一问题不解决,宗教的法制化建设就难以完成。因此,要使我国宗教走法制化道路,最先要解决的就是必须出台一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地方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依据。只有基本法的出台,才能强化国家对宗教传播活动的法律监督,提高政府依法处理宗教传播活动的效能,尊重和保护合法的宗教传播活动,坚决打击违法的宗教传播活动。
2、规范地方宗教法规、规章的统一性。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宗教基本法,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制定了地方宗教法规及规章对各地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规范。由于没有全国性的宗教法为宗教事务的管理提供统一的标准,各地的宗教立法在对待宗教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宽严松紧程度不一,存在很大的差异和矛盾,这就导致了同一宗教的同样问题因地区不同而采取的对待方式也不同,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与普适性。因此,对各地方性法规进行统一,有利于宗教界的内部稳定和法律权威的体现,也为政府管理更加统一规范提供了保障。
(三)加强爱国宗教力量建设,有效主导宗教传播
面对全球背景下纷繁复杂的宗教传播现象,不仅要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走法制化发展的道路,在具体的宗教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在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指导下,固本强身,发挥爱国宗教力量的积极作用,变被动为主动,掌控我国宗教传播活动的主导权。
1、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主渠道作用。我国现行的宗教管理体制是由政府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各级宗教团体的任务是协助政府对宗教职业人员、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活动进行管理,同时接受政府的依法管理。一方面,政府对宗教团体的人事、财务、教育培训、宗教活动、外事往来等各个方面的管理过多,使得宗教团体对政府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内部官僚化、世俗化的倾向加剧,在吸引信众方面缺少活力。另一方面,政府管理体制外的宗教组织和活动又在发展蔓延,如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天主教的地下教会、佛教和道教的小庙小庵以及一些邪教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宗教活动形式自由灵活、传教热情高,再加之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很容易吸引信众。针对以上情况,政府应该加大对爱国宗教团体的扶持力度,除给予经费资助外,重要的是要放宽对爱国宗教团体在宗教活动审批、人事任免、活动场所审批的政策,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使其更具活力,更具号召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发挥主渠道作用,消除信教群众的不满和失望,阻止宗教内部的离心和分裂倾向,拉回在管理体制外的信众,有效抵制境内非法宗教势力和境外的宗教渗透。
2、提高宗教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无论是引导国内宗教传播还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在宗教领域做到御外强内,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充分发挥宗教界内部的作用,而宗教教职人员则是引导普通信徒正确认识宗教、明辨是非、抵御渗透的重要力量,这是做好全球化背景下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保障。然而,与信徒人数不断增长成反比的是教牧人员的严重短缺和宗教职业人员的素质不高。此外,有些基层教会中一些自封传道人乘机登上讲台,容易误导信众,妨碍宗教和谐。因此,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宗教职业人员队伍,是我们掌握宗教传播主动权、正面引导信众的重要前提。第一,加大培养宗教职业人员的政治素质。提高宗教职业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同党和政府真诚合作的坚定信念,只有政治立场坚定才能在传教过程中把握好方向。第二,深化培育宗教职业人员的宗教素养。宗教素养是宗教职业人员的根本,然而由于我国现行的神学院、佛学院等宗教教育院校规模和师资有限,在培养宗教职业人员的教育水平上还与国外同类院校有着很大的差距,很多教堂和寺庙的宗教职业者还只停留在念经的肤浅水平。提高宗教职业人员的宗教素养,有利于他们树立与时俱进的宗教观,提高解读经典的专业能力,增强与世界对话的能力。因此,可以拓展交流学习的渠道,适当地送他们去大学或国外的宗教院校交流学习。第三,要提高宗教职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由于中国的宗教院校没有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院校的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大多是以学习宗教知识为主,缺乏文化知识的培养。在他们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几年里,他们获得知识的内容、渠道以及学习、生活的环境,必然限制了其文化素质和思维能力。文化素质是政治素质和宗教素养的基础和保障,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因此,为了提高宗教职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应使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进一步接轨,如在大学里增设宗教学专业,或在宗教院校加大文化课的比重,做到宗教知识与文化知识并重。3、鼓励正常的对外宗教交往。宗教的生命存在于交往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若要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正常的对外交往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以往我们提到对外宗教交往问题,总是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既怕走出去的时候受到国外宗教势力影响使得中国宗教被改变、吸收甚至同化,又怕请进来的时候会扰乱、撼动我国稳定的宗教局面,甚至担心国外政治势力乘机而入破坏我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所谓“走出去,请进来”,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开展正常的对外宗教交往。这不仅需要对我国宗教局面的自知,也需要对我国宗教政策的自信,还需要掌管我国宗教传播的主动权。鼓励正常的对外宗教交往,是宣传中国宗教政策、展现中国宗教面貌、促进中国宗教发展、增进宗教间理解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吴锦良)
B036
A
1007-9092(2011)01-0064-06
邹函奇,浙江中华文化学院科研处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宗教向度研究——以美国对华外交为例”(09CGZZ005Y BM)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