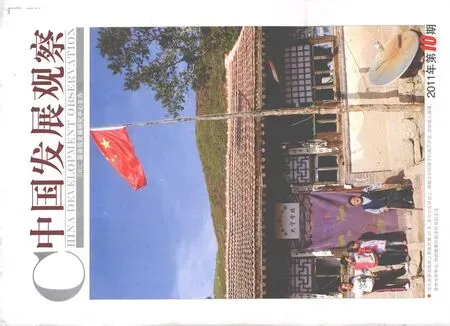司法的僭越和法治主义的致命自负——从《婚姻法》释法和“房产加名”征税谈起
■ 滕祥志
日前,随着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强势出台,一场保卫家庭和传统价值的论争不期而至。至此,家庭共同体与市场逻辑、个体权利和自由主义的冲突、婚姻法共有财产制度与商法外观主义和交易安全主义的冲突犬牙交错。这些冲突以往并不明显,然而,司法解释的横空出世,将这些冲突抛在世人眼前。慎思明辩之士,岂能无所思考或回应?
拜物教的武断和民情反弹
其第7条第1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窃以为,将婚后一方名下财产界定为个人财产,以“个人财产制”取代习惯法秉持的“同居共财制”,是婚姻法理念的重大突破。
其第10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第二款:“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窃以为,其用物权法“登记主义”,摧毁了“家庭财产制”和婚后所得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传统。难怪当婚姻法专家对此提出质疑之时,有指导此次司法解释修订的民法专家概叹,婚姻法专家“不懂物权法”!
论者认为,司法解释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将资本逻辑强加给家庭伦理关系,将摧毁一息尚存的中国传统的家产制。自2001年修法以来,婚姻法从原初意义的(1950)“人身关系法”逐渐演变成“投资促进法”。
论者认为,司法解释第10条就像一个挑拨者,离间了家庭婚姻关系,败坏了人伦亲情,必然引发婚前复杂的博弈。“恋爱成为谍战,结婚如同‘潜伏’,婚恋中男女的神经将更加脆弱,于是婚姻就像生意了”。
论者认为,司法解释不当扩大司法能动主义的范围,其秉承“感情与财产二分”的市场逻辑,以个人主义压倒家庭价值,使得涵养道德、培养善良风俗和民情的家庭细胞,感染上个人理性算计的病毒,父慈子孝传统将烟消云散。
拜物教的致命自负和不讲道德
上述批评和评析,笔者以为甚为至论。然而,更进一步,诸位难道没有看出,此中存在司法的僭越和法治主义的致命自负?
所谓法治主义,是指以人性幽暗意识为出发点,冀图构筑法治和制度主义大厦,以应对现代中国的治理难题。所谓司法僭越是指,不当扩充司法的权限和智能,夸大司法于社会治理之作用;司法僭越,乃是法治主义的组成部分。立法者理知能力的局限,造成制定法缺欠和不足。然而,法治主义坚信,其可以用整齐划一的制定法,规划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乃至家庭生活,婚姻法屡修和司法解释频繁变脸,就折射出这种自负。
法治主义之滥觞,于斯为盛。其宏大的法治理想,是以不断完善法治为名,行构筑眼花缭乱的法律体系以实现法律之治之实。而各式各样的法律专家,和无利不起早的法律执业者食利阶层,就是其法律之治的副产品。而法律执业者阶层奉行的是“客户利益至上”和“为客户服务”的商业伦理,并可以罔顾公义地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甚至玩弄法律,这就造成了律师业群体的整体堕落和身价贬损。可见,所谓法律之治,实乃法律共同体之治。法治主义沉溺于制造各路专家,却对支离破碎的法律部门的内在冲突视而不见:司法实务中,法官审理公司股东清算纠纷,不会考虑公司是否纳税而迳行判决,民商法审判不识税法;股权转让纠纷中,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就判决合同成立且生效,至于股权是否夫妻共同财产,是否要考虑民法共同财产的处置规则,法官在所不问,因为,公司法不理会婚姻法,而交易安全、善意取得和公示主义已成为教条;《破产法》的立法者,将《税收征管法》的税收优先权踩在脚下,而税法规则的制定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对民商法的基本概念不顾不问;在学理上,刻意作法制与法治的区分,认为前者乃是人治,而后者则是法律之治,道德上前者高于后者,宣称在实证意义上,前者已然失败,而后者则方兴未艾;在课堂上,法治主义传教共同体理念和专业训练,信奉民商事法所推崇的形式和外观主义,将“善意取得”、“取得时效”等有利于交换家的法律制度,奉为圭臬。
司法解释三第12条第1款,揭示了借“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交易第三人利益的制度秘密。正如论者所述,在司法解释的起草者眼中,房产不是全家人赖以生存居住的物理空间,只是炒家手中的“炒作工具”。司法实践中,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所谓“善意取得”尤其是不动产“善意取得”,纯属骗人的鬼话,因为稍作尽职调查和法律分析,即可查明卖方是否具有不动产处置权,而夫或妻一方以一己之名转让房产,实质是对配偶权的侵犯。但是,法治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第三人对此也“视而不见”,这何来丝毫善意?由此,“善意取得”乃是交换家意志的法律叙事,是资本扩张并独享尊荣的法律表达,而这一抄袭制度则将私利奉为神圣,视交易安全高于实质正义,因为交易本身即公正、神圣且等价有偿的化身;而所谓金融创新,经金融交换家精巧包装和点化,变成迷人的衍生品炒作工具,即可以出售的“产品”,于是,即便久经沙场的执业律师,也不免限于迷惑。2010年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某律师购买某外资银行金融理财产品受骗案,即为实例。
圣贤教诲遭遇西方拜物教
这些,离古代圣贤的教诲已渐行渐远。梁惠王曾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就告诫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并警戒道:“天下交征利,则国必危也”(《孟子·梁惠王上》)。
可是,在法治主义的利益至上的喧嚣之下,追逐私利具有神圣性,圣贤的教诲已不近“人间烟火”且不合时宜;在民事诉讼法中,其贯彻“当事人主义”,将“程序正义”推向极致,竭力推诿法院查明事实的职责,推销“法律事实”和“案件事实”概念,将举证能力不足的当事人陷于不利;在行政诉讼中,引进“两造对抗”和“不予调解”制度,但西法所开药方,在官民冲突面前,难免水土不服,凸显传统调解制度之高明,于是才有司法政策向“调解制度”的回归。在刑法领域,张扬“废除死刑”,直接挑战民众“杀人偿命,伤人及盗抵罪”的心理极限;法治主义还排斥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将民意和舆论监督斥为“干扰司法独立”,这造成司法过程的法律精英独断--某些案件中,主审法官既可利用其对程序和实体法的娴熟技能,操控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又可作到天衣无缝。因为,从实体到程序,一般外人无与问津,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乃至代理律师,亦未必是个中专家。如实务中,反诉与本诉是否应属同一法律关系、反诉受理与否、受理之后是否审理、审理之后是否处理,法律规则模糊不清,而法理研讨则莫衷一是,这就极易造成“法官独断”。加之德治被贬斥,群众的公正诉求不免受到高学历、深资历和缺良心法官的宰割,并由此引发司法不公的强烈反弹,其极端形式就是群体性事件。而这些偶发的维权事件,也会被别有用心者所误导,将矛头焦点指向政府和政治权威,并借助司法不公来发酵,其直接后果就是政治权威流失。但是,法治主义却把司法的种种乱象归咎于“权力干涉”或者“权大于法”,这真是一个十足误导。实际一般案件,主管庭长或院长本无暇顾及,只有大要案、极少数特殊案件或经媒体关注而演变成公共事件的案件才进入庭长、院长、上级或者其他权力机关的法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线性进步论与拜物教的无知
亦有论者认为:司法解释第7条只是提供一个选项,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家庭财产制,何以西法东渐之际即冰雪消融?其原因即在于无法解决“精确计算”和“风险分配”的问题,父慈子孝的反哺模式的式微,乃是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观念,笔者实不敢苟同。
以市场的逻辑处理家庭事务,乃是现代法治主义向传统家庭伦理领域不断侵蚀和扩张的确凿例证。法治主义走向极端,在当下,其主要表现为法律共同体主义,其结果,司法权凭借司法解释实现司法僭越,行政诉讼管辖权的不当扩张就是例证。而这在某些论者看来,是实现“有限政府”或者“小政府”的必经途径。在法治主义的鼓舞和喧嚣之下,司法过程逐渐演变为封闭的、法律共同体独享的、为法律精英所独断的“专业”活动,离人民群众愈来愈远。而“人民”,在法治主义看来,也是一个虚构的实体;“群众”的出场,或以民意的形式或以舆论监督的形式,都有损“司法独立”或“法治尊严”。
中国法制的近代化,也即西风东渐过程,非常复杂,岂“进步”二字足以囊括?线性化的进步思维,与历史事实不符,近五百年的世界近现代史,伴随着殖民扩张、资本压榨、战争惨剧、市场拓展,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个体权利的扩张和现代法治主义登场。现代法治的前世今生,以个体权利为依托,以自由主义为理论论证,以资本的意志为圭臬,以法治宪政为张本,岂能以进步概括其质地?启蒙思想,开启构筑了线性进步的观念,其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和道德自负,假以资本的威势不断攻城略地,席卷天下,其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而卢梭则认为,现代性所昭示的一切,不是“进步”而是退步,应警惕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正日益败坏人的心灵。“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人类反思和抵抗现代性的最初呐喊,卢梭的沉思,乃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先声,于今亦有意义。
然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然破产。事态也为卢梭不幸言中:在现代性的高歌猛进之下,地球人已经无处安顿肉身和心灵;而当代中国人,不仅遭遇生态失衡、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的现代性危机,尚且遭遇持续的传统家庭价值危机。而家庭价值和伦理关怀危机,只是中华核心价值之一。在全盘西化的紧逼之下,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正日益消解。中华文脉危在旦夕。
西方拜物教冲击中华文脉
以家庭伦理为例,中国古代先哲推崇家庭价值,将个体价值构筑在修身齐家之上,即《大学》所谓“修齐治平”。齐家乃是连接修身和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环节。家庭之内以孝慈为本,即所谓父慈子孝。孝者以敬顺为本,即孔子所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家庭之外以仁爱为本,即所谓“仁者爱人”。在家庭价值和社会秩序和公义发生冲突时,儒家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论语·子路》),即在司法程序中,亲人之间不得互相揭发,以为社会存留家庭价值,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不存,社会机体毛将焉附?毫无疑问,“亲亲相隐”为现代司法所不容,但是,伴随着儒家理念进入刑律,亲亲相隐为历代所尊奉,成为一项普遍司法原则。这次《刑事诉讼法》修订,规定亲人受到犯罪指控,亲属之间可以拒绝作证,法律终于回归到尊重传统,实乃西风东渐以来,难得的明智之举。有论者认为,原来,老祖宗的这一制度和理念并不落后,反而先进。
资本一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兄弟被迫离妻别子,为了生计而远走他乡,家庭已然受到无情冲击。农村变成空巢,仅剩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在文化意义上,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尽管如此,每到春节,他们依然顶风冒雪,千里跋涉,奔赴故乡,与亲人团圆。这种浓郁的温情、家庭观念和大一统意识,将国人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中华文明则于此独领风骚数千年,虽历经浩劫,但经久不绝。然而,当法学感染上西学病毒之后,包括家庭价值在内的传统道德沦为价值相对,而自由民主人权则上升为普世价值;法治主义对文化传统缺乏基本敬畏,不断围剿国人的婚姻家庭传统价值,自2001年《婚姻法》修法以来,于兹为烈。按照司法解释三第6条,婚前或者婚后承诺赠与房产但未过户的,可依照《合同法》186条撤销赠与。家庭婚姻关系,至此被裁剪为冷冰的契约和物权法律关系,《物权法》的“登记主义”和《合同法》关于“交付前可撤销赠与”的规则,开始统领婚姻家庭生活,至于一诺千金和因为对方的承诺而对爱情婚姻的付出,均可在所不计。一句话,只要房产不登记过户,任何关于婚姻的赠与承诺--无论婚前还是婚后承诺,均可以出尔反尔!至此,善良风俗、美德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声称要保护的价值,均被扫地出门。而法律与道德风俗、人情伦理的冲突,则不断被司法过程制造出来,千奇百怪的、普通百姓一眼洞穿的、判决不公的案子,诸如南京彭帅案、云南李昌奎案、北京孕妇致死案等,在一些人看来,则“合法”且符合“法治理念”;其为之辩护,则振振有词。法治主义之不接地气和盲目自负,由此可见一斑。
拜物教由婚姻法侵入税法
无独有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一颁布,就引发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的热潮,普通百姓开始绝地反击,打响一场婚姻保卫战。
然而,法治主义的信奉者,又将税法作形式主义的解释,而放弃税法的实质正义,搞不清“婚后加名”既不属《契税条例》之 “转移不动产”,也不属民商法之“赠与”。因为,“婚后加名”行为,乃婚前有房一方将房产带入家庭,将个人所有变更为夫妻共同共有,以保障家庭不受《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损害的自救行为,其本意是为保卫家庭,而非财产赠与,此其一。
其二,男方置房赢取新娘,女方置办嫁妆进入婚姻,依传统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实质上,女方对家庭的付出奉献同样具有经济价值,这样,婚前一方的房产自然进入家庭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婚后加名”行为貌似没有对价,实质具有对待给付,且具有不可计量的经济价值,这就与民法的“赠与”要件不合,因民法赠与系单方、无偿和交付之前可以撤销的行为。如果把婚前房产婚后加名视为“赠与”,必然缺乏“赠与”的“交付”环节,且因双方并不签订“赠与合同”,故不符合征收契税的形式要件。
其三,税法“转移不动产者”,实乃房产产权的整体转让,而民法“赠与行为”,须经税法的拟制才转换为“转移不动产”,受赠人才负有纳税义务。“婚后加名”,法律形式上由个人独享变更为夫妻二人共享,本质上是为婚姻存续和家庭幸福提供担保和抵押,因此,将之混同为民商法的“赠与”实乃言不及义。经“视同”赠与和“视同”转移房产,两次“视同”转换,判断已经失真!况且,在共同共有之下,产权份额和税收客体之计量,诚为法律难题。
其四,若发生离婚时,依照“同居共财”的习惯法,接受房产的一方取得一半房屋产权,如同企业清算,股东分得原来价值的资产不应认定为收入,只是投资的取回,无须缴纳所得税。同理,离婚取得分割财产,实乃原来共有财产的取回,这一房产分割取回过程,未发生发生权属转移,不存在契税税收客体。
法治主义的教条应该缓行
古人云,善治应以德治为基础,因为“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法密而禁厉,则“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董仲舒《天人三策》之一);“法愈密,吏权愈重”(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查我国《宪法》之制度安排,审判权不作为独立权力一极出场。但法治主义则从“司法独立”的西学原理出发,比划宪政的理想蓝图,不断对政治权威施加影响,以便造成一个“有限政府”。转眼之间,治道传统中“执政为民”、“以民为本”具有道德寓意和依托的人民政府,被其忽悠为“有限政府”和“必要的邪恶”!
当代中国,既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也是中华文明的承载体。当代中国的有效治理,要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法治和法学理论,不要一头倒进西学怀抱的且盲目自负的法治主义;要德法并举,更要奉行德治,以德率法,以德化民,以德服人;丢掉德治,就自毁中华文明的内功和立身之本;要全盘化西,但绝不要全盘西化;要汇通中西,返本开新,因此不要无限夸饰法治的法治主义,尤其不要沾染西学病毒的、致命自负的、为交换家和强者张目的法治主义。
——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