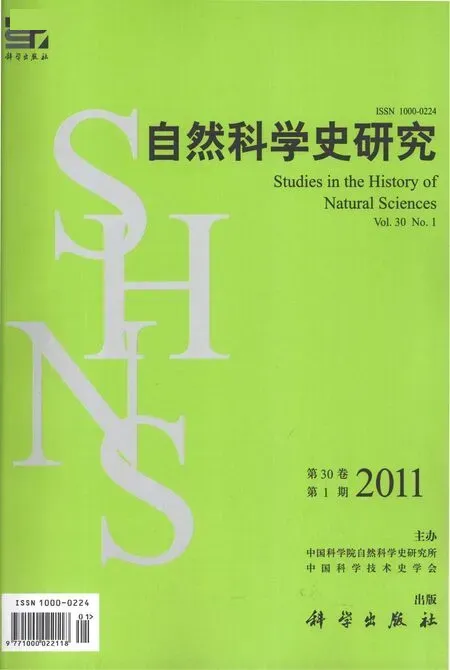科学、知识与权力
——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
韩 琦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是清代科学史上最饶有兴味的篇章。科学不仅作为康熙皇帝的业余爱好,而且也成为他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权力的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康熙勤奋学习西学,事必躬亲,不仅因为他的确有此爱好,更是因为他试图藉欧洲新知来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之目的。本文将根据宫廷官方文献,结合汉族大臣的文集与欧洲所藏档案,以1711年日影观测为例,希冀从社会史、政治史、宗教史的视角,探讨康熙皇帝、耶稣会士和文人在历法改革中的不同作用,并阐释康熙时代科学传播,以及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
1 引子:晷影测量的历史
圭表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测量仪器,主要通过测量正午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并测定方向。它由表、圭两部分组成,立表用于投射日影,圭是水平安放的标尺,用于测量影长。由于太阳正午高度随季节变化,日影长短也随之变化,夏至时最短,冬至时最长。日影观测已有悠久的历史,传说中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观测日影,以定地中。《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元代郭守敬用四丈高表观测,同时使用景符来调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精确的测量,屡为后世所称道,还受到传教士的赞扬,享誉欧洲。明清时期,钦天监设有晷影堂,用来观测日影。明代在仪器方面因循守旧,在晷影观测方面鲜有进步。①冬至、夏至日的测量是历法中重要的内容,日影观测之结果可用来计算黄赤交角,中国古代多有这方面的观测记录。参见陈美东《古历新探》,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年)对中国古代日影观测作了系统的研究,从而影响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对黄赤交角变化的结论。
欧洲也有晷影观测的传统,或在教堂,或在天文台。日影观测在欧洲之所以重要,教会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复活节的确定和计算,都需借助日影观测。[1]晚明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之时,传入了很多西方仪器,如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还传入了星晷(盘)、日晷等记时仪器,特别是日晷的制造,成为耶稣会士笼络汉人士大夫的重要工具。耶稣会士因此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等著作,国人陆仲玉也撰写了《日月星晷式》。在钟表没有普及的时代,相对于昂贵的钟表来说,这些简单的记时和测量仪器比较价廉,满足了一般人掌握时间的需求。
万历年间,在钦天监工作的周子愚曾与利玛窦谈及“律吕之学”,觉得西学可以补中国传统学问之缺,于是请其传授,利氏“慨然许之”,但不久利氏故去,合作没有成功。周子愚觉得中国古代虽有日影观测,而没有专书介绍,并注意到西方在圭表方面的成就,任意立表取景,“西国之法为尽善矣”,[2]于是向龙华民(NiccolóLongobardo,1559—1654年)、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年)等人学习,因此有《表度说》之作,详细介绍了欧洲圭表观测的方法。崇祯改历时,介绍了不少新传入的仪器(如望远镜,或称窥筒),也提到了西方测量日影的知识:
三曰表臬者,即周礼匠人置槷之法,识日出入之景,参诸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后累测日景,以求相等之两长景,即为东西,因得中间最短之景,即为真子午,其术更为简便也。([3],50页)
在谈到郭守敬用高表观测日影后,《明史》引用梅文鼎之语,也谈到了西方的方法:
西洋之法又有进焉。谓地半径居日天半径千余分之一,则地面所测太阳之高,必少于地心之实高,于是有地半径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气,能升卑为高,则晷影所推太阳之高,或多于天上之实高,于是又有清蒙差之减。是二差者,皆近地多而渐高渐减,以至于无,地半径差至天顶而无,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无也。([4],363页)
也就是考虑了地半径差、蒙气差等因素对日影观测的影响,使得观测精度有所提高。
2 日影观测与康熙学习西学之起因
明代的历法改革,主要因日月食的预测不准所引起。而耶稣会士的到来,正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天启年间,耶稣会士因准确预测月食,深得明朝士人的佩服。龙华民在《地震解》(1626)中曾生动记载了这个故事:“甲子(1624)谷雨日,谒李崧毓先生。坐次,蒙奖借曰:贵学所算二月月食,时刻分秒不差,真得推步之奇,想其师承诀法,必极奥妙。”[5]《崇祯历书》奏疏中对日月食的预测和推算也有详细的介绍。
不过在康熙初年的历法争论中,日影观测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668—1669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正是通过对日影和金星、水星的观测,最后击败杨光先、吴明炫,取得了胜利,重新树立了西洋历法的主导地位。
1668年,因钦天监所颁历法置闰引起纷争,康熙皇帝亲自过问,并在宫廷亲眼目睹了南怀仁和杨光先等人的日影观测。[6—7]此事对年幼的康熙触动很大,后来当皇子逐渐懂事,康熙对他们进行“庭训”时,曾重提旧事: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①[8],78—79页。康熙的训话主要由胤祉和其他皇子所记录。汤若望1666年已经去世,此处汤若望当为南怀仁。
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他也道出了自己学习西学的起因:
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9]
1669年之后,教案得到平反,传教士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康熙不仅对有一技之长、能担任修历重任的耶稣会士表示了欢迎的态度,而且自己也开始留心西学,以南怀仁为师,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地理等科学知识。当时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小,国内尚未平定,康熙所学的西学知识十分有限。
1688年,是清代科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南怀仁去世,洪若(Jean de Fontaney,1643—1710 年)、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 年)、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年)等法国“国王数学家”到达北京。②当时在钦天监工作的只有闵明我、安多、徐日升等人,而徐日升对科学所知不多。和南怀仁时代不同,法国耶稣会士除传教外,本身就肩负着皇家科学院的使命,并且和科学院的院士保持了密切的来往,因此更能及时获取欧洲科学的新知。([10],68—75页;[11])“国王数学家”一行带来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赠送的大量礼物,包括“浑天器两个、座子两个、象显器两个、双合象显器三个、看星千里镜两个、看星度器一个、看时辰铜圈三个、量天器一个、看天文时锥子五个,天文经书共六箱,西洋地理图五张,磁石一小箱,共计大中小三十箱。”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在乾清宫大殿接见,“天颜喜悦,赐茶优待。”[12]这些西洋礼物给康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重新燃起对科学的兴趣,大约与这些西洋仪器也不无关系。从此,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
1688—1691年间,康熙一周数次,频繁向传教士学习几何、算术,[13]乃至天文、音乐、解剖学知识,也时常询问一些欧洲的形势,表现了对西方新知强烈的好奇心。现在保留下来的张诚、白晋日记,生动勾勒了当时康熙勤奋学习的场景。①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西文手稿部藏1689—1691年白晋日记手稿,藏书号Mss.fr.17240,参见[14]。对康熙学习的具体内容,他所了解的西方新知,仍然值得作深入的研究。
张诚、白晋到达北京后,经常受邀随康熙出巡,作为科学顾问,随时备询天文、数学乃至其他知识。1691年5月,康熙外出,途中要求张诚、白晋一起复习实用几何学,并向张诚请教星象知识,也提到了有关日影观测的问题。张诚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11日,我们像前一天一样清晨就出发了,我们在一个离密云三十里叫Chin choan的村子里午餐,晚上则睡在一个叫Che hia的镇子上,一天我们共走了60里。我们到达之后不久,皇帝派人来问我此地北极高度(纬度)要比北京高多少,并想知道在计算正午日影时需要作哪些变化。([15],254页)
康熙以耶稣会士为师,勤学不怠,不耻下问,科学水准有了大幅提升。之后,在与大臣的接触中,历算、音乐便成为交谈的话题,亦可说是康熙炫耀的资本。康熙三十年(1691)十月十一日辰时,康熙到乾清门听政:
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张玉书,学士彭孙遹、西安、王国昌、年遐龄、王尹方、满丕、图纳哈、思格则、布喀以折本请旨后,上顾谓大学士等曰:“《性理大全》所言三分损益、径一围三之法,尔等以为可行否?明时人有论乐律之书,前令熊赐履看阅,昨赐履阅毕进呈,其意仍以蔡元定之说为主。朕问蔡元定之说果吻合乎?赐履云:‘似亦相近。’以朕观之,径一围三之法推算必不能相符,若用之治历,必多违舛。今试以此法算日月交食,其错缪可立见矣。又有为密率乘除之说者,径一则围三有奇,径七则围当二十有二,递推之,皆用此法,然止可算少,不可算多,少则所差微渺,积至于多,而所差或什伯或千万矣。即圆十方九之说,其法似乎少密,若数多,亦未能悉合。明末有郑世子载堉,其论乐律,极言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之非,但其说亦不能无弊。总之,算法明显易见,不容毫厘有差,试之于事,皆可立验,虽不谙文义之人,亦能辨其是非,欲以空言取胜,不可得也。”王熙、张玉书奏曰:“凡事必求实验,况算法争在铢黍,关系最要,律度量衡,皆从此出,历代论岁差亦只重算法,胶执偏见,茫无实验,何补于用?”([16],第二册,986—989 页;[17],卷七,“侍直恭纪”,1—2 页)
其中谈到的径一围三,就是圆周率;隔八相生,则是音乐的问题。张玉书对此也有记载,从不同方面勾勒了这场对话的场景,使得事件更为清晰。非常有趣的是,康熙还在这一场合首次提到了数学家梅文鼎:
上又谕曰:近日有江南人梅姓者,闻其通算学,曾令人试之,所言测景,全然未合。从来测景之法,某日某时,太阳到某度,影之长短,其辨至细。此人立表甚短,虽所差微渺,但一寸中差一分,至尺则差一寸,至丈即差一尺。彼因算法不密,故测景用短表,以欺人不见耳。②[16],第二册,989—990页;或作“此人立表至短,曾不踰寸,一寸中差一杪,至尺则差一分,至丈即差一寸。”见[17],卷七,“侍直恭纪”,1—2页。
接着说:
算法之吻合者,其本原具在,止因人不能穷究,如熊赐履言算法,皆踵袭宋人旧说,以为是径一围三之法,深晰其非者有人,今若直指其误,必群起而非之,以为宋人既主此论,不可不从,究竟施诸实用,一无所验。尔等第依其法试之,当自了然也。王熙等奏曰:前人所言,岂能尽当?径一围三之法推算不符,虽蔡元定之言,何可从也?皇上洞悉律数,究极精微,真是超越千古。臣等疏陋,得闻所未闻,不胜欣幸。①[16],第二册,990—991页。又见[17],卷7,“侍直恭纪”,1—2页,但文字略有差异。
梅文鼎当时在京城已颇有名声,②1691年夏,梅文鼎移榻李光地寓邸,1692年仍在北京。参见[18]。康熙大约是从李光地的口中得知他的名字,还专门派人考察他的日影测量知识,结果却令康熙大为失望。梅文鼎未能马上受到朝廷的重用,大约也与这次测试有关。康熙这番对算法的大肆造作,是不折不扣的做秀,却对汉人官员造成了很大触动。康熙借机当着大臣张玉书、王熙的面批评熊赐履对历算的无知,显然是对汉人的一种警示。
3 1692年乾清宫的日影观测
时隔不久,1692年正月,康熙在乾清门听政,又旧话重提,现身说法,再次作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其中也包括日影观测:
甲寅(初四)。上御乾清门,召大学士九卿等至御座前。上取性理展阅,指太极图谓诸臣曰:此所言皆一定之理,无可疑论者。又指五声八音八风图曰:古人谓十二律定,而后被之八音,则八音和,奏之天地,则八风和,而诸福之物,可致之祥,无不毕至,其言乐律,所关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从出,其义不可不知。如《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此法若合,则所算皆合,此法若舛,则无所不舛矣。朕观径一围三之法,用之必不能合,盖径一尺,则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积累至于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为舛错可胜言耶?因取方圆诸图,指示诸臣曰:所言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之数,若围圆,则必有奇零,其理具在目前,甚为明显。朕观八线表中半径勾股之法,极其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之法即从此出,逐一验算,无不吻合;至黄钟之管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此旧说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则古今尺制不同,自朕观之,当以天地之度数为准。至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此一定之理也。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第八声,仍还本音。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义耶,以理推之,固应如是。上又曰: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其法先量闸口阔狭,计一杪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又命取测日晷表,以御笔画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之处。遂置乾清门正中,令诸臣候视。至午正,日影与御笔画处恰合,毫发不爽。诸臣等奏曰:臣等今日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
([19],卷154,698—699 页;[20];[21])
乾清宫是皇帝接见大臣、议政和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一位大清帝国的皇帝,在御门听政的场所,和大臣讨论的却是历算问题,时值严寒,还命大臣“候视”日影,更命人当场演奏音乐,这是何等不寻常的一幕!这一记载,充分显现了康熙借助西学,“活学活用”的真实场景。皇帝口授音乐理论,而且亲自测量日影无误,当然更使得大臣们钦服不已。
通过上述史料,可以看到康熙关注律吕(音乐)、圆周率等问题,以及水流量的计算、日影的观测,涉及数学、天文学、音乐等理论。比较两次听政,可以看到康熙对圆周率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康熙科学素养的提高,则是这场作秀成功实现的关键。结合耶稣会士的记载,可以知道,其中的某些知识(如日影观测),康熙刚刚学到不久;而音乐知识,则很可能得自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omás Pereira,1645—1708年)的传授。经过1688—1691年约三年的时间,耶稣会士系统的历算教育使康熙受益匪浅,使他能够运用欧洲新知,来作这场精彩的“演出”。
除《圣祖实录》之外,在场的大臣对此事也有记载,如王熙“奉召于乾清门,同满汉正卿及翰林掌院学士等恭睹上亲算乐律历法,并令善算人于御前布算《九章》等法,测日水平日晷,午后始出。”①[22],内年谱“六十五岁”条,但年谱给出的日期是“初五日”,比官方史料晚一天,可能有误。半天之内,大凡音乐、数学和天文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计算等等,都有涉及。康熙的举动给大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叹之余,也感到无形的压力:“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于是向康熙建言,编纂乐律、历算著作,“垂示永久”。([17],卷2,“请编次乐律算数疏”,9—11页)康熙这场作秀实际上隐含了重要的政治动机,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炫耀,而是从文化方面向汉人“示威”,突显满族君主的才能,以慑服汉族大臣。②在其他场合,康熙的表演也让儒臣“佩服”得五体投地,恭维不已,康熙为此也沾沾自喜,陶醉其间。凭借自己的博学和科学才能,康熙甚至公然批评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大臣李光地之所以聘请数学家梅文鼎,和学生一起学习算学,其目的正是为了迎合皇上的兴趣。参见[23]、[24]、[25]。这场作秀不仅对在场的大臣产生了很大触动,还载诸邸抄,对文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翰林院检讨毛奇龄在看到报道之后,还专门恭进乐书,以迎合康熙。[26]
不幸的是,历算改革的倡议当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究其原因,历算人才的缺乏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当时梅文鼎著作尚未刊刻,其他擅长算学的人也很少。加之1692年之后的数年间,康熙国事繁忙,有亲征噶尔丹之役,历算教育似乎出现了停顿,种种因素使得历算改革不能及时进行,但是康熙在这段时间内所积累的天文、数学、音乐知识,却为他晚年从事《律历渊源》的编纂打下了基础。
回过头再来看康熙的这场“历算秀”,无疑是早有“预谋”。当时不仅有满汉大臣在场,还特地请来了明代遗民方以智之孙方正珠,情形实属罕见。③上面王熙年谱中提到的“善算人”可能就是指方正珠。官方史料对此并没有任何记载,幸运的是,清初文人王士祯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场景: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有旨召内阁满汉大学士、满汉尚书、左都御史、吏部汉侍郎彭孙遹、兵部满汉侍郎朱都纳、李光地、翰林院汉掌院学士张英等入。上御乾清门,命礼书熊赐履、兵侍李光地、学士张英近御座,上指示诸图,论古今乐律得失大旨,以隔八相生为合,围三径一为未合,复命侍卫鼓瑟,教坊司吹管以验之。再试江南桐城监生方正珠开方立方算法,移晷而退。方,明崇祯庚辰进士、翰林简讨以智之孙也。隔八相生,谓宫一徵二商三角四羽五,变宫六,变徵七,八复为宫。李少司马
云:自昔论乐律诸家,无人研究及此。([27],3页)
专门征召方正珠,并测试其数学水平,不仅表明康熙对数学的一贯兴趣,康熙也希望借机让更多汉人了解自己的历算才能,而这场“历算秀”无疑扩大了“演出”的观众面,因为方正珠回到桐城之后,势必也会向人道及此事。除了王士祯的记述之外,皇帝和方正珠的见面,旁人也有所闻。桐城县志对此便有记载:
方正珠,字浦还,中通二子。幼承家学,精于律数。康熙壬申春,以明经召对,问律吕之学,示以中和乐诸法器,奏对称旨。进父中通所著《数度衍》,并自著《乘除新法》,一时从学者奉为准绳。([28],552—553页)
从这里可以看到,方正珠向康熙进献了其父方中通的数学著作《数度衍》,以迎合康熙的算学兴趣,不过康熙对此书的反映如何,迄今尚未发现任何资料记载。从1691年底对梅文鼎历算水平的测试,到1692年初对方正珠的征召,可以看出康熙对略懂历算的汉人十分重视,不过梅文鼎和方正珠的表现都不能令他满意。直至1702年,康熙还说“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29],卷17,“理气”)。
从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南怀仁的日影观测,到1692年乾清宫的君臣之对,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历算活动。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康熙有关历算活动的作秀并不多见,这并非说明康熙对西学失去了兴趣,实际上,在不同场合,康熙仍有不少关于历算的言论。
4 康熙、耶稣会士与1711年的日影观测
杨光先反教案之后,西学在清廷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上谕钦天监:“尔衙门专司天文历法,任是职者,必当习学精熟。向者新法旧法是非争论,今既深知新法为是,尔衙门习学天文历法满洲官员,务令加意精勤。”([19],卷62,804页)明确表示“新法为是”,西法优于中法。康熙不仅相信西法,也重用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国王数学家”到达北京之后的一、二年内,康熙的求知欲极强,经常把传教士请到宫中,传授西学。此后的近二十年间,他对西学颇有好感,深信不疑。直至1704年,他还断言“新法推算,必无舛错之理”([19],卷218,202页)。清初沿用明末编成的《崇祯历书》(后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所采用的仍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年)的折中体系。然而到了康熙五十年十月十六日,康熙提到钦天监用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与实测夏至日影不符,于是对大臣说:
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犹之钱粮,微尘杪忽,虽属无几,而总计之,便积少成多。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今且看将来冬至如何。①[16],第二十册,11004—11005页;又见[19],卷248,456页,但缺“今且看将来冬至如何”一句。
也就是1711年夏至的日影观测,让康熙对西学的看法有了转变,认为欧洲天文学精度不高,希望钦天监对此加以注意。那么康熙是如何发现其中的奥秘的呢?
有意思的是,宫廷文献对此事起因有一定的描述。事情可以上溯到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九日,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年)、纪理安(Kilian Stumpf,1655—1720年)收到康熙“手谕算法”,“细读毕,喜之不尽”。并吹捧康熙“乃天生圣贤,无微不通。虽算学之七政皇历日食月食等诸原理,精通详核,故每年节气所定时刻,较推算原理又甚难,且皇上之圣学渊博,得之如此,此亘古未有者矣”。还提到“唯杨秉义(又名杨广文,Franz Thilisch,1670—1716年)之算法,不知本自何年,或京城、或热河地方经度几何,亦未书之。臣等尚未明了,故不敢即奏。”接着详细解释了康熙皇帝的日影观测和钦天监可能不同的原因:
再,查阅钦天监验算皇历官员向来所学新法文表内所开,日差分秒均无错误。又查得,七政皇历中夏至、冬至,以新法里数验算,必用日差之分秒增减。若修皇历,唯用时刻分数,此皆遵循旧例定书者。倘若衙门常用表中有细微误差,亦一时难以核查。虽在西洋表中,亦有所不同。因非一人所修,名虽同,或处相异。再者,用表虽知有误,亦不可即信。必于数年中核查一次,用测量之法加以核对,是亦所以纠正也。唯皇上日晷之法甚善,大小日晷其皆一。西洋人每观测日影,向南立高墙数丈,凿孔以通日影于地,铺一铜板于平地,分为万分之数观之,则见之甚易。比较铜板之日光照在何宫,则较目视日晷,极其清晰。等语。([30],“康熙五十五月十二日闵明我、纪理安奏折”,1675页)
十三日,闵明我、纪理安、钦天监衙门官员对日影进行了计算。十五日,内务府官员王道化、和素收到“计算之书”,并转递康熙皇帝。康熙在看了这份奏折后,作了批示:
初六日夜,初七日子时,日在何宫何度,初八日子时,日在何宫何度,加此二宫之度而平分,方得初七正午日之位置。若谓尔七政皇历无误,著尔等即将尔七政皇历分算奏来。何其卑鄙!([30],“康熙五十五月十二日闵明我、纪理安奏折”,1675页)康熙用“何其卑鄙”这样的词句严厉斥责他一向信任的耶稣会士,显然是十分震怒。皇帝对自己的计算与观测十分自信,加之他已通过杨秉义得知一些新的知识,因此更觉得闵明我等人的答复不过是找出种种理由来推托,没有应有的勇气来承认自己的错误。王道化、和素在接到康熙朱批之后,“即召闵明我、纪理安、钦天监衙门官员来看。”闵明我、纪理安等跪读毕,奏言:“所谕甚是。前我等苟且粗算便奏,至怠报迂。闵明我、纪理安我等不胜惶愧。今蒙颁旨指教,详细分算七政皇历谨奏。”钦天监监正明图等亦跪读毕言:“奴才等亦钦遵训旨,详细分算七政皇历再奏。”十六日,王道化等将闵明我、纪理安、钦天监官员此奏报康熙皇帝,十八日收到康熙朱批:“彼等无论怎样着急,还是彼等之皇历也。此次可以固执,俟回宫后,当面计算,或许知之矣。”([30],康熙五十年五月十六日“王道化等奏报计算太阳位置折”,723页)十九日,王道化等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奴才等恭阅,思之,闵明我、纪理安极为固执,竟掩饰己咎,因此愈觉其卑贱。钦天监等先仅照闵明我等法子计算,今遵皇上训谕计算,始赞皇上计算详细。奴才等斥责闵明我、纪理安曰:尔等掩饰失误,甚为卑鄙,尔等可欺我等,岂能逃皇上睿鉴?等语。所有皇上御制算法一张,闵明我、纪理安、钦天监等计算满汉文奏折二件,一并谨奏。([30],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九日“王道化等奏报闵明我等人情形折”,724页)
从上述官方文献中可知,闵明我和纪理安是这场争论中的主人公。闵明我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时任钦天监监正(由纪理安协助),他于1669年到达广州,这年适奉反教案平反,1671年因通晓历法,和恩礼格(Christian Wolfgang Herdtrich,1625—1684年)奉命赴京。([12],87页)闵明我到达北京后,在钦天监从事历算工作,1685年受命到澳门迎取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年),1686年底又到广州,动身往欧洲,①关于闵明我出使,参见[31]。1694年8月28日返回北京。1688年南怀仁病故不久,因闵明我谙练历法,受命顶补南怀仁,治理历法,当时他“执兵部文出差”,出使欧洲期间,天文历法工作由徐日升、安多负责。他从1688到1711年在钦天监治理历法,期间因年老体弱,曾挑选庞嘉宾(K.Castner,1665—1709年,1707年到京)于1707年11月至1709年协助,但1709年11月庞氏去世。闵明我曾编有《方星图解》(1711),主要根据法国耶稣会士巴蒂斯(I.-G.Pardies,1636—1673年)的星图而作。([32],967—986页)大约是受到康熙的斥责,在夏至日测量之后不久,闵明我就提出了辞呈,由纪理安接任,康熙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据《康熙起居注册》记载,康熙五十年十月十六日,上御畅春园,“又覆请钦天监治理历法闵明我年老告休一疏。上曰:闵明我年老,准其告退,着季(纪)理安治理历法。”②[16],第二十册,10998页。大约是批准闵明我辞职的当天,康熙旧话重提,谈到了夏至日日影的测量。
纪理安为德国耶稣会士,1694年到澳门,康熙听说他很聪明,让他到北京任职,次年抵京。他非常精通光学,擅长修理仪器,在北京期间,负责修理的天文与其他仪器多达600件,自己也动手制作了一些仪器。1700年,纪理安和安多送给康熙一幅地图,康熙很满意,并打算测量地图,但是因为纪理安体弱、安多年老,于是康熙要求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到中国。1711年,纪理安接任闵明我在钦天监的工作,直至1719年病退,主要从事太阳位置计算,以及天文表的制作。1715年,他设计制作了地平经纬仪,为此熔化了古代的天文仪器,遭到梅瑴成等人的批评。[33]1705—1720年间,他作为视察员,负责教会的事务,维护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利益,不遗余力。
实际上,在这场日影观测的背后,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新来的波希米亚耶稣会士杨秉义。杨秉义1710年与麦大成(João Francisco Cardoso,1677—1723年)到澳门,11月27日,作为数学家,经大运河启航北上,同行的人中有数学家Cordero神父,此外还有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年)、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1669/1670—1714年)和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年)。([34],37页)
康熙五十年四月,康熙和往年一样到热河避暑。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年)和德理格、马国贤、杨秉义、罗德先(Bernard Rodes,1646—1715年)等人随行,杨秉义作为数学家,罗德先作为外科医生,马国贤作为画家,巴多明、德理格主要担任翻译之职。根据西文档案,康熙在热河就日影问题询问了刚到中国不久的杨秉义,杨秉义不知皇帝的用意,就用耶稣会士利酌理(G.Riccioli,1598—1671年)的表计算,结果发现夏至点在午前20分,与钦天监的计算不一致,这使康熙知道西方已有新的天文表,确信是钦天监出错。③参见本文附录傅圣泽报告。康熙试图强迫杨秉义赞同他的意见,但是这位神父坚决不认可,他总是回答说天文表之间的差别不能称之为错误。康熙不能在他身上得到满意的答复,转而将计算结果寄送北京,并且还附上一份他亲笔书写的谕旨,要求对何以出现这一错误进行检查并向他报告。而这正好可以和上面所引的满文奏折互相印证。此事让康熙对传教士产生了怀疑,更加深了因教廷特使来华之后所引起的对欧洲人的不信任感。
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康熙从热河回到北京,在畅春园过冬,而那里总有一些传教士随时备询。自从夏至日影测量事件之后,康熙对历算问题练习得更加勤奋。据传教士记载,皇帝是这样度过那些日子的:“他醒着的时候思考的问题,使他彻夜不眠。他把杨秉义神父和翻译巴多明神父从早到晚留在宫中,并且不断给他们送去有关几何、数字和天文学的问题。这些考察和试验显然是一种不信任的结果。”(见附录)
那么,是何种因素引起了日影观测结果的变化?这需要对当时天文学背景作一回顾。
从1668南怀仁的观测日影,到1711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欧洲天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明末传入的蒙气差理论,到了18世纪初,已有了较大的修正,对这些因素作出重要改进的是天文学家卡西尼等人。其次,“地半径差”(parallax)理论在当时也有新的变化。上述因素,也导致了黄赤交角数值的变化。1711年日影观测的争论,和耶稣会士传入的欧洲天文学的新进展有密切联系。后来康熙御制《钦若历书》(雍正初改名《历象考成》)和乾隆时《历象考成后编》的编纂,正是引进了上述新的成果。①这些新的天文学成果,多为来华法国耶稣会士所掌握。参见[35]、[36]。
1711年,是康熙科学活动十分频繁的一年,他不仅参与了日影观测的活动,还于二月初九日带领皇太子、亲王和大臣测量大地,并进行指导,并谈到《易经》、算学、阿尔朱巴尔(代数)、西学中源等问题,科学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意思的是,康熙还重温旧事,谈及算学家梅文鼎:
“昔有一善算者,名梅文鼎,年逾七十,朕召问算法,彼所识甚多,彼所问朕者亦皆切要,然定位彼却不知。朕执笔画圈纸上以示之,彼顿省悟,呆视泣下。”副将胡琨奏曰:“彼时臣曾侍侧,彼言吾研穷至老,了不知此,若不遇圣主指示,吾将没世不知矣。因悲喜交集,不禁泣下。”上复取矢画地,作数圈示诸臣曰:“此即定位之理,虽千万品类不能出此,即今凡物若干,几人应得若干之数,用此顷刻可得,不特此也,声音之高下,亦可测之。”([16],第十九册,10512—10513页)
这段记载生动地重温了君主和布衣之间的交谈,并通过侍臣的恭维和补充,凸现了康熙算学的高明。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谈话的背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 年)等人及其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7—39]
5 康熙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与历法改革的缘起
1705年,教廷派遣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年)来华,引起了清廷和教廷之间的严重冲突,[40—41]这不仅给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蒙上了阴影,成为中西关系史上的转折点,也导致了康熙皇帝对欧洲人信任感的丧失,进而影响了康熙科学策略的转向和西方科学在华的传播。
多罗来华宣布禁止中国教徒敬孔祭祖一事,对康熙造成了很大的触动。他预感到天主教日后在中国会后患无穷,1706年底,熊赐履和李光地在向康熙皇帝讲完朱子书后:
上令诸内官俱退,呼余(李光地)和孝感(熊赐履)近前,云:汝等知西洋人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29],卷6)显见,康熙继续让传教士在宫廷任职,只不过是为了“用其技艺”。
与此同时,康熙进一步加强了对澳门的管理,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下旨让封疆大吏处理有关澳门事务,打听西洋消息,有时也通过内务府官员询问和了解传教士的情况及专长,请他们从澳门入京工作。1700年之后,有许多传教士来到澳门,广东督抚加以考核,将有技艺之人送到北京,负责此事的有两广总督郭世隆(1702—1706年)、赵弘燦(1706—1716年)、杨琳(1716—1722年),以及广东巡抚范时崇(1705—1710年)、满丕(1710—1714年)、杨琳(1714—1716年)、法海(1716—1718年)等。为使传教士更好地在宫廷发挥作用,康熙有时会让新来传教士在澳门学汉语,[42]或“留广州学汉话”,因为“若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43],第三册,6—11页)有的传教士起先未得到清廷的容许,为进入内地传教,往往也会在澳门停留一段时间,加强语言和技艺的学习,伺机以别的名义进京。
尽管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已经大不如前,但对“技艺之人”仍相当重视。他曾让内务府官员佛保传旨给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康熙四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两广总督赵弘燦、广东巡抚范时崇在收到御旨后,上奏称:
今查有新到西洋人十一名内,惟庞嘉宾据称精于天文,石可圣据称巧于丝律,林济各据称善于做时辰钟表,均属颇有技艺巧思。其余卫方济、曾类思、德玛诺、孔路师、白若翰、麦思理、利奥定、魏格尔等八名,俱系传教之人,并非内外科大夫,遵即暂留广东,不许往别省去。见在候旨遵行。今将庞嘉宾、石可圣、林济各三人,臣等专差家人星飞护送进京。([43],第一册,701—704页)
“用其技艺”后来成为康熙对待传教士的一贯政策,一直到晚年,仍不时请人从澳门派遣懂得历算、医学、技艺的欧洲人到内地。①康熙时耶稣会士闵明我、徐日升、安多、纪理安、庞嘉宾、杨秉义、孔禄食(L.Gonzaga,1673—1718)、严嘉乐(K.Slavicek,1678—1735)、戴进贤(Ignaz Kögler,1680—1746)等人相继到达北京,参与了历算工作。除白晋、张诚等国王数学家外,1700年之后,白晋、洪若所带来的耶稣会士,如杜德美(P.Jartoux,1669—1720)、傅圣泽等人,也成为御用教师,对康熙时代的历算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44]。
对于多罗来华所产生的冲突,康熙试图加以沟通,并两度派遣传教士回罗马,打听教皇的确切“旨意”。由于使节迟迟没有返回中国,康熙甚为焦急,不时向传教士打听“西洋来的消息”。由于天不作美,时空的遥隔大大阻碍了罗马教廷和康熙的及时沟通。消息的阻塞,使得“礼仪之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一些传教士出于传教利益的考虑,有时隐瞒消息,藏匿有关教皇禁教的旨意和信件,但时间一久,不免为康熙所察觉,最终导致康熙对传教士的怀疑。至迟在1711年,康熙对传教士已缺乏信任,称“现在西洋人所言,前后不相符,尔等理当防备。”([30],741页;[45—46])而正好在同一年,康熙发现了夏至日影计算有误。
康熙对传教士失去信任和上述有关日影观测的一连串事件,成为康熙时代历算活动的重要转机。1712年,皇帝传旨,希望能有人给他讲授天文学原理,于是杨秉义和傅圣泽(J.-F.Foucquet,1665—1741年)受命向康熙介绍天文学。为此傅圣泽开始翻译西方数学、天文学著作,向康熙介绍了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年)、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 年)、腊羲尔(Philippe de la Hire,1640—1718 年)等人的学说,许多是根据皇家科学院的著作写成的。其中有《历法问答》等天文译著,以及代数学著作《阿尔热巴拉新法》、佛拉哥(A.Vlacq)的对数著作等。①关于《历法问答》,参见[47]、[48]。《历法问答》介绍了法国“格物穷理院”、“天文学宫”(亦即法国皇家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在天文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以及法国天文学家到各地进行测量的情况。[49—50]他们还介绍了开普勒的椭圆运动理论,涉及到哥白尼日心学说,为此遭到了纪理安等人的反对,因为纪理安认为新天文学的介绍会让中国人觉得西方天文学并不可靠,会使南怀仁以来传教士在钦天监的地位受到损害,此外还有碍天主教教义,表现了其保守的一面。
1713年,康熙下旨设立蒙养斋算学馆,让最懂科学的皇三子胤祉来负责历法改革,为此从全国召集了一百余位学有所长的人才,编纂《律历渊源》,成为清代最大的科学工程。②关于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人员及其工作,将有另文讨论。师洋人之“技艺”,为我所用,便成为康熙晚年的重要目标,他觉得中国人应该自立,编纂历算著作,最后达到摆脱洋人垄断之目的。
6 结语
1668年的日影观测,给康熙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之后康熙向南怀仁学习,而法国耶稣会士的到来,更让他沉迷于西学。大概是从传教士身上,康熙学到了欧洲科学的实证精神,加之他十足的好奇心,时时打听西方新知,进步很快。1689年康熙在南京所作的有关老人星的观测,以及1692年日影的观测,都是康熙早有准备的作秀,科学知识无疑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环。正是通过对西学的学习和宣扬,康熙塑造了博学多能的自我形象,从而赢得了汉族大臣的尊重,进而达到了控制汉人之目的。③亲历这两次场景的极为少见,而李光地躬逢其事,感触颇深。1689年之后,李光地虽然已和梅文鼎有了接触,并向他学习数学,但仍然还不能和康熙皇帝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无论是1689年,还是1692年的表演,康熙的谈话对象都是汉人。二十年后,也就是在1711年,康熙则将所学到的知识转而用来批评洋人,科学仍是其权力运作的重要部分。从中西史料可以看出,康熙非常善于运用人际关系,通过内务府官员的居间周旋,利用传教士缺乏对“形势”的判断,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杨秉义因新来乍到,不知状况,最后泄露了“天机”,使得康熙借此乘胜追击,借助西方科学的新知,掌握了科学的话语权。日后杜德美、傅圣泽等法国耶稣会士奉命翻译欧洲新的天文学著作,也正是因为这场日影观测所引发的直接后果。最后导致了1713年蒙养斋的开馆和《律历渊源》的编纂。从这一角度看,1711年的日影观测,实在是康熙时代科学史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科学活动的背后,也使康熙的心理暴露无遗。作为堂堂大清皇帝,康熙总要显示自己的威严,加之通过对西学的学习,更为自信,更何况对夏至日影的“真理”了然于胸,耶稣会士的态度让康熙觉得传教士缺乏诚信和谦虚为怀的人格,因此他出言不逊,在朱批中大骂传教士“何其卑鄙”。而闵明我、纪理安等耶稣会士出于保守心态,不愿使用新天文表,被康熙抓到把柄,只得找出各种借口,聊以塞责,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而居间传话的内务府官员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更让传教士倍觉诚惶诚恐。
综上所述,日影观测看似简单的科学活动,但其背景却极为复杂。它与权力运作、满汉和中外关系,甚至与宗教也有密切的关联,特别是与礼仪之争纠结在一起,成为康熙朝政的一个缩影。以往在研究中往往叹息康熙朝汉文资料的不足,现在不仅有满文资料的补充,而且还有欧洲文献的互证。因此,不仅需要查看满汉文宫廷资料,查阅士大夫的文集,更要佐以欧洲的档案(尤其是耶稣会士留下的丰富信件、报告),以(欧洲)史证(中国)史,才能对事件的诸面相有完整的认识,才能生动重现真实的、丰富的历史场景。本文只是作了初步尝试,试图以小见大,说明康熙时代科学传播的复杂经过。但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日影观测,还有许多细节需要作进一步考证和厘清,才能获得一个更加完整的历史图像。
致 谢本文的部分内容曾以“知识与权力:康熙皇帝的科学兴趣及其背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06年10月19日)、“知识与权力: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国家图书馆善本部,2006年12月16日)为题作了报告,全文(“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时代历法改革的缘起”)曾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季风亚洲与多元文化”系列研讨会上报告(2010年5月12日),对上述机构的邀请,特致谢意。
附录
1711年6月至1716年11月初在北京发生的与欧洲天文学有关事件的详细报告① “Relation exacte de ce qui s'est passéàPéking par raportàl'astronomie européane depuis le mois de juin 1711 jusqu'au commencement de novembre 1716.”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书号ARSI,Jap.Sin.II 154。又见John W.Witek,A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man at the Court of the K'ang-Hsi Emperor:A Study of the Early Life of Jean Francois Foucquet.Thesis(Ph.D.),Georgetown University,1973.
自从安提阿宗主教多罗事件发生之后——宗主教已经享有枢机主教头衔与尊荣在澳门去世,中国皇帝看起来对于欧人有厌恶之心,对于他们的好意表示也明显减少许多,令人担忧他试图摆脱他们,有确切理由证实这种担忧年年递增,并且如今似乎到达了最后关头,所有与传教士有关的事都面临被永远逐出这一庞大帝国的危险。
1711年皇帝这种不友善的态度在天文学上面以一种相当明显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一事件发生在夏至,根据人们所说,皇帝本人亲自计算并观测夏至点。当时这位君主身在鞑靼,他一年中要在那里待5—6个月。根据他本人对夏至点的计算和观测,他发现,或者说他相信自己发现,它应该在出现在午前。但是钦天监却在历书上标明夏至点是在午后56分。当时有位刚刚来到宫廷的波希米亚传教士名叫杨秉义的,因精通天文学而被引见给皇帝,随驾去到皇帝的避暑山庄所在地热河。他受命检查为何计算结果有差别,并进行观测。他利用利酌理(Riccioli)的天文表计算出夏至点在午前20分。他受命将计算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皇帝看到之后更坚信钦天监出错了。皇帝企图强迫杨秉义也赞同他的意见,但是这位神父坚决不认可。他总是回答说天文表之间的差别不能称之为错误。当时有位内监奉命传达旨意与带回神父回复,然而来回数次均无功而返。同时带去的还有许多有关杨秉义神父使用的天文表的问题,而由此皇帝也得知在欧洲有着不同的天文表。以上这些出自杨秉义神父之口,并且当时担任他翻译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所说与他一致。皇帝不能在他身上得到满意的答复,转而将计算结果寄送北京,并且还附上一份他亲笔书写的谕旨:要求对何以出现这一错误进行检查并向他报告。圣旨于6月26日(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一日)到达北京。
钦天监官员试图走出困境,回答说他们依据自己的天文表,而根据他们的表夏至点就是应该在午后。但是葡萄牙副省的神父们却倍感担忧。他们聚集在会院里,商议这件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件。他们对于商议的内容严加保密,法国神父根本未被邀请参加,因此无法清楚了解事情的经过。法国神父只是大致被告知在给皇帝的回复中,包括有以下几点:1)对影子的观测造成一些错误。2)历书是给没有精确概念的一般百姓用的,并不需要深究其价值。3)陛下使用的小型仪器,而在钦天监使用的是大型仪器,这可能会引起一些差异。
这一答复使得皇帝大为震怒,他对于自己的计算与观测十分自信,认为钦天监出错了,并且强迫神父们承认这一点。那位内府官员名叫王道化的,曾经预见到皇帝会被触怒,并且确实曾经建议神父们不要呈上这样的回复。他警告他们说皇帝等待的是一种顺从,以某种方式承认自己曾经出错。他甚至对德国耶稣会士纪理安——当时作为钦天监监正闵明我的副手说道:震怒之下的皇帝完全可能将钦天监交给别人。“那好吧,如果他愿意就给别人好了”,纪理安神父回答说,“我来中国可不是为了这个。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位官员说,“您就是死了也没什么关系。不过要是钦天监被人从欧洲人手中夺走,那对别人可就大有关系了。你们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它之上的。南怀仁神父可不会这样回答。”这位多嘴的官员后来在法国耶稣会士面前重复讲述了这次对话,也就是从后者那里我们才了解到情况。尽管皇帝很不高兴,但是他表面上并未完全表现出来。他只是将这份回复留下了,并在上面用御笔批道:这份回复出自“恶劣卑下之人”。他说此话之意是指神父们未有好人所应有的勇气与谦虚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位内府官员受命向他们传达旨意。6月30日,闵明我和纪理安两位神父被传到宫中聆听旨意。上述所有情况都出自一位居留北京可靠人士的日记:日记写于北京,与发生事件的时间同步。
皇帝于1711年11月初由鞑靼回到北京。他在距北京城两哩半的行宫畅春园过冬。期间他会回北京城几次,准备祭祀上帝,或是为了什么别的事务。但通常他只待很少几天,之后马上又回畅春园。当他在北京的时候,欧洲人通常都要全数到宫廷,以这种不懈怠的方式表示他们执行皇命的迅捷。如果有人不到的话会让皇帝很不高兴,并且他自己也会查询看是否全数到齐。当他在畅春园的时候,总有一些欧洲人在那里,都擅长他当时正在学习或是正在拿来消遣的东西,而这些学业或是消遣常常变换不定。有时是绘画,有时是音乐,有时是数学,就这样这些艺术与科学轮番上阵。不像是在欧洲,那些大人物都以自己的无知为荣,这里可不一样。这里的大人物中都以有知识为荣,而皇帝本人特别喜欢这种荣耀,想在各种知识方面都表现得出类拔萃。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听他说过他学习数学已有40年之久,他还补充说:“对我精通数学也不必感到吃惊,我有过优秀的老师并且我勤加练习。”自从测量夏至点事件之后,他练习得更加勤奋了。他是这样度过那些日子的:他醒着的时候思考的问题,使他彻夜不眠。他把杨秉义神父和翻译巴多明神父从早到晚留在宫中,并且不断给他们送去有关几何、数字和天文学的问题。这些考察和试验显然是一种不信任的结果。而他的这种不信任在另外一件事上表现得更加清楚:在很多满汉朝臣在场之时,皇帝遣人询问所有欧洲人,他们测量的喀喇和屯的纬度为何与他本人测量到的有几分的差别。而不信任与怀疑表现得更加突出则是当他回到北京城时,所有欧洲人都根据惯例来到皇宫,有关官员过来向暂时代理病中的闵明我神父职务的纪理安神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为何神父们在钦天监教导多年的人还是那样无知,而由皇上亲自教导几何学的人却学得既快又好,最先懂得他给他们所演示的知识。皇帝确实是建立起了某种形式的学校。每天一些选中的人都来到他的面前,皇帝亲自给他们讲解欧几里德的某些原理,享受着显示精通抽象科学的乐趣,同时也享受着这些新学生一定会给他的赞美,通常他听都不听。但是这个学校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它只是当时皇帝策划的一个“学院”的开始。他曾经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省份寻找精通数学某些方面的满汉人士。那些巡抚大员们,为了讨好皇帝,举荐给他最优秀的精英,学习科学最有才能的人。人们从各地将人送来,就在这批精英中,他选择了一些人,多为年轻人,放进上文提及的“学院”。那里已有超过百人,有管事的官员,有算术家、几何学家、音乐家、天文学家,还有各门学科的学生,这还没有将人数可观的制造仪器的工人计算在内。他将畅春园内房舍众多的大片地域划归这一学院,并且指定他的第三子作为这个新建学院的领导。他有18个儿子,这还没有计算那些仍然留在宫中由妇女和内监照顾的(年幼者)。在这18个儿子中,有三个已经去世,即第六子、第十一子与第十八子。长子与次子即皇太子如今被监禁。对他们的囚禁是让其他儿子的心里产生惧怕,由此他作为一个专制的父亲,儿子对他的绝对依赖在欧洲不可想象,罕有其匹。为了帮助第三子管理这个新学院,他又派了第十二子、第十五子与第十六子辅助。在这四位皇子中,第十二子对数学知之甚少,而第十五子及十六子都还年轻,每天都还在学习,其中十五子只有25岁而十六子约22岁。说到第三子,他40岁左右,从小就学习数学并且颇有造诣。他的老师是佛兰德尔耶稣会士安多,教给他算术与几何。他现在教导两位年轻的弟弟。但是依据惯例,他每天早上带领他们去见皇帝,由皇帝亲自教导他们三个,并且检查皇帝布置给他们的作业的结果。人们说皇帝让他们做这些事,尤其是对于第三子,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是为了阻止他们寻衅生事。所有读至此处的人都根本无法想象皇子们在他面前表现出的谨慎与谦虚。他们跪下与他说话,至少是为了长时间与他们说话,他也不令他们起身,只是让他们把膝盖搁在一种高些的台阶之上,而他本人就坐在上面如同坐在宝座之上。第三子除了用某个满语词表示赞同之外,几乎一言不发。而两位较年轻的皇子除非被提问,也不敢打破这种沉默。这就是我们与皇子们同在皇帝面前时不止一次所看见的景象。皇帝经常在接见大臣之时,让他们在房门口等上两三个小时。正是用这种方式他使得他们那样温顺、那样服从。皇三子在此之外可是一位骄傲的皇子,生性严厉而苛刻,甚至会做出某些不可靠的事情,与他的出身地位大不相称。他在那一群里不受爱戴,特别是对于欧洲人很不友好,如今他想用他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同样的科学来摧毁他们,因此他被看作是欧洲天文学的最可怕的敌人。他立誓要毁灭它,并且他不遗余力竭尽所能来达到他的目的。夏至日事件很多与他有关。他极力保持和扩大皇帝对于钦天监使用的天文表准确性的怀疑。由于他手下的数学家中有一些人非常精于计算,因此他在日月食的观测中发现了这些不准确性。他让手下的人检查钦天监的计算。一旦他发现其中的错误,便立刻报告给他的父亲。三年前由此曾让以纪理安神父为首的官员到皇帝面前来承认错误。与此同时,他还借助官府,或者说借助强力将几部欧洲著作据为己有。他在Prestet书中第二册的末尾发现了一张平方及立方数表。他将数表带给了他的父亲,后者在此之前曾下令计算过类似的表,以此来向皇帝说明欧洲人甚至不了解自己的数表,或是曾经将这张表隐藏起来。这就是皇三子的性格,他的行为使我们不能不产生必要的担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使得这种担忧与日俱增。
1712年4月6日,皇帝回到北京。8日,所有欧洲人都来到宫廷,一位内监传来皇帝的旨意:他希望能有人给他解释天文学原理,而原理一词在此表示的是通过某种理论方式使得一个懂得几何与算术的人可以制作出天文表。旨意里还让欧洲人选择两位能胜任此事的人,尤其是解释中要用图形使得原理更易理解。主持欧洲人事务的官员与他们一起商议。那时已经担任钦天监监正的纪理安神父提供了几个名字,但是那些官员希望能带给皇帝确切的回音,即明确的两个姓名。于是德国纪理安神父、葡萄牙苏霖神父以及法国巴多明神父,三位都是皇帝任命负责欧洲人事务的神父,他们相互询问并且也询问了其他一些神父,最后他们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推选了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与杨秉义神父,后者已经为皇帝熟知并且因为去年夏至点事件而著名。值得一提的是巴多明神父那时正担任法国神父团体的负责人,而傅圣泽神父当时就住在这个团体当中,因此巴多明神父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了。皇帝允准了欧洲人的提议。官员从皇帝房间出来就向两位被任命的神父宣布了让他们立刻工作以便使皇帝满意的旨意。……
1 Heilbron J L.The Sun in the Church:Cathedrals as Solar Observatorie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 (明)熊三拔口授,周子愚、卓尔康笔记.表度说[A].周子愚序.天学初函(五)[Z].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
3 崇祯历书·奏疏[Z].卷1.
4 明史[Z].卷25,志第一,天文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明)龙华民.地震解[A].康熙18年刊本.钟鸣旦、杜鼎克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Z].第五册.台北利氏学社,2009.
6 Golvers N,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S.J.(Dillingen,1687):Text,Translation,Notesand Commentaries[M].Nettetal:Steyler Verlag,1993.
7 钦定新历测验纪略[Z].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inois4992.
8 庭训格言[Z].雍正刊本.
9 满汉七本头[Z].约1707年刊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10 韩琦.康熙朝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2):68—75.
11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2 韩琦,吴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 韩琦,詹嘉玲.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22(2):145—155.
14 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Les leçonsde sciencesoccidental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Kangxi(1662—1722):Texte des Journaux des Pères Bouvet et Gerbillon[M].Paris:EHESS.1995.
15 Halde J-B du,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M].Paris,1735.T.4.
16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Z].故宫博物院(台北)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17 (清)张玉书.张文贞公集[Z].松荫堂藏版,乾隆五十七年.
18 李俨.梅文鼎年谱[A].中算史论丛(三)[Z].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19 圣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 熙朝新语[Z].卷5.嘉庆二十三年刻本.2.
21 (清)吴振棫.养吉斋余录[Z].卷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98—299.
22 (清)王熙.王文靖公集[Z].康熙46年王克昌刻本.
23 韩琦.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J].清华学报(台湾).1996,新26(4):421—445.
24 Han Qi.Patronage Scientifique et Carrière Politique:Li Guangdi entre Kangxi et MeiWending[J].Etudes Chinoises.1997,16(2):7—37.
25 韩琦.康熙时代的数学教育及其社会背景[A].法国汉学(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3.434—448.
26 (清)毛奇龄.呈进乐书并圣谕乐本加解说疏(康熙叁拾壹年伍月拾伍日)[A].西河合集·文集·奏疏[Z].乾隆间重修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4—8.
27 (清)王士祯.居易录[Z].卷15.康熙辛巳年(1701)刊本.
28 (清)廖大闻等修、金鼎寿纂.【道光】桐城续修县志[A].卷16·人物志·文苑.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Z].17辑1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9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Z].傅氏藏园刻本.
30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1 Witek JW.Sent to Lisbon,Paris and Rome:Jesuit Envoys of the Kangxi Emperor[A].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Cinesi(Attidel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Napoli,11—12 febbraio 1997)[C].eds.Michele Fatica and Francesco D'Arelli(Napoli,1999).317—340.
32 韩琦.耶稣会士和康熙时代历算知识的传入[A].澳门史新编(三)[M].澳门基金会,2008.
33 韩琦.“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态度之改变及其背景[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1(3):210—221.
34 Ripa M.Memoirsof Father Ripa,during Thirteen Years'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M].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o Prandi.London,1844.
35 韩琦.《历象考成》的内容[A].陈美东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668—670.
36 韩琦.《历象考成后编》的内容及其改进[A].陈美东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10—712.
37 韩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J].汉学研究.1998,16(1):185—201.
38 韩琦.再论白晋的《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响[A].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15—323.
39 韩琦.科学与宗教之间:耶稣会士白晋的《易经》研究[A].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M].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4.413—434.
40 Rosso A S.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M].South Pasadena:P.D.& Ione Perkins,1948.
41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M].台中:光启出版社,1961.
42 康熙罗马使节关系文书[Z].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44 韩琦.康熙时代的历算活动:基于档案资料的新研究[A].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0—60.
45 韩琦.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J].文化杂志.2005,(55):1—14.
46 韩琦.瀛洲圣阙关山重——1709年教皇信滞留澳门始末[J].文化杂志.2006,(59):133—146.
47 Witek JW.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F.Foucquet,S.J.(1665—1741)[M].Rome,1982.
48 Hashimoto K,Jami C.Kepler's laws in China:A missing link?J.-F.Foucquet's Lifa wenda[J].Historia Scientiarum.1997,6(3):171—185.
49 韩琦.“格物穷理院”与蒙养斋——17、18世纪之中法科学交流[A].法国汉学(四)[C].北京:中华书局,1999.302—324.
50 韩琦.从《律历渊源》的编纂看康熙时代的历法改革[A].吴嘉丽、周湘华主编.世界华人科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化学系,2001.187—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