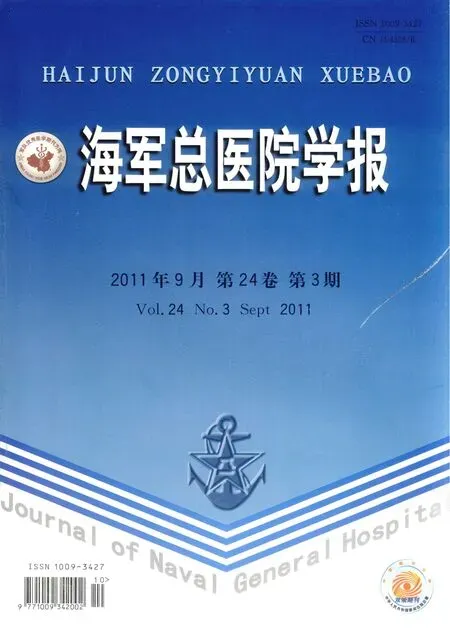神经源性炎症在变应性鼻炎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
韩晓博,彭朝胜
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也称为过敏性鼻炎,通常是指由IgE所介导的鼻黏膜炎症反应,其全球发病率在10%~25%。AR的主要临床表现为鼻塞、流鼻涕、鼻痒、打喷嚏以及嗅觉功能障碍。此外,它还可以导致鼻窦炎、咽炎、中耳炎、气管和支气管炎、哮喘和眼结膜炎等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鼻部神经源性炎症是指由鼻黏膜感觉神经末梢释放的神经肽及其介质所介导的炎症反应。自神经肽类物质被发现以来,其与变应性鼻炎的关系就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在鼻黏膜受到刺激时,局部感觉神经末梢通过轴索反射释放神经肽类物质(如P物质、降钙素基因相关肽等)。神经肽类物质本身有扩张微血管的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特异性受体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肥大细胞等,加速炎症介质及细胞因子的释放。因此,减轻神经源性炎症,阻止神经肽类物质的释放,可以为变应性鼻炎的治疗提供新方法。
1 神经源性炎症
1.1 神经源性炎症的物质基础——神经肽 神经肽主要存在于鼻腔的3类神经中,即C类感觉神经、副交感神经及交感神经。目前已发现的神经肽有上百种,其中分布于呼吸道的神经肽有近20种。依据功能不同,可将鼻黏膜内的神经肽分为4类:①感觉神经肽,存在于感受伤害性刺激的C类感觉神经纤维,主要有P物质(substance P,SP)、神经激肽A(neurokinin A,NKA)、神经激肽B(neurokinin B,NKB)、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CGRP)、胃分泌素释放肽等,前3种又统称为速激肽;②拟副交感神经肽,与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共存于副交感神经节后纤维,主要有血管活性肠肽;③拟交感神经肽,如神经肽Y,与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共存于交感神经节后纤维,是强有力的血管收缩剂;④炎性神经肽,如缓激肽等。感觉神经肽是形成神经源性炎症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促炎作用的感觉神经肽主要是SP、CGRP及NKA。其中这些神经肽的局部释放在人鼻黏膜中起着重要的生理和病理作用[1]。
1.2 神经源性炎症的发生机制 感觉神经末梢释放的神经肽或介质所介导的炎症反应被认为是由对辣椒素敏感的感觉神经元激活来调节的,尤其是位于无髓C纤维中的感觉神经元。
正常情况下,由于鼻黏膜上皮的完整性,C类纤维受体隔绝于鼻腔而不受刺激。鼻超敏反应时,由于炎性细胞释放的某些细胞毒物质,对鼻黏膜上皮的损害,致使C类纤维受体暴露,并感受化学介质如缓激肽、前列腺素等的刺激,刺激通过轴索上行性传递,若一部分刺激逆行性传至侧支,则引起SP、NKA、CGRP从感觉神经末捎释放。这种感觉神经末梢逆行性释放神经肽的过程称为轴索反射。在这一神经传导过程中,这些感觉神经元既充当传入神经纤维,同时也具有传出神经纤维的功能,其激活既能向中枢神经系统传递信号,也能在外周神经中释放神经多肽[2]。其结果导致血管扩张和血管通透性增加、炎性渗出、血浆外渗、黏膜水肿。表现在鼻部则出现了鼻痒、喷嚏、流涕、鼻塞等一系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症状。应用辣椒素作为神经阻滞剂可以减低鼻部对变应原的超敏反应。给予外周神经肽受体拮抗剂能有效阻止神经肽类物质引起的鼻塞症状[3]。
2 神经源性炎症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介质
2.1 速激肽
2.1.1 速激肽的种类与分布 速激肽是一类羧基端为Phe-X-Gly-Leu-Met-NH 2的神经肽,在哺乳动物又称神经激肽,其中最常见的有SP、NKA、NKB。SP是一种具有众多生物活性的11肽,广泛分布于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NKA过去又称物质K,含有10个氨基酸。NKB又名神经介素K,1983年首先从猪脊髓中分离出来,也含有10个氨基酸,多与SP、NKA共同分布于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与SP、NKA相比外周各部位的NKB含量一般较低。SP、NKA 、NKB 相应的受体分别为NK-1、NK-2、NK-3,NK-1分布在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NK-2主要分布在外周神经和器官,NK-3主要集中在中枢。鼻黏膜有丰富的肽能神经末梢分布,神经肽主要通过与其相应的受体结合而发挥其生物学作用。在呼吸道,速激肽SP、NKA、NKB主要位于C纤维中。免疫组化染色发现,动物鼻黏膜速激肽神经末梢广泛分布于鼻黏膜上皮细胞之间、上皮下、固有层及小血管和腺体周围。
2.1.2 速激肽的合成与释放 速激肽由神经元胞体内的核糖体合成,经轴突运送到突触末梢,储存在外周神经末梢突触小泡内,由突触前膜释放。多种因素可以刺激速激肽的释放,如干冷空气、辣椒素、组胺、柠檬酸、臭氧及过敏原等[4]。当鼻黏膜C纤维受到刺激,产生神经冲动,激发速激肽和CGRP释放,从而作用于多种效应细胞导致神经源性炎症,进而引起鼻部症状。
2.1.3 速激肽的失活 速激肽一般无重摄取机制,因而酶促降解是速激肽的主要失活方式。多种酶能使SP、NKA、NKB降解,包括内肽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等。呼吸道的速激肽主要由中性内肽酶(neutral endopeptidase,NEP)降解,NEP在呼吸道主要分布在上皮和黏膜下腺中[5]。各种因素诱导释放的神经肽很快被呼吸道内的NEP降解灭活,使两者维持动态平衡。
2.1.4 P物质在鼻黏膜的分布及作用 人鼻黏膜的SP免疫活性纤维来源于三叉神经节,其末梢广泛分布于鼻黏膜上皮细胞之间、上皮下、固有层及小血管和腺体周围,SP受体(NK-1)也分布于上述区域[6],并且在嗜酸粒细胞、浆细胞和肥大细胞表面均发现有SP[7]。在变应性鼻炎鼻黏膜中,含SP的神经纤维末端密度增加、染色加深、纤维增粗。SP在鼻黏膜神经源性炎症中的作用已受到重视,通过与其靶细胞或其他结构上相应的高亲和力受体结合而发挥其生物学作用[8]。
SP具有多种生物活性,SP最突出的作用是诱发内皮依赖性的扩血管作用,这一反应主要是由C类无髓鞘感觉神经末梢释放SP引起的,被释放的SP既可直接作用于血管,引起外周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蛋白渗出和鼻腔腺体的分泌增加,还可刺激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组胺、白三烯B4(leukotriene B4,LTB4)等炎性介质[9-10]。在病理状态下以神经肽为介质的轴索反射将C类纤维中逆向传递的动作电位放大;反过来,组胺和LTB4可以直接刺激C类纤维末梢,促进SP释放进一步增加。这种正反馈环路机制促成了神经性炎症的扩散。
2.2 CGRP在鼻黏膜的分布及作用 CGRP是一种含有37个氨基酸的神经肽,它与SP共存于气道黏膜上皮细胞C纤维中,是神经源性炎症的主要介质之一;CGRP活性纤维主要存在于扩张的小血管周围,其次在静脉窦,也见于上皮[11];黏膜内囊性扩张的腺体细胞内同样存在大量的CGRP阳性物质。由此推测,CGRP可能与腺体分泌增加、腺体的囊性扩张有一定的关系。
与速激肽相同,CGRP也是由感觉神经元胞体合成,并被转运,同SP等神经肽一起在鼻部神经源性炎症反应中起了重要作用[12]。CGRP是体内扩血管作用最强的感觉神经肽,可以控制不同血管床的通透性,在神经源性炎症和调控组胺诱导的血管扩张反应中起重要作用[13]。它也是一种强大的细胞抗损伤保护剂,对改善微循环,预防细胞、组织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抑制内皮素的生物活性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3 神经源性炎症的控制与变应性鼻炎的治疗
3.1 化学性脱敏疗法 1988年,Geppetti等应用辣椒素对正常人鼻黏膜进行了临床脱敏试验,取得较好疗效。此后多种动物实验及试验性治疗逐渐开展。Stjärne等[14]研究证实,变应性鼻炎经辣椒素治疗后鼻阻力及鼻腔症状明显降低。
辣椒素是一种存在于多种红胡椒和辣椒中的具有辛辣刺激性的复合物,它是一种香草酰胺衍生物,对感觉神经具有选择性脱敏作用。辣椒素主要在无髓鞘C纤维的传入神经元中作用于非选择性香草酸受体阳离子通道,通过开放通道,导致阳离子从胞外进入胞内,随之发生神经细胞膜的去极化,引起C纤维末梢速激肽类大分子释放于细胞外。其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作用机制为耗竭感觉神经末梢释放的神经肽物质(如SP、CGRP),引起感觉神经的电生理及生化变化,使感觉神经敏感性下降。研究还表明,耗竭作用与治疗作用相关,耗竭作用明显,治疗作用也明显。
国内也有试验性治疗[15]表明,辣椒素对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治疗作用。然而,对于用药剂量、药物浓度及给药方式仍没有统一的定论。
3.2 提高中性内肽酶活性 AR鼻分泌亢进及鼻阻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量速激肽的释放及其降解的减慢。酶促降解是速激肽的主要失活方式,气道的速激肽主要由NEP降解。NEP是一种含锌金属蛋白酶,该物质可以降解大量的肽类如SP、缓激肽等。其主要位于气道表面的上皮细胞内,但也出现于气道平滑肌细胞内、黏膜下腺细胞内和成纤维细胞内。通过对速激肽的灭活,减少气道神经肽的浓度来达到限制神经源性炎症的目的,从而对气道起到保护作用。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不同的刺激都可影响NEP在调节神经源性炎症中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各种因素诱导释放的神经肽很快被NEP降解灭活。而吸烟、呼吸道感染、吸入工业污染物二异氰酸甲苯酯、变应原暴露以及其他呼吸道刺激物,能够降低NEP活性,因而增强气道内速激肽的作用,加重神经源性炎症。NEP与神经肽和其他疾病相关因子关系密切,维持动态平衡。研究表明,皮质激素具有正调节NEP的作用。总之NEP能够有效地抑制神经源性炎症,它作为鼻炎治疗手段的临床应用目前正在研究中[16]。
3.3 速激肽受体拮抗剂 速激肽与变应性鼻炎的关系之前已作详细介绍,速激肽依赖其受体发挥作用。因此,应用速激肽受体拮抗剂治疗变应性鼻炎是针对其病因学治疗的又一方法。Tsuchida等[17]在动物模型中应用速激肽受体拮抗剂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其对抑制鼻塞的作用与地塞米松效果相当。Nabe等[18]的研究也发现速激肽受体拮抗剂对鼻高敏反应有较好疗效,其中NKB受体拮抗剂可能对变应性鼻炎的治疗更有效。虽然速激肽受体拮抗剂被认为对变应性鼻炎治疗有效,但是目前尚未见应用于临床。
3.4 选择性神经切断术 石崧等[19]对新西兰兔鼻腔行腔蝶腭神经切除术后再用卵蛋白致敏,观察鼻黏膜SP及CGRP的变化。结果显示,神经切断术后,动物模型的鼻部症状减轻,免疫组化也显示与对照组比较鼻黏膜中的SP和CGRP明显减少,其中组织内、血管旁SP与 CGRP以及腺腔内SP与CGRP都明显减少。Iked等[20]研究表明,手术切断鼻后神经抑制了副交感神经的促分泌作用及神经源性炎症。Pfaar等[21]认为鼻痒和喷嚏等变应性鼻炎的症状与神经源性炎症及神经肽类物质密切相关,调整包括神经肽及神经生长因子在内的神经源性炎症有可能作为抑制三叉神经的激活的方式之一。变态反应的鼻黏膜中SP、CGRP含量与感觉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活动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更精确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3.5 抗神经生长因子 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 th factor,NGF)是神经肽的一种潜在的诱导剂。免疫组化染色发现神经生长因子位于上皮黏膜细胞和黏膜下腺体[22]。多项研究表明,神经营养因子可以调节C类感觉神经末梢释放神经肽,参与变应性鼻炎发病的病理生理过程[23]。另外,除了调节神经肽的作用外,NGF还参与免疫反应。研究表明[24],NGF可以促进肥大细胞生存和分化,并且可以诱导肥大细胞脱颗粒和释放介质。因此,抗神经生长因子抗体作为可以特异性结合NGF,阻断其与受体的结合的物质,可以有效下调神经元的兴奋性,改变神经肽的高分泌状态。但是,目前对于神经肽类物质生物合成的调节研究较少,神经肽类物质生物合成调节的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3.6 其他 目前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一线药物为鼻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及抗组胺药物。有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有降低哮喘患者肺泡中SP含量、上调NEP活性等作用,其对于鼻黏膜中SP神经纤维的影响目前未见报道。选择性组胺H 1受体拮抗剂,过去认为对SP没有作用,最近的报道中[25],组胺H3受体激动剂(H3R激动剂)可以减少变应性鼻炎大鼠鼻腔灌洗液中SP的含量,但具体机制尚不清楚。
综上所述,神经源性炎症在参与变应性鼻炎的病理生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感觉神经末梢所释放的神经肽可以通过轴索反射产生一系列炎症反应,同时炎症细胞及炎性介质也可以直接释放神经肽,对炎症起放大作用,从而使变应性鼻炎症状进一步发展。针对神经源性炎症的病因治疗,如辣椒素化学性脱敏疗法、速激肽受体拮抗剂、提高中性内肽酶活性及选择性神经切断术等,目前已成为变应性鼻炎治疗研究的热点,但作为治疗手段应用于临床还有待进一步实践。随着对神经源性炎症及其相关因子研究的深入,最终有望为变应性鼻炎的治疗提供新方法。
[1]Heppt W,Dinh QT,Cryer A.Phenotypic alteration of neuropeptide-containing nerve fibers in seasonal intermittent allergic rhinilis[J].Clin Exp Allergy,2004,34(7):1105-1113.
[2]Barnes PJ.Neurogenic inflammation in the airways[J].Respir Physiol,2001,125(1/2):145-154.
[3]Kaise T,Akamatsu Y,Ikemura T,et al.Involvement of neuropeptides in the allergic nasal obstruction in guinea pigs[J].Jpn JPharmacol,2001,86(2):196-202.
[4]Schierhorn K,Hanf G,Fischer A,et al.Ozone-induced release of neuropeptides from human nasal mucosa cells[J].Int Arch Allergy Immunol,2002,129(2):145-151.
[5]谢启文.神经肽[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03-231.
[6]Gungor A,Baroody FM,Naclerio RM,et al.Decreased neuropeptide release may play a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asal polyps[J].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1999,121(5):585-590.
[7]方秀斌.神经肽与神经营养因子[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43-55.
[8]Hosokawa T.Involvement of kinm and tachykinin in airway hyperreactivity[J].Nippon Yakurigaku Zasshi,1998,111(4):243-248.
[9]Kulka M,Sheen CH,Tancowny BP,et al.Neuropeptides activate human mast cell degranulation and chemokine production[J].Immunology,2008,123(3):398-410.
[10]Hanf G,Schierhorn K,Brunnée T,et al.Substance P induced histamine release from nasal mucosa of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allergic rhinitis[J].Inflamm Res,2000,49(10):520-523.
[11]Mauviel A.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a key mediator of fibrosis[J].MethodsMol Med,2005,117:69-80.
[12]Knipping S,Holzhausen HJ,Riederer A,et al.Allergic and idiopathic rhinitis:an ultrastructural study[J].Eur Arch Otorhinolaryngol,2009,266(8):1249-1256.
[13]Watelet JB,Claeys C,Perez-Novo C,et a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1 in nasal remodeling:differences between chronic rhinosinusitis and nasal polyposis[J].Am J Rhinol,2004,18(5):267-272.
[14]Stjärne P,Rinder J,Hedén-Blomquist E,et al.Capsaicin desensitization of the nasal mucosa reduces symptoms upon allergen challenge in patients with alllergic rhinitis[J].Acta Otolaryngol,1998,118(2):235-239.
[15]方晓群,章如新.P物质神经阻滞疗法治疗变应性鼻炎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2004,12(5):248-249.
[16]Lacroix JS.Chronic rhinosinusitis and neuropeptides[J].Swiss Med Wkly,2003,133(41/42):560-562.
[17]Tsuchida H,Takahashi S,Nosaka E,et al.Novel triple neurokinin receptor antagonist CS-003 inhibits respiratory disease models in guinea pigs[J].Eur J Pharmacol,2008,596(1/3):153-159.
[18]Nabe T,Tsuzuike N,Ohtani Y,et al.Important roles of tachykini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ergic nasal hyperresponsiveness in guinea-pigs[J].Clin Exp Allergy,2009,39(1):138-146.
[19]石崧,周水淼.感觉神经肽在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J].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2006,13(3):177-178.
[20] Ikeda K,Yokoi H,Saito T,et al.Effect of resection of the posterior nasal nerveon functional and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inferior turbinate mucosa[J].Acta Otolaryngol,2008,128(12):1337-1341.
[21]Pfaar O,Raap U,Holz M,et al.Pathophysiology of itching and sneezing in allergic rhinitis[J].Swiss Med Wkly,2009,139(3/4):35-40.
[22]Bresciani M,Lalibertè F,Lalibertè MF,et al.Nerve growth factor localization in the nasal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allergic rhinitis[J].Allergy,2009,64(1):112-117.
[23]Raap U,Fokkens W,Bruder M,et al.Modulation of neurotrophin and neurotrophin receptor expression in nasal mucosa after nasal allergen provocation in allergic rhinitis[J].Allergy,2008,63(4):468-475.
[24]赵素萍,周新富.实验性变应性鼻炎鼻粘膜神经生长因子的测定[J].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2001,36(4):275-277.
[25]杨旭东,孙光明,许学谷,等.组胺 H3受体激动剂IMETIT对豚鼠变应性鼻炎作用的初步探讨[J].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0,24(12):559-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