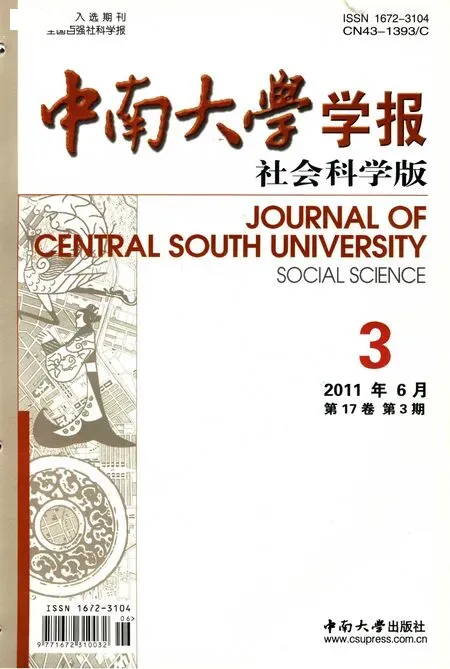《德意志意识形态》城市思想探微
牛俊伟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在19世纪40年代写下的重要文献,是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奠基性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始终不能忽略的经典之作,关于它的版本、结构、作者、思想内容、理论地位等方方面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在思想内容的研究方面,人们较多关注分工与所有制、市民社会与交往实践、全球化与世界历史性、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而对于其中涉及到的城市思想鲜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城市深刻转型,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问题频发,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从中汲取有益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城市起源于社会分工,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唯物史观一经确立,就为马恩正确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理论武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分工导致了城乡的分离,从而产生了城市。
《形态》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520)马恩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此基础上他们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的三种所有制形式,阐明了城市是前资本主义的产物。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分工很不发达,人们仅靠渔猎牧畜或简单耕作为生,这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城市,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把这种所有制形式称作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并明确指出:“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2](131)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首先是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1](521)这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了。马克思后来在《手稿》中也做了进一步论述:“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1](521)这时的城市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农民的居住地,“这第二种形式不是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以城市作为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经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而不是[像在第一种形式中那样]村庄表现为土地的单纯附属物”。[2](126)二是作为军事组织的功能,公社共同体为了保持对土地的永久占有或占有新的土地以维持共同体是生存,就必须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和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处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2](126)
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1](522)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影响下,欧洲发展了封建所有制,在乡村中,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在城市里,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这种城乡之间的对立。后来在《手稿》中马克思也谈到“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2](131)土地所有者以独立家庭的形式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此时仍然还有公社,但它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存在,公社不像在古代那样作为国家或国家组织而存在,因为它不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当然,公社除了存在于自由土地所有者的集会外,也存在于城市本身和掌管城市的官吏等等的存在中。所以“当联合在城市中的时候,公社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经济存在”。[2](131)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为了反对土地贵族的盘剥和逃亡农奴的竞争以及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而在城市里聚集并联合为行会,逐渐发展起来以师傅与学徒为主要形式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城市行会制度,城市手工业产生了。这时候总的来说分工还不是很发达,各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城市发展缓慢。
总的看来,马恩认为,由于前资本主义的三种所有制都是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人类社会还处于农业文明社会,城市虽然已经产生,但在社会生活中只起从属作用,主要担负着军事的、政治的和文化(宗教)的功能,仍然处于乡村的统治之下。
二、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确立的最初场所,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必然产物
首先,马恩在《形态》中重点考察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的形成以及城乡之间的相互对立,结果发现,尽管在封建生产方式下,乡村庄园制经济关系处于统治地位,城市屈从于乡村的统治,城市发展缓慢,然而,正是中世纪的城乡分离和对立,首先在欧洲孕育出了资本主义萌芽。随着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分工也在不断发展,“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是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1](559)交往日益集中在商人这一特殊阶级手里,这样就产生了同临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的可能性,“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不久每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性开始逐渐消失”。[1](559)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1](562)资本主义所有制出现了。
其次,资本主义所有制一旦形成,极大的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中世纪的城市仍然是政治性、文化性、宗教性的,经济功能居次要位置,而且相互之间处于隔绝状态,规模小,人口少,城市呈现乡村化。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行会制度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代替,由于商人的活动开拓了城市之间的交往,商业城市在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马恩指出:“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势力占统治。……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1](564)“……当时的商人同手工工场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1](565)这里所说的后一时期是指 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象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566)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再次论证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促成的城市化:“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36)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更为明确的指出:“如果说水力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绝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4](312−313)乡村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必然景观。
最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资本现代化的过程。《形态》具体考察了随着前资本主义城市向资本主义现代城市转变,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摆脱它的自然形成的性质而彻底蜕变为决定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生产和其他一切关系的“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2]P31马恩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1](557)从中世纪的行会城市到17、18世纪的商业城市,再到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大工业城市,资本从萌芽一步步走向成熟,先后经历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重商主义影响下的活动的商业资本、体现劳动和货币关系的工业资本,资本的神奇统治魔法日趋成熟。
等级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是中世纪城市行会制度下集中于行会师傅手中的资本,直接体现为手工劳动工具和简单生产资料,以自身劳动为基础并支配着少量帮工,内部几乎没什么分工。按照马恩的说法,“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的资本”。[1](558)可见,等级资本的特点是规模小、积累慢,通约性差,基本上是简单再生产,城市之间相互隔绝,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结构变动很小。
商业资本是聚集在商人手中直接体现为货币财富的资本。17~18世纪,封建行会制度开始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生产和交往分离,交往集中于商人手中,迅速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逐渐控制了手工业的生产。马恩指出:“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聚到个人手里,一部分违反行会法规定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1](560)资本在商人手中积累,立即改变了资本的性质,自然的等级资本开始向活动的商业资本转化。《形态》指出:“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1](561)商业资本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直接体现为货币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原来带有的那种自然性质,即直接体现为特定工具和特定劳动的物,本质上是一种活动的资本,在商人的易货贸易中会实现增殖,因而积累起来比较快,从而加快了资本运动的速度,最终击溃了行会制度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工业资本是资本的成熟形态,它已经完全褪去了一切自然形成的性质,它虽然在客观形式上表现为物(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货币等),但实际上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借以继续占有的工人的活劳动的积累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用《手稿》中的话来说就是“……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2](168)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外在表征。当然,在《形态》时期,马克思还尚未对经济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所以在《形态》中还未能对资本的本质做出说明,但他们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工业资本的巨大吸纳能力、祛魅能力、空间塑型能力。他说:“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象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566)至于资本更完备的形态——金融资本这时还尚未进入马恩的视野当中。
三、城市孕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两大阶级的对抗引发了城市革命运动
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最初场所,从城关市民中分化出了最初的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形态》指出:“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开始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立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从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1](570)
城市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施展魔法的空间,在资本积聚的同时,人口也大量积聚,必然加剧两大对立阶级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形态》指出:“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造成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1](567)对于不合理的城市制度的反抗早已有之,“因此,平民至少还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是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与行会制度本身的存在有关的小冲突。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起义都是从乡村爆发起来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成熟,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1](558)相比之下,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却为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创造了条件,城市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廉价而便利的交通”,成为他们集体行动的物质条件。“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1](567)大工业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工业资本的残酷剥削,使大城市成为了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历史上的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条件下爆发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主战场是在城市,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也就表现为城市运动或城市革命,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城市性决定的。
四、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历史,城乡对立是私有制社会的必然现象,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
《形态》把城乡分离看作是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社会分工,并把它看作是城市、国家及文明的历史的起点,“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1](556)原因是,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①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分工在依然是一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异己性敌对力量,人们处于“必然王国”支配之中。马恩指出:“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536)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仍然受着不合理分工的制约,“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1](537)自发的分工和不合理的私有制必然导致城乡对立,“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556)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分裂为经济利益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阶级,城乡分离因此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性质和意义。而阶级的实质意味着对他人劳动及其成果的无偿占有:居住在城市的剥削阶级利用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盘剥乡村劳动人民,形成了城乡之间“中心-边缘”,即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依附的二元对立格局,并使乡村陷于贫穷和愚昧状态之中。马恩认为:“只要这种力量(指不合理的劳动分工,笔者注)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1](557)也就是说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必经阶段,会持续很漫长的历史,直至分工的消灭,人类步入“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笔者注)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1](557)马恩的意思很明确,城乡的对立和分离不会永恒存在,仅仅是私有制的伴随物,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能够消除二者的对立,但在《形态》中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还尚未对如何消除城乡对立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五、结论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是社会分工在空间地理形态上的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必然以显著的差异、深刻的对立甚至是剧烈的对抗布展开来。今天,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会分工已经全面国际化,城乡的对立也已经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而全球化,国际性资本仍在深刻改造和再造社会地理空间,全球资本以几个主要国际大都市、大都市区、城市圈、城市带为聚集点,而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整个吸纳进它那永不厌食的“肠胃”里,把它们重新夷为一片一片的穷乡僻壤。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空间正义问题,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成为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到九十年代末,随着我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大规模扩张和城市内部空间普遍更新,资本力量在城市空间的生产日益彰显威力,导致了诸如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城市原著民失居等诸多严重损害公众空间权益的非正义现象时,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无论如何,马恩都应该是研究城市问题的理论先驱,面对当代的城市问题,中外学者都不约而同的从他们那里或多或少的汲取了理论资源。这是因为,马恩从分工的角度,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理解和解决一切与城市有关的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时间——空间——资本三元辩证的方法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城市演变发展的三维立体的生动历史画卷,从而为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城市问题提供了一把科学钥匙。那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批判资本、扬弃资本、超越资本,从根本上克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从而化解空间占有资源矛盾,优化空间结构,消除城乡鸿沟,实现城乡融合,彻底解决空间正义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在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两大时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和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指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是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592页.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