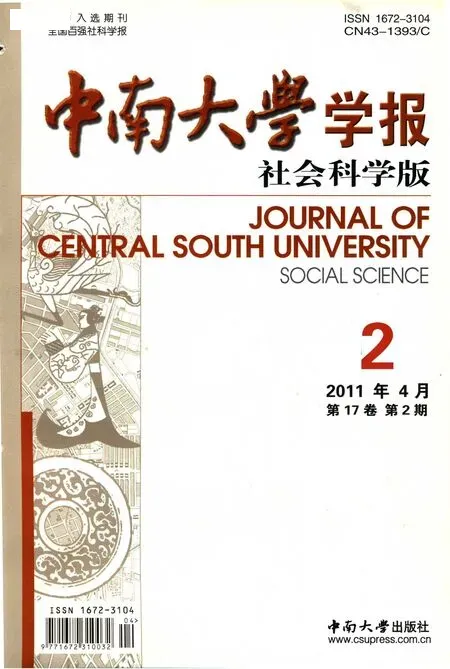吕柟与阳明学
米文科
(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陕西宝鸡,721007)
吕柟与阳明学
米文科
(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陕西宝鸡,721007)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
吕柟;阳明学;朱子学;关中地区;关学
随着阳明学在嘉靖初年的流行,整个思想界都不约而同的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冲击,那么,颇具地域性特色且“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1](11)的关中理学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本文即以“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2](1)的吕柟(1479~1542)为考察对象,探讨明代中期关学与阳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进一步去认识阳明学在明代思想界的地位和吕柟之学的基本特征。
一、良知与“因人变化”
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被明清两代关中学者视为是集关学之大成者。正德三年(1508)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吕柟因议大礼而下狱,不久即被贬为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判官。嘉靖六年(1527)转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此后,吕柟在南都为官近九年,亦讲学九年,曾先后讲于柳湾精舍、鹫峰东所、太常南所,“风动江南,环向而听者前后几千余人”。[2](44)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吕柟)九载南都,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东南学者,尽出其门。”[1](138)可见其讲学影响之大。除与诸生讲学之外,吕柟还常与邹东廓、穆孔晖等阳明弟子相互往来论学。此时阳明学正风行于大江以南,但吕柟却站在程朱学的立场上与其展开一系列的论辩,表达了他对阳明心学的认识和态度。
首先,吕柟认为王阳明讲学单提“良知”,未免过于浑沦,使初学者无处下手做工夫:
诏问:“讲良知者如何?”先生(吕柟)曰:“圣人教人,每因人变化。如颜渊问仁,夫子告以‘克己复礼’;仲弓,则告以敬、恕;樊迟,则告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盖随人之资质、学力所到而进之,未尝规规于一方也。世之儒者诲人,往往不论其资禀造诣,刻数字以必人之从,不亦偏乎!”[3](87)
在这里,吕柟以孔子为例,指出圣人“未尝规规于一方”,只教人“致良知”,而是“因人变化”,随所学者的资质、学力或不足之处而诲之,就像孔子弟子问“仁”,孔子的回答并不完全相同一样。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吕柟又用了一个医者用药的比喻,他说:“凡学者各受病处,如疮疥之类一般,有发之手者,有发之足者,有发之面目者,须是自其脉络贯通紧要处整治,才易愈。圣人之教人,正如医者之用药,必是因病而发。”[3](147)相较之下,王阳明则执定“良知”一言,“不论其资禀造诣,刻数字以必人之从”,因此是有偏差的讲学。
对于阳明讲学的这种“偏颇”,在吕柟的讲学语录《泾野子内篇》中曾多次提到,并有数处专门讨论圣贤教人之方的,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而其结论也总是:“拘拘执一者非也。”[3](90)如吕柟说:“予前日亦曾与邹东廓说来,圣贤说话,亦有不曾一句就说尽了的。如首章言个戒慎恐惧的工夫,可位育得天地了;然下面便继以智、仁、勇,又继以九经、五达道,又继以诚明;然又必须要个好资质,才做得这工夫。故说个慎独,中间便自有许多条理。不然,只一句说了,下学怎么得下手的去处? ”[3](167)
吕柟认为,不仅是王阳明、邹东廓这些心学家,即使如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也都是“各执其一端”。他说:“纵是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曰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执其一端。且如言静,则人性偏于静者,须别求一个道理。曰诚曰敬固学之要,但未至于诚、敬,尤当有入手处。如夫子《鲁论》之首,便只曰‘学而时习’,言学则皆在其中矣。”[3](89)对于朱子,吕柟也认为其以“诚意正心”规劝人君,亦未尽善,因为“人君生长深宫,一下手就叫他做这样工夫,他如何做得? 我言如何能入得? 须是或从他偏处一说,或从他明处一说,或从他好处一说,然后以此告之,则其言可入”,因此,“告君须要有一个活法”。[3](122—123)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因材施教”的考虑,或者说要跳出程朱、陆王之争,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儒学天地中,吕柟强调《论语》一“学”字即可涵括上述各家之旨,“言学则皆在其中矣”。并强调人们应该以圣人为学,而他所谓的“圣人”,即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这也就是要求回到先秦的孔孟儒学。
不过,对于吕柟的“因人变化”之说,黄宗羲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夫因人变化者,言从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体,本体无人不同,岂得而变化耶? 非惟不知阳明,并不知圣人矣。”[1](138)即认为阳明以“良知”教人,乃是为学者指出大本大源所在,亦即“先立乎其大者”,讲的是本体,而不是工夫,怎能以“变化”来论,但吕柟却以入手工夫来批评阳明的良知本体,这是不对的。梨洲之论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是否真如其所说,吕柟并不知道王阳明讲的“良知”是指本体而不是工夫,因此吕柟并不真正懂得良知学,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果从《泾野子内篇》、《四书因问》等吕柟的著作来看,对于理气、心性这类形上问题,他确实很少谈论,而主要关注的是躬行、实践,强调的是“甘贫改过”、格物、慎独、致曲等下学工夫。薛应旂(字仲常,号方山)就说:
是时海内讲学者相望而起,然或未免空谈。先生(吕柟)与诸生约,每会即以六经四书质正,就于其中探讨精义,勉其体认践履。或问朱陆同异,先生曰:“晦庵、象山同法尧舜,同师孔孟,虽入门路径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为同哉。学者不务力行而胶于见闻以资口耳,竟于身心何益? ”闻者多感发兴起。其训释经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所未发者,故所至学徒如云滃雾集。[4]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1557~1627)也说,吕柟“重躬行,不事口耳”、“不为玄虚高远之论”。[2](46)由此可见,吕柟强调“因人变化”实是为了避免学问流于形而上的“空谈”,而强调实际的工夫践履,这自然与阳明从形上超越的道德本体来立论不同,因此双方并没有交集。这种不同,还可以从下面吕柟与邹东廓的辩论中进一步感受到。
二、知行与格物之辩
在吕柟所交往的众多阳明学者当中,王阳明的弟子邹东廓则是其最密切的讲友。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相互讲学最早可追溯到嘉靖三年。当时,两人都因议大礼而下狱。在狱中,吕柟与邹东廓“日讲学不辍”。[5]吕柟转官南都后不久,邹东廓也随即由广德州(在今安徽)判官升为南礼部主客郎中。此后三、四年多的时间里,两人更是相互往来论学不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包括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可以说吕柟对阳明学的具体看法,正是在与邹东廓的论辩中展开的。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吕柟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坚持知先行后,反对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论。
先生(吕柟)曰:“君(邹东廓)尝谓知便是行,向日登楼,云不至楼上,则不见楼上之物。”东郭子(即邹东廓,下同)曰:“非谓知便是行,但知便要行耳。如知戒慎就要戒慎,如知恐惧就要恐惧,知行不相离之谓也。”先生曰:“若如此说,则格致固在戒慎之先矣,故必先知而后行也。”东郭子曰:“圣人原未曾说知,只是说行,行得方算得知。譬如做枱,须是做了枱,才晓得枱;譬如做衣服,须是做了,才晓得衣服。若不曾做,如何晓得? 此所以必行得,方算作知。”先生曰:“谓行了然后算作知亦是。但做衣服,若不先问衿多少尺寸,领多少尺寸,衿是如何缝,领是如何缝,却不错做了也? 必先逐一问知过,然后方能晓得缝做,此却是要知先也。”[3](127−128)
从以上引文可见,邹东廓主张知即是行,认为“圣人原未曾说知,只是说行,行得方算得知”,并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3](128)这显然是针对朱子的“知先行后”说而发的,意在纠正“知先行后”所带来的当时那种知而不行、空谈性理的弊病。这与王阳明所讲的“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6](42)意思相同,都是在强调“知行合一”。但吕柟却坚持认为“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后行,不可一偏”,[3](89)就像做衣服,必须先知道尺寸多少,袖领如何缝,然后才能做得好衣服,所以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随”。故吕柟指出,知与行的关系就如形与影、目视与足移一样。如果没有形体,影子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目之视,足的移动就会失去方向,甚至寸步难行,所以“知得便行为是,谓知即是行,却不是”,[3](146)邹东廓以行代知,是偏于一面。
知行先后关系可以说是吕柟与邹东廓论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两人曾进行过多次辩论,如邹东廓曾以《中庸》为例,认为《中庸》讲完天命之性和率性之道后,接着就讲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因此是只说了“行”,而没有说“知”,所以“圣贤教人,只在行上”。[3](146)邹东廓甚至认为传统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也都是在讲“行”,而不是“知”,等等。对此吕柟一一进行了反驳。
从双方关于知行关系的辩论来看,其意义即在于如何对待儒学传统中“学”、“问”的一面。吕柟非常重视先秦儒学所讲的博学多闻,他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如礼乐、制度、钱谷、甲兵、狱讼之类,皆当究心,庶几他日可以应用。至于各年通报,诸臣条陈政务,亦各有善处,可览记之。”[3](88)因此,吕柟坚持朱子的格物穷理说,反对邹东廓把“格物”解作“正物”,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他说:“格物之义,自伏羲以来未之有改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求诸物,近取诸身。其观察求取,即是穷格之义。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3](129)又说:“格物还只是穷理,若作正物,我却不能识也。……若不穷理,将不至于冥行妄作乎? ”[3](129)在吕柟看来,若把格物看作是“正物”,那么儒家传统的多学多闻与所谓舜之“好问好察”、孔子之“好古敏求”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吕柟坚持“格物还只是穷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吕柟主张格物穷理,并不专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是以修身为本,他说:“所谓格,在随时随处格。凡念虑所起,身之所动,事之所接皆是,皆要穷究其理。……若离却己身,驰心鸟兽草木上,格做甚。”[3](147)即博学多闻必须见于躬行,用以修身,否则便是口耳记诵之学,于身心无益,于世道无补。故黄宗羲评价说:“先生之学,以格物为穷理,及先知而后行,皆是儒生所习闻。而先生所谓穷理,不是泛常不切于身,只在语默作止处验之;所谓知者,即从闻见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过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无从躲闪也。”[1](138)此诚为的论。
但对邹东廓来说,所谓“知”则主要是指“良知”,而“行”则意味着良知的实践即致良知,亦即良知由本体向工夫的转化与落实。若从这一方面来说,格物穷理、多闻多见在这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中就显得没那么重要。因为对阳明心学来说,良知是每个人生来都具有的、不学不虑的先天道德本体,故学问的重点是如何去“致”良知,使吾人心体光明,时时是此“心”。所以邹东廓说“圣贤教人,只在行上”、“知即是行”,即是此意。但吕柟却不是这样来理解知行关系中“知”的含义的,他认为若不穷理,不预先对事物有一客观了解,就是冥行妄作。即使是就善恶的道德之知来说,吕柟虽不否认人有先天的良知或恻隐之心,但在他看来,现实之人的良知并不会时时都能呈现发用,因此还必须有学问思辨的工夫,才能戒慎恐惧,“是天理便做将去,是人欲即便斩断,然后能不间歇了”。[3](163)所以吕柟的最后结论就是:“圣门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紧的,虽欲不先,不可得矣。”[3](163)
三、“修己以敬”与“用敬修己”
邹东廓的良知学是以“敬”为主,他说:“圣门之教,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故出门使民,造次颠沛,参前倚衡,无往非戒惧之流行,方是须臾不离。”[8](515)并认为“敬”上接洙泗,而一洗朱子学支离之习。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得力于敬。”[1](332)因此,吕柟与邹东廓围绕着“敬”也展开了一场争论:
东郭子曰:“圣贤论学,只是一个意思,如‘修己以敬”一句尽之矣。如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此敬也;如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亦敬也;如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亦敬也。我看起来,只是一个‘修己以敬’工夫。”先生(吕柟)曰:“‘修己以敬’固是,然其中还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许多的工夫。此一言是浑沦的说,不能便尽得。……必格物致知,然后能知戒慎恐惧。”东郭子曰:“这却不是。人能修己以敬,则以之格物而物格,以之致知而知致,以之诚意而意诚,不是先格物致知,而后能戒慎恐惧也。”先生曰:‘修己以敬’如云以敬修己也,修字中却有工夫。如用敬以格物致知,用敬以诚意正心。”[3](127)
东郭子曰:“人子果有敬存于中,则外面自有许多的事。且如敬以搔之,敬以扶持之,皆由有敬于中,故能如此。先生曰:“敬抑搔,敬扶持,是用敬抑搔,用敬扶持也。”东郭子曰:“用字却不是。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自然能得许多节目。”先生曰:“深爱言却好,然未能如此者,必敬搔、敬扶持之,却是学。”[3](129)
一般来说,程朱理学所讲的“敬”只是“心”的一种涵养,即指身心的收敛、谨畏、主一无适、整齐严肃等,亦即使意识常常凝聚于理上并顺理而行,但这并不是对本体的体证,而只是一种“常惺惺”的态度,因此还必须有格物穷理的工夫。但邹东廓所说的“敬”却与程朱理学在工夫修养上讲的“主敬”、“用敬”不同,而是“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或“敬也者,此心之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也”。[8](529)也就是说,“敬”即是指良知本体的呈现,此时人心处于明觉状态纯乎天理而无私欲之杂。而“敬”的具体工夫,则是戒慎恐惧。这样一来,本体就与工夫合而为一了,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所以邹东廓认为,只要能戒慎恐惧,如出门使民、造次颠沛、参前倚衡等“无往非戒惧之流行”,则亦无往非性体之流行;如果离开戒慎恐惧,那么良知本体也就无从得见。故黄宗羲说:“吾性体行于日用伦物之中,不分动静,不舍昼夜,无有停机。流行之合宜处谓之善,其障蔽而壅塞处谓之不善。盖一忘戒惧则障蔽而壅塞矣,但令无往非戒惧之流行,即是性体之流行矣。离却戒慎恐惧,无从觅性;离却性,亦无从觅日用伦物也。”[1](332)
正是出于对“敬”的这种理解,邹东廓反对吕柟把“修己以敬”解释成“用敬”来修己,也就是主敬。因为对他来说,“修己以敬”就是以吾心之良知为主宰,所谓“心有主宰,便是敬,便是礼;心无主宰,便是不敬,便是非礼”。[8](504)只要能 “敬存于中”,自然就会温清定省、出告返面、出入扶持,“以之格物而物格,以之致知而知致,以之诚意而意诚”,故工夫只是一个“敬”,亦即戒慎恐惧。但吕柟则指出,这种说法固然很好,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心未必能纯乎天理而无私欲之杂,其良知也未必能时时发用流行,既然如此,就不能把“敬”理解为良知在主宰,就必须还要有格物穷理、诚意正心等工夫,因而吕柟坚持“修己以敬”就是“用敬修己”或“以敬修己”,认为“修”字中还有许多工夫。他说:“亦须知得何者天理,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惧个甚么? ”[3](146)当然,吕柟与邹东廓之间的辩论结果可想而知,谁也没有说服谁,正如吕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的那样:“东郭持守师说,牢不可破,近与屡辩之,殆少然诺,恐亦未肯尽从也。”[7]
从以上吕柟与邹东廓关于知行先后、格物穷理与“修己以敬”等问题的辩论来看,吕柟并非不了解阳明心学的理论,而是认为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王阳明或邹东廓讲的那样,他说:
子敢以阳明之学为是乎? 子敢以阳明之学为不是乎? ……昔先正以一言一字发人,而况阳明之学痛世俗词章之烦,病世途势利之争,乃穷本究源,因近及远,而曰行即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尝不是乎? 但人品不同,受病亦异,好内者不可与言禁酒也,好奕者不可与言禁财也。……若曰见守齐举,知行并进,此惟圣人能。故阳明之学,中人以上虽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无所归,故《论语》不道也,亦何尝尽是乎? 虽然,自夫俗儒而言,忘其良知而又不知以行之为急也,其弊至于戕民而病国,则阳明之学又岂可少乎哉?[9]
可见在吕柟看来,王阳明提倡良知学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世俗只注重词章、举业之学而不重视身心性命的风气无疑是一种补偏救弊之举。然而,阳明之学终究只适合于中人以上,而不适用于中人以下,因为“人之资质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学问有浅深,不可概以此语之”[3](121);否则,其言论“未免使后生废学”。[7]这既可以说是吕柟对阳明学的一个总的评价,同时也是其学问的根本主张所在。
四、结语
吕柟对阳明学的批评与拒绝在当时的关中地区及其友人之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如,被冯从吾称为与吕柟“司马金石相宜,钧天并奏”且为一生至交的另一位关中学者马理(谿田,1474~1555)就将阳明学斥之为“曹溪余裔”,[10]认为是阳儒阴释,危害甚大。而被关中学者视为得吕柟之传的泾阳(在今陕西)吕潜(槐轩,1517~1578),则“凡一言一动,率以泾野为法”;[2](55)吕柟的另一个弟子杨应诏(号天游),也“于心斋、龙溪,为阳明之学者,皆有微疵”。[1](155)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思想氛围之中,当时风行于大江以南的阳明学,虽历经嘉、隆两朝,却终未在关中地区取得思想主流的地位。虽然这一时期,有南大吉(瑞泉,1487~1541)、南逢吉(姜泉,1494~1574)兄弟在渭南宣传良知学,但其范围也仅限于渭南一地,且影响远不及吕柟、马理等人。这一状况的改变,则要等到万历中冯从吾在关中书院的讲学。
[1] 黄宗羲. 明儒学案(修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 冯从吾. 关学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 吕柟. 泾野子内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4] 薛应旂. 方山薛先生全集[M]. 续修四库全书, 第1343册.
[5] 宋仪望. 华阳馆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116册.
[6]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7] 吕柟. 泾野先生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61册.
[8] 邹守益. 邹守益集[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9] 邓球. 皇明泳化类编[M]. 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 第27册.
[10] 马理. 谿田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69册.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sixteenth century, Lu Nan as the most famous schoolar in Guanzhong district still adhered to Cheng-chu theory when facing the impacts of Yang-ming’s doctrine. He had quite heated argument with the yang-ming followers in many spheres, such as the teaching method, the relationship of knowing and doing, and so on.The criticism and refusal from Lu Nan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other Guanzhong’s scholars and effectively rejected the spread of Yang-ming philosophy in Guanzhong district, making it unable to achieve the mainstream of Guanzhong’s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Lu Nan;Yang-ming’s doctrine;Cheng-chu theory;Guanzhong district;Guanzhong’s Neo-Confucianism
Lu Nan and Yangming’s Doctrine
MI Wenke
(Philosophy Depart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B248.99
A
1672-3104(2011)02−0043−05
2010−11−08
米文科(1978−),男,山西汾阳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哲学思想.
[编辑: 颜关明]
——兼与朱子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