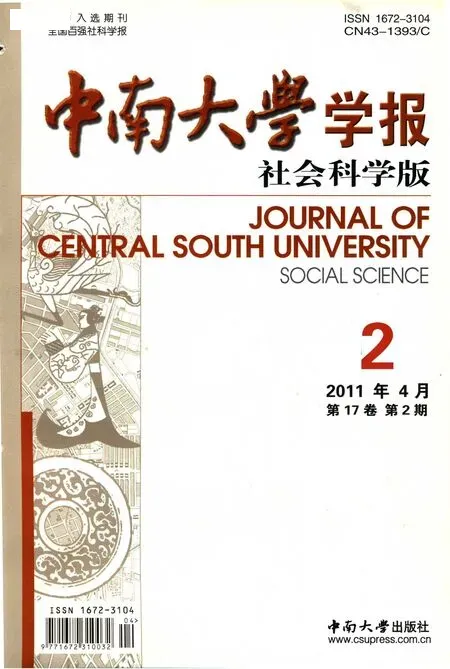从祭祀乐到雅乐
——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文化意蕴
刘书惠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从祭祀乐到雅乐
——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文化意蕴
刘书惠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在初始时期“乐”主要以“祭祀乐”的形态呈现,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情感。随着文化氛围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乐”更多的以“礼乐一体”的面貌存在。为了保持“乐”的独立性并提升其价值,儒家在“制礼作乐”的基础上将“祭祀乐”转化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雅乐”,“乐”便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相连,体现出儒家“乐教”理性与神性杂糅的特点。
乐教;祭祀乐;雅乐;礼乐一体;先秦儒家;理性与神性
音乐在原始宗教仪式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沟通天人的工具它将由外物映射至人内心而引起的各种情绪与想象,并同神话思维、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深层心理感受融为一体,以韵律节拍的形式抒发出来。音乐的出现证实了人们有表达情感的需要及驾驭表现方式的能力,也说明了人类产生了在精神上实现神圣连接的渴望。“乐教”是先秦儒家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它以充分展现情感又极具原始神秘色彩的“乐”为手段,通过达至心灵的美感触动和驯化民情的教育来实现自己掌邦国施教化的职责。先秦儒家对音乐原始文化意蕴的深刻认知,对积极运用音乐感化心灵的强调,对音乐社会价值的格外肯定,是其他先秦诸子所不能比肩的,正是先秦儒家对“乐”独有的敏感性,促使系统的“乐教”理论形成。
历代学人主要关注的是儒家“乐教”的社会意义及教育功能,而对其源起和文化涵义的研究则稍显单薄。实际上,要真正了解先秦儒家的乐教观,必须从它对“乐”的原始文化意蕴的同向认知谈起,透析其“乐教”主张中蕴藏的原始神话−宗教思维,与伦理价值观结合观察,并辨明其自身对“乐”的态度转变,这样才能展现出先秦儒家思想历程的发展演化,从而了解先秦儒家“乐教”的真正含义。
一、祭祀乐:儒家首重之乐
先秦时期,“乐”是一种集歌唱、舞蹈、奏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形式。正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吕氏春秋·古乐》)。乐的本原面貌是如此灵动多姿,与之相应,从古至今人们对“乐”之起源亦有各种推测,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劳动,“劳动实践本身,给予音乐以内容。劳动的动作和呼声,给予音乐与舞蹈以节奏和音调。”[1](2)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模仿,风摇水激编织出第一首欢快的歌;有人认为音乐起源于人类抒发内心情感的动物本能;亦有人认为音乐的产生与巫术活动密切相关,王国维于《宋元戏曲考》中直接叹问“歌舞之兴,其起于古之巫术乎”? “乐”之起源如此众说纷纭,不仅与社会发展水平、科学知识掌控程度的变化相应,与立论扬说者的知识背景及认知角度相关,更与“乐”这一名称指代的概念范围息息相连。从广义来讲,凡是具有节奏的音调组合均可称之为“乐”,那么以上诸说则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从先秦儒家视角考察,其所认同的乐不但要有综合性的表演形式,更是一种超于人间、凝结宇宙力量的神异存在,它既是伦理现实的,又是威严神秘的。由此,先秦儒家接受和推广的音乐并非普泛意义上的乐舞,而是受人们敬奉和信仰的祭祀乐。
从综合表现力上讲,祭祀乐作为娱悦祖魂神灵的有效方式及祭祀仪典中烘托氛围表达情绪的工具,为了辅助祭祀仪式实现连接天人、上传下达的预定功能,它必须有足够的活力与感召力,尽可能地引起内心的情感认同唤醒肃穆的神秘感,而仅用音阶变化来刺激听觉是无法完全激发人类激情的。由此,诗、乐、舞三位一体的音乐表现形式以相互配合、彼此需要的成熟形态出现在祭祀活动中,全方位地触动人类感官,不但唤起人们对于表达的强烈渴望,而且将人类的宗教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祭祀对于狂热的需要,先民沟通人神、表达情感的向往,共同激发了祭祀乐的产生,而祭祀乐的综合形态也将先秦古乐塑造得更为立体。
从发生机制上讲,乐舞的节奏和韵律是震撼人心的节拍被不断重复而引发的感受,先民将这种感受与神的喻示联系起来,希翼以声音和肢体的表达将自己的心境传达给神灵,从而实现人与神的通感。在祭祀仪式中,乐是人类达到超验心境,与宇宙天地、祖先神灵实现精神契合的前期准备和必要手段。“乐感天人”“乐通天地”“乐通鬼神”不只是先民潜在的心理需求,更是一种执著而强烈的信仰。天人之间的感应系统一旦通过乐舞建立,那么人们对于乐声的认知就不仅限于生理上的反映,而是又将其内化为精神意识的一部分,用以引导灵魂与鬼神的接续,并抒发宗教情感。人们“在祭祀乐舞这类艺术化了的形式中,证实了自己的所知所感,精神意识的东西与乐舞的表演、音声的感荡相互融合、共鸣,从而达到情与理、心与声、现实与非现实的统一”。[2](44)同时代的先秦儒者其心理机制亦与之相类,虽然孔孟之说有较强的伦理性和思辨性,但祈求“神人合一”的虔诚仍深植内心,在他们看来祭祀乐抒发的是一种宗教情感,是精神寄托与现实请求的象征,因此先秦儒家对此类音乐十分重视,更从神道设教出发,在强调乐之关键性的同时为自己的乐教理论找到一个神圣的来源,希望将原本灵活的心理体验仪式化、固定化,以理论的而非宗教的形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从文化背景上看,胡适先生曾在《说儒》篇中指出孔子时有所谓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小人儒”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3](183)“当时的儒者是各种方面的教师与顾问。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3](192)正是反复地观察乐舞表演,甚至长时间主持祭祀乐舞活动,才使得先秦儒者对于“乐”的性质有如此深刻的体验,并由衷地认同乐与祭祀、神、巫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儒家视野下,祭祀乐是完整乐舞的开端,这是因为早期阶段较有规模的乐舞均在祭祀仪式中表演。在形式上它满足了表达情感、配合仪式行为的需要,在实质上它实现了献媚祖先、愉悦神灵的功能,体现了整个祭祀活动的主旨与核心。在乐以娱神的神话观的影响下,尊崇乐声沟通鬼神、天地的作用,成为先秦儒家音乐文化意识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在儒家学说体系中,“乐”的神圣性与功能性始终如一,但其宗教性和神秘性却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掩藏于社会性与伦理性之下。从祭祀仪典中走出的“乐”虽不至于被彻底消灭,却改头换面,较少以祭祀乐的形态出现,而是通过与“礼”的相互交缠,以礼乐一体的面貌存在。
二、礼乐一体:乐的存在方式
祭祀乐肇始远古,而“按照《说文解字》的‘事神致福’的定义和王国维《释礼》的解释,则有祭献之事时就已经有礼存在。无论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来看,所谓礼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4](23)则“乐”与“礼”皆起源久远,又均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因此二者因时因势而关联,从不同角度审视会发现“礼”与“乐”的交错始终如一。
1. 从概念的涵盖面讲,礼包含乐,乐曲的演奏、乐舞的表演是礼仪、礼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乐”以节拍、韵律的形式抒发情感、表达意义,作为“礼”的辅助,为礼典的举行营造氛围与环境。又“乐的活动及其方式,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反映了礼的等级规范与观念。”[2](52)
2. 从礼与乐的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上讲,礼与乐是平级相交的关系,二者利用不同角度和方法规范疏导人们的行为,养成儒家期望的心理结构。“礼”是通过仪典与等级的差异而辨别确认行礼者的身份,并以此引导其行为走向,“乐”则是通过触动人的情感而净化灵魂,将生发于外的五声八音导入内心转化为自我约束、自我提升的内在要求。正如《礼记·文王世子》所言:“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乐”与“礼”内外共举,相互配合,密无间隙。
3. 从宣泄人的情感意识、塑造心境的功能上讲,礼乐是一体的。在祭祀仪典这类神圣氛围中,以“礼”规行的同时,“乐”感心灵,“礼”内化为“乐”,触动人的神经,“乐”外化为“礼”,以有节有度的方式表达情感心理。因此,“从宽泛意义上讲‘乐’就是所谓的‘礼’,原始乐舞的本质意义是宗教的神迷的狂热情感表达与象征,因此在远古的祭祀活动中乐与仪式一词代表的意义相同,它以歌唱、曲调、舞蹈的形式演绎了礼,与仪礼融为一体。”[4](25)“乐”与“礼”一开始就统一于原始先民的祭祀仪式中。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乐”与“礼”始终交缠,即便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乐舞与礼仪也保持着密切关联,无论是祭祀、庆典、飨宴还是出入迎送,都是乐舞与礼仪联袂表演的场合与时机。“乐”与“礼”作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在执行仪典的过程中彼此配合、相互包容,“礼乐一体”成为它们的存在方式,更使它们的价值得以体现。
随着“礼”政教工具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其宗教意味甚浓的原始意义渐变为其内涵的一个分支而隐性弱化。“乐”的性质也发生变化,人们更加重视其娱乐价值与社会性,得以张扬的是它的现世意义。而睿智的先秦儒者在高扬伦理的同时,又以礼乐并举传承了远古时期祭祀乐与祭祀礼合二为一的精神。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成功地以乐行教不能忽略乐的宗教性来源,亦不能将乐与礼单独抽离,只强调其神秘的通感的力量而忽视其伦理规范的能力,于是,儒家将“祭祀乐”转化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雅乐”,这既是礼乐一体的伸张又是礼乐一体的遗迹。这一转换的成功,不但为儒家乐教的实施提供了神圣的来源和坚实的材料基础,亦引导了中国音乐的分层。
三、雅乐:乐的衍生
在先秦儒者看来,最庄重、内涵最丰富的音乐就是在祭祀仪典上反复奏响的祭祀乐,于是在周初“制礼作乐”的基础上,儒家对祭祀乐进一步扩展,从中引申出一种在内容与形式上承袭祭祀乐,并兼采前代所传古乐,主要用于各种仪典宴会场合的典雅纯正的音乐——雅乐。可以说是儒家对“礼乐一体”的认同刺激了雅乐的诞生,使“雅乐”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兼具祭祀乐与政教乐的作用,以一个更宽泛的含义代替了“祭祀乐”在儒者心目中的地位。其“表演的目的是表达君子的志向、称颂先王之道、修身养性、和睦家庭、治国平天下,故又推崇之为‘德音’。”[5](23)雅乐源于祭祀乐,却又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变化,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联系更为紧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为代表的“俗乐”兴盛起来,并依靠其鲜活的生命力与表现力保持着与“雅乐”相争的态势。俗乐短小精悍、旋律性强、力求愉悦心情而无需顾及教化价值的特点,使其风头始终保持强劲,从而让儒家推进雅乐的进程显得步履维艰。面对“俗乐”与“雅乐”的相较相争,先秦儒者对“俗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最初坚决抵制、极力排斥,“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傲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乐记》);其后逐渐承认甚至接受“俗乐”的存在,“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孟子·梁惠王下》)。先秦儒家音乐思想在情与理、教化与享乐的挣扎中不断变化。可以说面对音乐世俗化的快速发展,先秦儒者已无力回天,他们不再希求完全摒除“俗乐”,而是在“雅”与“俗”中寻找制衡点,在给“俗乐”留下生存空间的同时,力求将“雅乐”发扬光大。其积极宣传和造势的努力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身体力行。儒家先圣孔子精通乐器、乐理,“学鼓琴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语鲁大师乐”(《论语·八佾》),“闻弦歌之声”(《论语•阳货》),知政教民生,他凭借自身良好的音乐素养对雅乐进行了一番整理,正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在教学中孔子更是反复强调雅乐在育人化心方面的重要性,广泛推行其乐教观,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将谙习雅乐看做是修身立业达于最高阶段的标志。而《荀子·乐论》及先秦儒家音乐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乐记》都是承孔门乐教精神而来,均表现出对雅乐的高度推崇。
其二,倡导雅乐的下移。战国时期是雅乐与俗乐真正交融的时期,宫廷的雅乐下移与俗乐结合,同时,民间的音乐继续自身的发展,并且传至宫廷。这种结合可以防止俗乐的势力过度发展将雅乐全盘颠覆,而用一种折中的方式存留雅乐。雅乐的下移是历史的必然,儒家倡导“雅”“俗”结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二合一的产物不能保有雅乐的全部特征,但这总好于毫无孑遗,至少为雅乐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其三,形成一套完整的“乐教”理论,以“雅乐”的伦理化和政教化制止世俗化。雅乐得以依存的“礼乐文化”基础在先秦社会变革中逐渐崩塌,因缺少广泛的文化认同,雅乐的继续存在变得十分艰难。为应对此种情况,先秦儒家坚持以“雅乐”为教育工具,使其功能与精神通过“乐教”的方式保存。《荀子·乐论》所谓:“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乐记》亦谓:“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即表明了儒家施教以雅乐导人向善的初衷和目的。儒家“乐教”升华了雅乐的意义,使得社会结构中但凡有礼仪与教化的存在就留有雅乐的空间,“雅乐”不仅仅是在盛大场合演奏的庄严隆重的乐曲,更是具有极大社会意义与教育价值的社会存在。可以说乐教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是先秦儒家为推行雅乐所做的最有成效的工作。
先秦儒者对雅乐的追求与推崇,从审美角度讲,与祭祀乐在其心中设定的期望值相符,在他们看来雅乐的美感就是来自于祭典音乐的延续和发展;从功利角度讲,雅乐的存在亦符合儒家神道设教的实施,雅乐活动作为一种基本教化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心理。总之,“雅乐”产生之后,“乐”便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紧密相连,除了作为娱神的工具外,“乐”又具有了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乐教”理论便在这一基础上经由现实的刺激而产生。
四、乐教:理性与神性的杂糅
先秦儒者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他们受原始文化与神话思维影响,却不及墨家那般的宗教狂热,他们的政治理性最先觉醒亦是倡导道德规范的先驱,却又受制于天命。《墨子·公孟》:“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胡适据此分析说:“(孟子)这个人正是儒家的绝好代表:他一面维持他的严格的理智态度,一面还不能抛弃那传统的祭祀职业。”[3](232)先秦儒家的这种天人交战牵涉到政治、修身、为学的各个方面。而以雅乐为基础的“乐教”理论的问世,就真切体现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理性与神性——神话思维的矛盾交缠。
从理性方面说,首先,“乐”是“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的产物,人类有所感即有所发,正所谓“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礼记·乐记》)乐因此而成为表达人类认知、抒发喜怒哀乐的有效工具。乐的效力如此之大,即便是先王亦要“慎所以感之者”,那么尊王崇圣的儒家学者自然会对其格外重视。其次,社会对人的外在规范要求需用礼来展现,礼又通过“乐”传达于心,外在与内在产生共鸣,人们自然会获得与乐营造的氛围类似的心境,心与物和谐安悦的关系自然呈现,儒家学说得以推行的心理条件由此形成。再者,先秦儒者在长期以乐化人的实践活动中体验到雅乐的曲调庄严肃穆、节拍较为缓慢且变律不大,这样的旋律很适合调节人们的行为,使其根据节奏进退行礼,举手投足间庄重感油然而现,儒家学说得以推行的行为条件也由此形成。因此,以雅乐行教对肯定理性、追求实际价值和现世意义的儒家来说,是其学说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从受神话思维的影响来说,乐教是一种神话−宗教思想发展的结果,它是祭祀仪式中“乐”这一因素与条件的升华与理论化。“儒家在长期的乐教实践活动中,运用意义联想与创造想象感知天地万物,把自己的人格比附、移注、渗透、投射到无生命外物,赋予外物以人的主观思想意识和道德感情色彩,进而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同一的效果。”[6](80)灵魂中蒙昧的、神秘的、神话的那部分时刻提醒着先秦儒者:乐的最大价值在于娱乐神灵、沟通人神、物我浑融。先秦儒者在知识上虽高于平民,但他们与普通民众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对于乐有相同的期望值和价值观,他们承认乐有神性、能够讨好神灵,对乐有功利的希冀,认为在合适的时机奏正确的乐能够带来好处。这是先秦儒者的思想根基,也是乐教立论的基础。也正是如此,民众才愿意认同雅乐的与众不同,从而接受儒家提倡的乐教。
总的说来,先秦儒家推行乐教“就是要驯化民之情性而使之和顺。而要达到使民内和外顺的教化目的,就必须以‘五礼’、‘六乐’去实施教化,以乐辅礼、以乐施教。《周礼·地官》所言‘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本质上是针对人心的改造、教化而言的,是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乐为辅助手段,乐教的道德教育内容与情感教育内容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以乐教和’的目的。”[2](49)儒家将从祭祀乐中发展出的雅乐作为乐教的主旋律,从本质上讲正是将祭祀乐曲从神圣的殿堂拉下来,融入社会生活,从而变成能与民进行精神沟通并实现教化的有效手段。
[1] 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 修海林.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3] 胡适. 说儒[A]. 载庞朴等编. 先秦儒家研究[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 张立文主编, 陆玉林著. 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 谭钟琪.《乐记》与中国古代的乐教[J]. 社会科学家, 2005, (3):123.
[6] 张建.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探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 80.
Abstract:Confucian school in pre-Qin dynasty held that Music originates sacrifice ceremony was presented as Sacrifice Music at the beginning, and expressed a kind of religional emotion. With the changing of culture atmospher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Music exists more as a form of Combining Li and Music. In order to keep the independency of Music and improve its value, Confucian school transformed Sacrifice Music into Elegent Music which meets more the need of the time based on Making Li and Playing Music, thus, Music was connected to social moral principles and moral education, which shows a character of combining the rationality and divinity in Mu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Musical Educatio; Sacrifice Music; Elegent Music; Combining Li and Music; Confucian school in pre-Qin dynasty; rationality and divinity
From Sacrifice Music to Elegent Music——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in the Music Educational tradition of Confucian school in Pre-Qin dynasty
LIU Shuhui
(Literary College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I206.2
A
1672-3104(2011)02−0039−04
2010−11−26;
2011−03−08
刘书惠(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