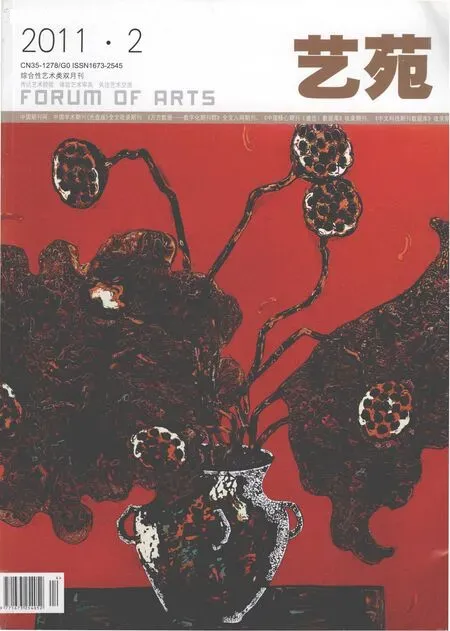计算不了的爱情——评《情话紫钗》的情境悖论
文/霍小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观众到剧场是为了娱乐,但在离开剧场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带走了激发出来的,由于认识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丰富起来的情感和思想。”[1](P90)能给观众这样感觉的戏在目前的中国剧坛并不多见。笔者初见香港导演毛俊辉的戏剧《情话紫钗》,却是报了这样的期望的。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剧场里反复看了两遍,饱飨一份视觉听觉盛宴的同时,却始终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未满足感,或者说是一种遗憾。那是什么呢?
重新结构经典剧本,或者是寻找一种改变原剧本的环境、风格和美学关系来对其重新进行诠释,对毛俊辉来说并不陌生。毛俊辉说:“《情话紫钗》就是从粤剧《紫钗记》着手,想想现代人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

《紫钗记》
一众现代男女在解读唐涤生的《紫钗记》。一段古典的李益(林锦堂)和霍小玉(胡美仪)的“堕钗灯影”,带出了谢君豪(现代李益)与何超仪(现代霍小玉)的相遇,继而展开一场互相追逐、试探的爱情游戏。
谢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把持不定,无力抗拒第三者;何悲伤激动,仿佛经历到古代霍小玉向黄衫客哭诉的“花前遇侠”片段。现代黄衣人出现,带着何去采访变幻无穷的痴男怨女,令她重新反思自身的爱情观。古代李益与古代霍小玉再出现于“剑合钗圆”的片段,两人的真诚相爱令人荡气回肠。
何与谢摊牌,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终赢得男子的真情剖白。一众现代男女继续为《紫钗记》寻找答案,最后集体演绎出他们心目中现代霍李的大结局。
古典跟现代的对话、揉合或者对照,从来难度甚高。因为,古典之所以是“古”代的经“典”,因为它生长在一个跟现代不同的时空,那个时空具备的是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因之形成的人伦关系和文化观念。这些具体条件和观念,又形成一些限制或者助力,使得当时的剧作家(在这里尤指古典戏曲的作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创造一个有意味的生活情境鲜明凝练的形象。现代人擅长的是用理论的概念来思维,既记录事物的个别表现形式,也展示事物的一般特性,而在寻找使剧作能够具体使用可触知形式来应付世界的知觉模式方面则略逊一些——这就使得剧作要强调与阐释的特殊主题呈现出一种无实体的透明性——诉诸于一般观众就是一种言之凿凿却又空泛乏力的空洞感。这一点在这部“看起来”不错的《情话紫钗》里,表现的也相当明显。
就具体的剧情分析,《情话紫钗》表现为以下几个不对称,正是这些不对称让我们体会到它带给观众的不满足感。首先在古今《紫钗记》人物关系上的不对称。唐涤生的《紫钗记》,虽然背景是比较开放的唐朝,一般女性到底难于经济上独立,本是“洛阳贵冑”的霍小玉才会有“自觉辛酸自惭被贬花,破落那堪共郎话”的悲叹,而李益才会自豪地说:“休说被贬花,他朝托夫婿名望,终有日吐扬眉话。”也因为丈夫变心的事从来多有,霍小玉即使真的被李益抛弃也无可奈何,汤显祖乃至唐涤生才会创作出一个行侠仗义的黄衫客,由他来为小玉出头,要杀尽世间负义之人﹗即是说,在男女经济力量不对等的时候,爱情本就沾染了社会地位高低的气息。所以,《紫钗记》中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其实不是霍小玉,而是李益。当一般男子都容易见异思迁的时候,他是怎样坚守信诺的?唐涤生创作出的“吞钗拒婚”成为全剧非常动人的一场,它对刻划人物非常重要:抒情性的语言、舞蹈化的动作、传统戏曲缠绵哀婉的音乐——由此出发,一种幻化的景象在观众的意识流中漂浮,使他们形成一种纯粹相信的直觉。
同样道理,《情话紫钗》中,与古典对照的一对现代男女,是怎样发生爱情的?又是如何捍卫爱情的呢?Kelvin (谢君豪饰)说:“我们在这个不清不楚的现代世界生活,你为什么要学人讲清楚的爱情?”这是很重要的自嘲或者反省。而吊诡的是,他和Jade (何超仪饰) 的爱情,虽然在著名剧作家庄文强、麦兆辉的仔细安排下,有拾手提电话、互诉款曲、互相欣赏等与《紫钗记》可以相呼应的布置,但是,由于在角色之间的交流方面着墨不深,考验也不够,就不容易令人信服他俩之间真的可以“讲爱情”。究竟Kelvin(谢君豪饰)爱Jade(何超仪饰)的什么呢?也许这是一种感觉。即便如此,戏剧家们也没有在舞台上让我们相信这份感觉浓烈到他们足以相爱了。他是在哪个骨节眼上开始爱上她的?依演出所见,实在有些含糊。
然后“黄衣人”出场了,从他全身金黄色的造型引来笑声开始,这一段戏的调子都是喜剧,刚好与“花前遇侠”的伤感背道而驰。“黄衣人”是蓝钻级保险经纪,专门推销“爱情保险”,直接地把人际关系化为风险和金钱的数式。“爱情保险”这桥段其实已有电视剧用过,已不算太创新,在这剧里设计为负心人心中有愧,藉保险金向被辜负的前度爱人补偿的方法,描述细节的部分引来观众不少笑声,也可以算得上是剧本结构上的计算。但这跟霍小玉的关系有多大呢?“黄衣人”作为保险经纪,虽然自白只是“想帮人”,但对这行业来说,结识多些人总有潜在的好处。于是这一场戏的设计,以“爱情保险”又展示了“功利的爱情”多一个向度,换来了观众的笑声,却失却了“侠”的元素。抑或是,“黄衣人”带Jade重访他两起个案,看到现代男女关系中的疏离、沉闷、失望和无奈等等面相,然后指出Jade需要在他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那么他最少成为了Jade的指路人。然而她后来反省了什么?如何从别人的故事中更加认识自己?演出中却没有交待,就直接让她在会议室中、众人眼前向Kelvin说“我爱你”。缺少了内心转变的铺陈,她勇敢示爱,“论理争夫”的举措便减少了说服力和感染力。
作为《紫钗记》第三者卢燕贞现代对照的富家女Sophie (马沛诗饰),在戏中有一句这样的台词:“我们都不懂得去爱﹗”对于如今不少是独生子女的当代青年而言,这句话无异于当头棒喝。因此,Jade在会议中公开表白对Kelvin的爱,或许正是这年轻一代要学习怎样去爱人的开始。爱,就从承诺开始,从学习怎样实践承诺开始。戏的这个安排本来很好,可是,由于随后Kelvin和Jade之间基本上只是以独白 (或者电话) 沟通,虽然谢君豪、何超仪在这方面的演绎很好,念白很有感情。但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既然不足,情节的推进就不免嫌单薄了。
这就不得不说到另一种不对称了。《情话紫钗》一剧以“情话”为主,多是高密度“精警”的语言对白构成;而在《紫钗记》里,角色直接唱出心中的爱慕、哀伤、悲愤、欢喜等等情感。例如“花前遇侠”一段,霍小玉的夫婿李益发配塞外,三年来音信全无。后来她误信李益已被卢太尉招入府中为婿,感被抛弃,悲痛中偶遇豪侠“黄衫客”,唱到“恨檀郎从无鸿雁寄我半只字,空听泣雁过声……日也孤清清,我夜也孤清清,去后我旦夕顾影独对那药灶悲家空物剩,身外物典将清,忍听妈妈泣怨声。”[2]配合演员的神情和姿态,悲从中来的感觉令观众也唏嘘不已。
所以大部分第一次观看粤剧的观众也不觉得这部戏里占据一半分量的粤剧陌生难懂,相反大有一见倾心之感。笔者认为这来自于戏曲经典的充满活力的具象性。有时候可以把经典或者杰作跟二流作品粗陋枯燥无味的特性区别开来,就是因为二流作品不足以超越它所呈现的特定状况,而杰作则涵盖了从感官直觉到经过提炼的思想这一类经验的整个范围。
剧中现代人的部分,处理方法却很不同。剧作者除了编写现代版本的霍小玉Jade和现代李益Kelvin的故事,还有五位“现代男女”以“生活化”的方式谈论与爱情相关的问题,穿插在整出剧之中。古今《紫钗记》似是他们谈论和观赏的对象,也是思考爱情的媒介。至于现代版本的《紫钗记》,一方面要表现现代人的计算,一方面又要让主角们在相互关系中角力拉扯,其风格像电视剧《壹号皇庭》和《妙手仁心》,由高密度的“精警”对白构成,时而含蓄时而直接地谈情说爱——如何看对方、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待关系——“情话”更多是有关爱情的思考和对话,而不是情感的表达。于是“感情”对于剧中人应是切身的,有时却好像是抽离的,他们需要一段距离才能看清楚自己与对方,观众则是看到迷迷糊糊。
剧中还有一处不对称值得留意,即古、今霍小玉的服装设计,这关系到情感表达和整体情绪的营造。《紫钗记》选段的视觉元素和演绎都简化了,看来没那么华丽丰富,减少了演员的造手等肢体动作,服装也更现代化,叶锦添将霍小玉的戏服都设计成大红大白的,强烈地表达她的情绪变化。当她与李益初遇,从头到脚的鲜红衬托她的心花怒放;后来忧心遭丈失抛弃,则大半是白,只有裙摆留下一圈红;到“花前遇合”之时,霍小玉一身惨白,头发渐散,已是接近歇斯底里的悲痛;最后李益归来,花好月圆,容貌端庄,一身浓重的深红,平静的幸福满满像是要溢出来。比较现代部分,现代版霍小玉——Jade在整出剧里一直是一身艳红。即使在现代版的“花前遇侠”部分,她和Kelvin争吵过后,应该是很伤心低落的,因为她知道双方都没勇气为爱情牺牲更多,但内心的挣扎却显出他们还未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也不能作出抉择——这里Jade鲜红的套装和她的愁伤和躁动并不配合。
可以说古装《紫钗记》的情绪是纵向的、大起大落的;而现代版走向广处,以不同的片段和面向展现“计算”和“功利”如何影响爱情。问题在于,现代《紫钗记》里的感情成了角色间谈论甚至谈判的客体,多用脑袋少用心,“精警”对白密度太高,正反映了编剧也处处“计算”着,心机有余,感动不足。虽然这正好配合“现代人充满计算”的基调,但剧作者的意图是否只此而已?若只是为了古今对比,现代部分大可更残忍一点,让Kelvin与Jade真心告白后,仍然留在财团太子女Sophie身边,彻底地放下真爱,蒙蔽真我去追逐名利和欲望。但现在是大团圆结局,导演安排古代霍小玉和李益在舞台后方,以欣慰的眼光看着台中要爱情不要黄金的Kelvin和Jade经过,像爱情路上的老前辈。导演的创作的意图很显然是想让当代人从古典里学习,学习如何找回自己的情感,继而懂得如何去爱。爱是一种能力,只不过被遗忘了罢了。然而这种学习须从脑袋(计算)和口(调情/谈判)转移到心(感受/激情)的运用和释放,最好就是让现代角色的感情抒发以“唱情”或其他方式打动观众。以精心算计的对白和角色设计来批评计算功利的现代人心态,可算是一种反身性的失误和讽刺。
[1]郑雪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导演与表演[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2]见《情话紫钗》演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