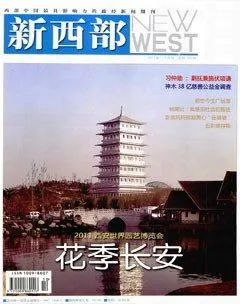村
长安塔高高矗立,黄邓村渐渐远去。一个历史悠久的“革命村”、“文化村”,因为世园会的举行,不得不接受整体搬迁的现实。村史记录者陈来忠老人说,这是黄邓村历史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我觉得每一位搬迁的村民,都应该记在村史上。”
“黄邓村的先祖先辈們:你們的业绩功载千秋;你們的教诲铭记心头;你們的德范名垂青史;你們的浩气万古芳流……”
2010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西安阴云低沉,天空将雨。在黄邓村的祭祖大会上,当村支书刘天军读到这几句祭文时,台下有位叫陈来忠的老者不住打量着祭台后面的一片坟地,心情复杂。
2011年的西安世园会,全世界都会把目光投向广运潭,而距离广运潭几百米的黄邓村却要搬迁了。村上几位老人和村干部经过商量,在搬迁之前举行了这个祭奠祖先的仪式,陈来忠成为起草祭文的参与者之一。
如今,在长安塔下,黄邓村正在渐渐远去,但对陈来忠来说,家乡将成为永远的记忆,包括过去二百多年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故事。
消失的不仅是村庄
2011年3月9日,记者走进世园园区,找到了黄邓村所在的地方。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整个黄邓村已是一片瓦砾之地。几个泾阳县来的农民正在将楼房废墟里能用的砖头装进旁边的农用车里准备拉走,一位老大妈则在捡拾着一根根或长或短的铁丝,说是要卖废品。
村子北头的门楼尚未拆除,透过门楼往南看,不远处高高矗立的长安塔清晰可见。捡铁丝的老大妈告诉记者,门楼是黄邓村原来的大门,几年前才新修的。门楼旁边有一块石碑,记录着黄邓村的历史。碑上的字迹虽有些斑驳,但内容仍可看清:黄邓村位于西安市灞桥北,距灞桥镇五公里……
陈来忠正是村史的起草者之一。
“这是村史的原稿,在我手里保存了十几年了,你拍照的时候小心点,别弄破了。”在位于灞桥区的西安市三十四中家属区,记者找到了陈来忠的家。不难看出,他对这份村史原稿很看重。
陈来忠是三十四中的退休教师,但更多时候,他是以身为黄邓村人而自豪的。
“滋水岸边,灞柳人家,黄邓村人历经沧桑,繁衍生息,在祖先留下的这块热土上,艰苦奋斗,创业发展,已二百余年。”村史中的一字一句,都寄托着陈来忠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据陈来忠介绍,黄邓村自建村以来,名人辈出,近代历史上还出过几位英雄:查明芳,黄邓村最早的革命先烈,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后被清政府处以绞刑:李濂,走出黄邓村的老红军,1924年投笔从戎,次年进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奔赴井冈山,据说经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生南北转战;刘焕礼,中共女交通员,当年在敌人重重包围下,Hd6Obo7KOHkkr1wTEBAJw4xyhmKjjVv5OatOXuPJVpI=经常与刘志丹设在三原县的联络站秘密联系,为红军购买枪支弹药,后被敌方杀害;华心诚,中共地下工作者,曾掩护红二十五军领导人郑位三北上延安,后在黄邓村创办“灞陵中学”,历任长安师范校长、陕西省教育学院教务长等职……
对于黄邓村的这些历史,陈来忠如数家珍。正因如此,当十几年前村上为整理村史、树碑立传的事情找到他时,他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这是光荣的事情,立了碑,黄邓村的历史就能保存下来。”
陈来忠告诉记者,撰写村史的工作,由他和同村人张寒暄一起完成。张寒暄写了较为详细的第一稿,他修改后成为定稿。
其实,黄邓村不仅是“革命村”,还是“文化村”。陈来忠翻开厚厚的《灞桥区志》,其中记载,解放初期,黄邓村一些爱好文艺的农村青年,自制道具、服装、布景,排练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于春节期间在各村上演,观众无数。“我就是演出队的,那时我才十四、五岁,我們到周围的村子去演出,不要钱,只要管饭就行,看的人多得很。”陈来忠说,黄邓村的“文化村”美誉就是那时传开的。
此后数十年,黄邓村的文化活动一直很活跃,其中锣鼓社火表演多次在区里得奖。去年拆迁之前,村里还有三支文艺队:秦腔自乐班、中老年腰鼓队和青年锣鼓秧歌队,队员总共有300多人。
作为“文化村”,黄邓村还一直保持着较为浓厚的尊师重教的风气。2005年,黄邓小学的老师为了学生們能上电脑课,便自凑工资,交付了购置电脑的订金。但是,电脑送来了,余下的钱学校无力支付,商家一直上门讨债。村民們闻知此事后也开始凑钱,这家50元,那家100元,帮学校还了欠款。
“村里考上大学的娃娃在外闯事业的不少,大部分是当老师。黄邓村走出去的老师教啥的都有,集合起来能办一所中学。”陈来忠说,村上对教育十分重视,每年都会奖励考上大学的学生,30多年来从未间断。
“为了世园会,黄邓村的拆迁是大势所趋。”陈来忠说,这也算是黄邓村人对国家的新贡献。但言谈之间,陈来忠也对黄邓村的消失流露出惋惜之情。村子没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形成的好传统就会被冲淡。今年春节,因为搬离村子的村民住的比较分散,村里坚持多年的锣鼓社火活动也没有举行。
这个“第一次”,让陈来忠感到很失落。
因为拆迁一夜致富
三十四中的对面有一家麻将馆,老板正是陈来忠的小儿子。
闲来无事,陈来忠就在麻将馆里帮儿子照看生意。在这里,他经常能遇见同村的乡党,有的还是与黄邓村相邻的香胡湾村的村民。陈来忠说,拆迁之后,这两个村的村民有的在外租房,有的直接买了房,有的投亲靠友,但大部分都住在灞桥附近。
在这些打牌娱乐的村民身上,陈来忠能明显感觉到拆迁给村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好多人都是开着小车来的,身上都装着几百元,谁要是输了也不在乎。”陈来忠说,以前村民們也爱打麻将,但都打得小,能买起小车的人也很少。去年8月拆迁之后到年底,黄邓村500多户村民,买了200多辆小车。
记者了解到,黄邓村和香胡湾村只要是持有农业户口的本村村民,每人都在拆迁中分到了12万元的现金和30平方米的安置房。村民的自建房,在扣除安置房面积后,也按照一定的标准(比如楼房一、二层每平方米500元)获得了赔偿。“差不多的人家都有百万元,有的甚至达到二百万元,最差的也几十万,还给分房子。”陈来忠认为,从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的角度考虑,拆迁确实是百年不遇的好事,一夜之间,村民們都富了起来。
陈来忠告诉记者,15年前,他从黄邓村搬到现在的学校家属楼里。在那之前,他在黄邓村先后建了两次房。
第一次是在1973年,当时农村的房子大多都是瓦房,土木结构。陈来忠说,那个年代,山里的木材禁止外售,他四处打问,才买齐了建房所需的木头。瓦是他雇人用马车从长安县拉回的。三间大瓦房建起来后,在村里显得很“新潮”,成为陈来忠光耀门楣的象征。
谁知,10多年后的一场大雨,让这三间瓦房变成了危房。陈来忠毅然拆掉房子,在原址又建起了两间宽的二层楼。“那还是1986年,二层楼在我們村很少见。”陈来忠又一次在村上引领了潮流。
从黄邓村搬离后,陈来忠将家里的房子留给了儿子。“大儿子的户口在村里,家里六分大的宅子,大儿子占了四分,余下的是小儿子的。”陈来忠说。
让陈来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們家第三次盖房竟然是为了拆迁而盖的。自从得知黄邓村被划入拆迁改造范围的消息,村民們为了得到更多赔偿款,都一窝蜂地开始加盖房子。陈来忠的两个儿子也像大家一样,将整个院子盖得满满当当。
而在陈来忠看来,随着拆迁的到来,黄邓村的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村史增添浓重一笔
“我三爷的坟在这儿。”“不对,不对,应该在这儿。”一个小型挖掘机旁站着十几个人,人堆里传出了并不激烈的争论声。
这是记者在香胡湾村迁坟现场看到的一幅景象。
香胡湾村与黄邓村隔着东三环,迁坟的地方正是香胡湾村之前的田地。村子拆迁后,田地也被征收,地头的祖坟,也要在施工之前被迁走。几位迁坟的村民因记不清坟堆的具体位置,发生了分歧。
据现场一位村民介绍,当地人去世之后,不管是土葬还是火化,一般都埋在自家的地头或者村上修建的陵园里。“黄邓村还没有开始迁坟,他們村的土地因价格原因还没被征收。”这位村民说。
这一说法得到陈来忠的证实,但他同时肯定地说,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多久。“村子拆迁之后,虽然地还没卖,但村民都知道自家的果树等不到下次开花结果,就会被砍掉了。”
拆迁之前,黄邓村村民大多靠种植猕猴桃、葡萄等经济作物为生。陈来忠说,以前村民为了方便管理,都在自家地里建了简易的房子,有时就吃住在地里。果树如果照看得好,一户人家一年能收入几万元。每年秋季,地里的果子成熟后,都会吸引不少城里的市民前来采摘,“农家乐”成了村里的特色产业。
“现在地虽然还没卖,你看谁还去经管果树?”陈来忠说。
陈来忠的大儿子当然也不会再去管那些果树了。村子搬迁后,他把心思全部放在了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身上。“土地是个金盆盆,我的儿子們以前还能靠土地生活,可到了孙子們,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以后还怎样在社会上立足?”陈来忠对儿子的做法表示了完全的理解。
黄邓村消失了,但黄邓村的历史还将延续。陈来忠说,黄邓村拆迁无疑是村史上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我觉得每一位搬迁的村民,都应该记在村史上。”
陈来忠在给村上祭祖大会的祭文中这样写道:“二零一一年世园会召开在即,黄邓人深明大义,做出了整村搬迁的抉择,为世园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相信列祖列宗一定会支持子孙的这一义举!”
这些文字,已经被刻在一块石碑上,代表着黄邓村全体村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