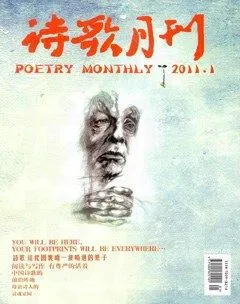东东的诗(8首)
魔术
你所见的一切并非真实
魔术师的手凌空向我抓来
我屏住呼吸仿佛他正
握着一条丝丝作响的蛇
这场景让我想起那年早晨
一队威猛雄壮的士兵
走过我家门口我指着黑魆魆的
枪管说我要我要我要
母亲小声说小心被他们带走
魔术师忽然转过身去面对观众
手中凭空多了一枚绿色纽扣
它被小心地安放在我胸口
好像它一直都在那里
我松了一口气
魔术师忽然对着观众高声说
看看你们的胸前
大家恍然大悟中低下头
每个人都多了一粒绿色的纽扣
奶奶
老师在黑板上边说边写
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规则是
先乘除后加减
曹秀英低头看了看手机短信
脸刷的白了
她通的站起来
老师我奶奶 ……死了
教室里出奇地静
老师慢慢地说
你先回去吧
曹秀英满眼是泪
慌忙收拾书包
三步两步冲到门口
哗的书包带子断了
书撒了一地
她赶紧蹲下收拾
学生们忍不住大笑起来
曹秀英好像也笑了
如果带括号的
先算括号里面的
后算括号外面的
老师继续在黑板上边写边说
黑猫
阿尔端着酒杯 我叫道
快看 快看 黑猫
阿尔头也不抬地在喝酒
快看黑猫的眼睛
阿尔弯下腰
从桌子下面看过去
一团黑乎乎的肉球
脊背弯成一张弓
阿尔有点失望的抬起头
快看 快看 黑猫的眼睛
阿尔再次弯下腰
一座上尖下宽的黑塔
直挺挺的立着
快看快看 眼睛 眼睛
这时 我惊奇地发现
黑猫的眼睛是绿色的
眯成一条缝
在墙角一堆垃圾里放着光
病
你的手伸进我体内说
再过十年你就会和我一样
我惊恐地看着她
她哈哈大笑
露出好看的白牙
没有人能看到
她的脚也一样白
手指柔软得像一滩水
她的头发生动有力
圆溜溜的脑袋
生气的时候
像个小小的法西斯
没有人知道
她空荡荡的大衣下面
是一条游来游去的鱼
她经常说 我又肥了
只有我知道
那根长长的针管吸走了她的脂肪
现在一览无余的
是白花花的一堆肉
新雪
向左 向右 再向左 再向右
他像个士兵跑来跑去
站台上的新雪被他践踏成一滩污水
3路车像个醉汉歪歪扭扭开过来
不用看就知道
市立医院 华夏商场 供电局 区政府
一路向西直通汇源酒店
他继续跑 向左 向右
再向左 再向右
15路车慢慢开过来
他知道经过他的目的地
他还是跑 向左 向右
再向左 再向右
他大口喘气看上去并不累
昨夜的新雪在阳光下
像明晃晃的刀锋
19路车懒洋洋地开过来
直达他要去的地方
他顿了一下
狠狠抽了口气
新雪的味道涌进他的胸腔
他继续跑
向左 向右
再向左 再向右
深夜 想给阿尔打电话
毫无睡意地坐到半夜
电脑里放着《广陵散》
身边找不到一棵竹子
我住在狭小的三居室
左边是卧房门
右边是厨房门
斜过去一点是洗手间的门
它们像怪兽的巨口
在我背后迷离地笑
琴声越来越快
我想冲进去
操起菜刀
砍一万根竹子
砍一万首诗
砍一万条毒龙
我想把这感觉告诉阿尔
却想不起是哪个阿尔
法国的荷兰的 还是安徽的
我放下电话
转身离开
老人
她坐在秋风里
第三次把我认错
第一次是在夏天
她像一截枯朽的树桩
包裹着一片枯燥的蝉鸣
我老远骑着车子过来
她突然“哇”了一声
“小金,回来了啊”
她张开的嘴像深不可测的黑洞
我不知所措地对她笑笑
第二次在不久前
我刚把车子放好
她又“哇”了一声
“你要找我儿子吗他在家”
我假装没听见
扭过头直接走了
现在我就站在她面前
她没有看我
只是大声地说
“哇”
哭泣
从肩膀的起伏
可以看出你在哭
好像还能听到
你低低的抽泣
我突然意识到
在这个场景里
我是个多余人
我想抽身离开
耳边却响着
若有若无的呜咽
我回过头
冬青树像我多年的兄弟
大槐树一副落魄之相
这时一切忽然定格
秋风红着脸
碰了碰白杨树
我竖起耳朵
请把音量调到最大
那些咆哮、哭泣、呻吟、嘶叫
聚成一滩肆意奔流的体液
停下 停下
我对音响师怒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