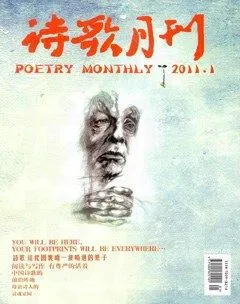春眠醒来寻梦迹
从大阪到京都不超过半小时。穿越内部通道纵横相错、熙来攘往人流湍急、似乎不打算让谁停下来细看的阪急百货店,进入要是描画在地图上就更像是集成电路板的京阪神铁道网,找准JR东海道本线快车,只来得及观察几眼端坐着用手机发短信的少女、拱背埋首瞌睡的中年人、抓着把手吊住身子前倾着翻看漫画书的小青年,京都就到了。
沿途最多的是房屋楼宇。建筑和建筑把都市和都市连成了一体。不过,走出车站,你立即就意识到这已经是另一座城市了。跟大阪或东京那种见缝插针丝丝入扣的紧张繁忙不一样,京都街头洋溢着不属于当下日本的自在安闲——而这本应该属于日本的。
记得唯美主义的谷崎润一郎写于七十多年前的《阴翳礼赞》,以挽留的笔调称颂日本古色古香,光线昏暗,洁净无瑕的那部份往昔,它们在大阪或东京这种当今最代表日本形象的超级都市里很难找到了,在京都却还保存得相当完好。谷崎润一郎觉得最有切肤之感,拿来例证可得精神之宁静休息的日本式厕所,在京都也还容易找到。
京都那些依然笼罩在阴翳之光里的小店,陈列着各色细腻精巧的工艺品、日用品、糕点小吃、偶人玩具,让你感到传统还鲜活地在其日常里继续生长;那些寺庙、庭院、宝塔、神龛,则把你引入美好的旧时代。并且,你更觉得,这地方正是从旧时代延展来到了今天,中间几无突变和断裂……听同行的朋友说起,太平洋战争时,美军特意没有空袭轰炸京都和奈良这样的古都。后来我又从一集有关古建筑的电视片里得知,是梁思成建议美军不要去轰炸敌国这两座古都的。历史积淀而来的美,并不与人类为敌。
京都站和金阁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京都。几天前我已经到京都游览过一次。那天我是从东京乘JR东海道新干线到京都,途中两个多小时,也像是在一座大城里穿行。春寒比以往走得稍迟,本该樱花盛开的日子,却只是偶尔见几处早樱点缀着空枝。富士山被雾气遮挡,在新干线经过它时,只让人远远地看到一点模糊的轮廓。
真正的惊喜是在抵达京都时到来的。JR京都站先就给了一个旅行者果然不虚此行的满意,它宏阔的现代感成为观光京都的奢华起点。这座由名建筑师原广司设计的宛如山谷的超巨大建筑,设置了音乐厅、百货公司、高级酒店和会议中心。车站的功能性空间只占去整栋建筑物的百分之五。1997年落成后,这座日本最大的车站成了京都的又一标志。它也是车站复合式经营获利的典范。1991年,原广司一提出设计方案,有关传统与现代的激辩就随之展开。有人说它太破坏京都古雅的意象了,而在我看来,它却刚好是一个让传统焕发新意的提示。高60米的中央广场式大厅、巨大的音响盒大楼,贯穿东西的约45米的空中通道、叠浪式上涌的传送电梯,171级高阶,上面以特定弧度倾斜的钢架组成了镂空的天花板。不妨把这种态势看成是对京都古意的一种未来式关照——游览京都正可以从这座车站的顶点开始,从那里下瞰京都全景,会觉得自己正欲从外星深入地球一角一座东方古都的往昔。
京都的另一个标志大概是那座金阁,它座落在京都西北角的鹿苑寺内。因为这座舍利殿“金阁”特别有名,鹿苑寺就又被称作“金阁寺”。三层金阁有着不同的风格:第一层是平安时代寝殿建筑样式的法水院,第二层是镰仓时代武士建筑样式的潮音洞,第三层则是中国禅宗佛教建筑样式的究竟顶。第二和第三层在天然漆上再镶贴纯金金箔,泛着亚光,下临水色比日本抹茶稍淡一些的镜湖池,果然精美绝伦。那些金箔是1987年修缮时重新贴上去的。1994年的时候,金阁寺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我对它久闻其名,是因为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小说结束时提到金阁被焚的情景:“从这儿看不见金阁的姿影,只能看到缭绕的烟雾和冲天的火柱。树丛中火星在飞腾,金阁上空仿佛撒下了满天的金砂。”小说中的金阁被焚显然是一种象征。在三岛由纪夫笔下,金阁正是日本古典静态美的典型。有意思的是金阁的顶上耸立着一只凤凰,于是它的被焚,不是也添加了新生的意味吗?因而它成了京都给我的又一个有关日本传统文化之现在的提示。
金阁只可旁观,不能进入其中。游人们多是以它为背景拍几张留念照,然后就离去了。金阁实在太耀眼了,很容易让人忽略鹿苑寺的其余美景。我反而更喜欢简单地卧着一块顽石的疏林空地,还有茶廊外那座朴素的夕佳亭。后来在三十三间堂和有名的东寺,我也更喜欢寺院里被冷落不顾的一二去处。
三十三间堂被视为日本国宝,因正殿內由间隔的三十三根立柱而得名。它的正式名称为莲华王寺,于1164年建成。在三十三间堂长约一百二十米的殿內,以中央一尊铜铸的千手观音坐像为中心,1001尊千姿百态的千手观音立像沿两侧整齐密集地一字排开,气势夺人,是为三十三间堂的镇寺杰作。東寺更早,始建于796年,是古代日本用来镇护国家的寺院,正式名称为教王护国寺。它的奇迹是那座高55米的五重塔,这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古塔,由空海和尚所建,后来幕府德川家光又重建了它。
花见小路觅樱
京都寺庙遍地,古迹太多,保存得又那么完好,那么郑重其事,让人不免严肃认真地一一细察,看得久了,便生倦意。外面大街上的气氛要松快许多,阳光和煦,色调明媚。京都街景的一大特色是主要干道的人行道上都做了雨廊,分明是鼓励人们多多步行。在京都逛街也的确是一种乐趣。很少看到那种旗舰甚至航母式的什么都卖的百货超市,沿街全都是些小店,卖的是专门的货色,许多意想不到又让人爱不释手的手工制品,游客们,尤其姑娘们进去就别想空着手出来。其实那些过于讲究细节的小物件并不实用,但却传达出一番古意和对于生活之慢(因而也就不是庸懒就是优雅——难道庸懒并非优雅?)的缅怀。有几条小街完全被雨篷遮盖起来,成了专营这些货色的步行市场街,是很多年轻人爱去的地方。
奇怪的是,日本那些衣着前卫打扮标新的年轻人,混迹在这种稍显晦暗的街角,盘亘在那般总是阴翳的店堂,却并不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或许一种日本传统文明的教养依然会从他们的气质深处隐隐透出?或许京都所代表的那种古意,在现代日本有着顺理成章的接续延展?反正,镶嵌在后现代风格样式的建筑之间的一方牌位、一个神龛、一处旧庙是如此正当;一个刚刚还在烧香参拜的老头一转身走进边上的电玩店里同样虔诚地赌一把运气也那么正常。至于一个老头用手机相机拍摄一朵樱花,那就太平常了。不过我第一次到京都的那天离樱花盛开日还早了差不多一周,所以在街头绿地见人访樱,也就不免驻足。樱花向来是定期开遍日本的,却也只在春天的某一周内盛开,然后立刻飘零,人们由是分外珍视樱花时节,早早就开始期盼。
在京都,花见小路是人们寻觅樱花消息的一个去处。那是一条最完整地保持了京都古老历史风貌的南北向街道,非常有名,不过我当时却并不知情,无意间走进了花见小路也还不知所在。但那种老街的氛围吸引了我,至于竹篱红墙的茶屋外面,抬头偶见枝横樱花,则实在令人赞叹——为什么别处不见,只是这地方独开一树呢?跟另一些老街不一样,花见小路有着浓郁的花街柳巷情趣,鳞次栉比的高级餐馆料亭,店头悬挂的小红灯笼上标有“舞妓”字样,示意店內有舞妓陪客服务。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运气好的话能在街上见到舞妓,正说着,果然就见有外出去别的场所献艺的舞妓挑帘出门,切脚小步急行而过。
花见小路上早开的樱花惊动了几个摄影师前来拍摄,其中有人雇了舞妓到樱树下摆样子拍照。几个欧洲游客见了赶紧揩油,强拉着两个舞妓合影。舞妓倒是好性情,听任指挥,哪怕这一服务是免费的。
我却去注意一家开在路口的首饰店。店面狭小,但布置得漂亮。最有意思的是店内就设了一个作坊,原来所卖的首饰等等都是在这作坊里现场做出来的。这家首饰店的二楼视野很好,从上面能看到垂柳斜樱下往还的行人,一条带着弧度的溪流沿街伸向不远处的闹市,清浅的水中,竟然立着一头鹤,正以为是个雕塑小品,它却振一振翅,迈步隐向小桥阴影里去了……桥上,又一个老头,端起相机在给他年轻的妻子还是女儿拍樱花下的留念照?我更愿意那年轻女子是他的情妇,似乎这才更配花见小路。
花见小路也像金阁那样太鲜明了,实则周遭另几条老街才是旧京都的一般面貌。在平常风景里那些电线是最讨人厌的,可是在那些老街上,团团乱麻似的电线却一点也不碍眼,反让这些老街变得更真实,并有了一种朝向现代和现在的美……
白沙村庄连歌
从东京到京都那次,一半是为了去看金阁,却最中意于花见小路。几天后我又从大阪来到京都,这次去的则是银阁寺方向。那地方叫白沙村庄,在京都靠东位置,跟银阁寺只一墙之隔,或许附属于银阁寺。大概半年前,一次将持续半天的连歌会就已经筹定,白沙村庄一座临池的木结构楼台,于是在这个白天迎来了一群临时骚客。白沙村庄虽然不是寺院,却是和尚们的产业,由僧人管理经营着,其中举凡小丘疏林、曲水板桥、花草苔藓、茅舍竹亭,样样别致,透着一种别样的禅意。连歌的主持者高诚修三先生选定此地,自是想给这种传统雅事一个相得益彰的环境,令其避开日本高速现代化的一面。
高城修三先生却也不是那种脱节于时代的传统固守者,这位芥川文学奖得主,有意要在当代日本发起一次新连歌运动,试图让这件中世纪的遗物再次用于日本人眼前的精神生活。他认为,连歌是“使人遭遇异质的事物、意外的构思和想象的装置。连歌是‘场的文学’、‘共同的文学’。” 他希望 “连歌”这种对时人而言过于高雅甚至腐朽的游戏能够新生。说起来,在手机、因特网发达的今天,似乎何人何时何地都可能成为连歌的“连众”,所以,好像连歌在这个时代会有些新的可能性。
在白沙村庄的这次连歌,更多的则只能算一次返回,据以想象古代文士墨客那实已不会再现的风雅。上午10点,参与连歌的人们在楼下脱了鞋,从一道窄小结实、将以往岁月的黯淡深吸进木质的楼梯上到二楼,那儿,几案已排开,杯盏放置得齐整,被水色映衬的连歌之屋的梁上悬着两块扁,一曰“老松白云源”,一曰“阳春白雪”。主持者座位背后靠墙的红色小桌上,放着一个偶人。原来此次连歌,是得到一个制作偶人的世家赞助的。尽管有赞助,参与者每人还得缴纳一万日元。
整个连歌过程被安排成一套漫长的仪式:茶道、一次次端上来的更是给眼睛享用的精细菜点、酒、连歌完成后的书写、合HCuIsrbYjqmpApIJUUp5yYkJg8o2Eec37SWB52+N8tk=影、移往咖啡馆的闲谈、见面和告别时没完没了的鞠躬……参与连歌的有近二十人,并不都互相认识,坐定后先就各自介绍自己,从中实已见出连歌作为一种社交活动的质地。除了主持者、宗匠和作家的高城修三先生,其余的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报社高级记者,也有世家子、画家、诗人和专门的俳人。赞助者被称为亭主也在座连歌;一位书法家负责记下主持者确认的句子;有个戴眼镜的人站起来说他是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京都市长的竞选人,即席发表了一通政见,拉起了选票。
连歌为和歌的一种,这次的连歌共计十二句,被称为半歌仙连歌,每句如俳句由十七音组成。连歌有很多特别的规矩,我在座中靠着翻译帮助,大约了解到高城修三先生宣布说十二句中涉及“恋、春、秋”的要在二句以上五句以下,并且第七句必须相关“月”而第十一句得要说到“花”。第一句也叫“表发句”,由俳人竹市悠纱念出,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译成中文或即:“春眠醒来寻梦迹”。主持者解说评议一番,在座各位便开始苦思,偶尔有人惴惴念出一句,却常遭主持者摇头否决。那个京都市长的竞选人有一次念出一句,更被高城修三先生痛批为“臭”!然而连歌在进行下去,有句子被采纳,便全体释然。下午忽然电闪雷鸣,一阵疾雨,也被有人一转念写下连成了又一句……这样经历了五、六个小时, 十二句总算集思广益共同凑成了。
作出的连歌优劣如何在我看来实在不重要。感人的情形在于,一群人能从四处聚到一起,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字斟句酌,为了一首诗,为了语言而沉浸投入。那样一个漫长的诗的白天在日本这么个金钱社会里太过奢侈了。从中你还是能体会到一种过于优雅甚或颓靡的反叛:就让那个新干线一样疾急的世界失控般飞旋好了,我就在一边慢悠悠鼓捣一首臭诗——人生难道就不该如此随心所欲?当然,实际上,这又仅只是一场语言和诗的舞会,一个交际场合,一种交往方式。孔夫子说:“诗可以群”,我把《论语》中的这句话转述给了高城修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