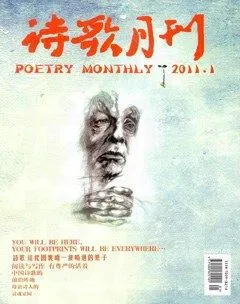给灰娃的信
灰娃诗人:
读新版《灰娃的诗》,见到去年《国旗为谁而降》,注明写于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病房,感到十分亲切,因为在那半年多以前,我也住进那家医院病房,为接受“搭桥”手术,不过是在其第二门诊部罢了。
我很同意屠岸先生为您的诗集写的序言,可谓知人论世。他对您的诗在当代诗创作中所独具的特色,分析得很具体,很中肯,用今天惯用的话说,很到位。
我在上世纪末从朋友处读到您的《山鬼故家》,即为之惊“艳”,除了昌耀以外,久不见此个性化的诗了。语言和意象的独创,使我感到惟此人有此诗思,有此诗境,有此诗句。有一种不可复制性,别人是摹仿不来的,硬要摹仿也只能是邯郸学步。而且,由于您忠于自己的感觉——诗的感觉,您也不会复制自己,这是屠岸先生说到了的。您的那些诗,曾让我重新思考所谓现实(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像有些理论家看得那么两不相干,又像有些理论家设想的那样可以从外部生硬地“结合”?
这一回我重读您的诗,包括曾结集为《山鬼故家》那部分,还有新增加的部分。在我的心里忽然浮现“纯诗”两个字。“纯诗”,这是有人论述过的,有人追求过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存在的。关于它,有这样那样的定义,莫衷一是。我不想从定义出发来探讨。我的这个反应,纯粹是出于对灰娃的诗的直觉,和对母语中的“纯”字的最朴素的理解。
从诗的生成来说,诗人作为主体是第一位重要的,也就是诗人的精神层面,灵魂层面。心地纯净,排除各种藉口的功利之念,才有可能为真正的诗人。王国维说,诗人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是天真,也是纯真。灰娃对童年家乡亲人的回忆,对少年时期延安生活的怀念,是直觉的,是天真或称纯真的,是理性的思辨所不可替代的。这样的心地,如海绵一样吸纳了各样的表象,感受,形成心象,营造出一个不同于客观世界的诗的世界。这个过程,是从生活“提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写出的诗,称之为“纯诗”,不是恰如其分的吗?
在这样的纯诗里,并不拒斥社会现实,但是对现实做了“诗化”的处理。在这样的纯诗里,自然不含世俗的渣滓。它是高于生活的更高的真实,只有在这样的真实中,才会有诉诸道德的和审美的可能。这更高的真实,体现了诗人的心灵的真实,因此是独特的,不可复制,不可摹仿的。
屠岸先生说灰娃无意为诗人,以及一连串的“无意”,即不是刻意为之。灰娃的诗中有大量的通感和象征,但可以想见,她绝不是学习了“现代诗技巧”一类讲诗艺甚至是“做法”的书以后亦步亦趋的,甚至我想,她也未必读过这些文字。“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在这里又可以得到一个证明。对于走上写诗的道路的人来说,不妨了解些有关诗的理论、源流、争议,也不妨涉猎一些有关诗艺的探讨,但归根结柢要从心灵出发,要从自己的真正的感受出发,要生活在自己诗的感觉中,这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灰娃的诗,可以看作是她“一个人的心灵史”,折射了一个时代,苦难的岁月,普通人的命运。一方面,是足以导致一个敏感的人精神分裂的矛盾和折磨,一方面是“为人类尊严拼死(地)抵抗”(灰娃语),这就是灰娃的诗。
这样的折磨和矛盾远远没有结束,这样的抵抗也远远没有结束。这就是灰娃的诗的泉涌不绝的根源,她仍然没有放下诗笔。愿她健康长寿。
灰娃大姐:写到这里,我不自觉地把第二人称写成了第三人称,因为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在这些尊敬您,喜爱您的诗的读者和知音面前一读,以弥补我不能前来的遗憾。
客套的话就不说了。我的有关“纯诗”的说法,也许不为文学理论家所同意,那我就换一个说法——灰娃是纯粹的诗人,灰娃的诗是纯粹的诗:对不对?
邵燕祥 2009年5月14日
(这是在一次关于灰娃的沙龙式研讨会前夕写给诗人的信,后据灰娃告知,在会上当作一份发言念给大家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