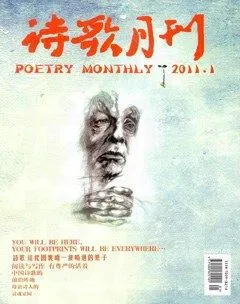谈话录:本土文化基因在当代汉诗写作中的运用(节选)
去年10月在安徽黟县和英国诗人帕斯卡·葩蒂(Pascale Petit)、尼日利亚诗人奥迪亚·奥菲曼(Odia Ofeimun)讨论东西方文化差异时,我谈到东方诗歌尤其是汉诗、日本俳句的“气息”问题。开始,他们觉得很玄。我说,噢,这从一个东方人的角度,可一点儿也不费解。《說文序》中讲,“文者,物象之本”。就是说在物象包括语言符码的背后,有一个被视为“本”的东西。从诗歌写作上分析,不妨把这个东西叫做“气息”:让字词在排列与构造中得到——呼吸——的那种东西。“气息”有时是纯技术性的,创造性的语言组成方式,修辞本身的陌生感,是一种气息。维特根斯坦晚年不是把写作看成语言的纯游戏行为吗?游戏之玩法的新颖性及其给读者的错愕感,说的就是这个。当代汉诗在这方面的尝试可谓多了,解构或消解词语本有之义,派生出新的感受。但这里面有个危险,即这类写作技法很快会被重复与超越,新游戏成为旧游戏,短时间内就会让人生厌。气息也可以一种情感,这是一种相对“古典”的认识。当你读一首诗时有所触动,它把你内心的某种东西唤醒了,这种“唤醒能力”也是一种气息。刚才念的我的短诗《前世》,算是这个范畴。当然,气息也可以是一种观念。总之是让你感觉到这首诗是“活着”的,是与你在互动的,这种“活着”本身所赋予你的一切——这需要作者与读者有效的共同作用——就是气息。不是鼻子、眼睛、嘴巴的简单拼凑与叠加,而且它们之间的匀称与愉悦。有些时候,这种气息甚至不在物象的背后,而是物象本身——视觉上的,声音上的,节奏上的——给人带来的纯粹形式的快慰,也是一种气息。中国人讲究“器”与“用”的关系,不妨把“用”看成一种运动,一种活力,语言之器在“用”之中,衍生出气息。语境(context)批评的倡导者穆瑞·克雷杰(MurrayKrieger)曾有过一个观点:语境是诗歌的一个基本策略。而在我看来,语境这个词完全可以被“气息”这个东方人更易于感受的词所覆盖。这是用非常浅显的方式涉及我所讲的本土文化基因问题。我们讲一种语言的当代性,事实上必须设立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真正懂得了它的本土性。它其实也是另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的变种。
有人说,中国诗歌尤其是古汉诗,缺少某种现场性,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在场”。我说这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当陶渊明说“飞鸟相与还”时,这里面,就有很深的个人寄托在内。中国封建时代的许多诗人,因为写作环境的多变,甚至还面临着“文字狱”一类的遭遇,所以写诗往往体现出“借物在场”的特点。西方的读者看《诗经》或《离骚》,可能被一大堆理也理不清的植物、地名绕得头晕眼花,而失去继续追索的兴趣。我碰得不少西方的朋友,都有这方面的困惑。这种“隐性在场”的个人的气息,是埋藏得很深的。物象对人心的传导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个“在场”的概念有它的复杂性,在他们的笔下,重生存状态而轻视生活的具体状态,是东方诗人的一贯选择,把握不好会给人造成“不真实”的阅读感受。这也是必须让当代诗歌写作者警醒的东西。我也写过一首短诗叫《丹青见》,从起句到尾句,都是物象的堆积。但这种堆积本身,就是为了展现人的内心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在行进过程中是加速的。撇开技艺上的尺度不谈,许多有本土文化基因的东方诗人,似乎都不偏爱如“我坐在车厢里吃橙子”一类的显性在场,它有悖于东方审美中隐忍的特点。所以我一直说,一个好的东方诗人,他的诗中永远有两个空间,在他的公共性空间之下潜存着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空间。公共空间被他们用以教化、述史、抒怀,而人个空间才是真正的阅读焦点所在。作者的个人空间隐忍在公共空间之下。读许多东方诗人的作品,确实要费些思量,但也会获得更多的深层滋味,让阅读者得到更深一层的满足。照我看,罗伯特勃莱正是受益于东方的“深度意象”手法而成功的西方范例。奥迪亚·奥菲曼(Odia Ofeimun)问我:这岂不是在苛求读者而缩小了读者的范围?我说,是。但,难道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诗的阅读扩展到只要认识文字就能懂得的地步?我推测一些所谓“口语诗歌”在作这方面的努力,通过生活的具状而不是通过意象来展示生存状态。这种方式,相对中国自古的“文人诗歌”,它赢得了更多的理解。但也难免存在泥沙俱下的现象,那中间的多数作品因为——预设了明确的读者对象,事实上也是写作对阅读的屈服、让步——其写作在艺术上往往是无效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中国诗歌的本土特质中,确实有许多方面需要捣毁。就整体特征而言,古汉诗是“重视形体的,音律的;重视隐喻和寓言的;以意象诠注生存状态的;重视生存状态而轻视生活状态的;重胸怀而轻反省的;个体生命隐性在场的;对自然与人世持适应性立场的;依存闲适性而轻视批判性立场的;重视修辞的”。这个概括,许多人不一定接受。只能说是我个人能够体会到的“本土基因”。这里面的许多东西早已失去了传继的现实基础,所以我说要捣毁。比如,轻视对个体生存的反省,是一种最要命的弱处。你看古诗中传递出来的诗人形象,一个个天下皆醉我独醒的“清醒者”的模样,一个个出世者的模样,他们拔剑高歌的样子遮蔽了他们提个菜篮子吃油条时苦闷的样子。有时候我厌恶这类形象。难道他们真的没有了具体的矛盾和茫然?没有市井间的焦灼与变态?对这些东西的追问与自省在哪里?如果逆推过去,我们可能从他们的诗中“回不到”他们那个世纪的真实性。生活的真实性与内心拷问的真实性。我有时在想,那些诗人对生活状态的高度适应性,是否跟东汉后普遍的佛教传播有关?甚至连《道德经》那样停留在终极问题上的追问,也不再有了。还有一个,就是过度的匠气与书斋味道,那种一吟双泪流的糟糕的诗人形象。失去了烟火味与血性的文字雕琢,我个人是很不喜欢的。当然,如前所述的深度意象,高度的形式感及与自然物象的共存性,发达到叫当代西方诗人惊异的修辞技艺,节制的表达方式等等,这些本土基因也应得到更进一步的传习。岂止是当代汉语诗人的传习与感悟?加里·司奈德,甚至博尔赫斯从这里得到的教诲还少吗?汉诗现代性是个大而无当的话题,我没做系统的理论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须从理清了本土文化基因、而后在具体的个人写作中捣毁部分本土基因上起步。
在汉文化的本土基因里,还有一个很独特、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时空概念。这不同于你们那边的埃舍尔、米罗、毕加索那种强行扭曲的时空感。东方诗歌、戏剧、绘画甚至古曲,在许多地方表现出一种共时性。在那里,“此刻”这个词,既是即时的,也是历史的。“这个人”既是现世的,也是前世的。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范本。这样的时空的交叉与共振体现了东方诗歌一种特有的美质。受这方面的启发,我也做过一些写作上的尝试。在《白头与过往》这首长诗中,我企图将多个维度的时间与空间凝聚于一体。用极为具体的细节陈述来加强时空的幻化。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一个东方诗人的做法。在东方的伦理学与美学观念中,“个体”之中仿佛永远座落着一个“集体”之中:一个人身上的血缘、身世与循环不息的感怀。而且,他会在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角度来表达这种理念。我在《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一诗中写到:“为了破壁他生得丑//为了破壁他种下了//两畦青菜”。这样的写法,得益于禅宗的一些思路。他会在另一个不相干的空间,用不相干的方式来完成他的目的,这就是东方式的曲折和美学。而且在这里,在许多真正的东方诗人那里,所有空间的安置、“物象”的选择,无一不是意味深长的。“一根竹子”,被画到纸上,被写到诗中,不再是一种物象,可能还包含着谤佛讥僧的许多想法。这种方法来自一种古老文化的思维定势,可能许多人会觉得很无聊、很腐朽,但同样也会有许多人喜欢这种寓言式表达。在我看来,一个西方诗人可能不会如此苦心经营这样寻常的一个物象。通过特异的时间安排、物象构造,诗人的个人信息从中奔涌了出来,刘勰不是说屈原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吗?辞与谈,那是表层的构成,志和意,才是真正要体现的东西,也正是靠着它们才完全撑开了诗意的空间。屈原、王维、王羿、马远这些人,从技艺上都是空间安排的大师。这,是否有助于当代汉诗写作中那种因尽力于生活的具状描述而导致的平面感、狭隘感呢?
当下中国的诗人群体整体上很浮躁。一方面,那些对汉诗传统持极端否定立场的人,事实上,其中的多数人或者不懂得什么是汉诗的本土基因。网络时代的即生即灭的即性写作样式庇护了他们“以不懂而快速新生”的状态。他们举着反对的旗号却不知要反对的是什么。这种过度感性的革命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出现过多次了。从方法的角度观察,许多诗人用的即便不是东方人自已的旧东西,也难免是西方诗人的旧东西。所以他们的新生状态,是可疑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我这样说,类似于一种诅咒了。另一类倾向是对传统的非常浅薄的表层复制,这就更不可取了。简单地大喊所谓的王道思想回归、儒家体统回归并像死了亲娘似的哭泣,是对“传承”二字的极大羞辱。“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里我也不想深谈。总之是,对汉语持有自觉性、严谨态度、自省态度的诗人太少了。而且,不同写作取向的诗歌群落之间,缺少有效的对话,更多的时候,形成一种相互攻击的关系,在诗坛造成一种浮泛的热闹,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至少我本人深恶痛绝。当然,从具体的诗人角度来谈,没有一种写作,需要承担起“非个人的使命”。但当代诗人集体,对汉语现代性的建设,实实在在是太重要了。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不足百年,又是一种缺陷性过渡,激烈的白话文变革是由少数几个大师主导着完成的,在大陆又很快被铁板一块的政治话语笼罩着,使她在语言疆域上的可能性,呈现一种紧缩的状态。以语言拓展为使命的诗歌写作,理所当然地就被赋予了一个重要使命。有一些学者认为,当代汉语的范式受翻译体“语言变体”、和未经筛选的方言表达形式的侵袭比较厉害。恰恰在这时,曾被维特根斯坦否认的“私人语言”,确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个体主观主义(individualistic subjectivism)语言学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重要。他们认为“语言的基础是个体的创造性言语行为。语言的根源是个体的心灵”,而“解释语言现象,也就是把语言现象当成是有意义的个体创造行为来看待”。当代汉语诗人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私人语言实践者。奥迪亚·奥菲曼(Odia Ofeimun)告诉我,在他的国家里,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我在想,他们那边,可能是另一种类型,不同于现代汉语因为从原母体的蜕变时间太短,在这太短的时空之中,受意识形态操控的集体话语权力统治又太长。他们那边,是受另一种外来语言的奴役问题。如果让我发言,我要说,从“本土基因”的取舍上出发的,立足于私人语言经验之上的当代汉诗实践,对这个民族的语言发展是多么地有意义啊。相对其它文体的贡献,它的重要性无疑将更进一步地显示出来。
(注:根据2007年秋天的一次即兴谈话整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