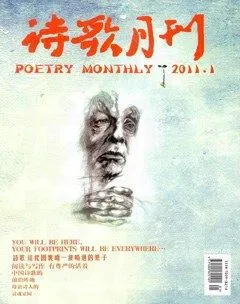诗歌不只是为了“疼痛”和“苦难”
希望人们见到郑小琼的时候不要再鲁莽地叫她——“嘿,打工诗人!”
谈论郑小琼的诗歌是困难的,因为在当下这会不可避免地与时代语境(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新普罗文学”的时代)以及“非诗”的力量纠结、胶着在一起。我与郑小琼的交往只限于短信和电子邮件,我想这已经足够了。记得有一年郑小琼到北京北三环路边的一个餐吧领取“宇龙诗歌奖”的时候我本想上前和她打招呼,但是围拢着她的黑压压的人群和不时闪烁的镁光灯让我看到了这种场合下的诗歌交流是有些多余的。
郑小琼的诗歌写作是从2001年开始的,而新世纪诗歌写作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以往要少。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提问:在一切都可能成为消费品和“娱乐至死”的全球化语境和泛网络的全媒时代里我们该如何进行真正的诗歌写作?当我们的思想被主流诗歌话语再一次集体“征用”和“消费”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词与物、诗人和现实的关系?由此在政治、现实、情感甚至底层命运和乡村苦难都成了“消费”对象的今天,我们来谈论郑小琼的诗歌写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低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商业化、消费主义化的开放、自由和个性的写作时代。但是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商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列车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和思想的深度,只是我们过于迷信和乐观于时间的进步神话。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写作者制作出种种难度和困境,政治年代如此,经济年代同样如此。当1972年冬天北岛把偷偷写好的《你好,百花山》给父亲看的时候遭到了父亲的不解和反对。而当政治年代早已远去,在2009年11月12日北京罕见的大雪中,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北岛在受奖词中表达了对全球化语境下诗歌写作的难度与危机,“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
郑小琼在这个时代显然成了一个标志或者象征。她的个人博客的首页上写着:“主要业务:台湾TOSG 丝攻、铣刀、螺纹塞规、搓丝板、滚丝轮、OCC圆车刀、日本OSG 丝攻……”。郑小琼有一篇文章叫做《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而可悲的是当下的诗人、读者和评论家们尤其是各种媒体和宣传机构对诗人的自陈却视而不见。今天当人们谈论郑小琼和她的诗歌时,人们会立刻想起两个关键词——“80后”和“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从2001年开始,而在短短的几年内郑小琼无论是在所谓的体制内还是在“民间”经济体中都获得了如此众多的赞誉甚至追捧,各种诗歌奖和文学奖也都如此热衷地垂青于她。人们似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而她诗歌中“铁”和“断指”的意象以及“痛苦”、“泪水”似乎成了人们说到打工诗歌和底层诗歌的一个时髦的“标签”。显然无论是作为一个“80后”诗人的代表,还是作为打工或底层写作的代表,郑小琼无疑成了一个“被”“体制”化了的诗人。换言之郑小琼在一个写作效应和写作方向越来越涣散的时代却获得了凝聚式的空前认同,甚至一定程度上她的身份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学意义的象征符号,她的诗歌也成了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家寓言。如此令人吊诡的现象似乎正呈现了这个在媒体越来越发达、写作越来越“自由”的时代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评价和流通机制,这个机制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就是时代伦理和“主流”美学的驱动。新世纪以来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文学评论和文学奖的评选中,题材(写什么)作为文学和时代的双重伦理已成成了时下的圭臬和衡量的标尺。强大的时代伦理的规范令人反讽地看到几十年前中国大地在政治风云中文学尴尬和荒诞宿命的重新上演。那么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诗歌写作个案和急需厘清的时代伦理甚至社会学的切片,郑小琼带给整个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在传播和接受机制中我们接受和生产了一个怎样的“郑小琼”?可悲、可笑的是在看似多元化的写作和传播机制中郑小琼却被呈现出一个刻板印象,或者说我们目前所看到和所接受的只是郑小琼的一个侧影,而诗人的全貌却仍然被消隐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
几乎所有的诗歌选本、报刊媒体和批评文章都给郑小琼挂上了一个时髦的牌子——底层写作、打工诗人。确实如果我们从郑小琼的社会身份、阶层归属和其诗歌文本综合层面考量,郑小琼确实很容易被纳入到底层、打工和草根、弱势群体上来。从2001年开始郑小琼的诗歌确实和打工产生了如此不可分割的关系,她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写于打工期间并且当时是手指甲盖受伤。把她归入目前流行的甚至占有了强大话语权力的“打工诗歌”中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甚至包括郑小琼本人在内也曾强调外界不要将她简单归结为一个打工者在写打工的诗歌。如果说当一个时代伦理性诉求越来越强烈,某种题材的写作方向在时代和文学的诸多合力中,在更为广泛的读者和民众中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偶像性效应的时候,那么这种与时代伦理暗合或主动迎合的主流写作提供给诗歌史的是什么呢?历史已经证明,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事实已无需我多言,迎合时代的主流写作尽管会产生几个重要的诗人和诗作,但是更多的时候只能会产生文学的垃圾。更多的时候这些主流的曾经风靡一时的复制性的诗歌写作更多的是在运动情结中制造了政治甚至社会学的轰动,而当时过境迁,历史并不会收割一切,更多的稗草已经灰飞烟灭。那么在新世纪以来,打工和底层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上越来越主流的词汇,这种写作路径越来越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所谓的民间不约而同摇旗呐喊的大旗的时候,我想这种写作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文学本身的除了一部分有意义之外,更多的却是需要重新的反思和检视。谈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底层”、打工和“新农村”诗歌写作已经成为了诗歌主潮,而普遍的简单仿写和平庸复制已经成为这一流行性写作日益明显的缺陷和危险。我想我们需要写作“底层”和“新农村”等具有现实介入题材类型的“当代性”诗歌,我们需要具有直面现实和担当精神的诗人,但是我们需要的又不是简单的“伤痕性”的、“感动”的、“疼痛”的诗歌和简单庸俗的时代伦理道德的“苦难”和空洞的能指,更非消失个性和良知的被集体“征用”和“消费”的写作。显然阶级文学传统和中国“新左派”所关注的底层、控诉贫富差异在“底层”和“新农村”的诗歌写作中得到了最为及时和有力的呼应。甚至在一些诗歌中打工者、底层、农村和弱势群体成了被反复展览人性“丑陋”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底层”和“新农村”概念是与所谓的中产阶级诗歌相对立而出现的,过于强烈的阶级归属和道德属性使得这些作品在整体性上出现了思想探索性的下滑。在当下的各种杂志和媒介中,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是以惊人的速度复制,甚至这种带有阶层和苦难叙事的写作类型已经成了新一轮的主流话语。在2009年《诗刊》社第25届青春诗会入选诗人中,为数众多的诗人都是在写工厂的机器、眼泪,写农村荒凉的土地、干草车,而无论是在思想深度的探索上还是在言说方式上的乏善可陈都值得我们思考。由此可见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运动的语境中“新农村”和“底层”诗歌已经不再是中性的题材问题,这一人们谈论的“公共话题”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和道德论倾向。
以郑小琼为例,如果说她仅仅只是一个“打工诗人”的代表,如果她的诗歌写作能够被打工这个词汇全部涵括,如果说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仅仅是为了呈现一种时代漩涡中个体疼痛的话,那我想中国文学界太无知了,无知到以一种标签来对一个诗人似乎并不简单的写作予以定论性的标识。在此吊诡的时代语境下几乎所有的关于郑小琼的文章都在反复强调她的打工者身份和她诗歌题材的“打工”属性甚至“底层”烙印,而恰恰忽略了郑小琼这个年轻诗人丰富的诗歌个性,当然也包括她诗歌题材的多样性。郑小琼的当年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作《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最初就是发表在民刊《打工诗人》上,这也给读者和批评者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似乎郑小琼从2001年南下打工开始她文学写作的宿命和伦理只能是“打工”。从此,人们面对郑小琼的所有诗歌甚至散文等文学作品都会第一直觉的将之收拢到“打工”的视界之中。人们对郑小琼诗歌语言、技巧和结构已经不闻不问,只对诗歌题材中具有社会性、伦理性和阶层性的内容予以高强度的关注和阐释,其他的层面则被巨大的筛子无情筛掉了。我想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在优美的抒情上,还是在伦理的深度上都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恰恰是普遍缺乏从稀松平常的日常生存场景中带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复活和提升能力,更多的诗人沉浸于虚幻的个人化和时代伦理的双重泥淖之中。那么郑小琼是否是一个单一化的“打工诗人”?或者说在时代和文学伦理的双重诉求中郑小琼只是为我们提供“疼痛”的诗人?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包括读者、批评者和诗人都应该静下心来全面读读郑小琼的诗歌文本。确实在郑小琼的抒情短诗甚至长诗中,有为数不少的打工题材的诗作,如《五金厂》、《机台》、《三十七岁的女工》、《钉》、《爱》、《深夜三点》、《生活》、《铁》、《人行天桥》等等,人们在郑小琼的这些诗歌中发现了一个时代的关键词——铁、机床、宿舍、异乡、疼痛,人们也在这些关键词中反复强调有关这个诗人的身份界定——女性、农民工、诗人。但是在这种强大惯性的时代阅读的幻觉和带有快感的“二流”性质的欣快症中郑小琼丰富的诗歌文本,带有着多重向度,既关注当下生存又深入到往事和记忆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诗作却被普遍忽视了,而这些被忽略的诗恰恰是构成郑小琼诗歌写作个性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交谈》、《碎石场》、《蜷缩》、《非自由》、《草木还保留着旧有……》、《一生》、《白桦树》、《六月》、《给父亲》、《旧事》、《葵花》、《天鹅》、《图书馆》、《光阴》以及《玫瑰庄园》等诗作中,郑小琼呈现了一个加速度前进的后工业时代诗人身份的多重性和写作经验以及想象力的无限可能的空间。这些诗作与打工毫不相干,这些诗作同样是从诗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个体生存和历史场阈中生发出来的平静的吟唱或激烈的歌哭,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诗作闪现出在个体生命的旅程上时光的草线和死亡的灰烬,这些诗作呈现出一个诗人宿命般的时光感和生命的多种疼痛与忧伤,在对乡土、往事、历史、家族和生命的追忆中,这些诗歌带有强烈的挽歌性质,更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草木还保留着旧有朝代的秩序生长 / 窗外的河流如秦朝时一样流动 / 啊,今天却已换走了昨天 / 它们挤出了时间的皱纹 / 我的悲伤无法赶上落日 / 骑马的历史不断更换 / 我活在其中,却只能旁观 / 啊,过去从三个方向压了过来 / 万物有规则的凋零,那么多的大事件 / 像海浪一样漂移过来 / 时光染白我对山河的敬畏 / 我无法原谅自己迟于过去年代 / 那些激情仍让我内心充满了火焰”(《草木还保留着旧有……》)。
当我们面对一个诗歌写作者的全部,而不是在阅读的筛子中自慰或强奸,那么郑小琼呈现给我们的文学文本是如此的丰富,然而在这种社会和人为的工厂和流水线的制造中,郑小琼只留下了一个看似越来越清晰的侧影,而她更具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全貌却越来越模糊。当然对于像郑小琼这样的一个年轻诗人,我们需要宽容也需要鞭策,更需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她诗歌写作如此复杂和多元的一面。然而强烈的带有社会学特征的时代阅读和批评甚至写作的诉求与合谋中诗人写作无疑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基于此,在这样的诗歌生态和批评语境中如果诗人对自己的写作没有自觉性和适当的节制,没有对时代的伦理所制造的天鹅绒般的监狱和陷阱缺乏警惕和自知的话,其写作就很容易在时代所制造的强大幻觉中自我沉迷与反复麻木。显然郑小琼是一个相当自省、自知并在多方面进行诗歌努力和尝试的诗人。我想郑小琼这样具有写作潜质和发展势头的诗人缺乏的不是对打工身份的强调和打工诗歌的写作,所需要保持和提升的恰恰的是如何在时代的限囿面前葆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多样化的写作路向以及诗歌情怀,而不是仅仅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道德疼痛和时代苦难的“打工”诗人。
郑小琼近期更为繁复、路向更为多样的诗歌写作尤其是《玫瑰庄园》、《时间广场》等长诗、组诗都让我侧目。这些诗歌自身已经证明了郑小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看到了她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和生长的拓殖空间。希望人们再见到郑小琼的时候不要再鲁莽地叫她——“嘿,打工诗人!”
简 介:霍俊明,1970年代出生于河北丰润农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等,曾获2009“诗探索”诗歌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