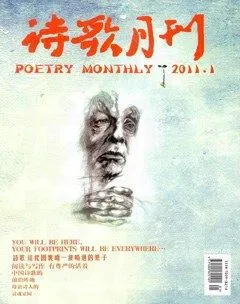进入冬天的飞行
W:你在一首诗中提到艾伦·金斯堡曾对你说,他想放弃诗歌,因为诗歌说谎。②
J:(大笑)
W:而你说,真是这样,但在我们用于表达的诸多方式之中,诗仍然是一种比较诚实的方式。我想知道的是:为了成为一个好诗人,为了击中目标,你是否不得不为了读者而进行调整?
J:嗯,是真的,但这样也危险。可能会变得过于智力化。严格说来,诗实际上不应该智力化。诗,在我看来,要给它更多自由。为什么我曾问你,人们走进来,带着一连串问题——这让灵感激发变得困难。我不需要你让我看起来很棒。当我们两人之间有什么事情开始时,也许滑出常轨,有时带出你更多的东西,带出我更多的东西。如果你把它全都写出来,那就很难再有诗应该有的自由了。
W:你能告诉我匹兹堡是什么样的吗?在《沉渣的滋味》这首诗中有一句:“因为匹兹堡仍然缠结在他心中,让他/清晰地看到上帝的头颅/在丛林根部被撕碎。”
J:是的。
W:匹兹堡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在你成为诗人的道路上,它怎样影响了你?
J:嗯,首先,匹兹堡在某种程度上是原始的。我记得走在山坡上……匹兹堡是在一个山谷里,我沿山而上,那儿有个女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劈木头。它那么原始,那么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寻常的地方。匹兹堡不是一个文明化的地方,它比那样的要好。
W:它比那样的要好?怎么说?
J:因为,如果你文明化了,几乎所有事物就都对你隐藏起来了。
W:通过对行为方式进行代码化?
J:首先,它不是那么有自我意识。它是一种原始类型的文化。如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权衡我们说什么或做什么或我们看起来怎么样,我们是否该脱去外套,等等。我们从来都不是真实的,我们是现代的产儿,想着我们要怎样与别人打交道。如果人们的自我意识如此强烈,他们就很难变得清晰可见。
W:你在日本呆过些时间。
J:我在那儿住了两年多。总共。
W:对我来说,似乎有一种张力,在日本的文明化和宗族化之间。你怎么看待他们的世界?
J:你看不明白他们。是整个文化使然。不让你看他们。他们试图变得完美。花了那么多力气,如果你完美中矩,那就太自我意识了。
W: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擅长艺术的社会……
J:非常擅长精确,但我觉得那儿的人很难做到真实。一切都是有自我意识地产生出来的。你在那儿的时候难道没有注意到吗,一切都被移动过、计算过,完美,整洁,符合规则……已经这样几千年了。
W:但我也感到在他们的语言中,在他们的人格中,含混也留有一定的余地。
J:噢,他们使之完美了。这也是我正想说的。如果你变完美了,你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因为你做什么事都不是自发的。几乎没有什么事情,照我的看法,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能允许它自然而然地存在。
W:你曾有过一个日本妻子,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J:非常美好,但她与众不同。她父亲是这个国家的要人,掌握国家,所以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父亲允许她打破所有规则。她与他们不同。从某个方面讲,她不像日本女人。她放松,这几乎让她疯狂,因此她最终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曾有人采访一位著名演员,采访者说:“噢,你多么放松啊。”可演员说,“啊,但我不放松。”采访者说:“我看你非常放松。”演员说:“我是在演戏。”日本人就是这样。他们摹仿放松的样子。这是一种很难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但对我不是这样,因为我有些疯狂。我打破所有规则。
W:这是外国人在那儿的优势。在海外住了好几个地方,你发现这是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优势吗?你发现你能避开在国内生活的限制感吗?
J:又一次,你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
W:你曾在希腊住过,你发现自己违反了那儿的规则吗?
J:当然。但我不知道我有多接近边界。
W:你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
J:我的生活都致力于认真地去爱,不是廉价地,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我重要的那种,对我的生命真正重要的,是真正地恋爱。不是说爱上两年,然后生儿育女、看着他们长大。我想要某种为我自己的东西。这样做并不是对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成,但我想以一种我能够真正体验的方式活着。不是颤栗,我不是在谈论颤栗。我不是在谈论必须时不时出头露面,教书,或是在这儿照顾家庭。
W:是你的生活喂养你的诗歌呢,还是你的诗歌喂养你的生活呢?哪个占先?
J:生活。我不会为诗歌而改变自己。
W:你不想为写一首好诗而住到一个地方吗?
J:从不。
W:你写到你的贪婪。你似乎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你说自己贪婪是哪个方面?
J:对我的生活。
W:怎么说?
J:对我的生活而言,主要的事情,从我十四岁开始,就是过我的生活,而且,我能做任何事情,但我对自己发誓说我要过我的生活。我是真正地非常贪婪。我知道我敬佩许多有家有室的人,但他们必须为此付出。这是值得的,但不值得我去做。我总是告诉自己,我要首先知道妥协和做出更多努力的危险。我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在我有生之年不会放弃、甚至不会为家庭而放弃的,就是在以后我的生活中在场。你明白我这样说的意思吗?
W:明白。为了在你的生活中完全在场,你放弃了什么?
J:嗯,明显地,我放弃了几乎所有舒适的东西,还有其他一些我有机会拥有的东西。我几乎总是被死神缠着。我并不是怕它。我不责备上帝或掌控这个地方的任何人,这是我真正拒绝做的事情,作为替换,无论多么好,多么聪明和舒适、明智;如果要求我不过我的生活,我就停止。
我停止很早,当我第一次开始获得某种成功的时候,我几乎马上就停止了;我一直写诗,但有六年或八年,我没给任何人……我在八十年代有好几次被发掘出来,但我只是退出。我本来应该远走海外了。
实际上我不是一个职业诗人。我不为谋生或出名而写诗。我为自己写诗。
W:当你写的时候,谁在你的头脑里?
J:我。
W:没有涉及听众吗?
J:涉及虚荣。我很软弱,事实上这也是我放弃朗诵的一个原因。我那么轻易地屈服于虚荣。我擅长朗诵。我走上这行当的半道时就已经擅长朗诵了,非常擅长。你登过台吗?那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做得对。我能让坐在第二排以后的人摇头晃脑,控制听众而不让他们觉察。你能控制听众。我很擅长——我觉得——太擅长此道了。其他人应该也还行吧。我正变成一个婊子,我那么喜欢控制听众,让他们鼓掌,让他们印象深刻。这是不是伟大?这是控制。演员经常干这个。许多演员在第一次成功之后……很快他们的成功就消失了,他们的余生被诅咒。
W:他们再无法东山再起。
J:嗯……他们想要这些。他们追求这些……他们为了重登舞台而不惜做任何事。所以我收手了。
W:你收手了?
J:让我收手很难。我几乎能放弃其他任何事情,只除了那种影响力,我对于诗歌和听众、好的听众的影响力,不仅因为我能欺骗听众,而且因为能与听众、一个倾听你诗歌的好听众站在一起。
W:你的诗歌似乎越来越棒了。
J:谢谢你。
W:也许这是现场朗诵的另一面;你能带入写作中的东西……
J:我当然不能信任自己,但我确实认为这是我诗歌的一个主要因素;即,我写诗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一个想像中的听众。
W:你似乎是利用诗歌沟通过去,“在一根绳子上打结”③, 还提到肯·克西④利用写作做标记……
J:你知道他实际上是做什么吗?他告诉我,当他写作时,因为他用许多药物,他兴奋时写下的那些,是标记。当你走进树林,你不想迷路,你就做标记。他说,他写的下的东西是要做标记,让他能找到路,回到他发现东西之处;我写东西不是这样。
W:而你利用写作回到美智子身边?
J:我觉得不是这样。情况类似,但我觉得,凭借写作,我能看见、我能越来越多地发现我所拥有的东西。但谈论这些有些困难,因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失去了控制,某种程度上我从来不曾失去控制。这是能做到这样的最近的方式。写一首诗,唤醒了那些已经在我身上并为我所知、但我并不知道它就在那儿的东西。所以有两件事持续不断地发生。我意识清醒,当我写作时,我对于我正做的事非常清醒。但同时对被揭示的东西我又非常脆弱。我不想仅仅是在写诗。我想陪伴着那首就在我身体内、在我身体内出生的诗,但我不想告诉这首诗去做什么。我只想随时恭候,意识清醒,心甘情愿被占用。
W:你似乎集中于地方、爱情、丧失,但似乎又不集中于什么事情。这是因为你不观察那个特别的地方,还是因为它们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入你的诗歌?
J:告诉我你这话的意思。
W:你经历过许多时期……
J:从我六岁就开始了。我觉得我在六岁时变成了我自己。
W:那应该在1930年前后吧?
J:大致是的……
W:从那时起,发生了许多历史事件……
J:当我大约六岁时,我意识到了自我。此前我喜欢我所是的那个人,但并不像我后来变成的这个我。这是从六岁开始的。
W:你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J:当我回头看的时候,非常清楚。
W:你认为你在写作中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吗?
J:我不落类型。
W:我试图弄明白为什么这些时期在你的诗歌中并不存在。它们几乎像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小胶囊。
J:我的心灵,我的精神,一直都在不停地探索,除了听起来有些自命不凡。对我来说,似乎我在我的生活中经历了许多;就是现在,我都对我如今的年纪感到奇怪。这比我以往知道的任何事更不可知。一切都如此充满含混和变化,都这样发展和生长。我不知道去做什么。一百岁是什么样子。你看到了,我现在兴致盎然。我不知道我会活着还是死去。这和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同。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够了。
W:到某个时候你就会知道是或不是吗?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J:随着我日渐衰老,随着我的能力减少,也许那时候我会发现自我的一个不同版本,像过去一直发生的那样。但我有一种预感:我如今已经走得太远了。也许我与此不同。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我后来的每个时期,我都觉得熟稔。如今没有什么熟悉的东西来度量死亡。老年;我有兴趣去看我能否有所发现。
W:这就是你在《拒绝天堂》这首诗中所写的?
J:噢,不。
W:你写道:你不能为了别人在宗教中所发现的东西而放弃你的生活。
J:嗯,我并不在意宗教能否让我变得渺小。在我的经历中,宗教通常被教导的方式……是事物的减少。宗教有一定的野心,它大致是把你的意识减少到非常少……浪费你的生命。不明白我们干嘛要那样。但至于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并不想按照官方的想法去做。
W:这让人想起《带来众神》这首诗的结尾:
那么你很平静,她说。我并不平静,
我告诉她。我想要失败。
我渴望我正在变成的样子。
你将怎么办?她问。我将继续向北,
双臂间携着过去,飞入冬天。
你怎么想要失败?
J:我还不想理解所有这一切。
W:你还不想理解所有这一切?
J:是的。当你理解了所有这一切,你就不再成长了。你就会到一个茫然的阶段。我想要所有这一切。
W:你想要所有这一切,而且你想要失败?
J:这就是你了解其他阶段的方式,因为危险的东西正是你学习如何去做事。也许最终发现与上帝平静相处的方式。我并不想与上帝平静相处。我想从那儿出发。是否这样就糟糕、可怕、让人痛苦,我想知道。而我不想满足。一旦我感到满足,我就不再会变成我可能变成的样子。
W:最后一行“飞入冬天”是什么意思?是变老吗?
J:是的。意思是还要继续。
W:还要更加苦行?
J:并不一定那样。必须超越。当你做什么事并学会把它做好的时候,你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当你做好的时候,你就停止成长。这是我对上帝抵制的一个地方。我不想要那样的快乐。我不想满足。我不想去相信。我想要还能够成长。
W:但你仍然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J:是的,我很快乐,但并非全然的快乐。美智子死了。我生命中另一场最重要的爱情也结束了。不仅是美智子,还有我至今仍然熟悉的那个女人……
W:琳达·格雷格?
J:是的。
W:她对你说:“一匹白马不是一匹白马。”
J:是的。如果一个人幸运他就聪明。这是说它不是名字,而是名字所指的事物。你说“一匹白马”,这是某物在你头脑中的形象,而这个某物并不在你的头脑中。是这形象在你头脑中。这不是你意识到你拥有的事物。这样说有道理吗?
W:是的,如果你取消这些我们用于应对事物、组织我们生活秩序、让我们进行沟通的概念,我们就不仅没有那一匹白马,我们也不再有一匹马。那匹马就成了我们不再拥有的、在田野里的某物。
J:精确。当然它迫使你拥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存在的其他经验。你不再把它转化为打上标签的某物。也不再有诸如一匹马这样的事物。
W:或一个诗人。
J:或任何一个聪明人。如果你认为它是让你变得一贫如洗的一种东西。
W:钢琴只有在它被演奏的时候才有音乐。
J:是的。
W:它想要被演奏吗?
J:不。
W:钢琴是为被演奏而存在吗?
J:机器并不在意。这种物件,你敲击而产生声音,它并不在意。它并不在意你演奏得好坏。是我们给予它评价。钢琴只是机器。正确地使用它,它就活起来了。物体并不在意。
W:手,当它抚摸一个美丽的女人,它在意吗?
J: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不。而一架钢琴并不拒绝我们,从不。
W:甚至哪怕它只是一个投影,也许只是这样,有些时候我的钢琴应和我,而其他时候就困难一些。
J:那是你在发明什么东西。是的。不错。
W:当我的手在做它喜欢的某件事时,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W:那你发现意识居于何处?
J:在我身上。
W:我?我们这儿又回到了白马?我是指杰克·吉尔伯特吗?
J:在我身体内。深处。头脑,整个身体。
事实上我不是一个职业诗人。大多数诗人是,这么说有些污辱人,大多数诗人是在谋生。为此,他们通常讲授诗歌。他们不是因为喜爱诗歌而做这些。他们大多是做一段时间,养家糊口或满足虚荣。但他们在做的是一种职业。我喜欢把诗歌想成一场恋爱。我的许多诗从来没有印刷出来。
W:你不想印刷?
J:我无所谓。我不是为出名而写诗。从根本上说,我不会为钱去这么做。我写诗,不管是否出版,因为我在恋爱。而许多诗人过了一段时间就恨它,诗歌,因为你过了25岁,35岁,很快你就再没有诗了。你不得不写些像诗的什么东西,但事情的本质是要作假就格外难。他们都写诗。他们把这些写出来。他们知道所有规则,但魔力没了。这不是他们的错。这就像“为什么女人容颜不再?” 这不是她的错。这是我们生来的规则。
W:你怎么写诗?
J:首先我必须有诗。我不是走到书桌边坐下,说我今天要做六首诗。从根本上说,我写我有的诗,它到我这儿来。
W:有时你带着一个念头坐下,让它展开?
J:噢,当然。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业务。
W: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你的诗已经完成?
J:我知道!一个诗人应该知道。
W:一年后你又找出这些诗,你说这首诗依然是得体的,或者你有时候略加修改?
J:噢,有些甚至就完蛋了。让我再次读一首诗而不对它做点修改,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我写作的方式。我不是抓住那个念头,让它越来越漂亮。如果你看我的诗,你就明白它们是反反复复地写出来的。
W:你不让它越来越漂亮?
J:不必要。不。如果它有瑕疵,我把它修改好。但我通常做的是让它越来越活,越来越接近我希望拥有的诗。
①译自The Cold River Review 杂志2006年秋季号,原题“Flying into Winter”,由该刊编者William Sandoe(W)对杰克·吉尔伯特(J)进行访谈。
②出自吉尔伯特的诗作《被遗忘的巴黎旅馆》,收入诗集《拒绝天堂》(Refusing H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