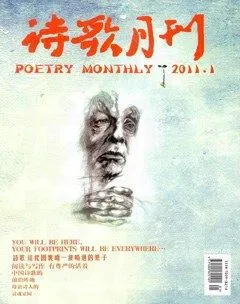杰克.吉尔伯特诗选
只在弹奏时,音乐才在钢琴中
我们与世界并非一体。我们并不是
我们身体的复杂性,也不是
在那棵大枫树里无目的地游荡的夏日空气。
我们是风在枝叶间穿行时
制造的一种形状。我们不是火
更不是木,而是二者结合
所产生的热。我们当然不是湖
也不是湖里的鱼,而是被它们
愉悦的某物。我们是那寂静
当浩大的地中海正午甚至削弱了
坍塌的农舍边昆虫的鸣叫。我们变得清晰
当管弦乐队开始演奏,但还不是
弦或管的一部分。像歌曲
并不是歌者,它只在歌唱中存在。
上帝并不住在教堂的钟里面,
只在那儿短暂停驻。我们也是转瞬即逝,
与它一样。一生中轻易的幸福混合着
痛苦和丧失。总在试图命名和追随
我们胸中扬帆的进取心。
现实不是我们所结合的那种感觉。而是
走上泥泞的小路,穿过酷热
和高天的东西,以及向远方延伸的大海。
他继续走,经过修道院到旧别墅,
他将和她在坐在那儿的露台上,偎依着。
在宁静中。宁静是那儿的音乐,
是寂静和无风的区别。
超过六十
手头拮据,所以我正坐在
农舍的凉荫里清洗
从柜橱后面发现的小豆。
一边聆听无花果树上的蝉鸣
与屋顶上鸽子咕咕声混杂在一起。
我抬起头,当听到一只山羊在远处
下面山谷里受伤,我发现大海
与我儿时用水彩画它的时候
一模一样地蓝。
又能怎样,我快活地想。又能怎样!
我们该唱什么样的歌曲
当我们向它招手,头顶上那只巨大的鹤
就飞了过来,放下
它沉重的双爪,尽它所能
温顺地等待,当我们扣上
那块三平方英寸的铁板。
带走这沉闷不堪的
现实吧,当我们再次招手。
我们给这些取什么样的名字?
给它的嗓音配什么样的歌曲?
耶和华的另一张面孔是什么模样?
这个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
蛞蝓和雪貂,蛆和鲨鱼。
给这些配什么样的颂歌?
是否是那然而之歌,
或者是我们的内心帝国之歌?我们
把语言作为我们的头脑,但我们
可是那只死去的鲸鱼,气势恢宏地下沉
许多年,才抵达我们的内心深处?
正在发生的,与它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关
十一年的爱情栩栩如生,
因为它已结束。此刻希腊历历在目
因为我住在曼哈顿或新英格兰。
如果正在发生的,是围绕着多发事件
而上演的故事的一部分,那就不可能
知道真正发生的是什么。如果爱
是激情的一部分,是美食
或地中海别墅的一部分,那就不清楚
爱是什么。当我和那个日本人
一起在山中行走,开始
听到水声,他说,“瀑布声
是什么样的?”“寂静,”他最后告诉我。
那种静我没有注意到,直到水倾泻而下的
声音,使我听了许久的寂静
变得明显。我问自己:
女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该用什么词语来称呼
让我那么长久地在其中追寻的
那种安静的东西?深入欢乐雪崩的内部,
那东西在黑暗的更深处,还要更深地
在床上——我们迷失之处。更深,更深地
下到一个女人的心脏掌控呼吸之处,
身体里遥远的某物正在那儿
变成我们无以名之的某物。
好意地把她安排在荒僻处
那是希腊岛上常见的一条狭窄后街,
八英尺高的刷白墙壁上有一扇门。
美丽的光与影荡漾在明净的空气里。
大铁门闩从外面把什么东西
锁在了里面。有几天里面的撞击声
让沉重的木门抖个不停。经常有一个嗓音
尖叫。那是个发疯的老女人,人们说。
如果把她放出来,她会伤害孩子们。
掐他们或是吓他们,他们说。
有时候一片寂静,我会磨蹭着
直到我听到微弱的啜泣声,那表明她知道
我在那儿。一天傍晚,我去取油的路上,
看到门被打破了。她在对面地上
靠墙的草丛里,上衣搂起,正在小便。
像头母牛。能够自理,在最后的光亮里安安静静。
一丝不挂,除了首饰
“而且,”她说,“你一定不要再谈论
狂喜。这是孤独。”
女人走来走去,一边捡起
她的鞋子和绸缎。“你说过你爱我,”
男人说。“我们说谎,”她说,
抚理着一头秀发,一丝不挂,除了
首饰。“我们试图相信。”
“你无能为力,对于欢乐,”他说,
“悲叹和哭泣。”“在梦中,”她说,
“我们对自己假装我们在抚摸。
心对它自己撒谎,因为它必须那样。”
说你爱我吧
她床上的天使们,是只在我心里
贴近我的天使吗?
她窗子里的绿树
是我在熟李子上看到的颜色吗?
如果她总是向后看,
上下倒着看,却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还有什么机会吗?我心头萦绕着
那种感觉:她在说
融化的死神、雪崩、河流,
以及通过的时刻。
而我回答:“是的,是的。
鞋子和布丁。”
黄昏与大海如此这般
黄昏与大海如此这般。那只猫
从两块地以外横穿葡萄园。
如此安静,我能听到甘蔗林里
空气的声音。金黄的麦子暗下来了。
光亮从海湾离去,热气散去。
但他们在另一个农场还没有点亮灯,
而我突然感到了孤独。让人吃惊。
但空气安静,热气又回,
我感到我又好了。
燃烧(不太快的行板)
我们都在时间里燃烧,但每一个都是
以他自己的速度来消耗。每一个都是他的
精神折射的产物,他的心智变调的
产物。是我们生活的步幅
让世界在我们身边。无论是
身体的如狮怒吼,还是丛林等待,不管是
心灵的硕大胃口,还是我们的灵魂
远离上帝和女人时悲伤的控制力,
总是我们生命的步态决定了
能够看到多少,知道什么秘密,
那颗心能够从风景中嗅到什么
当墨西哥火车继续向北
小步跑着。宏伟的意大利教堂
覆盖着人们只有漫步
才能够看到的细节。巨大的现代化建筑
一片茫然,因为没有时间从车上细看。
一千年前,当他们建造京都花园时,
许多石头斜放在溪流里。
无论谁,走得快就会摔跤。当我们慢下来,
花园就能选择我们注意的地方。就能改变
我们的心情。在石泉,一处厕所的墙壁上
许多年前有一个药剂师售卖管装的
让男人生殖器麻木的药膏。名叫“逗留”。
逍遥在外
我们已经生活在真实的天堂里。
马儿在空荡荡的夏日街道上。
我吃着自己买不起的热香肠,
在冰天雪地的慕尼黑,泪流。我们能
回想起。一个孩子在场外等待着
一年中最后一个飞球。天那么暗,
黑色衬着天堂。
嗓音向着晚餐,逐渐变弱,
在极远处微弱地呼唤。
我站着,双手张开,看它
向上弯曲,又开始向下,变白
在最后一刻。手放下。盛开。
从上面看见
最终,汗尼拔从他的城中走出来
说:罗马人想要的只是他。为什么
他的士兵要向他们的刀剑示爱?
他独自走出来,辽阔旷野里
一个小人物。他的大象已死
在阿尔卑斯山裂缝的深处。这样我们就可能
在胜利中走向我们的罗马之死。我们的爱
由大理石和巨大的褐色玫瑰铸造,
在我们收获的无尽失败中。
我们已经与死神终生共眠。
它将研磨出它的不光彩的胜利,
但我们能在胜利中脚步蹒跚地走过
寒冷的途中沙漠。
被遗忘的巴黎旅馆
上帝馈赠万物,又一一收回。
多么对等的一桩交易。像是
一时间的青春欢畅。我们被允许
亲近女人的心,进入
她们的身体,让我们感觉
不再孤单。我们被允许
拥有浪漫的爱情,还有它的慷慨
和两年的半衰期。当然应该悲叹
为我们当年在这儿时
那些曾经的巴黎的小旅馆。往事不再,
我曾经每天清晨将巴黎圣母院俯视,
我曾经每夜静听钟声。
威尼斯已经物是人非。最好的希腊岛屿
已加速沉没。但正是拥有,
而非保留,才值得珍爱。
金斯堡有一天下午来到我屋子里
说他准备放弃诗歌
因为诗歌说谎,语言失真。
我赞同,但问他我们还有什么
甚至能表达到这个程度。
我们抬头看星星,而它们
并不在那儿。我们看到的回忆
是它们曾经的样子,很久以前。
这样也已经绰绰有余。
花园
我们来自一片岁月的密林
进入一座名叫“孤独”的
未知国度的山谷。没有马或狗,
头顶上的天堂深不可测。
我们像马可•波罗归来,
珠宝藏在旧衣缝里。
一种甜蜜的悲哀,一种艰辛的幸福。
这个初来者拼凑起一座房子,
在那儿煮扁豆汤,一夜
又一夜。坐在那块巨石上——
这是门槛,在炎热的黑暗中
散发着松树的气息。当月亮升起
在高高的树干之间,他歌唱
没有天赋但怡然自乐。然后进去
与他亲爱的幽灵殷勤致意。
早晨,他观看两只五子雀,
一对燕雀带着初生的儿子。
以及山雀。还有金花鼠
在他的指间,用它们精致的手
寻找果实。他参观他的私生花园,
薄荷和洋葱一起蓬勃生长,
挨着西红柿和茄子。
它们是稀缺的,因为无知而被忽略。
一直想知道他到达何处,为什么
允许他拥有如此之多(甚至
糖枫树叶上的雨水),为什么
还要来那么多。
寂静如此完整
寂静如此完整,他能听见
自己内心的低语。大多数名字
是女人的。已离去的或死去的女人。那些
我们轻易地爱过的女人。怎么回事,他疑惑,
我们当时拥有,而今不再拥有,
我们曾经那样,而今不再那样。
似乎活着回到当时,是那么自然而然。
很快就会只有浣熊的足迹
在雪地上沿着河流渐渐消失。
我们内心的友谊
为什么是嘴?为什么我们用嘴迎向嘴
在最后的时刻?为什么不用著名的腹股沟?
因为腹股沟太远。而嘴贴近心灵。
我们一整夜绝望地结合,在开始
数年的牢笼之前。但这是身体的告别。
我们吻我们爱的人,作为棺木闭合前
最后一件事,因为这是我们的存在
触摸未知的世界。吻是在我们内心的边界。
这是调情成为求爱之处,
起舞结束、舞蹈开始之处。
嘴是我们进入私密的要道,
而她在其中安居。她的嘴
是大脑的门廊。心的前院。
通向被加冕的神秘。我们在那儿
在天使中间短暂地相遇。
超越快乐
逐渐地我们意识到:什么被感觉到并不像
感觉包含了什么那么重要(无论孤独或残忍)。
重要的不是我们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
发生的事情包含了什么。肯·凯西坐在树林里,
在漆白的摩托车栅栏之外,说:
当他写酸时,他并不是在写酸如何如何。
他用他所写的,作为火焰,去发现路径,返回
他那时所知道的东西。诗歌记录
感情、快乐和激情,但最好的则搜寻
能超越快乐、在过程之外的东西。
激情并不像热情能够接近的东西
那么重要。诗歌引导我们发现一个世界
一部分一部分地,当摄影打断了给我们时间
去独立且充分地看每样事物的那种连续性。
诗作从我们无尽地向前流动中选取一部分
去用心了解它的优点。
被遗忘的内心方言
多么令人惊讶,语言几乎总有意义,
多么让人害怕,它并不完全有意义。“爱”,我们说,
“上帝”,我们说,“罗马”和“美智子”,我们写,
而词语
误解了它。我们说“面包”,它的意义取决于
哪一个民族。法语没有家这个词,
我们没有严格的快乐这个词。
印度北部有一个民族即将灭绝,因为他们古老的语言里
没有亲爱这类词语。我梦到已经消逝的
词汇,它们可能表达了某些
我们再也无法表达的东西。也许伊特鲁里亚的文本
最终会解释为什么坟墓上的那对夫妇
正在微笑。也许不会。当数千个
神秘的苏美尔匾牌被破译的时候,
它们似乎是商业记录。但如果
是诗文或圣歌呢?我的喜悦如同十二只
埃塞俄比亚山羊静立在清晨的阳光里。
噢,主啊,你是盐板和铜锭,
壮丽如成熟的麦子在风的吹动中弯曲。
她的胸脯是六头白色公牛,戴着
埃及长纤维缰绳。我的爱是一百罐
蜂蜜。大量的金钟柏是我的身体
想对你的身体的述说。长颈鹿
是黑夜中的欲望。或许,螺旋状的弥尔诺斯语手稿
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幅地图。我们感受最多的
没有名字,除了琥珀,人马座,樟树,马和鸟。
俄耳甫斯在格林尼治村
将会怎样,如果俄耳甫斯
由于对他罕见的技艺
充满信心,
而从这干净光明的世界
毅然沉入地狱?
然后,面对
围得紧紧的野兽,
正准备好他的七弦琴,
那时,他突然发现
它们没有耳朵?
白色,声音和阿尔基比亚德
在拉提姆,许多年前,
我坐在路边观察
一头牛,一整天。
远远地看,硬白。
偶尔它到树下。
在毒太阳里无色。
在浅浅的树荫里变得柔和。
在近处的强光里,粉白。
在近处的树荫里,花瓣一般洁白。
亚麻,石头的白,和牛奶。
牛的白色经过我面前,又走去
进入光的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