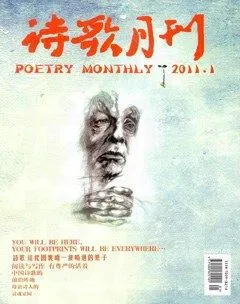余怒的诗(9首)
元旦之诗
当我们还有呼吸时我们要明白
哪些东西容易使我们产生疲劳。
读书,醉酒驾驶,
一日三施的性生活。
戴着夸张的帽子,假装与
朋友谈心,非要熬到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才
起身告辞。“新年好,呵呵,新的一年
终于来了。”葡萄酒喝完了,还有啤酒。
礼花缤纷,好看着哩。有人带来
几个漂亮的街头女子以助兴,这下你不会
打瞌睡了吧?(有人甚至恶作剧地
牵来一头红眼睛的母狒狒)
总归是动物嘛,不说也罢。
像是很多天没睡觉似的,
感觉脑袋始终漂在水面上。
是不是因为
吃饭时听到的一首音乐?是不是走着
走着,突然感到没希望了?音乐很操蛋,
像一团猪下水。
连音乐都如此,更遑论其他。
相互做人工呼吸吧,或者吸一点氧瞧瞧。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用两根指头塞住
她们叽里呱啦的嘴。即使她们是小鸟
也不行。何况她们不是什么小鸟。
他妈的悲伤
时时把脑袋
埋在沙堆里,不顾
别人的看法。我喜欢这么自我怜悯,像一只他妈的
刚做完爱的长脖子细腿的鹳。
如果有人乐意花钱,我甚至可以
来一下脱衣舞或肚皮舞表演。不是说
什么事都不在乎,灵魂,性,肿瘤,
神经质的股市行情。你就是驴子骆驼
也有受不了的一天。我没有给
家人带来体面一点的生活,我羞愧,为一套他妈的房子
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我对世界的理解就像
对按揭的理解一样单纯。
我曾是复杂多变的年轻人,双目有神,头上有
刀疤,爱读书,爱与人扳手劲,被诗人
“相信未来”之类的鬼话鼓舞着,差点去了西藏安家。
现在呢?唉。
西藏不过天蓝一些,
其他还不是一个样?
星期天,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艺术,我瞧瞧
这个瞧瞧那个,直想骂娘。他妈的悲伤就像冰淇淋,
弄成艺术倒挺美的,不信你看看割掉了
生殖器的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无极》。
你认为他们亵渎了悲伤,可制片人却看到
悲伤所带来的票房收入。
艺术与我们有个鸟关系。富人用宝马撞人,我们的孩子
被迫喝下三聚氰胺。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有人
烂醉如泥。SARS之后是H1N1。这个月,你口袋里的
钞票花光了,印钞机会印出崭新的更大面额的。
单位里有上司咆哮,隔墙有电锯在响。
每天我只有将他妈的生命
浪费在无聊的运动上,慢跑、冷水浴、长时间憋气、
扭脖子、摇晃身子、仰卧起坐。但这样也好。
章鱼
天气晴朗,有利于听觉和视觉,
像干爽的衬裤。
有人问,你今天好吗,我回答不好。
朋友们好吗,不好。
地球转动给我们的感觉,
冰块、鸟的残骸和围绕我们灵魂的章鱼
给我们的感觉。只有天知道。
章鱼身体。比基尼。K粉。
一个生活的失败者蹲在路边卖旧书,
回到家,他边哭边干那事,
边念叨维特根斯坦。他说一秒钟
也不愿多活。他是我多年的朋友。
而我呢,蓄着络腮胡子但不想
与艺术发生关系。
我没有杀过人,但我有欲望: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
对我而言维特根斯坦仅是冰毒也就是说
我对世界的看法有可能比章鱼更古怪。
菠萝
将爱吃菠萝的嗜好
美其名曰“夜生活之小盹”。通过
保持嘴巴的湿润来治愈我的歇斯底里。
菠萝的酸味,令人想到制服里的女性。
想一想——当一颗流弹
击中一只菠萝而
水淋淋的菠萝碎片漂浮在你的四周。
有一次,我刚爬出一家歌舞厅的窗户,就被抓了。
审讯我的是一名年轻女警察。我说我要
吸烟她说好的。我说我要
吃菠萝她说好的。
仿佛她只会说好的好的似的。
可当我慌张地射出一泡尿并将烟蒂
摁在椅子腿上时她轻轻附在我耳边说的一句话吓了我一跳,
她说:谢谢你的故事。
时至今日
时至今日,已经没必要
仇视所有的没完没了。天上的
行星、树上的梨子,水中的螃蟹以及
令人头疼的逻辑学。
世界这么大,我在其中。行星与我。旋转是负担。
被划破肚子的马哈鱼
在大海里,仍然想着
逆流去产卵。当然你也可以将这种事
视为精神上的某种诉求。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训练如何感知别人,跟在
陌生家伙的屁股后面,从模仿他走路到
跟着他哭和笑——一次在外地,我甚至
试图改变我的安徽口音——如同你们
训练一只狗,如何去嗅客人的衣角。
我希望有人与我想法一致,
在某个时刻,最好任何时刻。但不同于
做爱,不同于两人在草地上打滚。
在306国道上,货车一辆辆驶过去,一路
鸣着喇叭。有时我也有招手的欲望。
此时一个压低嗓音的摇滚歌手,在路边
摇晃、唱:“我不帮你脱身,我不帮你脱身”。
就像他故意如此似的。
休息日所思
我在办公室里写诗。
这是休息日,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
一株盆栽植物,叫不上名字,
肥大的叶子,粗壮的茎。
每天,有一名工人来为它浇水(今天他没来。)
虽然见过他很多次,我仍然记不住他的脸。
他走路低着头。他不需要我记住他。
我在他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对于我俩
都不重要,反过来他也是。
我在痛苦、干枯之时,不需要他。
我要安静、要写作时,更是如此。
回想我这一生,被不同的人或事物打扰,
使我巴望衰老早至,更无意占据
这株植物和这名工人留下的空缺。
楼梯这儿
一天我爬楼梯,在它与电梯之间
我总是选择它。我看见一只蜣螂
在台阶上,也在往更高的台阶上爬。
我知道蜣螂,是因为田野里的那些粪球
和一本插图本百科全书。
悬在阶沿上,有一会儿它一动不动。
相对于电梯,几乎没有人愿意走楼梯这儿。这蛮好。
我不渴望别人来了解我,虽然不能说
占有这具身体就独自拥有处置这具身体
的权利,比如用它去转动粪球,但我得时时回答
心中所想,即便一动不动。
小晨曲
清晨想唱歌。很古怪的想法。又很自然。
因为是清晨,不是其他时刻——吃过
早餐,肚子胀,陷在椅子里懒得
动一下手指头。不是货车司机
的午休时间和机场售票员的傍晚。
没有这样的时刻了,至少眼前。过一会儿送
报纸的要来,查水表的要来,还有妻子的朋友,
叽叽喳喳的海马脸狐狸脸女人们。她们会不时
对我嚷:好啦好啦,水开了,下雨了,卫生间又堵了。
过一会儿,邻居大妈将挎着菜篮子,牵着
小孙女去幼儿园;对面阳台上,一个男人将
例行公事似的抓住一个女人的胳膊,往上举,
女人双腿乱蹬,手里抓着晾衣杆。
现在空气很好,树静静的,世界像
刚被做过一次耳鼻喉科手术。这时候,很多情绪
都他妈的。我对此要有所交待才是。
老青蛙
一个老头,边走边咳嗽。我跟在
他的后面,走了好几个街区。不知道他身上
什么东西吸引了我。街上车流
滚滚,我俩都忘了危险。
我想喊他,但最终还是没喊。我快步
绕到他的前面,但最终还是侧身
让他过去了。我用手中的棍子
打他的影子。打一下,影子就跳一下。影子
忽长忽短,常常使棍子够不上。小时候,
我也这么赶青蛙。它朝池塘的方向跳,我偏将它往
公路上赶。它很聪明,索性四脚朝天。
这个老头也是个聪明人,虽然不停地
咳嗽,眼神却不含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
他在兜圈子,故意在车流中穿梭。可能他的咳嗽
也是假装的。无聊的老青蛙。当他突然转身
迎面朝我走来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我扔了
棍子,站住了,声音有些颤抖:哦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