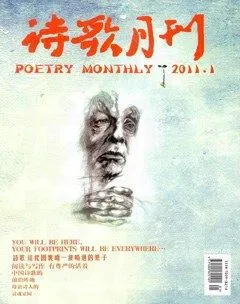韩东的诗(9首)
卖鸡的
他拥有迅速杀鸡的技艺,因此
成了一个卖鸡的,这样
他就不需要杀人,即使在心里
他的生活平静温馨,从不打老婆
脱去老婆的衣服就像给鸡褪毛
相似的技艺总有相通之处
残暴与温柔也总是此消彼长
当他脱鸡毛、他老婆慢腾腾地收钱的时候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某种罪恶的甜蜜
山东行
驱车行驶在山东的土地上
意识到,这是老区,这是老区
看见了白杨树,啊,永远的白杨树
灰蒙蒙的远山,仿佛有硝烟漂浮其间
石头垒砌的院墙像堡垒一样结实
悬挂的玉米棒子何时迸裂——像手雷
将和平的种子撒向这贫瘠的山乡
在这里,战争似乎已经获得永生
就像一块土地的季节性休耕
战时的儿女不改沧桑坚毅的面容
仿佛在一部老电影里旅行,或者
正在撰写新的传奇
大娘的三个儿子都在城里上班
她和老伴坚守在走空了的村子里
去年老伴也被一辆农用汽车轧死了
对方无钱赔偿,进了班房
大娘的脸上没有悲戚,颜色
就像她卖的栗子一样深
我们冲大娘咧嘴憨笑,直到牙龈毕露
犹如这漫山遍野绽开的红石榴
电梯门及其它
电梯的门打开,又关上了
一些人从里面出来,另一些人
又进去
就像门后有一所很大的房子
人们在那儿安家,就像
有一个大厅或者大会议室
需要用麦克风讲话
一些人的嘴张开,又闭上了
在反复的开合之间,一些词语
从里面出来,一些冷风
窜了进去
就像他们来自一个大地方,来自世界
就像我所在的世界不是我的
仅仅是他们的
在电梯门的背后
只有深井,一只金属箱子或者盒子
那些词语的背后有着同样的狭窄和局促
聪明之门已经关上了
灰白的小街
楼下有一条灰白的小街
我经常在那里吃面条、买烧饼
除此之外,我和他们的生活
是毫不相干的
太阳出来,小街变得明亮
有人在树上晒被子
有人在路边打麻将
有一些狗,有一些鸡
而我记住的只是灰白
那些模糊不清的面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就像阳光一会儿就没有了
我每天把那里忘记一次
在世的一天
今天,达到了最佳的舒适度
阳光普照,不冷不热
行走的人和疾驶的车都井然有序
大树静止不动,小草微微而晃
我迈步向前,两条腿
一前一后
轻快有力
今天,此刻,是值得生活于世的一天、一刻
和所有的人的所有的努力无关,仿佛
在此之前的一切都在调整、尝试
突然就抵达了
自由的感觉如鱼得水
愿这光景常在,我证实其有
和所有的人的所有努力无关
克服寂寞
我的小狗被封闭在家里
对门邻居也养了一条小狗
被封闭在家里
两条小狗隔着两道门从两边吠叫
犬声相闻,偶尔也在楼道见面
虽是男狗女狗,但不配对
虽说狐朋狗友,它们并不是狗朋友
彼此之间怀有敌意,也许
敌意比友谊更强烈
更能克服寂寞
结局是对门的那条狗死了,我的小狗
仍吠叫不止
也许虚幻的敌人比现实的敌人
更能克服寂寞
致庆和
一条街会变得非常美丽
一个人会从我们中间消失
有一种空旷造成的气氛
被阳光填满
有人在水泥球场上运球
就像那种嘭嘭的声音
有一种天蓝色是某人留下的
现在他面对四面白墙发呆
似乎风吹不到他的身上
吹不进他的心里
窗外的夜色温柔稠厚
好像把他黏住了
老人
老人曾是那么年轻
精力无限地养育我们
为我们而战
又为自己的晚景和子女苦斗
喋喋不休,吵吵嚷嚷
惹人厌烦
忽然就像风吹落叶
遮天蔽日的景致已然不再
她的手臂真的就像一截树枝
比握着的手杖还要干枯
不为那养育之恩
也不为朝夕相处
只为这衰败和流失
为这屋里静悄悄的沉默
追悔并痛惜
工人的手
他悬挂在高楼上
抓着墙的手纹丝不动
我觉得是女人就应该爱上这只手
就应该接受它的抚摩
是男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手
结实、肮脏,像吸盘肉垫
是女人就应该做那面墙
降低一些吧
最好躺下
是男人就应该死死地抓住那女人
浑身大汗淋漓,但手不出汗
心不跳,腿也不抖
如果是个恋物癖就这样恋吧
工人的手也是最棒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