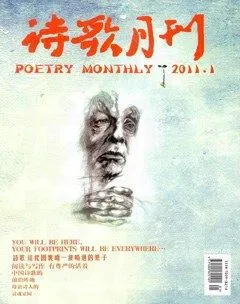多多的诗(5首)
从马放射着闪电的睫毛后面
东升的太阳,照亮马的门齿
我的泪,就含在马的眼眶之内
从马张大的鼻孔中,有我
向火红的庄稼地放枪的十五岁
靠在断颈的麦秸上,马
变矮了,马头刚刚举到悲哀的程度
一匹半埋在地下的马
便让旷野显得更为广大
我的头垂在死与鞠躬之间
听马的泪在树林深处大声滴哒
马脑子已溢出蝴蝶
一片金色的麦田望着我
初次相识,马的额头
就和我的额头永远顶在一起
马蹄声,从地心传来
马继续为我寻找尘世……
(2000年)
北方的天空携带石块隆隆运动
巨型云朵,偶尔隐现双亲的侧影
像送走两只碗的河面那么平地
疼,也不再牵连大地了
哑孩子靠着石灰墙
听门后锄头的淌血声
把要诉说的田野送进九月的天空
一种类似说话的哭泣声
也就从一块蒸发着马粪的高地
留驻了弯腰者的风景……
(2000年)
不放哀愁的文字检查棉田
青铜,流放证人的舌头
青草,诉说词语的无能
听亲人带着抗体离去后
篱笆留下的撕裂声,不听
河流与河床间永无止境的诉讼
怨妇,早把河堤跪得白白净净
河流,重又投入血液的解释
用集体的徘徊驱赶蝗虫
看端碗的石像恒久伫立
弱者,蔑视历程而唯有里程……
(2000年)
搂着废弃的农具
为麦田边缘的急雨伫立
不知家乡在哪里
绷紧丝绸,越过菜畦
秋季,一季接着一季
望着哪里,再不言语
再,一声夜鸟的长嚎
再往盛过母亲的碟里
撒一把米……
(2001年)
听冬日雷声爆炸过的寒冬
胸墙以下的岁月也牵动
沉寂中心的重锤,是它
用被摧毁的人做向上的阶梯
留下爬出来的半张脊背
到达哺育者,炮筒中
我们的声音,我们心理的总量
体内的炭一直存留着
已被尘埃吸收的挽歌
向着重新灌溉吼声的田野
从你,我们不训练的旷野
从我们,你回声之滞留
要死者跟上,要他们的根跟上
(2005年)